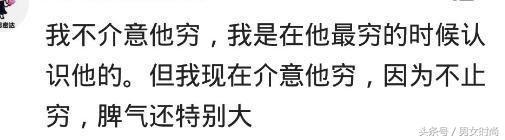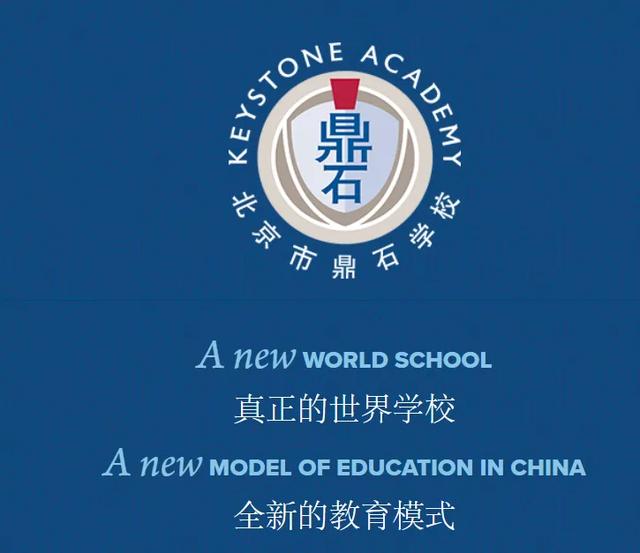90岁高龄的张家二姐张允和出版的《最后的闺秀》,记录下张家生活的点点滴滴,引领着高节奏极富现实的现代人,穿梭回能够孕育名门闺秀极富国学涵养的特殊时代。
深宅大院,教育开明,安逸富足和时代磨难众因素叠加催化,终塑出高在云端又深扎泥土的精致的四位极品女子。

张家有十姐弟
张家有十姐弟 ,原籍庐州今安徽合肥,算作当地的名门望族。四姐妹的曾祖父张树声是淮军名将、晚清重臣。他为张家积累下无上的荣耀、丰厚的财富和崇高的社会地位。
张允和还记得当地曾有民谣《十杯酒》,其中有两句:“一杯酒,酒又香,合肥出了李鸿章……三杯酒……合肥又出张树声……”
张树声生有9个儿子,长子张云端膝下无子,从五房过继一个男孩,即四姐妹的父亲张武龄。

张武龄与陆英夫妇
而张家到了张武龄这一辈也已经褪去军人色彩,成为家境殷实的士绅。光绪三十二年(1906),母亲陆英从扬州嫁到合肥,据说送嫁妆的队伍从四牌楼一直延伸到龙门巷,足足排了10条街,这一盛况在当时被人们津津乐道。
父母一起琴瑟和谐地生活16年,共孕育了10个子女,其张家四姐妹中打头的4个都是女孩。 关于她们的名字,张允和在《亲爱的父亲》一文中有过这样的描述: 父亲对我们四个女孩子尤其钟爱,他为我们起的名字不沾俗艳的花草气: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名字中都带两条腿,暗寓长大以后都要离开家。
但其父从小给了她们最大限度地自由发展个性、爱好的机会,让其受到了尽可能好的、全面的教育,却不同于那个时代一般的被禁锢在家里的女子,让其迈开健康有力的双腿,走向社会,比一般家的男子都要有过之而不及。
下面按照四姐妹的排序逐一展开来简介。

四姐妹
一、昆曲为媒:张元和与顾传玠的不弃不离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底,在张父张武龄和母亲陆英婚后一年,张家诞生了第一个孩子,即大女儿张元和。张武龄的母亲未能生养过,因而对于过继儿子的头胎格外珍视。这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女孩由奶妈子喂养到5岁,且一断奶就搬进祖母的厢房,受到奶奶额外的关爱和呵护。每天,她和祖母的早饭与午饭是单独享用的,可供选择的花样非常多,有火腿、碎肉、香肠、咸鸭胗,甚至连她的主食米饭也要做成精致的蛋炒饭。
此外,家中惩戒孩子的各种形式对于张元和来说从未碰及。以致于其性格显得优雅而略带孤傲。元和10岁时,张家举家搬到苏州九如巷。后来,元和在父亲张武龄创办的乐益女中就读一段时间后转到南京一所寄宿学校,不久升入上海大夏大学。在大学校园里,张元和与另外3名同学因品学兼优、才艺出众,被同学们誉为“四大金刚”,张元和更是被称为雍容华贵的“皇后”。二姐张允和说:“大姐生得端庄秀美,穿衣的颜色、式样都很雅致得体。”

名伶顾传玠
张元和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字是昆曲,她热爱昆曲、表演昆曲,最终将自己嫁给了一代名伶顾传玠。实际上,张家的女儿们和昆曲结下一世之缘,离不开张武龄的“处心积虑”。1921年,张武龄请来一位专业艺人教女儿们学习昆曲这种极端精细的南方戏曲。在金安平的《合肥四姊妹》一书中,张允和对这件事的缘起有如下记忆: 那天是除夕。准备年夜饭是件大工程,因为我们家里少说也有四十个人。
那晚孩子们吵吵闹闹,玩得开心极了。他们跟着工人在一旁丢骰子、玩骨牌、赶老羊,每一盘下几分钱的注。张爸看在眼里,很是郁闷。凡是赌博,他都讨厌,即使只是赌着玩,或一年只赌一次也不行。所以那晚他和孩子们谈了个条件。他说,如果我们不玩骨牌、赶老羊等,就可以跟老师学昆曲,等到可以上台唱戏了,就给我们做漂亮衣服。过了两天,他真的为孩子们请来了老师。从此每星期家里的孩子都在爸爸的书房里学唱昆曲。 张元和与顾传玠相识时,顾传玠已经改行很久了,虽然这个名字曾经红透了姑苏繁华地,更唱响在浩荡上海滩,但他并没有在昆曲表演这条营生路上坚持走下去。

四组妹
实际上,作为狂热的昆曲爱好者,张元和很早就知道顾传玠。这位极具天赋的戏曲演员台风潇洒、唱腔绝妙,曾被评价:“一回视听,令人作十日思。”
据说,顾传玠最擅长扮演具有悲剧色彩的帝王。某次,他扮演唐明皇,人戏合一,在唱完“恨只恨,三百年皇图一日抛”后,他匆忙下场,竟吐出一口鲜血。 在上海读大学时,张元和常与要好的女同学去听戏,顾传玠彼时是舞台上挂头牌的演员。有一次,她们几人还写了封信给他,请他演出《牡丹亭》里的《拾画》和《叫画》一出。过了一段时间,顾传玠真的在舞台上满足了她们的愿望。
后来,顾传玠弃伶就学,在学校中结识了张家兄弟宗和与寅和。当时张元和从海门海霞学校的教职离开,回到阔别多年的苏州,跟着昆曲老师周传价的见面,她曾做过这样的描述:一九三五年,我向周先生学小生戏的时候,我弟弟宗和、寅和有个同学不时来我家。他来的时候,如果我正在学戏,一定会立刻打住。我知道他是顾传玠。几年前,他是上海最红的小生。后来他离开了戏班,如今在南京和我弟弟上同一家学校。他一出现,元和就不唱了,否则多尴尬呀。那时我跟他不熟,他是我弟弟的朋友。 契机发生在1936年夏天,在昆曲的发源地要举办昆山救火会义演。

张元和与顾传玠结婚照
张元和受邀前往客串,而顾传玠恰也受邀登台。这一次,顾传玠演出的两个角色分别是《惊变》 中的唐明皇和《见娘》中的小官生王十朋,两场戏下来,他筋疲力尽,再也不肯多演一场。在后台,顾传玠却被宗和、寅和兄弟拉住,央求他私下里为他们和元和唱一出《太白醉写》。这一场戏顾传玠将李白的飘逸洒脱和风雅傲气表现得淋漓尽致,张元和评价他当晚的演出“十全十美,令人叫绝”,让她为之陶醉。
然而,两人身份地位的悬殊还是让这种结合在当时引起了不少喧嚣,上海各小报不惜篇幅,大肆渲染张家大小姐下嫁顾传玠的新闻。张元和的昆曲老师周传瑛说过:“昆曲是高雅之至的了,但唱昆剧的戏子终归是下贱的。”即便是名伶,在昆曲最盛行的时期,仍然是为人所轻视的职业和身份。
一个是名门闺秀,一个是戏曲演员,二人的相恋结合在当时无疑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而顾传玠也似乎在用一生的时间改变和提升自己,无论是读大学,还是做生意,他做了无数尝试与努力,但都没有获得成功。这位极具天赋的戏曲家或许并不擅长其他领域的开拓,然而他偏偏铁了心不愿意再走回艺术之路,元和则始终如一地陪伴在他的左右。1949年,顾传玠坚决要离开大陆去台湾,至于原因则是一个谜,元和也未能完全理解,但她义无反顾地随行。

大姐张元和
张元和的一生,从未远离过昆曲,并留下了一本标准、精致的《昆曲身段谱》。顾传玠去世后,有一次元和在票友演出中上场,出演《长生殿·埋玉》中的唐明皇,戏末杨玉环被安葬于浅坟之中。张元和感叹道:“原来我埋的不是杨玉环,而是顾传玠这块玉啊!”
由此可见两人的感情有多深多厚。
二、“半京半肥”侠义女与同学兄喜结连理
二小姐张允和的性格颇为激烈直爽,她将自己的个性归因于出生时母亲的难产,正是那种拼命求生存的精神让她得以在世间走一遭,再加上她有个对自己颇为维护的保姆,在家里简直“所向披靡”。张家的每个孩子都有一个自己的保姆,允和的保姆窦干干是个心直口快的主儿,她对小姐的疼爱和呵护简直无人能及。
据说,张家有条惩罚孩子的措施,就是将犯了错的孩子关到一间小屋里面壁思过,每次允和因错受罚,保姆窦干干都哭得撕心裂肺,央求太太快快把她的二小姐放出来。母亲陆英常说:“这二猫子,谁也管不了她。老窦老护着她,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允和从小就不像一般小姐喜欢戏曲里风花雪月的爱情,她更痴迷于那些疾恶如仇的英雄角色,特别是义薄云天的关羽,这似乎也隐约间暗示了她的做事风格。

二姐允和
在大姐元和读大学二年级时,继母韦均一觉得学费太贵,不愿让她继续读书。允和跳出来为大姐打抱不平,当时继母是乐益女中的校长,允和就跑到学校门口鼓动学生罢课,她说如果校长都不支持自己的女儿完成学业,那乐益女中的学生还上什么课?这一举动让张允和家颇为尴尬,后来家族商讨了解决方案,用地租为元和筹集学费。
或许是受这一事件影响,张家的孩子再未受过学费的困扰,都顺利地完成了学业。 允和从乐益女中毕业后,先是在中国公学读书,她自述当时自己有两个绰号:“一个叫鹦哥,因为她爱穿绿;另一个绰号就不妙了,叫'小活猴’”。在1928年上海《新闻报》上有这么一篇报道:“《中国公学篮球队之五张》,其中有张允和玲珑活跃、无缝不钻,平时有小活猴之称……惜投篮欠准……”。
后来,她转入光华大学就读,并与周有光相恋。实际上,二人相识很早,周有光的妹妹与允和是乐益女中的同学,两家时有来往。但是,直到允和上大学,两个人才开始交往。周有光儒雅谨慎,他的追求和爱恋像是文火煮汤,拿捏有度,而正是这种分寸感颇合张家二小姐的脾胃。 结婚前夕,周有光在写给允和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大致意思是:“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允和的回信长达10页,主题很明确:“幸福是要靠自己去创造的。”

张允和与周有光结婚照
据说,在二人的婚礼上,小妹张充和唱了昆曲《佳期》中的一段助兴,事后周有光询问张允和,四妹究竟知不知道她在唱的是什么?原来,曲中唱的是洞房之事:“一个斜欹云鬓,也不管堕却宝钗,一个掀翻锦被,也不管冻却瘦骸。”
婚后的允和仍然个性鲜明,甚至在新婚期间做出“不可思议”的举动。一名未婚先孕的高中女同学来看望允和,并表达了想要堕胎的想法。允和考虑到母子两人的安全,劝阻了已怀胎6个月的她,并收留她住在自己婚房内室的一个小房间以安心待产。这件事直接影响了允和的家庭关系,但是她顶住各方压力直到孩子诞生。
之后,允和与这名女同学一起带着孩子坐火车到杭州。因为孩子的父亲一家人就在杭州居住。她们用假名登记入住一家旅馆,之后将孩子放在床上,并留给孩子奶奶一封信,换下旗袍,迅速离开了旅馆。次日,杭州当地的报纸上就登出了这则神秘女子遗弃婴儿的新闻。与她瘦弱纤细的身材似不相称,这种侠义之举无疑是允和的性格缩影,只要是她认准的事情,就不会屈从于任何外界的压力。
战争打碎了许多安稳度日的美梦,允和自述从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直到战争结束,她至少经历了“十次大搬家,二十次小搬家”。颠沛流离中,女儿小禾因突发疾病未能得到及时救治,缠绵病榻多日最终离去;儿子小平被流弹击中,经历九死一生终得安然无恙。这些危急时刻,周有光多数因工作没能陪在允和身边,允和对婚姻生活的描述是:“大部分危机总是留给女人去处理。” 不过,允和始终是一个理智清醒的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丈夫周有光被下放到宁夏某闭塞的村庄接受劳动改造,允和并没有同行,她清楚自己的身体经不起折腾,不如留在北京为丈夫提供一些后勤保障更为现实。
在那期间,周有光患了青光眼,病情得不到控制有失明的危险,而当地的小医务室里根本没有治病的眼药水。允和想尽办法,定期将眼药水装进小木盒里寄给他,有时还在里面塞进几条巧克力糖。对周有光而言,在最孤立无援的时刻,张允和寄去的温暖或许就是坚持下去的勇气源泉。在一张两人晚年的合影中,周有光这位著名的语言学家依然儒雅安详,那位极具个性的名门闺秀脑袋微偏靠近先生,曾经的苦难岁月似乎并没有磨灭她的美丽,领口的旗袍盘扣里仍流淌着一份雅致与从容,甚至还渗透着小姑娘般的俏丽与娇美。
有趣的是,虽然成长在吴侬软语的苏州,后又在北京生活多年,允和的口音里仍然带着合肥的味道,有人问起此事,一贯风趣幽默的允和说,她的普通话别具一格,是“半精(京)半肥(合肥)”。

张兆和与沈从文
三、淳朴节俭的兆和与鼎鼎大名沈从文的一生情愫
在张家四姐妹的合影中,三小姐张兆和颇为不同,从肤色上看她并不是那般白皙,气质中也略带些接地气的淳朴,似乎不如姐妹们秀气妩媚。这或许与她从小的成长环境有关,作为张家第三个女儿,娇宠与惊喜感似乎已不如姐姐们。
兆和小时候食量惊人且从不挑嘴,有时候门房的老头从碗里拨一些糙米饭给她,她也能吃得津津有味。她的保姆朱干干对她的教导方式也很有趣, 遇到被二姐欺负、被老师责罚的沮丧时刻,朱干干会对她说:“别想了!没什么了不起。去喝你的粥,吃腌豇豆吧,吃完就没事了。”
在朱干干的照料下,兆和像个男孩子一样粗粗壮壮,顽强生长。 所以,当兆和在中国公学读书广受男孩子欢迎时,无论是姐姐们还是她自己都感到十分意外。仰慕者们给这个皮肤略黑的小姐起了“黑凤”“黑牡丹”的外号,尽管兆和并不喜欢这些美绰号。
情书如雪片般一封封飞来,兆和从来不回复,她给来信者取上代号,然后给情书编写号码。这其中,“青蛙13号”正是著名作家沈从文的来信。彼时,沈从文在中国公学任教,生长于湘西小城凤凰的他以家乡风土人情为背景创作的一系列作品曾在中国文坛引起极大反响。尽管老师一片炽热,学生却冷若冰霜,兆和的答复是自己正专注学业,不需要什么男朋友。

沈从文与妻子及妹妹(右)
沈从文得以被聘用,离不开胡适的大力支持。 当时,胡适正是中国公学的校长,非常欣赏沈从文的才华。当沈从文向胡适吐露自己的恋爱苦恼时,胡适提出愿意出面说项。当然还没等到胡适出面,张兆和倒是先找到了他。这位倔强的小姐是来向校长表明态度的,尽管胡校长给予了沈从文极高评价,并表示他“顽固”地爱着张小姐,兆和也直截了当地回复:自己“顽固”地不爱他。
沈从文无法释怀对兆和的爱恋,虽然开局不利,但他连续三年不间断地给她写信,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竟开始融化坚冰,打动了兆和的芳心。
于是,他写信向张家提亲,说道:“让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开明的张武龄并没有阻拦和反对,二姐允和立刻发了封电报去报喜,这个机灵的姑娘用了一个“允”字语带双关地传递信息,既是许可之意,又是自己的署名。
兆和得知后也不放心,害怕沈从文不能领会,又偷偷跑去发了一封:“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
婚后的生活给兆和制造了不少挑战,本来有一笔丰厚的嫁妆却被沈从文谢绝,一无所有的二人迅速卷入柴米油盐的现实生活。沈从文的九妹前来和他们同住,这个备受宠爱的孩子花钱的招式层出不穷,加上沈从文有收藏癖好,作为主妇的兆和总是在捉襟见肘中努力维持着家庭的正常运转。
兆和最为朴素,她并不喜好那些奢侈浮华的事物和不劳而获的生活,她曾对丈夫说:"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很难想象,兆和是个出身名门,从小锦衣玉食,受到优良教育的小姐。
当然,这个家庭也未能躲过特殊的时代浪潮。1958年,沈从文一度被严厉批评,他的作品被评论为颓废、色情,是“桃红色文艺”,北大校内针对他的大字报有些就出自他的得意门生。后来,沈从文患上了抑郁症,甚至多次尝试结束自己的生命。最终音乐成了他救赎自己的良药,沈从文慢慢痊愈。张兆和为了适应新的时代,选择去华北大学深造。
“文化大革命”期间,夫妻二人被下放到湖北乡下的“五七干校”,兆和的主要工作是看守厕所,防止有人偷粪便。到1972年,两人终于回到北京。实际上,张兆和一直希望沈从文能重新写作,但是她却似乎始终未能完全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不能理解他为何放下笔。
1995年,在沈从文去逝7年后,张兆和在整理出版了丈夫的晚年的通信,并在《后记》中写道: 六十多年过去了,面对书桌上这几组文字,校阅后,我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

晚年的沈从文与张兆和
经历荒诞离奇,但又极为平实……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太晚了!为什么在他的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
悔之晚矣,人生其实就是这样。
四、充和北大教授国艺与西语系外教傅汉思的跨国姻缘
四妹张充和与姐姐们有不同的成长经历,在她8个月大的时候,被叔祖母收养,从苏州回到合肥,一直生活到16岁。这位叔祖母是李鸿章的侄女,颇有修养,她相当重视充和的教育,充和不到6岁就能读写不少单字,还会背诵《三字经》《千字文》。
叔祖母还特意为她重金聘请良师,其中,教授充和时间最长的一位老师名叫朱谟钦,是吴昌硕的弟子。从11岁到16岁,充和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老师在书房中度过,跟着老师学习《汉书》《左传》《史记》等史书、各种唐诗宋词以及《论语》《孟子》《中庸》《大学》。 成长在合肥的充和习惯在童年时光里享受独处,所接受的又是传统教育,这些塑造了她宁静的气质。与苏州的姐姐们相比,她或许并不熟悉城市里的时尚,对于科学和政治更是不甚了解,但是姐姐们对四妹却有着一份格外敬重的感情,她们深知充和虽然年纪小却具备最深厚的国学功底,让她们自愧不如。
自幼的生长环境也影响着充和的生活态度:“新世界虽好,你们去吧,我还是自己玩算了。”这个内心安宁的女子一辈子都在玩,书法、绘画、诗词、昆曲,真正地乐在其中。张充和 1933年到北平参加三姐兆和的婚礼,之后她决定留在北平。
家人建议她参加第二年夏天的大学入学考试,她觉得不妨一试。考试内容中有一门数学,充和简直一窍不通,家人朋友想尽办法为她补习,可她压根学不进去。
考试当天,家人为她准备了圆规和曲尺,不过充和根本没用,她自述连题目都看不懂。充和的考试结果给考试委员会出了不小的难题,数学毫无争议考了零分,但国文又得了满分。

张充和
委员会中有惜才爱才的学者希望北大能录取这名考生,但根据考试规则单科为零分则不能被录取。于是,考试委员会要求批改充和数学试卷的老师重新阅卷,看能不能找补回几分,可是从头到尾审阅了一遍,老师还是给出了零分。最后,委员会只好自己想办法,强行让充和通过。
抗战爆发,充和随同沈从文一家流寓西南。很多人爱恋着这位超凡脱俗的四小姐,写过《断章》的著名诗人卞之琳就是其中之一。卞之琳当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教文学翻译,是沈从文的好友。不过,对于诗人的炽热情感,充和显得颇为冷淡,她觉得卞之琳的诗歌“缺乏深度”,人也“不够深沉”“有点爱卖弄”。
充和的追求者中还有一位方先生,被她称为“书呆子”。这位方先生是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的,充和在北大读书时,他常常去充和的住处看望她,但是这位木讷的追求者每次来都带本书,充和请他坐下喝茶,他不坐也不喝,就站在房间的一角看书,然后告辞,二人几乎不交一语。方先生也会给充和写信,只不过用的都是甲骨文,充和完全看不懂。后来充和离开北平,方先生叹息有“凤去台空”之感。
充和最终为自己选择的归宿是外国人傅汉思。

张充和与傅汉思结婚照
1947年,充和在北大教授书法和昆曲,借住在三姐兆和家一处小房间。是年9月,缘于姐夫沈从文的介绍,她与北大西语系外籍教授傅汉思相识。傅汉思出身于德国的犹太人家庭,精通德、法、英、意文学,到中国学习中文。那时候,傅汉思常到沈家喝茶聊天,不过,沈从文很快觉察到傅汉思的真正来意,于是,每每遇到这个外国人来访,他就马上叫来四妹,自己则悄然离开。 1948年11月,充和与傅汉思结婚。次年1月,新婚夫妻从上海搭乘戈顿将军号客轮前往美国,充和随身携带的除了几件换洗衣衫,还有一方古砚、几支毛笔和一盒500多年的古墨。
从小生在合肥乡间的充和一直梦想能有一个坐落在溪水边的小园子,种上花草树木,邀请志同道合的朋友前来喝茶。在美国,她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心目中的小世界,在居所的后面她种了一片竹林,还种下牡丹、玫瑰,甚至还有长葱、葫芦和黄瓜。有时候,她还会用自己种下的竹子手工制作笛子。
或许充和是幸运的,从允和与兆和后来的种种经历来看,她的远渡重洋为自己寻得了一片净土,也躲过了许多时代的劫难。很长时间里,张充和在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书法课,同时也表演和传授昆曲,在异国他乡播撒最原汁原味的国学文化种子。
她带出的四位高足,在促成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一事上,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张充和与傅汉思结婚52年的时候,一位美国学生为她出版了一本诗词集,名为《桃花鱼》。这本诗词集只印刷了 100册,宣纸质地加上手工线装,显得古色古香,颇有味道,内容是汉英对照的,其中的英译文部分出自先生傅汉思的手笔,可谓珠联璧合。

张武龄与四个女儿
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一度想将张家四姐妹的故事搬上荧幕,可选择演员就是一大难题,特殊的时代背景,深宅大院与开明思想碰撞下熏陶出的她们,大约真的是“最后的闺秀”了。
江坝的老渡口 午后江岸骑行 “芜湖铁画”锻制作技艺作品进入江北白茆红色传承馆
黑沙洲的前世与今生 那年那月奋进的黑沙洲学子 黑沙洲天然的三间窝棚房 因水而生倚水而兴的白茆洲 生态白茆,绿色之洲一一一美丽乡村套北人间天堂 土地革命时期的“六洲暴动” 白茆洲上好人多 人杰地灵白茆洲 从今年安徽高考作文题《跨越,再跨越》说起 古埠新生更繁昌
编后语:读了《绝代风华四姐妹》,难抑将其分享给各位的冲动,尤如独食美味而觉无味一般,故稍作改动后将其转发,改编于《传奇安徽》一书;图片均源自成书,若有侵权联系即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