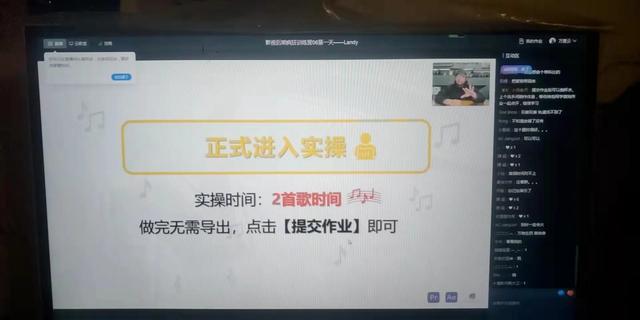妃:大家对这个字都印象一般,其意思不言自明。在陕北白于山区一带口语中,这个字还经常出现。夫妻斗嘴,丈夫气不打一处来,会开口大骂“贱妃”!好像一介村夫也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这一表达是否准确真不重要,重要的是陕北人在封建社会崩溃百年后,仍然随时可以过把皇帝瘾。
陕北话真正有内涵的,倒不是如上所说的口气,而是其使用的词汇,从古又到今、从东南西北又到中,无所不包。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血火洗礼的凤凰涅槃之旅,改朝换代、外族入侵,“一将功成万骨枯”,腥风血雨之痛,都是由普通老百姓来承担的。孟姜女哭长城,花木兰从军,“府帖昨夜下”,“有吏夜捉人”,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将军白发征夫泪”,儿女情怀刻骨铭心。五千年来国家960方平方干米河山的宏大叙事,陕北方言也是一览无余。
待诏:本义是待天子之命也,汉《扬维传》“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诏雄待诏承明之庭。”唐,王绩《晚年叙志示翟处士》:“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清,惠士奇《送蒋树存之官馀庆》:“待诏吾留金马门,修书君上南薰殿。”可见在中国历史长河的相当长时期,“待诏”还十分活跃。汉代以才征召士人,优异者待诏金马门,以备顾问或召用。唐代不仅文辞经学之士,就是医、卜、画、书亦供制内廷待诏。到《水浒传》第四回中鲁智深道:“兀那待诏,有好钢铁吗?”说明那时“待诏”已从指专侍皇帝之身怀绝技的手工艺人,流落民间了。可惜这个词在现代汉语中已几乎消失,一些字典中亦不见踪影,但陕北“待诏”却存在,只不过专指剃头匠而已,而这一称谓源于中国历史上那段不堪回首的血腥往事。

明末吴三桂引清入关,清年在占领中国南方后见大局已定,即颁布“剃发令”以“不从者斩”为手段在中国强制推行“剃发易服”的文化征服运动,这就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恐怖史实。我们知道,汉民族自古以来就非重视衣冠服饰,《孝经》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有收毁伤,孝之始也。”作为孝的起点,汉人成年后结发头顶,而清政权强制推行“金钱鼠尾”发式,剃前顶发,留后脑辫,对士可杀不可辱的志士来讲,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所以激烈反抗。鉴此1645年6月15日,多尔衮再颁剃发令:“全国官民,京城内外限十日,直隶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剃发。1月9日又颁布了配套的“易服令”,“官民既已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就是要以此来毁文灭志。江南百姓为此发出了“宁为束发鬼,不做剃头人”的誓言,以致出现了“江阴三日”“嘉定三屠”这样的大屠杀。江阴城破后,清兵大开杀戒三日,报复性屠杀17万之众,全城仅53名老幼者免难。
更悲催的是,这一惨绝人寰的剃发令竞是汉奸孙之獬的主意。由于在明朝孙投靠阉党为人不齿,因此清入关后,自恃桥才不遇的孙之獬带领全家剃发易服以表忠心。清军甫入关,为安定人心,招降纳叛,孙被委以为礼部侍郎。本来为收买人心,清廷还允许降清的汉官穿汉服,上朝时汉、满官员分立两侧,孙剃发易服成为另类,又为其他降官记恨,孙一不做二不休,上书剃发易服,以绝汉人复国志,正中多尔衮下怀,导致剃发成令。但对成千上万的个体,剃发谈何容易?除了百姓抵抗,剃头匠告急,清廷只得将剃头匠集中“待诏”出勤,以至“待诏”一词深深印入陕北人的脑海中,成为一种特指。

多尔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