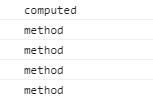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52期,原文标题《打破“黑箱”:伊藤诗织被性侵案胜诉的背后》,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黑箱”不仅指私密空间里的取证难度,也暗示日本制度中对性侵案件的长期淡漠、日本文化中不对等的性别与权力关系。而首先来打破这个“黑箱”的,是伊藤诗织这样一位非典型的日本女性。
记者/黄子懿 严岩

伊藤诗织是日本第一个公开姓名和长相的被性侵的女生(法新社 供图)
“苦中带甜”
53岁的山口敬之(Noriyuki Yamaguchi)坐在新闻发布会的台上,他穿一件米黄色西装,稀疏的头发往脑后梳得整齐。或是因为愤懑,他嘴唇紧咬,嘴角往一边上扬,右手握笔放在台上,双眼不时瞟向他方,听律师用英语陈述着昨日的判决是如何的错误。“我是冤枉的,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随后,山口敬之用英文对着满屋记者说,他将提出上诉。
台下,上诉对象伊藤诗织(Shiori Ito)静静坐在席间,以记者身份目睹了这一切。她今年30岁,穿一身深色职业装。整个发布会,她面无太多表情,偶尔平静地望向台上,听对方说些什么,在电脑上做着记录。发布会快结束前,她提前起身离开,从侧门走出,没有看对方一眼。
一方急切地说不服判决要上诉,而另一方以记者身份出席见证,无论是哪国司法界,这场景都不多见。有人看到伊藤诗织参加发布会后,评价说“太酷太勇敢了”“她确实颠覆了一贯的受害者形象”“她真的是在以身作则地告诉女性,应该背负‘羞辱’的是施害者,受害者无需掩藏,也不必愧疚”。
一天之前的12月18日上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女记者伊藤诗织遭性侵的民事诉讼案做出裁决,判决伊藤诗织胜诉,被告山口敬之赔偿其330万日元(约21万元人民币),同时驳回山口控告伊藤侵犯名誉的起诉。这场日本历史上女性首次公开具名指控职场性侵害案,以女方胜诉暂时告一段落。
当法院宣判伊藤诗织胜诉时,她展现的形象却是柔弱的。她向法官深深鞠躬,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高举着“胜诉”的牌子冲出大门,场外瞬间传来一片欢呼声。冬日法院外,伊藤诗织裹着一身厚衣服,拿着白底黑字的牌子向所有人展示。她哭红双眼,哽咽着说:“太久了,真的太久了,太久了。”此时,距离2015年4月那个案发夜晚已过去四年有余。

伊藤诗织胜诉后在法庭外向所有人展示着“胜诉”的牌子
四年前,伊藤诗织是纽约大学新闻专业一名应届毕业生。2013年,她在纽约酒吧打工时结识了时任日本TBS电视台驻华盛顿分局的局长山口敬之。山口敬之是日本资深记者,也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好友,曾出版两本安倍晋三的传记,有“安倍御用记者”之称。
2014年,伊藤处在毕业的十字路口,给山口敬之等认识的媒体人发邮件寻找实习机会,后者引荐了一个实习岗位,伊藤心存感激。2015年,伊藤毕业回国后考虑回美国工作,向山口发邮件咨询。山口表示有实习机会,也有一个正式的制片人岗位供她考虑,伊藤觉得惊喜。于是,山口邀她在2015年4月4日晚在东京碰面,商谈工作与签证事宜。那一晚的见面,改变了伊藤诗织的一生。
据伊藤自述,当晚,二人先后去了一家餐馆、一个串烧店以及一家寿司店。在寿司店,伊藤诗织几杯酒下肚后就突感身体不适。她觉得很奇怪,自己平时酒量很不错,不容易醉。她不得已连去两趟洗手间,在洗手间,她感到天旋地转,顺势跌坐在马桶盖,头伏在水箱上,瞬间昏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伊藤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酒店房间里,被山口压在身下侵害,无法动弹,异常痛苦。无论她如何抗拒,山口都毫不在乎甚至更加兴奋。事后,山口用一副戏谑口气说:“很好,你合格了。”
伊藤落荒而逃,回到家中对身体进行紧急处理。之后,山口在她的试探性邮件中矢口否认对她进行侵害,称她是酒后乱性,两人自愿发生性行为,并在此后坚称伊藤当时是清醒的。
事发后第五天,伊藤走进警署报警。在与警署、司法系统、媒体打交道的过程中,她遭遇到重重阻碍,也开始有了创伤应激反应(PTSD)。她耗尽数月搜集证据,案发两月后,警方根据证据,申请了逮捕令并获得了检方许可。但在计划逮捕山口敬之当天,行动被日本警视厅最高层叫停。负责该案的所有警官和检察官也被全部调离该案。之后,案件展开了新一轮调查。2016年7月22日,警方宣布因证据不足,判定此案不予进行刑事起诉。
万般无奈之下,伊藤诗织决定站出来接受采访、召开记者会,并对山口敬之提起民事诉讼。这让伊藤诗织成为日本第一个公开身份和样貌的性侵案指控人。她出版了记录事件全过程的纪实作品《黑箱》(Black Box),BBC为此也制作了纪录片《日本之耻》(Japan's Secret Shame),直指日本社会和治理体系中对性侵案的淡漠。这在日本引起复杂反响,也让山口敬之名誉受损,后者决定反诉,要求伊藤诗织赔偿1.3亿日元(约830万元人民币),并公开道歉。
12月18日的判决中,法官铃木昭洋指出,综观各种主客观事证,法庭认为山口的证词矛盾,在事发过程中山口不仅全程清醒而且做出了许多违反常理的供述,故此判断“伊藤诗织的证词相对较为可信”,并驳回山口的反诉。伊藤诗织在现场接受采访时说:“即使胜诉了,但并没有减少我受到的伤害。”虽然案件已过四年之久,“但哪怕只有一点,也是一个改变”。
“这是一个苦中带甜的结果。”与伊藤诗织有过接触的日本上智大学(Sophia Univeristy)文化心理学教授出口真纪子(Makiko Deguchi)对本刊记者表示,判决之前很多人都不太确定能不能赢,“之前的刑事诉讼是被推翻了的。我很高兴,能苦中带一点甜”。

性侵案另一主角山口敬之是日本资深时政记者
走进“黑箱”
“这种事情太常见了,立案调查有难度啊!”报警后两天,警方这样告诉伊藤,“事情发生在私密的室内,不会有第三方知情。检察官把这种情况称作‘黑箱’。”办案警员一再强调,“黑箱”里取证的难度很大,更何况对方还是知名人士。伊藤在《黑箱》中写道,警员甚至劝她,“对方是有名望、有地位的人物,你今后恐怕没法在新闻界立足啦,以往付出努力换来的人生也泡汤了”。
伊藤很吃惊,一个女性被强奸了,警方的反应竟是这样。作为新闻记者和当事人,她越是试图打开“黑箱”,就发现了越多的“黑箱”。比如,警察的取证方式之一,是拿一个人偶还原现场场景。他们让伊藤躺在一个垫子上,用人偶摆弄各种姿势还原。“是不是这样?”现场警员都是男性,一边拍照一边问。“这些闪光灯让我眩晕和恶心,我不得不停下来思考,才能不试着去想我正在经历些什么。”在接受BBC纪录片采访时,她如此说道。这给她造成了严重的“二次伤害”,有批评家甚至称其为“二次强奸”。
而随着调查的进行,证据开始浮现。警方在伊藤的内衣上检测出山口的DNA染色体。当晚载两人离开餐厅的出租车司机证实,伊藤中途曾多次要求将她放到车站,但山口却让司机前往酒店。伊藤下车时,司机发现她已昏迷。监控录像显示,伊藤当时已无法行走,被山口掐在怀里拖拽着,脚不沾地地穿过大堂,消失在电梯的方向。酒店门童一脸同情地目睹了这一切。
这些证据,却没能换来对山口敬之的强制性调查与刑事起诉。警方告诉伊藤,叫停逮捕山口的,是日本警视厅的最高层,并劝她放弃调查,私下和解。她多次想过要自杀,前后写过三次遗书,或因打不通自杀热线,或被医护人员救了回来。“我是一个记者,记者的工作就是讲述真相,如果我都不能说出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那我又如何做好一个记者?我将无法面对自己。”伊藤诗织在出口真纪子的课堂上这样讲述为何要站出来,除了记者身份之外,她也想给家中妹妹树立榜样。“当时我听到这段话时,觉得非常有力量。”出口真纪子说。
2017年5月,伊藤诗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身份,并宣告已向检方审查机构提交复议申告书。9月22日,检方再次判定不予起诉。伊藤此后走向民事诉讼。民事判决出来后,舆论关注的一点是:为何刑事案件检方不起诉,却在民事案件中以“非自愿性性行为”被认可?
曾代理过性侵案的日本律师星野天对本刊记者解释,日本不存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况,二者是分开的。刑事罪责认定要比民法严苛很多,有“疑罪从无”原则,“被告哪怕只有10%的可能无罪,法院就不能判定其有罪”。而民法不同,只要原告能在“普通人不会质疑的范围内证明了事实”,法官就可认定该事实发生。法官判定山口民事侵权,“但这不意味着可反推山口犯了强奸罪”。
然而,在法律层面,日本对于“强奸罪”的定义也比一般国家更高。刑法中对“强奸”有不同分类,强奸罪之外还有“准强奸罪”,即“利用女性丧失意识或无力反抗的状态”与其发生性关系。强奸罪则通常在出现暴力和自卫迹象下才会成立。如果施暴方或受害者喝过酒,那相关部门便不鼓励受害者起诉——2017年之前,日本涉及强奸的法律已有110年之久没有修改过,要求“亲告”,即受害人亲自提起诉讼才会受理。
“受害者必须要证明自己拼命反抗过才行,你要逃跑,要反抗。”出口真纪子说,不然法院不会认为这是强奸。她介绍了伊藤诗织之外另一起在日本非常有名的性犯案,那是一名父亲多年来侵犯女儿却被判无罪的案例,同样在日本引起了轩然大波。
2017年8月,日本爱知县的一名父亲因涉嫌性侵自己19岁的女儿,以“强奸罪”被起诉至法院。这位父亲的侵害持续数年,从女儿上初二就开始。但2019年4月,法官宣判父亲无罪。法官表示,虽然被告承认了强奸女儿,但不承认女儿无法进行反抗,“女儿多年来受长期性侵后,已渐渐失去反抗想法”。
“这种情况下,日本女性怎么会站出来讲述她们的故事?”出口真纪子认为,伊藤一案最大的意义在于,法院开始认定受害人的非自愿性了,“法院终于承认伊藤那晚的性行为是非自愿的。要认识到这一点,对日本社会来说非常重要”。
镜子的另一面,正是日本极低的强奸报案率。2017年日本政府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只有4.3%的强奸案受害者去报警,67.5%人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哪怕是朋友和家人。相比之下,美国大约三分之一受害者会选择报警。伊藤在公开演讲中说,她后来曾和日本很多性侵受害者聊过为何不报警。她们说,因为不愿和男警官聊这件事,“他们非但不懂,还会质疑,让你必须回忆犯罪现场和事发时的一幕幕”。
日本的警察总数量有26万人,而女性警官只占比8%。伊藤报警时曾要求向一位女警官陈述案情,当她崩溃着说完案发经过,女警才告诉她:“真的很抱歉,我只是个交通警察,我没有权力受理这个案子。”最后,案情又让全是男性的刑警部门接过,有了男警用人偶摆姿势取证的一幕。
2014年,在日本一桩25岁男人强奸15岁女学生的案子中,东京最高法院也判决被告无罪,理由是法院认定这名女孩没有做出足够的反抗,因为从当时他们的性交姿势来看,“她只要把腿在空中踢一下就能跑开”。

2019年6月11日,东京有上百人参加了“鲜花展示”运动,以示对受害者的同情以及对日本性侵法律的不满
不平等的“性”
2019年7月,伊藤诗织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做演讲,几乎场场爆满。第一站的北京场,她问台下观众:“中文里有没有明确表示拒绝的词汇?”台下观众回答:“滚!”后来,伊藤诗织反复跟随行的中国友人学习着“滚”。
事发当晚,她被山口性侵,却无法自然说出一句表示抗议的强有力日语。她用日语表示拒绝,却让对方更加兴奋。情急之下,她用英语骂了脏话:“你他妈在干什么?”(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对方不以为意,还戏谑地说,她生气的样子蛮可爱。
伊藤后来说,在面对年长位高的男性时,日语缺乏明确表达拒绝、不同意的词汇,他人也很难明确区分“拒绝”和“欲擒故纵”。在她后来与山口来往的日文邮件中,也多用敬语。“所以哪怕是语言,我们都是被限制了。日语应该也引进‘fuck off’(滚开)这种词,或者把中文里的‘滚’翻译成日语。”
“日本文化总是避免冲突的,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出口真纪子说,在群己边界(boundaries)上,日本文化有一种基础上的模糊性(fundamental fuzzyness),即口头上不会明确表达个人意图,需他人推断。“我们是试着去阅读他人的想法,而不尊重他人嘴上说什么。我们不会强迫他人说出真实想法,而是假设‘一切都还好,不用多说啥’。”
出口真纪子说,这带着东亚儒家文化的特征,与中国类似,但日本的特点可能比中国还强。她班里有几位中国留学生,曾向她抱怨过日本人都是“两面人”(two-faced people),她问为什么,中国学生说:“日本人从不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然而在性文化上,这种含蓄的文化特征表现为男女双方的理解错位与不对等。那位叫停逮捕行动的日本警视厅高层,接受日媒采访时表示:“女方也有希望对方帮忙安排工作的企图。所以才会见面饮酒,此事充其量不过是男女纠纷而已。她甚至还跟着对方去了第二家餐厅啊!”
日本NHK电视台曾做过一种调查:哪种行为会让对方误解你“同意上床”?有11%的人认为,如果两人单独在外吃饭就可以;23%的人认为两人乘坐一辆车即是默认。如果是喝醉,这一比例将上升至35%。“你敢相信吗?这可是NHK的调查。”伊藤很吃惊,为什么日本男性对何为“同意”一无所知?难道特定穿着和场合就意味着“同意”吗?
出口真纪子说,这项调查恰恰反映了日本性教育的失败。日本的性教育从小学四年级开始,“但其实更像是生物课”。男女分开上课,研究人体构造与生育过程。“我们缺乏对性文化‘同意’的教育,但另一方面,我们还不断地涌现出新的性侵害的受害者和施暴者。”
日本是一个性文化开放、性别文化却极其不平衡的社会。在12月17日新出版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日本在153个国家中排名第121名,创下新低,落后于中国、韩国。
“二战”后,日本经济起飞。男人被认作是顶梁柱,要加班加点养家,女性是家庭主妇,要做“贤内助”和“乖乖女”,男性主导了国民经济与相应的社会文化。“整个昭和天皇时代(1926~1989)基本就是这样。”星野天律师说。出口真纪子则表示,在日本社会中,理想女人的形象就是要女性化(feminine)的、不能太有主见(not assertive)。
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日本也发展出了成熟的色情业,成人媒介产品在市场自由流通。“当我们很容易获得色情产品,却缺乏很好的性教育时,男士们也许会认为那就是对待女性的正确方法,这是非常恐怖的地方。”伊藤诗织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这是日本性文化中不平衡的症结。
这种情况下,日本性骚扰频发。一个典型案例是,日语中有“痴汉”(Chikan)一词,专门代指那些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骚扰女性的男子。在伊藤诗织的青少年时代,她和朋友就有过多次被骚扰的经历,日本后来专门开通女性专用车厢。伊藤曾针对痴汉犯罪做过采访,得出的结论是:它超出了性嗜好的范围,更像是一种支配征服的个人冲动。“大部分性侵案件发生在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中,这并非事关性企图,而是关乎权力,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加的权力。”
在这种权力不对等情况下,很多女生默不作声。2017年12月,在一堂名为“关系结构心理学:理解多数人的特权”的课上,出口真纪子邀请了伊藤诗织给她的学生做分享。一位女生在课堂上说,自己中学时常穿校服,在电车上经常被人骚扰,但她们此前都没有意识到不对劲。“当时就觉得‘我们是高中女生,好像就应该被人摸’。”
即使这样,“强奸”在日本仍然是禁忌话题,让人不悦。如果有强奸案,警方甚至从来不用“强奸”这个词,而是用“侵犯”,如果受害者年纪比较小,则会用“恶作剧”(いたずら)。“日本男性会倾向于做侵略者(aggressor),女性则被认定就是要被动(passive)的。所以当一个女性真正被侮辱了并且发声了,这就违背了那种已被广为接受的日本女性形象了。”出口真纪子说。
伊藤诗织召开发布会后,面临着很多网络暴力和“荡妇羞辱”。很多人说她是外国人,让她“滚回韩国去”。她的家人、住址都被曝光。出于安全考虑,伊藤搬到了英国,在那里进行自己的独立记者生涯。
从很多角度看,伊藤诗织都是一个非典型的日本女性。她说一口流利英文,有西方教育背景,喜欢吃辣,酒量好,常年游历在亚非拉国家拍纪录片。她说,她从小在家都是一个异类,9岁开始当模特,16岁不顾父母反对、离家去美国求学,多年来半工半读。毕业前,她游历过60多个国家,看到了世界的广阔性与更多可能性。她将16岁出国留学形容为一个“睁眼看世界”的过程,“如果只会日语,我的世界将被局限和被禁锢在充满日本心理的地方”。
遭遇性侵前,伊藤有个男友,后因受不了男友让她做家庭主妇的想法而分手。被性侵后,父母和警方都劝过她表现得更惨一点。召开发布会前,一个朋友还让她穿一件白色衬衫加外套出席,“看上去更体面”。伊藤拒绝了,她想打碎这套受害者“人设”,只想把眼泪留给自己。“不管受害者穿或没穿什么,都不该因此而遭受责难,也不该将其视为她受害的理由。”
“伊藤是一个非常世界主义的国际化女性。”出口真纪子说。伊藤曝光自己后,最初在日本社会并没引起太多媒体关注,直到当年末的《纽约时报》发出了相关调查报道。出口真纪子曾在班上做过一次调查,大多数学生都不知道伊藤。她与学生讨论伊藤,很多学生都觉得她不像是受害者——发布会那一天,她穿了头两颗扣子未扣的衬衫,被媒体批为“荡妇”,还被拍到面露微笑的照片。
“那时候我意识到,她跟我们不一样,她是另一种非常强大的自由女性。”出口真纪子说,当时的日本社会,哪怕是女性都不一定会同情伊藤,“因为她看起太自信了,虽然这本身与案子没什么关系”。后来,在伊藤做分享的那堂课上,出口真纪子对班上180名同学做了匿名调查:有多少人在现实生活中认识被强奸的人?数量是让她震惊的22人。“这可是强奸,不是电车痴汉骚扰啊!”
伊藤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2017年,日本百年来第一次修改强奸法:首次将性侵受害者范围扩至男性,最低刑期从3年增加到5年,强奸罪改为强制性交罪,并且为非亲告罪(受害者不亲告,检方也可以起诉)。星野天律师说,刑期是一个重要修订,“3年刑期是可以缓刑的,改成5年就意味着必须要坐牢”。

2017年秋,美国加州的“Metoo”集会,运动正是从这里走向了全球
从Metoo到Wetoo
2017年10月,《黑箱》在日出版。在同一时间的大洋彼岸,美国掀起了一场“#Metoo”(我也是)运动,伊藤诗织也被称作“日本#Metoo运动第一人”。她公开身份后,日本2018年提起诉讼的强奸案数量增加了35%,达到410起。考虑到日本1.27亿的人口,这数字依然很低。
在成都的一场读者见面会上,伊藤说,她之后日本并没有很多人站出来。女性保持沉默的原因仍是“很难直接去讲述性骚扰”,特别是没有专门法律去保护。根据日本媒体民调,超过60%的女性曾遭受性骚扰却不敢发声,“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制度与权力结构的关系问题”。
2018年4月,日本朝日电视台一名女记者对外披露,她在工作期间受到了日本财务省事务次官(财政部常务副部长)福田淳一的性骚扰,并且公开了录音。58岁的福田淳一随后宣布辞职,但仍不承认性骚扰。其上司、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则多次公开坚称“性骚扰罪不存在”“若果有问题,女记者可以被男记者替代”,引发女性团体抗议。
“跟韩国相比,日本现在还没有形成一场#Metoo运动,不过现在说这个也有点早。”出口真纪子说,从大环境来看已有了改变的迹象。另一个转折点是前述2019年4月宣判的父亲强奸女儿一案。此案判决在民众当中引起强烈反响,数千人在日本各地街头抗议,手捧鲜花以示对受害人的同情。这场被称为“鲜花展示”(Flower Demon)的运动,蔓延到日本九大城市,如今已成为一项反抗性暴力的聚会,定期在每月11号举行。
在大学,学生也开始组织工作坊,讨论性关系中的“同意”问题。2019年1月,曾有一家名为《周刊SPA!》杂志对日本的女子大学进行排名,讨论哪所大学的女生最易被“哄骗”以及相关哄骗技巧。报道一出,学生激烈抗议,他们在网上发起请愿,在线下去总部讨要说法。涉事杂志公开道歉并承诺,将在此后推出关于“性同意”的报道。
伊藤的故事也鼓励着东亚其他国家的女性发声,包括中国。在成都的那场见面会上,一位女性律师分享说,几年前她曾代理过一起与伊藤类似的案件。一个姑娘被一位男性友人灌醉后被侵害,报警后也遇到了仔细盘问。案件推进过程中,BBC纪录片《日本之耻》推出,姑娘看后非常激动,将纪录片刻盘后送给了办案警方。最后在警方与检方的努力下,侵害人被判3年半有期徒刑。
这位律师还说,在一次赴美之行中,纽约一位官员曾告诉她,当地遭受性侵的女性中,亚裔的数量超过其他族裔,但东亚女性更倾向于不报警。“这里面有一种亚洲的沉默文化在里面。伊藤能更多地鼓励我们,东亚女性其实遭遇到的性暴力比其他族裔更多,更加需要站出来。”
伊藤诗织当场回应,是否可以将“#MeToo”变为“#WeToo”(我们也是)。“我希望每个人都从整体上考虑这个社会,而不是成为受害者、袭击者和旁观者。”性犯罪的减少和性观念的改变,需要社会层面参与和救助,而并非被侵害女性群体的抗争。一个有效的支援系统、一个能够互相理解的社会氛围、一套健全的法律都必不可少。
2015年事发后,伊藤曾联系了当时东京唯一的24小时性侵犯救助中心,她打电话给他们,想要咨询自己应该怎么办。对方则让她本人亲自过去,而她只是想知道该去哪家医院而已。“我当时太害怕了,出不了门。”后来,她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探访类似的24小时救助中心,后者依托在当地医院,有专业的性侵证据采集包(Rape Kit),会在受害者不知所措时帮助搜集物证,为之保留6个月。“这在之后的调查阶段是非常关键的,也能给你半年的时间去捋顺。”伊藤说,她就是在被侵害之后不知怎么办,只想回家洗澡,并因此而失去了很多取证机会。她一直怀疑自己当晚被下药,但报警时已错过了最佳检测时间。
瑞典是全球强奸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16年,瑞典每10万人的强奸案数量为73件,而排在瑞典之后的欧洲国家,每10万人强奸案数量连续6年无一超过60件。这是因为,瑞典对于强奸的定义比一般国家更低,同时案件数量也是根据强奸次数处理的。
2017年底,瑞典修订刑法,在性侵害犯罪中采用“积极同意权”(Affirmative Consent),即不再将犯罪者必须使用暴力或胁迫视为必要条件,重点放在性行为是否自愿。按照新法,性行为必须要自愿,只要受害人在性行为前没有明确同意,即可控告对方强奸。
日本一些性别团体和律师也据此建议,日本此前的强奸法修订步伐还不够,受害者必须反抗才能构成强奸罪的条款并未废除。而已有太多案例证明,有70%的受害者会因过于恐惧而身体“僵硬”,无法拒绝。“我们仍需做出改变。‘不可以’就是‘不可以’(No means No),更重要的是,只有‘可以’才代表‘可以’(Only yes means yes)。”伊藤诗织在多个场合强调。
如今,她的工作和生活重心早已转移到了英国,在全世界各地拍片。审判之前,随着案情深入,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支持她,包括事发当晚的酒店门童也愿意提供新的证据。审判当天,她的母亲也第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为女儿加油打气。
前几年,每次她回到日本都觉得不安全,不得不伪装隐藏自己。但从2018年起,她觉得不能再逃避了,不再躲藏。让她惊讶的是,人们开始在街道上认出她,主动分享自己的故事,倾诉感受,没有一起谩骂和负面评论。“日本人和陌生人说话是不太常见的,但他们确实这样做了。”伊藤诗织说,“于是我意识到,谩骂都在网上,而不是现实世界。”
(感谢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春民律师,以及本刊实习记者肖舒妍的帮助)
更多精彩报道详见本期新刊《青春崇拜:2019年度生活方式》,点击下方商品卡即可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