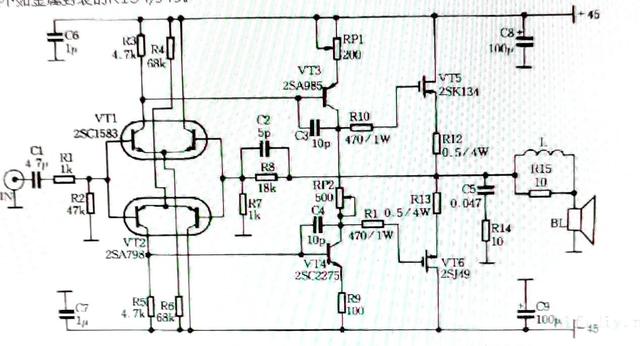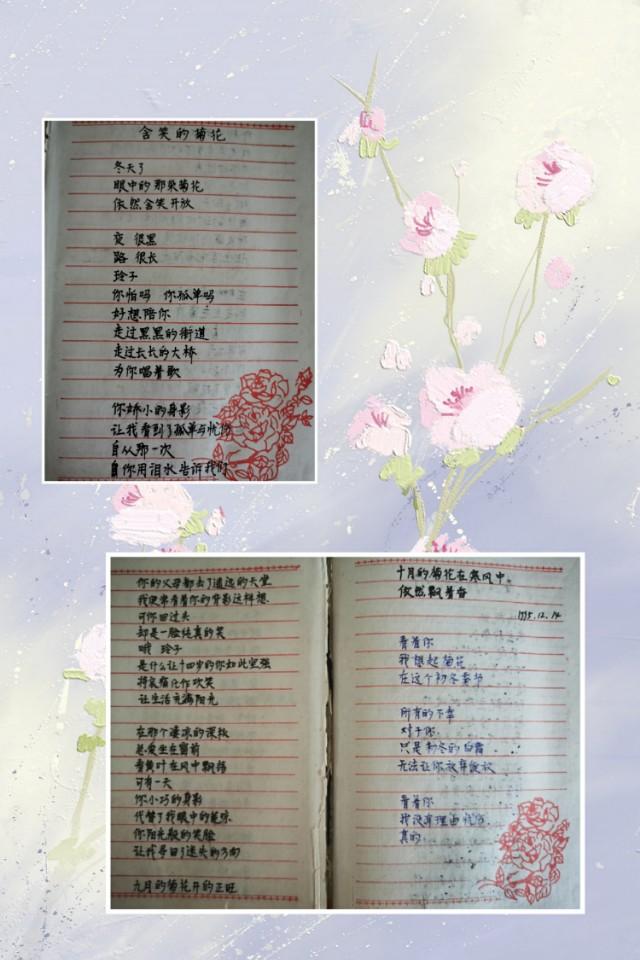1.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论语宪问篇第十四章深度赏析?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论语宪问篇第十四章深度赏析
1.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论语》第十三章开篇第一句,这第一句便是要求人不能懈怠偷赖。之前子张问政,孔子就说“居之无倦”,这次回答子路还是“无倦”。无倦其实就是不要懒惰,世上碌碌无为的庸人,很大程度上的通病就是懒惰,懒惰有多可怕呢?
懒惰的可怕之处,在我看来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对自己,另一方面是对别人。先看对自己:
儒家王阳明讲知行合一,这里的“行”在我看来也可以理解为不懒惰,我理解的知行合一,知是行的里子,行同时也是知的里子。人懒惰便少了行,少了行便少了知觉,少了知觉也就是少了心(王阳明讲凡知觉处便是心)。心都无了,这人就不仅仅是没有知那么简单了,实际上他的生命便已经断绝了。再看对别人:懒惰的危害,对别人就是“恶”。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华杉讲透论语》中华杉先生的举例非常好,他引用了《国语》中的一段话论证了这一点。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这里的“逸”就是懒惰安逸之意。一个人懒惰,便会将自己陷于安逸的境地,安逸久了难免身沁淫事,按照上述的路线一路发展下去便会生恶。为什么有那么多豪富的人,都会做坏事?就是因为他们懒惰了,太安逸了,不爱干正事了。
2.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这段话和前几天讲的:“先难后易”,“无倦”,“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道理一样。这里细说了一下,放过别人小错,这是做领导应有的格局,不能容人,也很难带人。
3.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这段话又出现了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其实是在探讨卫国的内政,因为当时卫国统治集团内部对于王位的竞争非常激烈,导致得位者往往都缺少合法性,所以孔子说要先正其名,子路却认为这是没必要的举动了,王位的实际拥有者没必要再纠结这个事了,所以才引发了这段争论。比起这个争论,我却觉得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这最后一句话“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才应该是重点。
很多人都会出现名不副实的情况,名不副实很大程度上在于自己对于自己的宣传,我们要问问自己是否总是将自己夸大,是否总是说话吹牛呢?总是吹牛,那就是名不正了,为了圆这个吹牛的谎话再继续吹也就要犯难了,这就开始言不顺了,再往后别人真的要求自己按照吹牛的话做,当然就事不成了,因此对于普通人而言,说话要慎重,无所苟矣就尤为重要了,这是孔子一再说的道理,“讷于言”、“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都是在讲这个道理。
4.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这段话有意思,以往呢大家找孔子都是学习为政、做人之类的事,这回樊迟来问了专业问题,怎么种地?孔子没有直接批评他,而是之后批评,为什么呢?因为樊迟没什么错,但是他问的地方不对,孔子是研究什么的,樊迟都没弄清楚。后面孔子说了一个道理,统治者的作风可以直接影响到民众。为什么呢?因为统治者有至高的权力,民众不能不服从他,孔子总讲君子如何如何?君子在古代就是指有封地的封建主,他们的存在是有意义的,只有一个大的至高权力在上才能使社会不乱,但是这里存在一个巨大隐患,谁约束这统治者(君子)呢?孔子的解答就是礼,通过让统治者(君子)守礼,而让他明白拥有一颗仁义之心,过着充满仁德的生活状态,才是最幸福的人生。
而普通人呢,本身也没条件学习君子之道,因为普通人没有选择,普通人大多迫于生活压力,只能任凭社会潮流所左右,而那些统治者(君子)却可以主导潮流。你让普通人强行君子之道,对于他而言根本就不切实际,他们的做派也只能跟着那些统治者(君子)所发起的潮流而行。所以,统治者(君子)一人就足可以改变世界,当人人都行仁义之时,自然上下一心,任何问题都可仍刃而解,但是千百年来大家都不信这套(至少大部分人都不信),现代人就更不信了,因为不信了,所以不讲了,因为不讲了,所以更没人学了。现在大家都开始将社会潮流左右的权力都交给了经济规律,交给了自然规律,人道之理越来越微弱了。
5.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这段话,孔子说出了他关于读书的态度。读了很多书,却与己无益,那是不正确的学习,或者说是没有学习而是一种娱乐。许多人很多时候都是貌似在学习,其实是假学习,实则是在偷懒娱乐,最可悲的情况是自己还认识不到这一点。
6.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之前季康子向孔子请教政务的问题,孔子总是要求他端正自己这段话,正好可以看作孔子的进一步解释。做别人的领导或是要求别人如何如何,首先自己要率先垂范,身先士卒,这样别人才容易服你,别人也可以在你的亲身践行下,确认你说的道理,从而在心里和行动上都愿意听从你。这也是儒家一贯主张的领导力,其本身也是一种端正的处事态度,同时还是一种理念教化,是国君或者领导者开创大同世界的必要前提。
7.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鲁国和卫国的国君家族,从源头上讲始祖都是周文王。“之政”指两国的政治,春秋时期传统规则开始崩坏,鲁国和卫国都相继出现以下犯上,君臣颠倒的情况发生,鲁国是三桓家族当政架空国君,卫国是父子争位,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两国无论从源头还是发展现状上看情况都类似,真是兄弟之国啊!这又是孔子的一句无奈的反讽之语。
8.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生活中很多人总是觉得自己少这少那,很少能好好想想自己是否是真的缺少那些东西?把精力都放在无穷的物质享受上,这本身就是违反儒家精神的思想。儒家思想提倡人们要,去人欲,立志向,为人生意义而拼搏,而不是为单纯的物质享受而拼搏,这才是正确的人生状态。人们总是要自己得到的多一点,再多一点,久而久之便会陷入无底的欲求深渊,最终迷乱心智。反过来,我们永远追求比自己预想的少拿一点,再少拿一点,久而久之,使自己蓄德而心明,也不失为一种人生智慧。
9.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之所以受人敬佩,与他的先见之明非常有关,他总能想到别人在上千年之后才认识到的问题。古代由于生产力的原因,人口一直很少,即使到了后来大一统的汉朝,全国人口也不过只有几千万人,所以在古代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提倡多生育。进入到现代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全球粮食产量足以养活数十亿人口,导致很多国家都人口膨胀,人口多固然是好事,但是往往人口多的国家都很贫穷,穷则生乱,这些地方同时还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复杂社会问题。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洞察到了这一点,人口多的地方,首要任务便是“富之”,否则就会出现动乱。
人民都富裕了,这时再教导他们礼义,教导他们正确的生活方式,正确的人生状态,正确的“幸福观”,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中国社会,彻底脱贫之后,早晚也要走到这一步,很多人都不懂得什么是正确的人生状态,从里到外都沾染着西方人的生活习气,这真是一种悲哀!
10.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这段话,可能是有人认为孔子的道理见效慢,因为孔子讲的是“道”,普通人总是想要马上可以解决眼前问题的“术”。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一个现象,那便是行大道见效未必慢,好比走路,门前的宽敞大道看似没有翻墙走的快,但是这条路非常稳妥、踏实,鲜有意外,而翻墙没翻好,很容易将自己摔伤,到时候路都走不了,更别说快了。
11.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中国传统文化是贤者居之,不肖者遵之,尊老,尊长,为什么呢?不应该是谁对,谁强听谁的吗?那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早就探明了一个道理,“对”和“强”都是表象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唯有德是一个人的根本,人不懂德的重要性,是永远不会获得真快乐,真幸福的。所以要听有德者之话,将有德者居于上位,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居上位者往往也会变,会无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人往往都不愿守分。
人出生后,首要明白的道理便是守分,人各安其分而不慕财权则天下安。你出生注定当帝王,那你就守分,专心学好礼仪制度、治国之道,一生做好天下臣民礼仪生活的表率,不要妄想着体验普通人的生活,像普通人一样处几个酒肉朋友,没事时唱歌喝酒。
你出生注定是普通人,那你就本本分分,依靠自己所长劳动生活,不害人不犯法,一生身体康健,内心无愧就好。人之所以会产生非分之想,都是因为自身愚蠢而受诱惑,看到别人发达了、有钱了、爽了,就想着自己也可以那样,殊不知人家乞丐变天子是因为环境形势特殊,是天意;人家有钱了,是因为时代不断改变,人家自身所长,正好遇上时代赋予的红利。所以,人要懂得守分的道理,在自己的道路上目不斜视安心前行,如果总是左顾右盼,心神难安,往往也难得快乐。人若守分,在自己的路上一路前行,心神专注,你的成就,你的幸福指数也会一路上升,因为没有干扰,也不需知那无用之事。
如果人人都想通了守分的道理,那么居上位者即使没有圣人之才,之少也会是个善人,人人都守分,则上下安宁,人心归善,刑法杀伐无所用处,久之,自然就胜残去杀矣。
12.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孔子讲善人执政一百年,就可胜残去杀,今天紧接着就讲了圣人执政。圣人执政一段时间,天下归仁,仁就是恢复周礼了,达到了理想的社会状态了。为什么要一世这么久呢?因为三十年,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就过去了。没有接受过仁政教化的人,积习难改,有些人还很顽固,他们已经变不了,但是年轻一代从小生长在仁政环境中,长大后也适应了这种正常的状态,于是天下归仁。
13.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之前孔子面对季康子的提问,就一直要求他端正自身,端正了自己,这样才能治好盗贼,这段孔子又在强调这个道理。人都是这样,想掌控这又想掌控那,一旦不如意就懊恼,就怨天尤人,其实人若想掌控一切,第一步便是要能掌控得了自己,这一点对谁都一样,《大学》里讲: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就是控制自己,这是第一步,是根本,这步没成又谈何掌控别人掌控外物呢?
14.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这段话,可以看出,孔子平时非常关心政事,这也是一个人的性格秉性,孔子的学问思想已经将修身之道与国家政务深深地绑定了。对于国家大事,关键在于几个点,孔子所说的日常事务只是并不影响这些重点,可能是当时冉有所侍奉的季孙家的私事,不好对外公开的事情,这岂能瞒过孔子。
15.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这段话前半段,讲的是君臣之间互相理解的道理,普通人之间若能做到相互理解,就能处成很多事,君臣之间更是如此。要做到互相理解,就要懂得换位思考的道理。今天说君臣,就以古代君臣为例,我国古代很多皇帝都宠信宦官,比如,东汉的汉安帝、汉桓帝,明朝的明武宗、明熹宗等等。当时很多大臣都痛斥宦官,屡屡惹怒皇帝,皇帝也对大臣极为刻薄,往往闹到最后互为仇雠,臣说君昏,君说臣不忠。君说臣不忠这个好理解,臣说君昏就要讲一讲了,这君他为啥非要宠信宦官?
古代皇帝宠信宦官,很大程度是因为偌大的后宫,真正能带给他温暖的其实只有宦官,很多人以为皇帝已经富有天下了,就应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像个圣人一样生活,可是皇帝往往在没成为帝王之前,就只能依靠身边的这些宦官给予温暖、给予关爱,他一朝为帝,当然要大加重用及抚慰这些人。而那些高标准,严要求的大臣呢,他们之前又给予皇帝了什么呢?皇帝又凭什么听他们的呢!所以大臣们要是能理解皇帝的需要,皇帝也要能理解大臣的苦衷,大臣也是职业所在啊!各退一步,往往一件事,一句话,就可以扭转乾坤使国家形式好转。
如果说上半段是说臣,那么下半段就是说君。这后半段,讲的是君主独裁固执己见的问题了,这在历史上也很显见,比如唐玄宗,几乎所有人都劝他说安禄山会造反,他不信,等到安禄山真造反后,所有人都劝他不要让函谷关守军主动出击,他仍不听,结果长安被破,他本人也只能逃亡蜀地。居上位者要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水平,不要和下属比智,你都是上位者了,已经是成功人士了,还有必要和下属较劲吗?君主要识人,放心交付下属任事,不要乱干预,这也是居上位者需要拥有的智慧。
16.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这段话,又是一句名言,所谓“近悦远来”是也。这段话也道出了中国文明的优势,我们的文明不曾中断,上千年来不断包容周围人群,使中华的概念无论从文化还是地理疆域都不断扩大,不像西方的所谓日不落帝国,本来很辉煌,可是无限地缩小,一味的靠实力,靠压迫,没有包容性,最终只能是初始地的原型状态,而中国却彻底的融合壮大了。以上道理,国家文明是如此,组织个人也是如此,只有做好自己,包容他人,你的世界才能不断地壮大,不断地发展。
17.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论语》中有许多次关于问政的对话,每一次孔子都是针对提问者给予对应的答案,每一次都不一样。这次是子夏问政,孔子告诫他欲速则不达,子夏为学喜术,但是治国之道的实施却是缓缓出效果,不能说今天出个政策,明天就要见效,如果没见效,马上就推翻之前的政策,这是看不出效果的,所以要处理治国之类的大问题时,需要领导者具有沉稳的心态,要能稳住气,并一以贯之地执行决策,且慎重更变政策才行。
18.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这段话是讲儒家的亲情观了,儒家认为人爱家人是自然天性,人对于外人的爱也是由近及远的开展,由关系远近决定,这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感情基础,如果一味的按照规则而漠视了亲情,这是步入了邪道,是不可提倡的观念。
19.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之前樊迟曾问过仁,孔子当时的回答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今天的回答就不一样了,可见,樊迟所问问题的背景不同了,这也是孔子的一贯作风,所谓的“仁”就是因时因事的恰当做法。
20.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士,之前讲过是古代封建贵族最末一级,意为可以任事之人。孔子这次讲了士的三重境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任事之人的三重境界。第一重“行己有耻,不辱使命”这是要有张骞、苏武的品质了。第二重“称孝焉”这是讲能侍奉父母,对家能负起责任。第三重“言必信,行必果”,这是讲做事的最基本的准则了,如果连这都达不到,那就太不靠谱了,根本不足以任事了。值得感叹是,最后孔子评价当时的士人,就连这最后一重也算不上,可见孔子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风气的失望。
21.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这段话孔子提出了两种为人的品质级别,一种是“中行”,一种是“狂狷”。中行,就是中庸,就是仁,就是准确恰当,这样的人自然难遇,如果没能找到,自己也做不到,也不必气馁。还有第二种“狂狷”也就是争强与直言之人,在这种人身边,会有逼迫感,逼迫你进步。今天这段话我们可以得出,选择人际圈子也要有底线,不能和人品太差的人混到一起的道理。
22.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占卜,本质是为了解决选择问题,没有恒心的人,没有恒定意志,朝秦暮楚,时刻思变,那占卜又有什么意义呢?人一旦确定了一件事,认准了一个志向,就要一以贯之,不要再有犹疑,之前孔子就说过“思再可矣”,反反复复的算计得失,只能让人一事无成。
23.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这句话,又是《论语》中的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大家对这句话多多少少也都会有一些体会。我的体会是,君子做事向来是对事不对人,为了真理有时会直言伤人,而小人往往是表面亲切,实际却是将自己对人的种种关爱当成谋利的工具,真实内心冷酷无情,这本质上也是一种不识大道的思想之病。我们学习这句话,不是要认清谁是小人谁是君子,而是要在日常处事中,修炼自己,避免自己出现同而不和的小人行径,这才是儒者所为。
24.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这段话中的“泰”既指内心修养,也指外貌表现,总之就是博大、宽广、阳光、正面的形象。君子行事都是依凭着内心道德与客观规律而做,取得的成就也都是理当如此的,又有什么可骄横傲慢呢?这也是人日常应保持的正常状态,平和稳重,不卑不骄。而小人的见识智慧远不及君子,看不懂大道理,往往行事都依照私心所欲去算计,人生最爽的事就是显得比别人强,处处留意别人的眼光,一旦有些成绩就开始骄横傲慢了。因为自私导致的愚蠢,使得小人的所做所为总是给人一种狭隘的感觉,如果生活中我们自己有这样的时刻,就要及时提醒自己了,这不是一个人应有的正常状态。
25.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这段值得深思,一个人如果所有人都说他是好人,他真的能是好人吗?之前就曾说过,人天生就不是一伙的,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好坏往往是针对自己而言的。
26.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君子之所以是君子,正是因为他能做到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君子一心规整好自己,从不想着苛求别人,君子明道识人,明白世界应有的正常运转道理,理解别人的难处。小人无知,一心想着满足私欲,总是怪罪别人不好,小人的整个人生意义就是能让自己开心,这样的人一旦做了领导,他便会削尖了脑袋榨取手下的价值来为自己服务,因为在他的观念里世界都应该围绕着他转,这才正常的。
27.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论语》中孔子一再强调人不要巧言令色,不要太擅言词的道理,今天这段话也是一样。古人观念认为不擅言词是一个人优点,而今人则正好相反,认为善于言辞才是优点。哪一种好呢?我认为还是古人的观念好。因为世上的道理其实是很难真正讲清的,但是你用行动证明一下则大家一目了然,说的太多了,无论你是出于什么心,最后一定都有假、大、空的成分,说不好反而误人误事。我想也正是基于这样的道理,孔子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木讷的好处。
28.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之前子贡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的回答是:行己有耻。这次子路也问了这个问题,孔子的回答却是和睦互勉,这正是对症下药,子贡是商人,行商很容易见利忘义,而子路性格莽撞,喜欢与人争强,孔子故而告诫他要与人和睦,相互共勉。
29.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之前孔子曾说过:“‘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今天又是说善人,可是这句话没有前提,不好讲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我认为孔子应该是讲,让没有战争经验的庶民去作战需要训练七年,因为孔子那个年代打仗是贵族的专利,那个时候贵族从小就要练习驾驶战车,使用弓箭,而庶民没有这个权力,所以在当时人的观念里庶民是打不了仗的,要训练一群完全没有经验的人太难了,但是孔子认为如果是在善人的带领下,即便是普通的庶民同样也可以训练参战,因为善人能够获得人们的信任,促使大家众志成城一致对外。
30.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孔子那个年代,普通人没有资格上战场打仗,即便上了战场,他们没受过训练也只能遭受无畏的牺牲。这句还是讲这个话题,让普通人上战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当时各国之间战争越来越频盈,打仗的人越来越不够用,所以才有些贵族提议让平民也打仗,但又不愿意花时候训练他们,随着春秋时期旧秩序的进一步崩溃,这种情况非但没有解决,反而进一步恶劣的发展下去,最终中国步入到了全民皆兵的战国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