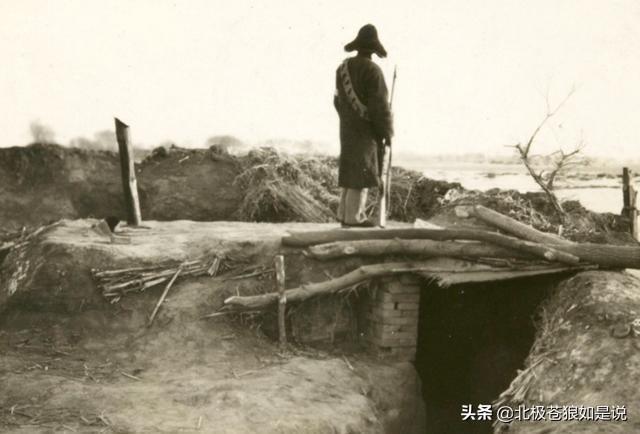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随着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城市发展模式的演变,全球各大都市圈的人口在总体规模、空间分布和年龄结构等方面呈现出一些共同的趋势和不尽相同的特点。本文选取伦敦、纽约和东京这三个世界主要都市圈进行研究,通过对各都市圈不同圈层自1960年以来的人口变迁趋势及其成因的分析,为国内都市圈未来人口发展的趋势研判和政策应对提供参考。
01 伦敦都市圈
伦敦都市圈的核心区域是由大伦敦政府(GLA)所管辖的由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和32个自治市所组成的“大伦敦地区”(Greater London),即伦敦市,其中又分为“内伦敦”和“外伦敦”。本文将“内伦敦”和“大伦敦地区”作为伦敦都市圈的第一和第二圈层。
伦敦都市圈的范围并没有明确的官方定义,综合考虑划定方法和结果的合理性、空间范围的稳定性和基础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由欧洲统计局(Eurostat)2021年划定的“伦敦都市区”(London Metropolitan Region)和2001年由英国“环境、交通与区域部”在《东南部地区区域规划导则(RPG9)》划定的“东南部地区”作为伦敦都市圈的第三和第四圈层。由于英国行政区划的调整,“伦敦都市区”的数据从1981年人口普查开始统计。各空间圈层的具体情况如下:

// 表1 伦敦都市圈各空间圈层情况


// 图1 伦敦都市圈空间圈层范围示意图
来源:《东南部地区区域规划导则(RPG9)》和网络
1.1 人口规模及变化情况
伦敦都市圈在过去的一百年中经历了“郊区化”与“再聚集”的过程。都市圈核心区域大伦敦地区的人口峰值为1939年的861.5万人;内伦敦地区人口峰值为1911年的500.2万人,二战后逐年下降。

// 图2 1961-2020年伦敦都市圈各圈层人口规模变化情况
1961-1981年间,内伦敦和大伦敦地区的人口分别从349.3万和799.7万锐减至242.6万和660.9万,降幅达30.6%和17.4%,占东南部地区人口的比重也由22%和49%跌至15%和40%。内伦敦地区1981年人口仅为1911年峰值的二分之一。同期,都市圈外围区域的人口持续增长。东南部地区除大伦敦地区之外的郡县总人口由818.5万人增至994.5万人,1961-1971年间更是出现了18.2%的大幅增长。

// 图3 1961-2020年内伦敦与大伦敦地区人口在东南部地区的占比变化情况
这段时期都市圈核心区域人口锐减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心城区的居住环境和城市品质日渐恶化,百业凋敝,空气污染严重,居民迫切地希望搬迁至环境更好的郊区居住;二是战后以小汽车为主导的城市规划理念和新城的建设加快了郊区化的进程,同时所谓的“郊区梦”也被房产开发商和媒体广泛宣传。在政府政策和市场的推动下,郊区成为伦敦居民购房的首选,并大批搬至伦敦近郊居住。

// 图4 1961-2020年伦敦都市圈各圈层人口变化情况(以1961年为基数100)
1981年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撒切尔政府上台后实施的市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伦敦在全球网络中的中心地位日渐巩固,金融、法务等相关行业蓬勃发展,经济逐渐复苏,都市圈总人口和大伦敦地区人口开始恢复增长。2001年,内伦敦和大伦敦地区人口为276.6万和717.2万,较1981年增长14%和9%。
1997年,由英国首相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政府上台,“城市复兴”(Urban Renaissance)成为其城市规划领域的核心政策。新政府领导成立的“城市工作小组”(Urban Task Force)在1999年和2000年发布了《走向城市复兴》和《城市白皮书》两本报告,成为近二十年来英国城市规划的指导理念。报告中提出的密度提升、棕地更新和可持续发展等理念贯穿伦敦的历版总规,促进了伦敦中心城区建筑密度和人口密度的持续提升。
新世纪以来,伦敦都市圈人口进一步向都市圈核心区域聚集,大伦敦地区人口增长占到伦敦都市区和东南部地区总增长量的72.0%和53.1%。
// 图5 2001-2020年大伦敦地区人口增长占伦敦都市区和东南部地区人口增长的比例
2001年,内伦敦和大伦敦地区十年人口增长率首次超过伦敦都市区和东南部地区整体水平;2001-2011年,内伦敦和大伦敦地区人口增长率为16.8%和14.0%,高于东南部地区的整体增长率10.2%,和都市圈外围区域的7.8%,2011-2020年也延续了同样的增长态势。2015年,大伦敦地区人口首次超过历史峰值;至2020年,大伦敦地区人口已上升至900.2万人。

// 图6 1981-2020年伦敦都市圈各圈层人口十年增长率
19年间,内伦敦和大伦敦地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增加了2800人和1164人,是外围区域增量的41倍和17倍。

// 图7 1961-2020年伦敦都市圈各圈层人口密度变化情况(人/km2)
1.2 人口结构及变化情况
在年龄结构方面,伦敦都市圈各圈层老龄化率低于全国水平,但呈现上升趋势。2001-2011年,随着人口自然净增长量(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的上升和年轻人口的净迁入,都市圈各圈层老龄化率均出现下降,其中大伦敦地区降低1.3%。此后的十年间,都市圈各圈层老龄化率均出现上升,截至2020年,大伦敦地区和伦敦都市区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2.2%和14.4%,而同期英国全国老龄化率为18.6%。伦敦都市圈各圈层15-59岁劳动人口占比持续高于全国水平,大伦敦地区2020年15-59岁人口占比为63.8%,较当年全国水平高6个百分点。

// 图8 2001-2020年伦敦都市圈各圈层老龄化率变化(65岁以上人口占比)

// 图9 2001-2020年伦敦都市圈各圈层15-59岁人口占比变化
此外,大伦敦地区的人口中位年龄低于全国水平,在2011年降低至33岁后,至2020年又上升至36岁。

// 图10 2001-2020年大伦敦地区与英国全国中位年龄变化(岁)
1.3 小结
总体来看,伦敦都市圈各圈层人口规模与全国水平相比增长更快,年龄结构更年轻。过去30年间,随着伦敦中心城区经济的繁荣增长和规划政策导向的转变,人口再次向都市圈核心区域集中,扭转了此前较长时期的衰退和人口流失,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也较快地恢复了人口增长。但近年由于房价和生活成本的上升以及新冠疫情的冲击,伦敦都市圈的人口状况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自2017年以来,由于国内移民净迁出量超过了国际移民净迁入量,都市圈核心区域的人口由净迁入转为净迁出,因此人口增长已完全依靠自然净增长,而自然净增长量也逐年下滑。

// 图11 2010-2020年大伦敦地区人口净迁入(出)量与自然增长量
来源:Trust for London
2020年初以来,新冠疫情对伦敦都市圈核心区域的人口增长趋势产生了负面影响,但目前已逐渐恢复至疫情前的增长态势。根据大伦敦政府研究中心(City Intelligence)的最新报告估计,大伦敦地区总人口在2020年大幅下降,但自2021年春季恢复增长,增长率较疫情前有所放缓。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上升使人口自然净增长量降至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人口迁移方面,工作人口,尤其是青年工作人口,在疫情初期大量迁出,但自2021年春夏季开始持续回迁;其他年龄组的人口的回迁趋势不稳定。
02 纽约都市圈
纽约都市圈又称为“纽约-新泽西-康涅狄格都市圈”,其空间范围为包括纽约市及邻近的新泽西州、纽约州和康涅狄格州的31个县级行政单元。纽约市规划局按照与纽约市的地理位置关系将整个都市圈分为七大地区,即纽约市、长岛、西南康涅狄格、下哈德逊河谷、中哈德逊河谷、内新泽西和外新泽西。纽约都市圈的核心区域是纽约市所辖的五区(县),即曼哈顿、布朗克斯、布鲁克林、皇后和史泰登岛。本文将曼哈顿和纽约市作为都市圈的第一和第二圈层;选取与纽约市通勤联系密切的长岛、下哈德逊河谷和内新泽西地区与纽约市共同组成核心通勤区作为都市圈的第三圈层,其余地区为外围通勤区;都市圈全域为第四圈层。各空间圈层的具体情况如下:

// 表2 纽约都市圈各空间圈层情况

// 图12 纽约都市圈空间圈层范围示意图
来源:纽约市通勤报告
2.1 人口规模及变化情况
1960年以来,除了在70年代受美国整体经济情况的影响出现小幅下降外,纽约都市圈人口规模整体呈上升态势,人口的变化情况经历了与伦敦都市圈相似的“流失”与“再聚集”的过程。
1960-1980年,曼哈顿和纽约市的人口由169.8万和778.2万减少至142.8万和707.2万,降幅达16%和9%。同期,核心通勤区内其他县以及更远的外围通勤区内人口显著增加,分别从700.9万和283.3万增至822.1万和389.8万,增长17%和38%。

// 图13 1960-2020年纽约都市圈各圈层人口规模变化情况

// 图14 1960-2020年纽约市五区人口变化情况
都市圈核心区域的人口流失由多重原因导致。首先,战后纽约郊区化进程加速,高速公路和铁路的兴建使长距离通勤成为可能,中产阶级家庭大批搬至郊区的新住宅区居住。其次,60年代至70年代,美国整体经济出现滞胀,经济全球化使纽约市的服装业和轻工业等支柱产业所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中失去竞争力,从业人员搬离纽约。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失业、犯罪等社会治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人口流失速度,导致纽约市税收下降,在1975年陷入财政危机,濒临破产,无力支持市政服务的正常运行,城市环境破败不堪。当时纽约市复苏的前景黯淡,时任美国总统甚至拒绝援助,任由衰退持续恶化。

// 图15 1960-2020年纽约都市圈各圈层人口变化情况(以1960年为基数100)
1980年后,纽约逐渐从危机中复苏,九十年代随着金融业和服务业的繁荣出现了高速增长,城市环境改善,就业率上升,社会治安日趋稳定,都市圈核心区域人口恢复增长,外围区域增长速度放缓。2000年,曼哈顿和纽约市人口为153.7万和800.8万,较1980年增加8%和13%。曼哈顿人口密度恢复至每平方公里2万人以上,与曼哈顿交通联系较好的布鲁克林、布朗克斯和皇后区均出现明显的人口增长。1990-2000年间,核心通勤区人口增长占都市圈总增长的比例由1980-1990年的46%上升至78.3%;纽约市人口增长率为9.4%,皇后区的增长率高达14.2%,超过外围通勤区;都市圈整体人口率增长由3.4%提升至8.3%,但仍旧低于全国水平。

// 图16 1960-2020年纽约都市圈各圈层人口十年增长率

// 图17 1980-2020年都市圈各圈层人口增长量占总增长量的比例变化情况
进入新世纪,由于911事件的冲击和2008年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经济衰退,纽约都市圈人口增速放缓。2000年至2010年,都市圈总人口增加72万人,不到上个十年的一半,增长率降至3.4%;纽约市的增长率由9.4%降至2.1%;核心通勤区人口增长占都市圈总增长的比例降至65.2%。
2010年后,随着经济复苏,工作岗位增加,纽约都市圈人口增速逐渐恢复,在空间分布上向纽约市和核心通勤区内聚集。至2020年,都市圈总人口为2354.4万人,较2010年增长6%;核心通勤区的增长率为6.8%,增量占都市圈增量的88.2%;纽约市增长率为7.7%,首次超过全国水平(7.4%)。都市圈所有县级行政单元中最大的增幅出现在与曼哈顿隔河相望,位于新泽西州的哈德逊郡和埃塞克斯郡,分别为14.3%和10.2%。同时,外围通勤区增长率降至历年最低,仅为3.2%,低于都市圈整体水平。曼哈顿和纽约市的人口密度高达23051人/km2和11002人/km2,十年间每平方公里增加1475人和786人,而外围通勤区仅增加8人。

// 图18 1960-2020年纽约都市圈各圈层人口密度变化情况(人/km2)
2.2 人口结构及变化情况
在年龄结构方面,纽约都市圈人口老龄化趋势持续,但纽约市和都市圈核心通勤区老龄化率低于全国水平。2019年,都市圈整体老龄化率与全国水平一致(15.6%);纽约市和核心通勤区为14.5%和15.1%,较2000年增加2.8%和2.7%;外围通勤区老龄化率增至17.3%,高于全国水平1.7个百分点。曼哈顿的老龄化率(13.5%)在2010年超过全国和都市圈水平,到2019年已大幅增至16.2%。这可能与曼哈顿房价高企,而迁入至纽约的年轻群体多选择居住在布鲁克林、皇后区以及核心通勤区内其他房价较低、交通便利的区域有关。

// 图19 2000-2019年纽约都市圈各圈层老龄化率(65岁以上)
随着老龄化率的上升,纽约都市圈15-59岁劳动人口占比逐年下降。曼哈顿和纽约市的15-59岁人口占比高于都市圈其他地区和全国水平,但从2000年的69.5%和64.0%降至2019年的65.9%和62.2%。2010年至2019年间,都市圈各圈层15-59岁人口数量也出现下降,劳动人口规模小幅收缩。

// 图20 2000-2019年纽约都市圈各圈15-59岁人口占比变化

// 图21 2000-2019年纽约都市圈各圈层15-59岁人口数量变化
此外,都市圈内只有曼哈顿和纽约市的中位年龄低于全国,在2019年为37.5岁和36.7岁;核心通勤区、外围通勤区和都市圈整体中位年龄均高于全国,其中外围通勤区最高。

// 图22 2000-2019年纽约都市圈各圈层中位年龄变化(岁)
(核心通勤区、外围通勤区、纽约都市圈为各县平均中位年龄)
2.3 小结
总体来看,纽约都市圈人口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核心区域人口持续聚集,人口年龄结构较全国和都市圈外围区域更年轻。随着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产业结构的改变,居民对于地理临近性的需求日益增长,更愿意居住在距离工作地点、服务设施、文化活动场所更近的交通便利的中心城区。在2020年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之前,2016年至2019年的人口估计数据显示纽约市人口逐年下降,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未来发展趋势的担忧,但普查结果有力地证实了纽约人口持续增长的趋势。
虽然纽约市人口总数保持增长,但与大伦敦地区一样,这些增长主要来源于自然净增长。在人口迁移方面,纽约市近年来保持人口总体净迁出,国际移民净迁入的状态。2020年的新冠疫情更是导致纽约都市圈居民加速向外迁出。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22年3月公布的数据,2020年4月至2021年7月,除外围通勤区人口小幅增长2.3万人外(0.5%),都市圈、纽约市和曼哈顿的总人口分别减少36.6万(-1.6%)、33.7万(-3.8%)和11.7万(-6.9%)。曼哈顿是全国人口最高的县级行政区,其余四县降幅均位列全国前十。

// 图23 2020.4-2021.7美国百分比人口降幅排名前十的县级行政区
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官网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解除,纽约都市圈的社会经济生活逐步恢复正常,有证据表明都市圈核心区域人口已开始回迁。纽约市主计长在报告中指出,纽约市的净迁出人数已开始减少,2021年7月至11月,净永久迁出人数比2019年同期减少6332人;6月至9月间净迁出总人数比2019年同期减少553人,且主要出现在都市圈核心区域,即曼哈顿和皇后区、布鲁克林的部分区域。此外,纽约城市大学人口研究专家Andy Beveridge根据邮政地址更改数据估计,截至2021年11月,四分之三在疫情期间迁出的人口数量已得到补充。当前纽约都市圈未来人口变化的趋势还未完全显现,是否会延续疫情前的增长态势和空间特征还有待观察,并在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发布后做进一步研判。
03 东京首都圈
东京首都圈以东京都区部为核心,覆盖东京都以及周边的七个县。首都圈的核心区域为东京都区部(第一圈层)和东京都(第二圈层),由东京都和埼玉、千叶、神奈川三县组成的东京都市圈为第三圈层;首都圈全域为第四圈层。各空间圈层的具体情况如下:



// 图24 东京首都圈空间圈层范围示意图
来源:网络
3.1 人口规模及变化情况
日本经济在二战后开始腾飞,作为日本经济和政治中心的东京地区经历了人口的高速增长,城市快速扩张。至70年代末,东京地区的城市发展以郊区化扩张为主导,核心区域东京都区部的人口在一段时间的增长后逐渐下降,向周边区域疏解。
1960-1980年间,东京都区部人口在1965年增长至889.3万人后持续下降,1980年人口为835.2万;近郊三县人口翻倍,从818.0万增至1708.0万,但人口增速在1970年后逐年下降;首都圈人口整体增加约50%至1192.2万人,外围四县也出现了18%的增长。

// 图25 1960-2020年东京首都圈各圈层人口变化情况
1980年后,日本经济泡沫开始破裂,人口进一步向外围地区流失。1980至1995年的人口变化趋势与前20年基本一致。1995年东京首都圈和都市圈总人口增至4037.0万和3254.5万,增长主要来自都市圈近郊三县,占到首都圈和都市圈增量的79.2%和96.0%。核心区域人口继续减少,东京都区部人口降至796.8万人;由于近郊三县人口增速下降,首都圈整体人口增速放缓,由1975-1980年的6.2%降至1990-1995年的2.6%。

// 图26 1960-2020年东京首都圈各圈层人口五年增长率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人口向首都圈核心区域再次聚集。1995-2005年,东京都区部和东京都人口增至849.0万和1254.8万,增量占首都圈总增量的比重持续提升,2000-2005年占比已提升至33.6%和48.4%,同时近郊三县增量占比逐渐收缩;外围四县人口在2000-2005年间开始收缩。

// 图27 1990-2020年首都圈各圈层人口增长量占总增长量的比例变化情况
2005年后,日本全国人口增长势头趋于停滞,2010-2015年开始出现负增长。东京首都圈人口继续增加,但增速降低,圈内人口变化呈现出两极化的趋势。东京都人口加速聚集,增量超过近郊三县,而首都圈外围四县人口降幅则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5-2020年间,东京都人口增量为首都圈总增量的70.6%,2010-2015年更是高达98.1%,是近郊三县增量的2.3倍。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东京都市圈的人口也出现了收缩,根据联合国人口预测数据,东京都市圈一都三县的总人口在2018年后开始出现下降,预计将会持续收缩。

// 图28 1960-2020年东京首都圈各圈层人口变化情况(以1960年为基数100)

// 图29 1960-2020年东京首都圈各圈层人口密度变化情况(人/km2)
3.2 人口结构及变化情况
在年龄结构方面,首都圈老龄化趋势持续,但东京都市圈内外呈现出两级化的趋势,东京都市圈内的东京都和近郊三县人口结构较日本全国更年轻,而首都圈外围四县老龄化情况则相对更为严峻。2020年东京都区部、东京都和东京都市圈的老龄化率分别为20.8%、22.1%和24.5%,显著低于全国的28.0%,而外围四县老龄化率(29.4%)超过全国水平。

// 图30 2000-2020年东京首都圈各圈层老龄化率(65岁以上)
与老龄化率相对应的是15-59岁劳动人口占比情况。2000年至2020年,首都圈各圈层15-59岁人口占比持续下降,东京都区部和东京都由65.8%和66.0%降至60.2%和58.7%,但高于全国水平52.0%;外围四县2020年15-59岁人口占比仅为50.8%。

// 图31 2000-2019年东京首都圈各圈层15-59岁人口占比变化
中位年龄情况也呈现相似的趋势,2020年东京都区部和东京都中位年龄为44.4岁和45.3岁;首都圈各县平均中位年龄为48.5岁,与全国水平(48.6岁)相近;外围四县平均中位年龄为49.8岁,高于全国和首都圈。

// 图32 2000-2020年东京首都圈各圈层中位年龄变化(岁)
(东京都市圈、东京首都圈、首都圈外围四县为各县平均中位年龄)
3.3 小结
总体来看,东京首都圈人口持续增长,变化趋势上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核心圈层人口增长加速并维持较为年轻的人口结构,而外围圈层人口流失,老龄化程度加剧。与伦敦和纽约都市圈不同的是,东京首都圈核心区域并未出现人口净迁出的情况。随着日本全国人口减少,预计东京首都圈人口变化趋势将持续,核心区域将继续吸引人口迁入,与日本其他都市圈一样,成为全国人口聚集的主要区域。
过去半世纪以来,东京首都圈各圈层人口情况的变化除了受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还与首都圈历版规划的理念和策略有关。58年、68年和76年的第一版至第三版首都圈基本计划以抑制东京扩张和过度聚集为主导理念,通过绿带和限制开发区等措施管控核心区域建成区规模,推动卫星城和新城的建设。从1986年第四版基本计划开始,日本政府对东京都聚集的观点开始有所转变,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人口和经济活动的聚集会对东京的全球竞争力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规划开始关注东京都市圈的区域竞争力,而不是简单的疏解人口,倡导建立一种网络化的区域空间结构,强化中心区和节点地区的能级提升。随着城市更新和各级政府城市治理能力的提升,更多的居民迁入都市圈核心区域以享受便利的生活和优质的公共资源,人口增长并没有对城市环境带来负面影响,而是促进了中心城区活力的恢复。
受新冠疫情影响,东京都在2020年下半年的每个月均出现了净迁出的情况,但大部分迁出人口还是留在了都市圈范围内;同时,2020年东京都市圈净迁入人口为99243人,较2019年的148783人降低33.3%。但在2021年,东京都人口净迁出的趋势应已扭转。根据2022年元旦的最新估计数据显示,尽管东京都出现了26年以来的首次人口下跌,但年度净迁入3897人,人口收缩的趋势主要由自然减少导致。疫情后民众工作和生活模式上的变化,为东京首都圈未来人口变化趋势增加了不确定性。
04 总结与展望
1960年以来,伦敦、纽约和东京都市圈的人口规模总体呈上升趋势。三大都市圈都在一定程度上经历了“郊区化”与“再聚集”的过程,这与全球经济发展格局、规划理念与实践,和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大伦敦地区、纽约市与东京都作为都市圈的核心区域在上世纪后期人口出现流失后,在新世纪恢复了强劲的增长。城市环境与治理能力的提升改变了过去人口增长与“大城市病”的关联,人们可以在享受良好城市品质的同时,选择在更中心的区域生活。
近年来三大都市圈的人口自然变化已成为决定人口发展趋势的关键因素。东京首都圈外围四县人口已出现长期收缩;新冠疫情后,核心区域人口净迁入低于自然减少,也出现了收缩的趋势。伦敦和纽约都市圈核心区域则由于生活成本的上涨,居民持续迁出,依赖人口的自然净增长,亟需通过规划和其他社会政策的积极应对以减缓这一趋势。
三大都市圈核心圈层的人口总体较全国水平更年轻,劳动人口更充足,但外围地区由于缺少年轻人口的迁入,老龄化情况加剧。但这一趋势并不一定是负面的,劳动人口向公共交通便捷、通勤时间短的地区聚集,对都市圈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各级政府需根据实际情况研判,有针对性的施策,如在都市圈外围地区关注老年群体的生活保障,调整并提供相匹配的设施及服务,在核心区域,利用人口的规模效应,更高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加大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力度。
新冠疫情给全球各大都市圈未来地人口变化带来了不确定性。疫情初期,伦敦、纽约和东京都市圈均出现了人口减少的情况,迁出人数增加。但近来,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升和疫情防控措施的调整,都市圈人口也出现回迁。疫情期间如居家办公等工作-生活方式上的改变是否会持续还有待观察。虽然面对面交流和办公室工作的很多方面都无法完全被远程工作取代,但可以肯定的是,公众将对多元的工作-生活模式持更为开放的态度,雇主也将允许员工更灵活地开展工作。回顾历史,疫情和重大历史事件所带来的衰退之后,大都市都能够恢复繁荣和增长。可以预见,在此次新冠疫情后,伦敦、纽约、东京等全球城市和都市圈能延续疫情前的人口变化态势,在全国和全球范围内继续吸引新居民迁入。
数据来源
[1] 伦敦都市圈人口数据来源:1961-2011年数据来自历年英格兰与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全国人口普查,2020年数据来自《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2020年年中人口估计》。原始数据可在www.ons.gov.uk, www.nomisweb.co.uk, data.london.gov.uk, casweb.ukdataservice.ac.uk, www.scotlandcensus.gov.uk, www.nisra.gov.uk 网站获取
[2] 纽约都市圈人口数据来源:1960年至2020年人口数据均来自历年美国全国人口普查;2019年人口年龄结构数据来自2019年“美国社区调查”中的人口估计。原始数据可在www.census.gov网站获取。
[3] 东京首都圈人口数据来源:1960年至2020年人口数据均来自历年日本全国人口普查。原始数据可在www.e-stat.go.jp网站获取。
参考文献
[1] Census Bureau, Over Two-Thirds of the Nation’s Counties Had Natural Decrease in 2021, https://www.census.gov/newsroom/press-releases/2022/population-estimates-counties-decrease.html, 2022
[2] City Intelligence, Population change in Londo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nnex - assessment of updated evidence, 2022
[3] Donnelly F., New York’s Population and Migration Trends in the 2021s, 2020
[4] Government Office for the South East, Regional Planning Guidance for the South East (RPG9),2001
[5] Kobayashi T., Pandemic-hit Tokyo reports population drop, 1st in 26 years, https://www.asahi.com/ajw/articles/14538387#:~:text=Due to the COVID-19,at 13,988,129 as of Jan., 2022
[6] Missika J. & Burdett R., Don’t write off cities just yet: they will survive COVID, 2021
[7] New York City Comptroller Scott M. Stringer, The Pandemic’s Impact on NYC Migration Patterns, 2021
[8] NYC Planning, Population – Current and Projected Populations, 2021
[9] NYC Planning, The Ins and Outs of NYC Commuting, 2019
[10] Overman H. & Nathan M., Will coronavirus cause a big city exodus?, 2020
[11] The Japan Times, Population Influx into Tokyo Area Decelerates in Pandemic-hit 2020, 2021
[12] Trust for London, Population Change, www.trustforlondon.org.uk/data/topics/people/,2021
[13] Wikipedia, History of New York City (1946-1977), 2021
[14] 张磊,都市圈空间结构演变的制度逻辑与启示:以东京都市圈为例,2019
作者:
史钟一 上海大都市圈规划研究中心,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规划师
本文转自: 上海大都市圈规划
注明:本公众号转载文章仅用于分享,不用于任何商业用途。如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后台联络授权或议定合作,我们会按照版权法规定第一时间为您妥善处理。
————————————
微信编辑:雨影晨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