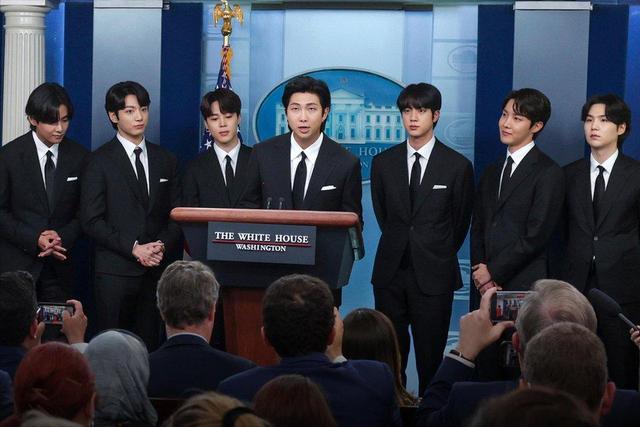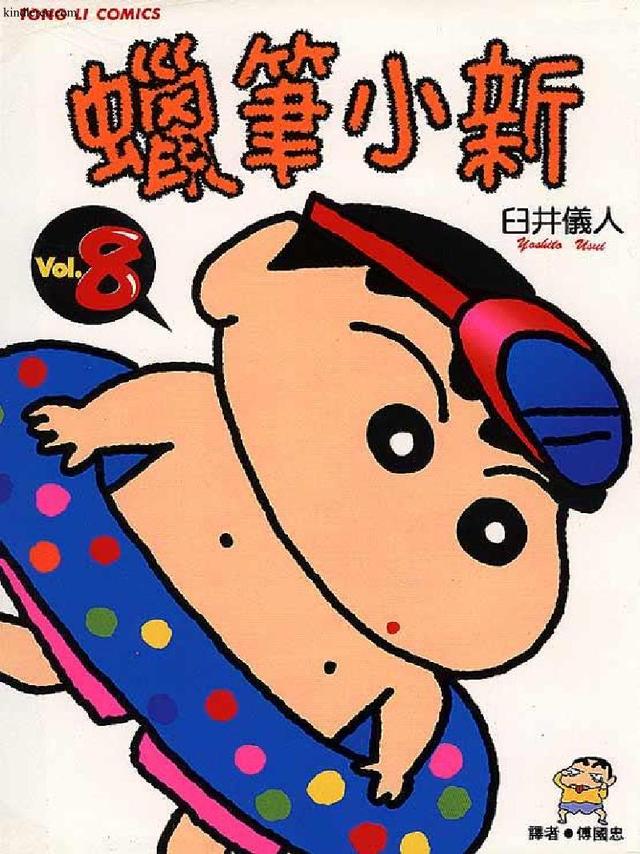《南音,我的乡愁》

南音、流水南音,是粤讴的一种,多出现在叙事曲目的说唱,可长可短,也作为曲牌融于粤剧音乐之中。是中国30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

这里说的不是粤讴的南音,而是我老家的乡音俚语,村戏和歌谣。
我的老家在怀岭南部,离县城不算远,就那么几十公里。屈指算来,我离开老家在县城生活近五十载,但“乡音无改鬓毛衰”,由于时有回乡走动,故没人“笑问客从何处来”。
按理说,离乡不算太远,又“常回家看看”,是不会有什么乡愁可 言的。别人的感受我不得而知,就我的感觉并非如此。南音,已刻在我 的记忆深处,一丝丝一缕缕,无时无刻不牵动着我的神经。
南音,是我的乡愁,或说是乡恋。
乡音俚语,是我的乡愁之一。
怀南地区的方言,大致上分两种,一是“标话”。被专家学者称为“语言活化石”的标话,与汉语言大相径庭,有很多是没有文字的,只 能用国际音标注明,如用汉字,得用近音字代替,但准确度是有偏差 的。例:卖叫“怕”,买叫“呵”,坐叫“破”,狗叫“摸”,大哭叫“罗 颇”,喝酒叫“饮啰”,茶水叫“南波”,外公叫“翁多”,老人叫“伦阻”,女孩叫“力挪”,母牛叫“伊婆”,东西多叫“乃货”,门外叫“屋芒”,没时间叫“不璃耗”,肚饿叫“勇虽”,吃饭叫“己高”,吃饱了叫 “己発”,走路叫“行壮”,番薯芋头叫“勒硬”,如此种种,有专家估计,此语言与侗族语言接近。持此语言的是永固镇和诗洞镇(两镇的标话亦有差异)。二是广州话的宁洞方言,即“宁洞话”。宁洞,今称桥头镇,我的老家又在桥头镇之南,讲宁洞话,杂以标话。持标话的宁洞人,在公众场合讲宁洞话,就像持各地方言者为了与人沟通交流而讲普通话一样。

我个人初步分析认为,宁洞话封开县封川、江口、渔涝、莲都一带 的话音较为接近。封川等地的话与宁洞话相比较,前者属“硬语”,后 者为“软语”。软语有歌唱的味道,换言之宁洞人的话在某种意义上不 是“说”,而是“唱”出来的(原话亦多为相近字音):
“你今在边黎吕”(你现在哪里),短短一语,起伏跌宕,后三字 “边黎吕”音调稍长,约占两拍。
“到我屋吃餐饭毛得是乜呀,敢砸礼”(到我家吃顿饭行不,这么客气),请人吃饭而对方客气,请者热情温婉的语调,甚是动听。
“吴姑你边跌毛苏然,望你人都落岗了,返去木吃敢多腊杂惹,有钱土跌中萧煲办吃”(大姐你哪里不舒服,看你人都消瘦了,回家不要吃那么多不该吃的东西,花钱买点肉类煮饭吃),两人路遇,一方对另一方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柔柔软软的疼爱话令人动容不已。

“你黎泡绒边跌土个委,咁亮夏”(你的红绒线哪里买的,太漂亮了)。“泡绒”一词,牵出了久违的话题和久违之物。回想“文革”破旧 立新前,宁洞妇女已婚者,挽髻盖头帕(外黑里蓝),上捆一组红绒线(2?4条不等),既能固住头帕又可作装饰;未婚女靑年則扎“马尾发”,或结辫子,缀(扎)以红绒线,多盖头帕。外地人称她们为“红线女”,如果头顶红绒线捆头帕的众多妇女聚在一起,便构成一道人文景观,这是别的地方甚少见到的美丽。宁洞女人称红绒线为“泡绒”, 她们认为杨白劳给喜儿扯的二尺红头绳应该叫“泡绒”才是,你喜儿过年才能扎上,可她们一年四季不断,显得很骄傲的样子。今天,“泡绒”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当然亦偶见“复古”的“红线女”,但大多中青年妇女已被流行发型同化。

俚语音好声甜,歌谣村戏更是动人心弦,是我又一乡愁。
自古以来,宁洞人管歌谣叫“南歌”,他们唱道:“唱只南歌抛过江,问妹摞柴是摞芒。摞柴摞芒弟帮摞,一人摞把得成双。“连情不用媒人引,唱句南歌来架桥”。“闻得那边歌声涌,必然是有南歌吹 (唱)。” “南歌叮嘱妹风流,劝弟回家莫要愁。”……
“歌”的前面冠以“南”字,是中国南方山歌的泛称。

1960年以前,宁洞歌兴戏旺,甜美悠远的歌声,日夜回荡乡间。到了年末,贵儿戏的锣鼓响个不停,好戏连连,村民赶夜观戏的火把如龙似蛟,在山路、石径曲折迂倒,照亮了这里的喀斯特山区。

记得有一年春日,具体是哪天我已忘记,为庆祝新春,公社(镇)领导发令,举行全社贵儿戏大汇演,作为文化站工作人员,我算是最忙的了。那天,“庆春堂”、“玩春堂”、“耍春堂”、“和春堂”、“联春堂”、 “迎春堂”、“游春堂”、“赏春堂”、“乐春堂“新德堂”、“共和堂”……各路的贵儿戏班从石谷、岩洞、山径奔涌而出,锣鼓喧天,旗幡(招兴、横彩)飘扬,谭陇岗头的草坪上一片欢腾。贵儿戏本是广场戏,各戏班在这草坪自选场地,数千观众各选看点一—文戏武戏、喜剧悲剧由人。开演令下,遍地“开花' 各演各的戏,各看各的剧,一圈圈一场场,演的各显神通,看的如痴似醉,看到精彩处笑声掌声四起。 一些戏迷抱怨为什么不逐台上演,说这种全面开花的做法相互干扰不说,要紧的是剧目让人看不过来,《薛仁贵征东》、《丁山射雁》、《梁山 伯与祝英台 》、《五虎平南》、《平贵别窑 》、《夜审郭槐》、《避火珠》、《春莺三破父奸谋> 等等,有些观众这瞧一眼,那瞄一会,花多眼乱,戏瘾没过足脏话出来了: “咁仍舞法望佢罗母!”我敢断定,这种集中一地、 场面壮观的汇演,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后来再也没出现过了,主办方也发觉此举虽热闹但不科学。然而余音未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宁洞人议论纷纷,赞弹参半,认为各有千秋亦各有不足, 说xx堂锣鼓打得好,有板有眼;xx堂声色超群,演员不赖;XX堂剧目内容新颖,有警世意义;也有人批评某些戏班的剧目内容和表演动作过于粗俗,只为赚取噱头,不顾社会效果。那次汇演没有评奖,优劣全在观众口碑。参演戏班扛着主办单位发的留念锦旗和一大包糖果,亦觉得有所奖赏,未说怨言一句——多么纯朴的宁洞艺人啊。

我的文学梦是在这样的“大染缸”中“发酵”起来的,几十年都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耕耘,诗歌、小说、散文、戏曲、音乐,学到的仅是三脚猫功夫,作品虽有在省市舞台现身或报刊发表,也获得某些奖项,但大多数上不了桌面。在南音的春雨沐浴下,我学会拨弄几下秦琴,叮叮咚咚地乱弹,《鄂伦春之歌》、《采茶扑蝶》、《平湖秋月》、《饿马摇铃》、 《双星恨》、《柳摇金》、《步步高》、《雨打芭蕉》之类的曲子,弹得有模有样。一个机会让我参加省里举办的民间音乐讲习班,学到了一点音乐知识,平时也会吼几句,吼的时间长了,当初像猪挨刀子的声音竟然消失了,便自以为是起来。那年夏天,我邀了一个广东音乐爱好者,携着招生简章,各背一件乐器,两人踏上了开往广州的长途汽车,去到沙河顶报考音乐专科学校,因没相关证件资料,校方不给报考,遂落魄而 归。我想来想去,大约与达尔文有关。从招生简章上看有一科是考达尔文的。那时我只知语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音乐,却不知达尔文为何物。多年后我才知道,达尔文不是课文而是一个人,他是英国博物学家,曾去厄瓜多尔,在太平洋的火山群岛一—加拉帕戈斯群岛考察生物,回国20多年后写出《物种起源》一书,他提出的观点改变了世界,使人们对物种起源有了新的认识。我恍然大悟,并非达尔文阻止我进入音乐学府的脚步,只怪自己不自量力。诚然,达尔文的研究成果也是一门重要学科,必要的考试是毋庸置疑的。

上音专之梦破碎,而南音之声曼妙,我奉它为天籁。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参与包括宁洞在内的全县民间歌谣、故事、读语、音乐、舞蹈的 搜集整理,个人承担编撰的《贵儿戏志》、《贵儿戏音乐》,被收人国家出版的有关志书、集成,获得国家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等部门的鼓励。本人又与人编辑出版《燕岩南歌> 一书。乡愁,不但隐伏在我记忆的深处,还收藏在华夏史库的深处。

南音,让我“剪不断,理还乱”,余下的路不知还有多长要走,只要有南音相随,日子就不会孤苦寂寥、平淡乏味。
南音,我的乡愁或乡恋

作者周如坤
作者简介
周如坤,1942年12月 生,广东省怀集县桥头镇人。曾任怀集县文化局局长、县文联主席、肇庆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戏剧家协会会员和广东 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1958年起从事业余文艺创作至今,在《羊城晚报》、《游旅》、《西江 文艺》、《西江曰报》等报刊发表文艺作品100多万字,其中有20多个作品在省、市获奖。结集出版小说散文集《梦断燕崖》 (花城出版社)、中短篇小说集《徒歌岁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南音之恋》(羊城晚报出版社)等书, 编撰地方文集多本。
编辑:徐文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