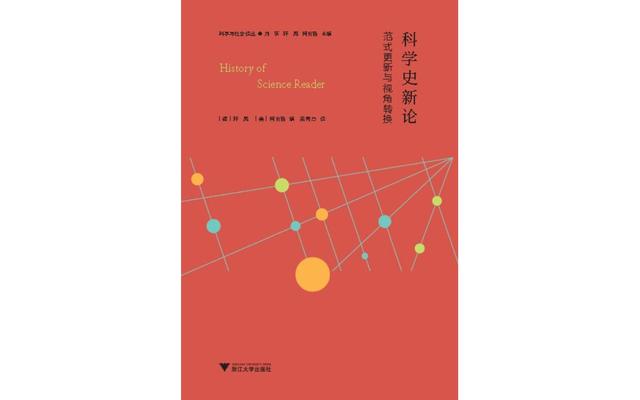“导师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这个借用康德《论优美感与崇高感》的神奇组合已经持续火了两天,它来自一篇期刊论文《生态经济学集成框架的理论与实践:集成思想的领悟之道》。
在这两天里,人们不断质疑该文:从学术撰写体例、期刊发表规则,到无限制吹捧导师及“师娘”,再到浪费课题经费、在讲座给人传授申请课题与发表论文的“歪门邪道”。被吐槽最厉害的,仍然是他浮夸文风下的“导师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网站刊登《关于<冰川冻土>发文不当问题处理情况的说明》,该院认为“该文确实存在与期刊学术定位不符问题,该刊编辑部存在学术把关不严问题”。
然而,随着讨论越来越多,在知乎、微博、豆瓣等社交平台有一种声音正在“悄然兴起”:我们都肤浅了,作者不是在吹捧,而完全是实力黑、高级黑啊,只是笔法隐藏太深。
参与讨论的人不禁感叹,“学术圈的明争暗斗”。他们继而在文中寻找蛛丝马迹,并摘出作者心底不满导师的“证据”:
“导师作为当时国内唯一的冻土方面的院士,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我非常羡慕这个特等奖,但我的名字没有编在冻土英豪集中。”
是吹捧,还是高级黑,各有解读,最后都不过变成饭后谈资。当然,即便是高级黑,也只是大家的一种猜测,没有证据不可当真。只是可以由此引申的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被归入集体作者,在学术界为什么就是如此被在意,以至于人们在进行猜测的时候,就认定这才是高级黑的原因?我们从2019年翻译出版的《科学史新论》一书论述中看到了一些答案。“集体作者”在实验类科学领域最为常见,它是学术分工的结果,但前提又是参与的个体;在那里认定作者,谁被接受,谁被排斥,从来无法消除竞争和不稳定性。这同时也是一个哲学问题。
原作者|彼得·伽里森
摘编 | 罗东
《科学史新论:范式更新与视角转换》编者: (德)薛凤 (美)柯安哲译者:吴秀杰版本:启真馆·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年4月
01
从“我”到“我们”
集体作者的哲学前提
面临聘任或者晋升时,该如何对单一学者进行评估?当团队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无法对最终出版成果进行评判时,如何能发现错误?这些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都不是我在这里要讨论的,至少不是我的首要考虑。
我关注另外一些问题,想探讨的是:一项致力于认识这个世界上某些事物的协作,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要想追问在何种意义上协作团体能认识、讨论或者展示某些事物,考虑到康德的一个类推也许并非无益。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一个核心论点,在同等程度上反驳了经验主义者和笛卡儿。笛卡儿以“我思”开始尝试获取知识,提出“我思故我在”;康德想质询“我”本身。康德要求回答的是:当我们假定在“我”所言说的东西中存在一个统一的自我时,我们正在做的是什么?
康德在这里重申,我们全部的世界表象都得回指到某些共同意识;要不是能回溯到单一的意识点,我们感知到的点和块就一直是散离的,周围的对象于我们而言就什么都不是。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译者:邓晓芒;校:杨祖陶;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与《论优美感与崇高感》(译者:何兆武;商务印书馆,2001年11月)书封。“导师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一文的用法也来自康德的《论优美感与崇高感》。
这里有一个比喻
(不是康德的比喻)
:无数位单独的天气观察员,每个人每小时各自记录一次气温,如果这些信息没有全部发送回某一个人手里,那么天气锋面的存在就从来不会认识到。只有当一个或者多个观察者能够看到这些孤立信息的空间组合构成了等温线或者等压线,作为一个概念的冷锋面才会出场。如果没有统觉的一体性,我们每一个人就如同那些单个的、互不相干的天气观察员一样,是没有整合的聚合而已。如果没有统觉的一体性,我们的世界缺少的绝不仅仅是冷锋面、暖锋面或者锢囚锋面,还会缺少客体的概念本身。
康德的洞察力在此:我们的个体意识的一体性,是任何客体呈现之一体性的必要前提。
实际上,意识的一体性对于在我们看来的任何客体都是必需的。正如气象锋面的比喻已经表明的那样,我在这里的考虑不是传统的康德的问题,而是这种统觉一体性在明确的协作式知识探索运作中的相关性。我在这里要问的是:协作团体在声言某一新事物存在或者对科学的影响时,由此引发出来的“我们”,是采用了哪些特殊机制才得以确保其存在的呢?谁在发声?或者更好的说法是,什么在发声呢?
02
“集体实验者”的诞生
孤单单地在长凳上工作的科学家不见了
集体实验者与先前的科学作者有所不同,这在 20 世纪 60 年代已经显现。当时气泡室物理学开始将协作团队的规模从个位数成员扩展到 15 或者 20 位。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氢泡室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负责人阿兰·桑代克
(Alan Thorndike)
在 1967 年有这样的描述:
我们一直讨论其活动的那个“实验者”到底是谁?“他”极少(如果尚有的话)的情况下是单个人。实验者可能是年轻科学家组的组长,监督和指导他们的工作;“他”可能是一个同行组的组织者,承担推进工作直到圆满完成的主要责任;“他”可能是绑在一起来共同进行工作的群组,没有内部明晰的等级序列;“他”可能是因为共同兴趣而走到一起的个人或者次级小组的协作团队,也许是从前的竞争者的混合,他们因为有着相似的研究计划,于是被更高的权威给合在一起。于是,实验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合成
(composite)
。“他”可能是三个人,更可能是五个或者八个,甚至可以多达十个,二十个或者更多。“他”可能在地理上分散各处,尽管经常是他们都来自一个或者两个机构……“他”可能是短期的,“他”的成员是变换的、开放性的,很难去决定其极限。“他”是一个社会现象,其形式各不相同,无法精确定义。不过,有一点“他”肯定不是。“他”不是传统形象中那位深居简出、孤单单地在实验室长凳上工作的科学家。
在这一不同寻常的文章中,桑代克勾勒了“协作团队作为作者”
(collaboration-as-author)
。这正是最令我有所触动的核心问题。人们可以提出其他问题,如个人如何决定加入群组,或者每个人如何攀爬事业之梯等问题,但是激发我兴趣的,是桑代克提出的更为极端的东西:他认定自己的协作状况不是实验者的集合,而是“协作团队作为实验者”。
正是这一事实的特质让实验者变成了“一个社会现象”,有着不确定的界限、地理上的分散、各不相同的形式以及偶然的内部结构。当桑代克说出来实验者变成了“合成”时,他抓住了战后物理学的某种关键之处,哪怕这在语法上显得蹩脚。
尽管有这种合成性质,在 20 世纪 60 年代,实验者仍然是以作者名字出现的个人。在桑代克所在的布鲁克黑文,谁都不难来确定桑代克小组
(Thorndike Group)
的核心人物是哪一位。尽管一个泡室要求有不同类别的专业知识,这些专家次级组都将报告提交给单一的中心。
阿尔瓦雷茨也负责数据处理领域,一如他也跟负责低温领域的工程师和物理学家打交道一样。最后,发表物理学成果的所有决定要由他做出,所有进入小组的资金也都经他之手。
出于所有这些理由,我认为实验组以负责人命名这一事实干系重大:20 世纪 60 年代的协作团队,是基于一位可赋名的个人缔造的,这位单一个人的行动,可能是在对他人进行咨询以及最终经由他人而采取的;但是,当阿尔瓦雷茨小组发现了一个新粒子时,在某一种意义上这是阿尔瓦雷茨本人的延伸
(至少对外界来说如此)
,因此阿尔瓦雷茨作为给小组赋名的核心人物。甚至当该组的活动增多,分化成低温、扫描、分析和机械各分组时,“阿尔瓦雷茨”的名字还是有两种使用方式,一种是他个人的,另一种是作为群组整体的“伪我”
(pseudo-I)
。
03
署名的规则
谁应该被包括进来?
在两英里长的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
(Stanford Linear Accelerator Center)
的尽头,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启动的斯坦福直线探测器。在团队开始运行之际,斯坦福直线探测器在一份出版物中发表了若干年前制定的作者署名政策来规范目前事务,以备不时之需。
他们要做的最基本、最简单明确的规定是,谁应该被包括进来。如果出版物中留给作者署名的版面有限,作者列表遵循依照字母排序的原则;如果署名的版面没有限定,则依照字母顺序列出机构名称,在机构之下作者名字按字母顺序排列。
“谁是作者?”斯坦福直线探测器协作委员会在 1988年7月提出这一问题时没考虑太多。但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却有着重要的影响,不光关涉协作中的个人,也关涉整个撰写和认证过程。委员会认为:“就物理学论文而言,协作中的所有物理学家成员都是作者。此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应该包括工程师。”从委员会专门提及“物理学论文”可以看出,显然还有其他形式的书面成果,有不同的署名管理条例。
实际上,对作者署名权的管理,既关涉受众范围,也关涉对知识的权益主张范围。如果对知识的权益主张范围限定严格,比如,限定在某个硬件的功能,作者名单可以仅仅为撰写者;如果工作是由工程师来完成的,那么可以将物理学家的名字全部删掉。
或者,如果受众范围限定得足够严格的话,如“内部备忘录”,单独一位物理学家也可以作为单一作者。相反,如果发表一项重大的物理学声明,比如发现了不规则衰变,要将该消息发布到全世界,那么必须由协作团队来作为作者,撰写者个人被降格为“发表者”的角色。
实际上,一项物理学出版物的核心问题是,要非常小心地去定义协作中谁算作涉事作者。这一定义徘徊在两个标准之间:一端是参与者升职结构的实际要求,另一端是哪类工作堪为“作者工作”的概念。
一方面,协作团队要找到某种方式来集体认知某些东西——完成论文;另外一方面,要以某种方式把协作团队的成果安排成如此的结构:带给外界的是单一的、令人信服的讯息。
费米实验室万亿电子伏特加速器的 DØ 探测器团队
(一项有 424 位物理学家参与的协作,其人数还在增加)
的作者署名文献坚持,所有的“真正的”参与者都应该出现在所有的出版物上。毫不意外,这里的问题是如何定义“真正”。
该团队在1991年3月14日发布的作者署名政策要求,除某些例外情况以外,如下人员可以成为作者:高年级研究生或者拥有更高学历者,在论文提交发表之日已参与团队工作至少一年。像绝大多数这类协作团队一样,这里也允许前工作人员在离职后一年内仍然有资格成为作者。但是,一位得到认可的作者必须在对该论文有重大意义的数据运行方面达到了平均轮值数的一半。
04
谁是作者
集体作者无法消除的不稳定性
在一定程度上,福柯也是在探究作者自我中的个人这一问题,尽管他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对福柯来说,确立什么算得上一位作者的“著作”,涉及一整套问题。他问道:我们要把他或者她写的任何东西都给予“作品”这一身份?如果是这样的话,什么算作“任何事情”?他观察到,只有某些为数不多的言语被视为是独有的,其不同于那些任何人都可以说出来的日常看法。比如,“几点了?”这个句子除非在特殊境况当中,不属于我们称为有作者的语言。
作者的名字被用来标记话语的某一样式。话语有作者的名字,人们可以说“这是由某人和某人写的”或者“某人和某人是它的作者”这一事实表明,话语不是平常的言语……相反,这一言语必须在某一特定样式中被接受,在一个给定的文化当中,必须得到某种身份。
然而,福柯将科学从他的分析当中切割出来。在他看来,17 世纪以后,作者的名字不再能赋予科学文本权威性,因为原则上科学中的“真理”总是可以“再阐述的”。福柯认为,作者名字只是用来给定理当标签,不然就是来装饰科学的成果。
不过,考虑到个人和协作团队用超乎寻常的篇幅来保护自己的“好名字”,从表面上看,福柯这种将科学类别与其他文本类别绝对对立的做法,与 1700 年以后科学家们所经历的世界大相径庭。
在福柯发表了《什么是作者?》这场演说之后,吕西安·戈德曼
(Lucien Goldmann)
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史家站起来说,他明白这样的作者是如何死掉的。当然,福柯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都没有主张过作者已死,他自己的兴趣在于:利用别人主张作者已死这一事实,来理解“作者身份”以何种方式在近期文化中改变其功用。
正是出于这种受哲学兴趣驱动而对作者功能进行经验研究的精神,我对物理学们齐心协力地去界定和塑造那类尚无先例的写作这一情况感到兴趣盎然。
如果作者署名意味着该作者的贡献对于整体结果是一项必要条件,那么,每个分支团队的确可以而且必须被视为必不可少的。可是,当“谁做了这个工作,也就是说,谁完全掌控了这项分析及其所依赖的基础?”这一问题被提出来时,那么给出答案就变得令人颇费踌躇。
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复杂的作者署名条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斗争中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在一个层面上,对作者权的争夺可能源于物理学学术共同体这一领域的特殊架构。不过,恐怕现在围绕着粒子物理学家、天体物理学家或者理论生物学家出现的大型协作的难题,毕竟并不那么非典型。
如果我们的构想是正确的话,一方面要将科学工作浓缩到一个“伪我”
(群组整体)
的单一点上,另一方面要承认知识是以分块的形式彼此关联存在于一个宽泛而模糊的储备库当中:在这两种感觉上的需求之间所存在的张力,并非一个小难题。它体现了获取知识活动自身当中,那种无法消除的不稳定性。
本文为独家内容。经启真馆授权整理自《科学史新论》。内容有删节、顺序有调整,大小标题皆为编者所取。
作者 |
彼得·伽里森
整合 | 罗东
编辑 | 余雅琴
校对 | 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