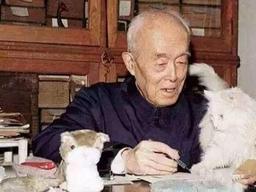清初东南沿海的迁界清顺治18年(1661),清廷强制东南沿海人民内迁30—50里,一直到康熙20年(1681年)才复界,濒海地区长达20多年沦为无人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亘古未有的奇观历史文献称这次迁徙为“迁界”、“迁海”或“禁海”福清族谱称“调迁”或“调移”各地复界的时间可能不同,有的文献说是康熙23年(1684年),但《闽颂汇编》、福清各族谱都说是康熙20年(1681年),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清朝时期的苏北地区?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清朝时期的苏北地区
清初东南沿海的迁界
清顺治18年(1661),清廷强制东南沿海人民内迁30—50里,一直到康熙20年(1681年)才复界,濒海地区长达20多年沦为无人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亘古未有的奇观。历史文献称这次迁徙为“迁界”、“迁海”或“禁海”。福清族谱称“调迁”或“调移”。各地复界的时间可能不同,有的文献说是康熙23年(1684年),但《闽颂汇编》、福清各族谱都说是康熙20年(1681年)。
顺治16年(1659年)四月,郑成功和鲁监国麾下的张煌言部联合攻入长江流域,打到南京近郊,被清军蹂躏十多年的江南人民,群起响应。17年(1660年),郑成功退守台湾后,以台湾为根据地反清复明。为了隔断大陆和台湾的联系,困死郑成功的抗清义师,顺治18年(1661年)八月,“降将罪臣”黄梧、房星烨向清廷建议:颁布迁界令,坚壁清野和迁海缩界(1)。
清康熙元年到三年,清廷连续下了三道“迁界令”,严令东南濒海人民“寸板不许下海,粒货不许越疆”(2),并全部内迁30里,界外房屋、土地全部焚毁或废弃。当时迁界的范围虽然包括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六省,由于郑成功义师的据点在福建,决定了迁界的政策:“江浙稍宽,闽为严,粤尤甚”(3)。负责福建迁界移民的是户部尚书苏纳海,降将黄梧伙同闽浙总督李率泰协助。
第一步是“画界”,就是确定边界的界限。第二步用暴力强迫迁移,即迁界。第三步是砌墙寨“截界”,阻断界内外的联系。“越界数步,即行枭首”(4)。
一、随意立界
距海多少里画界,各文献说法不一:或三十里,或四十里、或五十里,甚至二三百里。清廷发布的迁海诏书只规定三十里,但由于地势不同和官员的擅权专断,各地画界距海里数也不同。如:福清边,“边界以外斗入海八十里万安所,七十里牛头寨,五十里泽朗寨,四十里松下,十里镇东卫,附海五里海口桥、上迳镇,二里硋灶:俱移。(5)”
有的地方界边屡经后移,离海越来越远。如福建省长乐县在顺治18年(1661年)十月“命沿海居民迁内地,北从雁山抵金峰,南至大屿转壶井,直至三溪为界,络绎设八寨”。第二年,“复命八寨居民内迁,北至鹤岭,南至六都井门为界”(6)。
据《粤闽巡视纪略》载,福建的界边自省城闽安镇开始,北抵浙江沙埕670里,南抵广东的分水关1150里,统共1820里。当时各县的界边是:
诏安边以分水关、赤南山、凤山亭、大兴寨和梅洲寨等地为界。
漳浦边以梅洲寨、油甘岭、高塘洋、云霄镇、大梁山、高洋口、苦竹岭、秦溪村、荔枝园、浯江桥、赵家堡、张坑、横口等地为界。
龙溪边以三义寨、江东桥、东尾、九头、马髻山、莲花村为界。
海澄边以横口、洪礁、独石山、关厢村、蔡家庄、三义寨等地为界。
同安边以莲花村、乌头、孤山、凤尾山、灌口寨、苎溪桥、方坑岭、浦头寨、石浔、蹈石山、三忠官、严山、店头舖和小盈等地为界。
南安边以小盈、东岭、大盈等地为界。
晋江边以大盈、龙源山、鹧鸪寨、后渚澳和洛阳桥为界。
惠安边以洛阳桥、石任寨、下金山、下曾山、文笔山、柳庄溪、石寨、丘户村、九峰寨等地为界。
仙游边以九峰寨、枫亭驿、梅岭、壶公山尾等地为界。
莆田边以壶公山尾、壶公山首、天马山、清浦村、胜塔、江口等地为界。
福清边以江口桥、仙岭、蒜岭驿、绵亭岭、渔溪铺、玻璃岭、松树岭、苍霞岭、锦屏、松潭山、牛宅村、里美和定军山等地为界。
长乐边以定军山、高岭山、小石山、石屏山、石龙山和闽安镇等地为界。
闽县边以石龙山、象洋山和马门岭为界。
连江边以马门岭、浦口、麻岭、透岭和棊盘山等地为界。
罗源边以棊盘山、岐阳铺、护国铺、乌坑山、界首岭和白鹤岭等地为界。
宁德边以白鹤岭、县城、铜镜河、溪漓洋、头闽坑和小留岭等地为界。
福安边以小留岭、廉岭、县前洋、尾河、茶洋岭、大梅、柳溪和杯溪村为界。
福宁州边以杯溪村、州城、赤岸桥、杨家溪、店头和浙江沙埕为界(7)。各县界边以东或以南,一直到海边的居民全部迁到内地。这些濒海村庄都沦为“无人村”,长达20多年。
据文史专家俞达珠先辈考证, 福清的界边,相当于“沿现在的福厦公路向北,经桥尾、峰头、硋灶、蒜岭、棉亭、下里、上张、岭脚,转向东,经洋中、油塘到音西的霞楼转向东北到松潭,折向东至龙江南岸转向南,经东峤、晨光、青屿,转北过江到城里、前村、斗垣、牛宅、山下、塔仔门转向东,经首溪、岩兜、凤屿、里美后俸,转向东北经长乐江田一直往北而去。”
二、强制迁界
第二步就是迁界,驱赶界外的居民进入界内,界期三天,逾期强制迁移,否则杀人烧房,甚至把宅舍房屋甚至山林树木,统统焚毁,整个村庄夷为平地,以彻底断绝迁民回归故土的念头。请看:
“檄下民尽徙。稍后,军骑驰射,火箭焚其庐室,民皇皇鸟兽散,火累月不熄。(8)”
“部院住海边烧屋,讨长夫一千一百名……送至福清,因调移,王夫直用至漳,每名雇银四两……又部院往焚福宁一带海居,取夫一千名,每名雇银一两。”(9)
“初,(广东香山县)黄梁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平藩(平南王尚可喜)左翼总兵班际盛计诱之曰点阅,报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阜,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10)”
“惟是辛丑岁(顺治十八年)遭调移,庐舍化为灰烬,田园变成沧海,赤身奔溃,妻孥莫顾,兄弟星居,颠连异土……怠甲寅(康熙十三年)春,世代凌降,干戈不息,赋役横征,民率辛入伍”(11)。
“嗟夫,兵乱之时,遂而迁徙,人皆鸟栖而兽窜矣。千金之家,或耗而无留一者,可胜数哉?(12)”界外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财产,顷刻之间化为乌有。
“(迁界) 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如福清二十八里,只剩八里,长乐二十四都,只剩四都。火焚二个月,惨不可言。兴、泉、漳三府尤甚。(13)”
“当播迁之后,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囷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14)”
清顺治年间,福清全县人口62383人。据记载,被强制迁界的至少四万人。
三、砌寨墙截界
第三步,砌界墙、界寨“截界”,不许界内人民到界外去。若越界,就一律处斩。
在莆田县,“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武兵不时巡界。间有越界,一遇巡兵,登时斩首”(15)。这个县的黄石千总张安“每出界巡哨只带刀,逢人必杀。……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计”(16)
福建和广东的一样,开初以插旗、木栅、篱笆为界。后来就越来越严格,或是“浚以深沟”,或是“筑土墙为界”;再后来干脆征发民夫大兴土木,把土墙改筑为界墙,并且沿界建立寨、墩,派设官兵扼守。
“(康熙7年)正月奉文,着南北洋百姓砌筑界墙,从江口至枫亭。墙阔四尺,高六尺,每户计筑二丈一尺。界口起了望楼一座,遇海另筑界堤。(17)关于沿边设兵戍守的堡塞,福建称之为寨、墩,广东称之为台、墩。大致情况是:“界畛既截,虑出入者之无禁也,于是就沿边扼塞建寨四,墩十数,置兵守之。”(18)。“寨周阔百六十丈,墩周阔十丈不等”“五里一墩,十里一台,墩置五兵,台置六兵,禁民外出”(19)。
“康熙18年(1679年)己未,春正月,诏筑沿边界寨,自福宁及诏安,率一二十里置寨。量地险要,截内外,滨海数十里,无复人烟。(20)”
福清早在清廷下诏之前的康熙元年和九年就沿着界边建筑了镇东寨、杞店寨、九龙山寨、宏路寨、渔溪寨、苏溪寨、蒜岭寨、和峰头寨等八座新寨(21)。
那时,建筑界墙和界寨,要强迫人民自己出钱出力。“城外乡民按户征银,照丁往役。……一寨之成,费至三四千金,一墩半之。拷掠鞭捶,死于奔命者不知凡几矣”(22)。
迁界后,沿海迁民流离失所,没有田地可以耕种,没有正当的活口之路,为了活命,一部分人只得:“相率入田园,掠稻掠麦,摘果实,缚鸡豚”,为偷为盗,掠人钱财,以至掳人妻女,杀人越货,增加社会的动乱。另一部分人被逼上梁山,只得铤而走险,揭竿而起,“不为海寇,即为山贼”,甚至参加了郑成功的反清义师。
由于迁界给社会造成严重的祸害和后遗症,朝廷大员如福建总督姚启圣、两广总督吴兴祚、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等人也都一再上疏要求复界。
姚启圣于康熙19年(1681年)11月初四日再上《为请旨归还边界事本》的奏疏中说,迁界后大量人民无地可耕,无渔可捕,是导致盗薮丛生,望乡而止,有家不敢回的最根本的原因。
康熙20年(1681年),迁民们终于盼来了康熙皇帝复土展界的诏令。龙高半岛、江阴岛等迁民们终于在这一年里回到魂牵梦萦二十年并且早已成为废墟的家园。
一再上疏请求复界的姚启圣去世后,福清90个文人撰写了141篇悼念诗文。其中林日宣和林顺理的两篇如下:
嗟我迁氓妻号子哭公达
福清 林日宣 乡绅
宸聪绘图一幅 帝闵流离复我邦族三党六亲重叙敦睦
嗟我迁氓风飱露宿,今度旧基胥架我屋,宵尔索绹画相版筑,爰居爰处无用龟卜。
嗟我迁氓荒田未复,今皆举趾树艺粟菽,亦有薯蓣兼飱麦粥,沟瘠饿殍顿甦果腹。
嗟我迁氓儿女抛鬻,今复止居重寻骨肉,呼爷和娘扶伯与叔,携手同归全我鞠育。
嗟我迁氓棺露骸暴,今携故土瘞藏枯髑,載登荒陇刈芟翳木,以享以祀麦酿初熟。
嗟我迁氓频遭孥僇,今悉言旋形无觳觫,兵不讥诃界撤为陆,风静波恬兽匿蛟伏。
嗟我迁氓奔波劳碌,今复厥业家皆买犊,女也绩麻士也耕读,养老字幼渐蕃树畜。
嗟我迁氓饥寒颦蹙,今如冬日实安且燠,我海为田网罟盈,舳鱼虾市米贸易衣服。
嗟我迁氓最苦残黩,今无硕鼠吏清卷牍,更免杂徭不遭鞭朴,永式闽邦躬桓蒲谷。
嗟我迁氓营债经渎,今获其苏户无兵蹴,妇子载宁薄腌旨蓄,愿公寿考代膺福禄。
福清 林顺理 儒士
玉融称剧邑,迳水当其冲,舟车繁络绎,比户真可封。海艘入洲渚,食货阗商旅,蛤菜列市廛,仓箱看积貯。夜絃而昼歌,士女厌绮罗,奉令忽迁徙,翔鸟失其巢,田庐遭毁弃,村落丛薜荔,壮者散四方。须鬓俱憔悴,祖父遗腴田,乱草藉荒烟,老羸长㮙腹,不愿享余年,何幸逢制使,瘡痍倐为起,天下溺与饥,辄引为巳耻,封事上至尊。谆复累千言,仁人之利溥,因获沐皇恩,残黎归故土。欢欣尽歌舞,扶老携妻孥,田园复有主,茅屋足栖身。……
四、迁界的危害
清初迁界,不但没有切断沿海人民与郑成功的联系,反而给郑氏集团提供更多的商机。郁永河在《郑氏逸事》里指出:“成功以海外弹丸地,养兵十数万,甲胄戈矢,罔不坚利,战舰以数千计……而财用不匮者,以有通洋之利也。我朝严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而商贾垄断,厚赂守口官兵,潜通郑氏,以达厦门,然后通贩各国。凡中国各货,海外人皆仰资于郑氏。于是通洋之利,惟郑氏独操之,财用益饶”。迁界还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1、土地荒废
据记载,全省界外荒废的耕地:诏安384顷余,漳浦1287顷余,海澄(包括龙溪) 1166顷余,同安1941顷余,南安372顷余,晋江1252顷余,惠安1909顷余,仙游81顷余,莆田4430顷余,福清 4634顷余,长乐913顷余,闽县380顷余,连江547顷余,罗源266顷余,宁德160顷余,福安 484顷余,福宁1797顷余。(23)
据王先谦《东华录》说:“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福宁一州所属十九州县,原迁界外田地共二万五千九百余顷。”实际全省豁田达25904余顷;福清豁田最多,达463400余亩,占全省的18%。
据康熙11年修的《福清县志•地亩》载,福清各朝代所拥有的土地:
唐朝:山田5330顷79亩余,园地5302顷余,共10632顷79亩余。
宋朝:田园10633顷59亩余。
明洪武24年(1391年):官民田地5557顷14亩余。
明朝万历46年(1619年):官民园地、塘地、山5872顷53亩余。
大清顺治年间:官民田园地5872顷51亩余。
康熙元年(1662年)奉迁界外,实存额1166顷37亩余,内又除荒芜139顷38亩余外,实在官民田园地1026顷99亩余。
康熙17年(1678年),又荒芜315顷30亩余。(24)
这就是说,迁界后的康熙17年(1678年),福清的耕地只剩下711顷69亩即71169亩,只有唐宋时的6.7%,清顺治年间的12%。这是个惊心动魄的数字啊!
除了平潭、南日两岛外(25),福清有相当于现在的东瀚、高山、沙埔、三山、港头、江镜、龙田、江阴等八个乡镇的土地全部抛荒,有城头、海口、音西、上迳、渔溪和新厝等六个乡镇的土地部分抛弃。那时,界边已经逼近城关,仅距离三、四里。界外“滨海数千里,无复人烟(26)”。
2、人口减少
在上文土地大量荒芜的的数字背后,是斑斑血泪,累累白骨。迁界前,土地都得到耕种,尚且有人活活饿死。迁界后,只有十分之一的土地得到耕种,有的还不到十分之一,那还不是饿殍遍地吗?据人口专家曹树基等人估计,福建在迁界中死亡的人口至少可达180万,相当于50个福清县人口的数量,因为迁界一年后的康熙元年(1662年),福清人口只剩下35982人。康熙元年(1662年),莆田死亡的人口可能更多,“界内之民死于力役,死于饥饿,死于征输,至有巷无居人,路无行迹者。而招安贼伙又复横加欺凌,土著残黎又无一聊生矣。吾乡人民至是真九死一生矣”(27)。
以广东为例:“先是,人民被迁者以为不久即归,尚不忍舍离骨肉。至是飘零日久,养生无计。于是父子夫妻相弃,痛哭分携。斗粟一儿,百钱一女。豪民大贾致有不损锱铢、不烦粒米而得人全室以归者。其丁壮者去为兵,老弱者展转沟壑。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有司视如蝼蚁,无安插之恩;亲戚视如泥沙,无周全之谊。于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28)。
以广东潮阳县为例,迁界后:“康熙三年(1664年)米价踊贵,钱银斗谷,至采野苗树根以食,价日益贵,卖妻弃子,饥殍载道,甚至寻死者比比,而迁民十之八焉”(29)。
康熙元年(1662年)十一月,礼科给事中胡悉宁上言:“据福建抚臣许世昌疏报,海上新迁之民,死亡者八千五百余人。” “未经册报者又不知凡几?(30)”
在迁界中究竟死亡了多少人,清廷向来讳莫如深,严禁各地方志记载。从据康熙《福清县志》记载的征收人丁银的数字,就可以看出福清人口死亡的数字。
据康熙版的《福清县志• 钱粮简明全书》载,大清顺治年间,福清全县人口62383人。康熙元年(1662年),全县人口只有35982人。据县志载,从顺治末年到康熙元年(1662年),仅仅迁界一年,福清人口就“逃亡”了26401人,“逃亡”了42.3%。所谓“逃亡”,不是饿死,就是被杀害,二者必居其一,真正能幸运逃亡的又有几个? 迁界两年以至多年后呢?又有多少人逃亡?可惜没有具体数字。一直到雍正元年(1723年),福清人口才有37043人。乾隆年间,人口才稍有增长。
3、赋税减少
土地荒芜,人民饿死,自然无法征收赋税,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减少。以福清为例,据康熙版《福清县志》载,福清顺治年间原额男子应征银5847两多,迁界后的康熙元年(1662年)实征银3558两多。顺治年间原额妇女应征银374两多,康熙元年(1662年)实征银49两多。加上其他四项赋税,福清顺治年间一年原额应征银70187两,迁界后的康熙元年(1662年)一年实际征银12088两,只占应征银的17.2%,少征银58099两。江南各省的赋税不知少征多少。
4、渔业停产
除了赋税的减少外,渔业生产也陷入绝境。福清有独特的海洋资源优势:三面临海,东面还毗邻著名的闽东渔场。海里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福清沿海人民历来都是以海为田,以舟为家,万顷波涛任耕耘。福清三分之一的人民靠海洋养活。迁界之后,厉行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福清的损失最大。“万顷沧波舟楫绝,何人更有羡鱼心?(31)”“渔者靠采捕为生,前此禁网严密,有于界边拾一蛤一蟹者杀无赦。咫尺之地网阱恢张,渔者卖妻鬻子,究竟无处求食,自身难免,饿死者不知其几”(32)。
5、盐业停顿
福清的海盐生产居八闽之首。据《元丰九域志》载,宋时福建十县产盐,产量最多的是福清、莆田,这两县设盐仓。“闽中盐场有七,在福州者曰海口场、曰牛田场…在兴化者曰上里场,初迁多在界外”(33)。其中两个大盐场都在福清,都成了这次迁海的牺牲品。“迁海”使福建沿海盐场生产停止,盐民失业。直到康熙九年(1670年)以后才局部恢复生产。福建人民长期吃不到海盐,甚至引起盐荒。
6、海洋运输业的中断
福清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东濒海坛海峡,西临兴化和南日黄金水道,南近台湾海峡主航道。龙高半岛和江阴岛附近不少港澳都符合万吨级港口的标准。万安、牛头尾、江阴等地,更具有世界级大港的条件,可以建成东方鹿特丹。从宋朝开始,由于世界大港泉州港的提携,福清海外贸易业、海洋运输业特别繁荣。福清古地名到处是“澳”。“澳”在福清话中有澳口、港口的意思。“澳”的地名见证了福清曾经海洋运输业的繁荣。清廷推行迁海政策以后,福清海洋运输业被迫中断,对内对外贸易亦受到沉重打击。清初的迁界以及后来统治者的闭关锁国,使福清失去了成为东方鹿特丹的最佳时机。
清初推行的迁界政策,不但没有隔断沿海人民和郑成功的联系,而且制造了长达21年的“无人区”,导致了各行各业的破产,首当其冲地把福清迁民推向了灾难的深渊。他们背乡离井,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几万人客死他乡。龙高半岛、江阴岛等界外大片森林被砍伐殆尽,房屋被焚毁,土地荒芜,生态环境惨遭破坏,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给复界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参考文献:
(1)房星烨,有的文献说是方星华。
(2)夏琳《闽海纪要》。
(3)王沄《漫游纪略》。
(4)清乾隆二十七年《福宁府志》卷四十三《祥异》。
(5)、(7)、(19)、(33)、(36) 清康熙22年(1683年),工部尚书杜臻、内阁学士石柱等人视察了广东、福建的迁界情况,杜臻向清廷撰写了《粤闽巡视纪略》的报告。
(6)清乾隆28年《长乐县志》卷十《祥异》。
(8)高兆《长乐福清复界图记》,见《闽颂汇编》。
(9)海外散人《榕城纪闻》。
(10)清道光7年《香山县志》卷八《事略》。
(11)福清《东瀚蓝田林氏族谱》。
(12)晋江石壁《玉山林氏宗谱》。
(13)海外散人《榕城纪闻》。
(14)、(18)、(22)、(32)余飏的《莆变纪事》。
(15)、(17)陈鸿、陈邦贤《清初莆变小乘》。
(16)陈鸿、陈邦贤《熙朝莆靖小纪》。
(20)邵廷寀的《东南纪事》卷十二。
(21)《走进福清丛书之•史海钩沉》。
(23)《莆田界外》。
(24)乾隆版《福清县志•田赋》
(25)当时,平潭、南日隶属福清。
(26)夏琳《闽海纪要》。
(27)余飏《莆变纪事》。
(28)《广东新语》卷二,地语。
(29)《嘉庆潮阳县志》卷十二,纪事。
(30)《清圣祖实录》卷七。
(30)余飏《莆变纪事》。
(31)清康熙53年《漳州府志》卷二十九,艺文,张士楷《望海》诗。
(32)《闽颂汇编》的《恩德述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