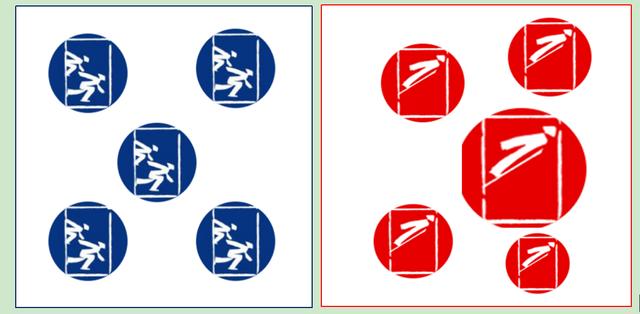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u Fenglu's Studies ofGongyang's Version of Spring and Autumn SHENTU Luming Center for Chinese Thinkers, 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210093,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发展的特点?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发展的特点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u Fenglu's Studies ofGongyang's Version of Spring and Autumn SHENTU Luming Center for Chinese Thinkers, 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210093
春秋公羊学沉寂千年,清代中叶始得复兴。武进刘逢禄精研公羊,有著作十三种,号称专门名家。刘氏春秋公羊学的特点是尊信公羊,排斥左传、谷梁。尊信公羊又偏主东汉何休一家之说。大凡何氏之说必力为疏通证明之,何氏未及者又引而申之,谨守今文师说,不杂糅牵引他家之说,确成一家之言,然何氏误解公羊处,也百般为之弥缝,乃至会曲说,未免不当。
Studies of Gongyang's version of Spring and Autumn weresilent for over a thousand years,and did not revive untilthe mid-Qing dynasty when Liu Fenglu of Wujin County,who wasto be termed "expert scholar", published thirteen works onthe topic.He gave the most credit to Gongyang's version ofSpring and Autumn,and undermined Zuo's version and Guliang'sversion.In the studies of Gongyang's version,he so believedin the theories of He Xiu,scholar of the Eastern Han, thathe would go to great lengths to prove whatever He had said.Where He had missed a point, he would give his owninterpretations by sticking to modern essay traditions of histime and never citing what other schools had said. Where Hehad misunderstood Gongyang's version, he would make everyeffort to protect He,to the degree of distortion.
春秋公羊学沉寂千年,清代中期始得复兴,转至晚清竟为显学。推原本始,此学由乾隆时期常州学者庄存与导夫先路。然庄氏《春秋正辞》不拘汉宋,杂糅古今,其学尚未臻精醇。庄氏门人孔广森、外甥刘逢禄继起,精研《公羊》,始为专门名家。但孔氏不信何邵公“三科九旨”说,刘氏则谨守今文师说,独尊何氏义例,排斥《左氏》、《谷梁》不遗余力,最为专门。在当时及后世的影响也最大,仁和龚自珍、邵阳魏源均从其受学。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刘氏的“春秋公羊”作些探讨,限于本人学识,浅陋之处在所难免,谨请方家指教为幸。
一
刘逢禄,字申受,常州武进人。嘉庆十九年进士,在礼部十二年,常以经义决事,为众所钦服,人称刘礼部。道光九年卒,年五十六。刘氏外祖庄存与,舅庄述祖俱以经学名世,逢禄尽传其学。长洲宋翔凤亦庄氏外甥,能传外家之学,述祖有“刘甥可师,宋甥可友”之语。[1] 刘逢禄的学术师承,其子承宽撰《先府君行述》云:“大抵府君于《诗》、《书》大义及六书小学,多出于外家庄氏。《易》、《礼》多出于皋文张氏。至《春秋》则独抱遗经,自发神悟。”[2] 今案:皋文张氏即张惠言,亦武进人。据戴望《故礼部仪制司主事刘先生行状》说,嘉庆五年,刘氏年二十五,举拨贡生入都应朝考。时父执故旧遍京师,刘氏不往干谒。惟就张编修问虞氏易、郑氏三礼之学,竟以此被黜。至十一年方举顺天乡试。[3]张氏之学以《易》、《礼》为尤精, 著有《周易虞氏义》、《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礼》等,故逢禄特往请业问学。刘子谓乃父于《春秋》独抱遗经,自发神悟,恐未必然。当是承外家庄氏之遗绪,而又有所独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逢禄的众多著述中也以《春秋》之学最有条贯。刘承宽列举了十一种:
主山东讲舍时,为《释例》三十篇,又析其凝滞,强其守卫,为《笺》一卷,《答难》二卷。又推原《左氏》、《谷梁氏》之得失,为《申何难郑》四卷。又断诸史刑礼之不中者,为《礼议决狱》四卷。又推其意为《论语述何》、《中庸崇礼论》、《夏时经传笺》、《汉纪述例》各一卷、《春秋赏罚格》三卷。凡为《春秋》之书,十有一种。[4]
除以上所举十一种外,今本《刘礼部集》中尚有《春秋论》上下二篇、《春秋公羊议礼》十四篇,故礼部《春秋》之书共有十三种。要说明的是,《春秋答难》原本为《箴膏肓评》一卷、《发墨守评》一卷,后改名《春秋答难》。《申何难郑》四卷,当指《谷梁废疾申何》二卷、《左氏春秋考证》二卷,共四卷。这些著述中有七种已刻入仪征阮氏的《学海堂经解》中。(注:这七种书为《公羊何氏释例》十卷、《公羊何氏解诂笺》一卷、《发墨守评》一卷、《谷梁废疾申何》二卷、《左氏春秋考证》二卷、《箴膏肓评》一卷、《论语述何》二卷。)
从上述书名中可以看出,刘逢禄春秋学的特点是“墨守公羊”,排斥《左传》和《谷梁传》,即所谓的“左氏膏肓”、“谷梁废疾”。这些恰恰是东汉何休(字邵公)的主张。据《后汉书·郑玄传》,何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郑玄(字康成)针锋相对,有《发墨守评》、《针膏肓》、《起废疾》之作。何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本来这场争讼已息,今刘逢禄重提这段旧公案,左袒何邵公而难郑康成。因此,刘逢禄的“春秋学”主要特点具体说便是“申何难郑”。
二
刘氏“申何”最有名的著作是《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简称《公羊何氏释例》)十卷,以及《公羊何氏解诂笺》一卷。他自述撰作缘起云:
禄束发受经,善董生、何氏之书,若合节符,则尝以为学者莫不求知圣人。圣人之道备乎五经,而《春秋》者五经之管钥也。先汉师儒略皆亡阙,惟《诗》有毛氏,《礼》郑氏,《易》虞氏有义例可说,而拨乱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响然,则求观圣人之志,七十子所传,舍是奚适焉?故寻其条贯、正其统纪为《释例》三十篇。又析其凝滞、强其守卫为《笺》一卷。[5]
在他看来,五经中《诗》有毛氏传,《礼》有郑氏笺,《易》有虞氏义,都有条例可说。作为五经“管钥”的《春秋》惟有《公羊传》有义例可寻,故“寻其条贯,正其统纪”作《释例》。《释例》一书确切地说是给何休的《解诂》作释例。众所周知,东汉末年的何休是汉代为公羊学作总结的人。何氏《解诂》是“略依胡毋生条例”而作,可见公羊师说本有条例。后世左氏孤行独兴,公羊先师传授之义法遂沉湮不明。(注:胡母生条例,散见于何氏《解诂》,未有专书。何氏《文谥例》,仅见于《公羊传》杨疏。《公羊传条例》,见于《七录》,今佚。)今刘逢禄作《释例》,讲明何氏义例,于《公羊传》厥功甚伟,意义很大,可谓是“孤绪微茫接董生”了。(注:夏曾佑赠梁启超诗云:“璱人申受出方耕,孤绪微茫接董生。”这是说清代今文学的学术渊源,刘逢禄(申受)、龚自珍(璱人)之学出庄存与(方耕),诸氏上承西汉的董仲舒,故有此言。见梁著《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二节,东方出版社“民国学术经典文库”本,1996年版。)
刘氏《公羊何氏释例》的体例是,先标举经传文字,即将原本散见于经传及何氏的《解诂》的内容,分别纳入相关的“例”中,刘氏自己的见解则以“释曰”的形式表而出之,附于每篇之末。其书三十篇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大例。张三世例、通三统例、内外例,此三篇是阐发何氏“三科”说的,故《刘礼部集》中迳标曰“释三科例”上中下三篇(刻入文集中的“释三科例”是《公羊何氏释例》中的“释曰”部分,文辞稍异于《释例》。又《释例》第十一篇《王鲁例》入于文集的“释三科例”中篇中)。时月日例、名例、褒例、讥例、贬例、诛绝倒例诸篇为“释九旨例”。三科九旨是何休从《春秋》中归纳出来的文例。何谓三科九旨?何氏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律意轻重例、建始例、主书例诸篇为“释特笔例”。不书例、讳例、阙疑例诸篇为“释削例”。朝聘会盟例、崩薨例、大国卒葬表、娶归终始例、郊禘例诸篇为“释礼制例”。公终始例、致公例、内大夫卒例诸篇为“释内事例”。此外,还有“释兵事例”、“释地例”、“释灾异例”等。
从刘氏归纳的上述名例中不难发现,这部本来充满着“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公羊传》及何氏《解诂》,经如此归纳之后,原原本本,极为清晰。更有原本晦暗不明之义,至此乃得大明。刘书出后,时人及后进学者极为推崇,视为汉学专门名家。与刘申受齐名,被人称为“常州二申”的李兆洛(字申耆)为其作《传》时称刘书“自汉以来,未尝有也”。[6]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谓“淹通经传”。[7]阮元编刻《皇清经解》于说经之书取去颇严,而此书得以收入,可见阮氏是将它视为汉学专著的。尤为难得的是持古文立场的章太炎也称“属辞比事,类例彰较,亦不欲苟为恢诡。然其辞义温厚,能使览者说绎”。[8]
刘氏为何如此重视何休的《解诂》,不惜花费很大心血为之作《释例》,意犹未尽,还作《解诂笺》一卷以“申何”?因为刘氏认为欲知《春秋》微言大义,必由《公羊传》;欲通《公羊传》必先通何氏的《解诂》。换句话说,何氏《解诂》是通向《公羊》的津逮,由此可知孔子“微言大义”之所在。刘氏这样重视公羊何氏,还有一个原因,当时学者谈《春秋》言必称《左氏》,对《春秋》的书法问题表示疑问。如乾嘉时期有大名的钱大昕就认为《春秋》之法直书其事,使善恶无所隐而已。这种观点是刘氏绝对不能同意的,为此特作《春秋》上下二篇。上篇专对钱氏而发,批评钱大昕以史法解《春秋》之误,他说:“《左氏》详于事,而《春秋》重义不重事。《左氏》不言例,而《春秋》有例。”[9]正因为《春秋》重义不重事,故所不书多于所书, 故有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如仅以事求诸《春秋》,则尚不足为《左氏》之目录,孟子何必说“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其实,以史法绳《春秋》的不止钱氏一人,也不自钱氏始。唐代刘知己的《史通》已开先河。《史通·外篇》有《惑经》、《申左》二篇,用史法绳《春秋》,诋《春秋》有十二“未谕”、“五虚美”。后世多沿袭这种观点,这是不解《春秋》之故。孔子因鲁旧史而成《春秋》,并非是将鲁旧史原文抄录一过,而是经过了一番笔削加工工作,(注:孔子与《春秋》的关系,本来不是问题,然近世以来有学者否定与孔子有关,如疑古玄同先生等。今人杨伯峻先生虽不否认《春秋》与孔子有关,但关系仅限于孔子曾将《春秋》作为教本教授过弟子而已。杨说影响很大,然实有可商之处。李学勤先生有《孔子与春秋》专文纠正杨说,谓孔子修改鲁史,成为传世《春秋》,自其本于旧作而言是“修”,由其终成新书而言是“作”。孔子自谦“述而不作”,弟子后人尊之为圣人,说他是“作”,其间没有矛盾。李说见《缀古集》第16—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版。)加进了自己的政治观点,也即孟子所说的“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表面上看写的是齐桓、晋文之类的事件,用的是史书体裁,实则是一部明义的书。《庄子·天下篇》云:“《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易》以道分,《春秋》以道义。”又《司马相如列传》云:“《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都说明了这个问题。惜唐代以后学者将三传束之高阁,《春秋》之义遂多不明。清代汉学复兴,提倡实事求是,《春秋》三传专家辈出,成就远迈前代。刘申受肯定《春秋》是“重义”的著作,诚为卓识。强调《公羊传》传孔子的“微言大义”,也不失为一家之言。
《公羊何氏释例》一书,梁启超对它有很高的评价,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凡何氏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诸义,次第发明。其书亦用科学的归纳方法,有条贯,有断制,在清人著述中,实最有价值之创作。”梁任公站在今文经学立场上发这番议论自然无可厚非。如果我们抛开门户之见,则可以发现刘氏次第发明的“张三世”诸义,不无可议之处。咎在刘氏偏信何邵公太过,甚至何氏误解《公羊》之处也百计为之弥缝,妄相牵合。这只能说有功于何氏,而无利于《公羊》。
先看“张三世”。“三世说”是何休根据《公羊传》“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总结出来的例。《公羊传》于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提到这个问题。何休《解诂》于隐公元年传下说:“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浅深,时恩衰义缺,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故于所见之世,恩己与王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无罪皆录之,‘丙申,季孙隐如卒’是也。于所传闻世,,王父之臣恩少杀,大夫卒,无罪者日录,有罪有者不日略之,‘叔孙得臣卒’是也。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粗,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狄于攢函’、襄二十二年‘邾娄鼻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衰录隐,上治祖祢。”今案: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世。吾师金先生有说,谓犹今人说现代史、近代史、古代史一样,远近异名、异辞是由于时间有远近,记事的详略,因而也不同[10]。这个比喻极为恰当。《公羊传》的本义是说所获得的史料有的是直接,有的是间接的,有的是再间接的,因而在写法上不能一样。也就是说史料是近者详,远者略,在写法上也应该详近略远。这本来并不费解,何氏用“恩有厚薄,义有浅深”来解释,求深反惑,此一误,何氏又将“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牵合一体,据此把《春秋》说成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谬之尤甚,此二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春秋》的一条大义。《春秋》成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邾娄人会吴于钟离。”《公羊传》解释说:“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可见《公羊传》的这番解释是从礼制的等级制度引申出来的,由近到远,由深到浅。与前之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世”本不相涉,何氏却妄相牵合,制造出一个据乱、升平、太平的“三世说”来,实在没有道理。顾颉刚先生批评此为汉儒臆说,顾氏云:“此三世之说殊难稽信也。事实上春秋世愈降愈不太平,政乱民苦无可告诉,可谓太平乎?使孔子而果修《春秋》,当不至扬乱世指为太平也。”[11](P15) 顾氏所云诚有卓识,而近世说《公羊》者往往将“三世说”视作圭臬,目为《公羊》之核心,郢书燕说,皆由何氏而起。弄清了这一点,则申受“张三世”的大义不待辨而明,无非是将何氏的怪异之论推进一步而已。梁任公盛赞之语,不可据为典要。
再看“绌周王鲁”。此说也见何休《公羊解诂》,千载诟病。而自刘申受以下近世治公羊学者却喜谈这个问题,认为这也是公羊学说的核心之一,舍此似不足以谈《公羊》,门户之见,可见一况。刘氏《公羊何氏释例》第十一篇即《王鲁例》,将何休学说发挥到了极至,请看他的“释曰”:
王鲁者,即所谓以《春秋》当新王也。夫子受命制作,以为托诸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引史记而加乎王心焉。孟子曰:“《春秋》者天子之事也。”夫制新王之法,以俟后圣,何以必乎鲁?曰:因具史之文,避制作之僭,祖之所逮闻,惟鲁为近,故据以为京师,张治本也。圣人在位如日丽乎天,万国幽隐,莫不毕照,庶物蠢蠢,咸得系命,尧舜禹汤文武是也。圣人不得位,如火之丽乎地,非假薪蒸之属,不能舒其光,究其用。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故曰:归明于西,而以火继之,尧舜禹汤文武之没而以《春秋》治之,虽百世可知也。
“王鲁”即以《春秋》当新王,《春秋》当新王即须“绌周”,此又牵涉“通三统”诸义,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已有斯意。董仲舒说:“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又说:“《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而殷周为王者之后,绌夏改号禹谓之帝禹。录其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何休取以注《公羊》,《春秋》宣公十六年说:“成周宣谢灾。”《公羊传》解释说:“成周宣谢灾,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何休《解诂》说“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灾中兴之乐器,示周不复兴。故系宣谢于成周,使若国文,黜而新之,从为王者后记灾也。”案:《公羊传》的“新周”应读为“亲周”,古亲、新通。(注:孔广森对“新周”有别解。孔氏云:“周之东迁,本在王城,及敬王避子朝之难,更迁成周,作传者据时言之,故号成周为新周,犹晋徙于新田,谓之新绛。郑居郭郐之地,谓之新郑云尔。”说见《春秋公羊通义》(《清经解》卷六八五)。陈澧对此评价甚高,谓“新周”二字,自董生以来,将二千年,至巽轩乃得其解云云,说见《东塾读书记》卷十,(《清经解续编》卷九五四)。案:孔陈二氏之说皆非。)前引董仲舒文作“绌夏、亲周、故宋”可证。又《史记·孔子世家》说:“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可知《史记》也作“亲周”。司马贞《索隐》谓孔子作《春秋》以鲁为主,故云据鲁。亲周是说孔子之时,周室虽微,然究为天下之宗主。此说甚是,“亲周”是表明鲁与周有特殊关系。鲁之始封伯禽为周公之子,正由于有这层特殊的关系,焉能不亲?如宣公十六年“成周宣谢灾”这件事,倘若发生在别国,完全可以不必记,而发生在“成周”就不能不记了,这就是“亲周”,《公羊传》写作“新周”,其意正同。何氏妄涉三统说,硬要解作“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荒谬之至。毋怪后之杜预驳之曰:“(《春秋》)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即周正也。所称之公即鲁隐公也。安在其黜周王鲁乎?”[12]王祖游也说:“《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起,于文为俭,通经为长。任城何休训释甚详,而黜周王鲁,大体乘硋,且志通《公羊》而往往还为《公羊》疾病”[13]宋代苏东坡《论春秋变周之文》也谓“黜周王鲁”,《公羊》无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14]清代陈澧也谓《公羊》无此说,且举《春秋》成公元年“王师败绩于贸戎”。《公羊》云:“王者无敌,莫敢当也。”既以周为王者无敌,必无黜周王鲁之说。[15]上引诸家驳议,可以澄清这一问题,很显然,孔子作《春秋》本欲兴周,怎么会“黜周”呢。如说“王鲁”,则诚如孔颖达所质问的“鲁宜称王,周宜称公”,显然这是说不通的。[16]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前引《王鲁例》是发挥何氏之义,在《春秋公羊议礼·制爵第四》中守的也还是何氏之义。(注:刘氏云:“以《春秋》当新王,始朝当元勋,进小国为大国,滕子进侯并其父以恩礼卒之,所谓善善也长。其书公朝王所,不为公朝起也。王使来聘,公使与诸侯同文,著新周也。鲁使如周不称使,当王也。公如京师,如齐、晋、皆不言朝,当巡狩之礼也。”从这一段话可知刘氏守的是何氏之义,且又有进一步的发挥。)但《刘礼部集》卷四的《释三科例》中篇却说:
《春秋》之托王至广,称号名义,仍系于周,挫强扶弱,常系于二伯,何尝黜周哉?《春秋》可以垂法,而鲁之僭,则大恶也,就十二公论之,……而免于《春秋》之贬黜者,鲜矣。何尝真王鲁哉?
在这里刘氏又谓“黜周王鲁”非真,未免是前后不一,令人无所适从。陈澧就提出质问“然则《春秋》作伪欲”?大概刘氏也觉得自己发挥何氏之说过偏而难圆其说,故有所修正。前举《公羊何氏释例》成书在前,此或晚年改定之说。
刘氏“申何”,不但体现在说《春秋公羊》中,还有《论语述何》之作,以何氏之学说《论语》,认为孔子“微言大义”惟何氏一家得之。这实在是尊奉何氏太过而走向极端的例子,此不作深论。
以上探讨了《公羊何氏释例》的一些得失,或问《春秋》到底有没有例呢?宋代的洪兴祖认为,《春秋》本无例,犹如天本无度,治历者即周天之数以为度一样。[17]洪氏的说法是对的。我们可以悬想孔子作《春秋》时必定有他自己的著书原则,这些原则体现在《春秋》之中,只不过没有明说。后之传《春秋》者众,传闻异辞,各尊所闻,因此各家归纳的例不尽相同。也可以这样说,所谓例是后人研习《春秋公羊》时,从书中归纳总结出来的条例。如传《春秋公羊》的胡毋生就作过条例,何休《解诂》就是略依胡毋生条例,隐刮成辞的。何氏本人也作过《春秋文谥例》。再如晋代的杜预也作过《春秋释例》,都属同一回事。而在刘申受看来,作为五经管钥的《春秋》是有例的,《春秋》的例只能从《公羊传解诂》中求之,那就失之偏颇了。这里不妨套用宋代洪氏的两句话:“独求于例,其失拘而浅;独求于义,则失迂而凿。 ”[17]综观《公羊何氏释例》不免有既拘而凿之弊。
三
刘氏一方面倡导《公羊》,做了大量的“申何”工作;另一方面大力排斥《左传》、《谷梁传》。贬低《谷梁》的专书有《谷梁废疾申何》二卷。由于《谷梁》在历史上素不能与《公羊》、《左传》争长短,因此刘氏对此二传的攻击程度不一。诚如章太炎所说:“《谷梁》见攻者止于文义之间,《左氏》乃其书与师法之真伪。”[18]可见刘氏攻击《左传》的程度要大于《谷梁传》。
《谷梁废疾申何》的主旨同样是为了“难郑”。盖郑玄《六艺论》说《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谷梁》善于经,而迹近孔子。刘氏最不满意的是“《谷梁》善于经,而迹近孔子”一语。如说《谷梁》善于解经,其义又符合孔子微言大义,岂非是《谷梁》压倒了《公羊》?为此他要大力说明“微言大义”惟公羊氏得之最多,而《谷梁》所传十不得二三,只能说是为《公羊》拾遗补阙而已。刘氏说:
窃尝以为《春秋》微言大义,鲁论诸君子皆得闻之,而子游、子思、孟子著其纲。其不可显言者,属子夏口授之公羊氏,五传始著竹帛也。然向微温城董君、齐胡母生,及任城何邵公三君子同道相继,则《礼运》、《中庸》、《孟子》所述圣人之志,王者之迹,几乎息矣。谷梁子不传建五始、通三统、张三世、异内外诸大旨,盖其始即夫子所云“中人以下不可语上者”。[19]
这里从传授师承上力争公羊氏是传《春秋》的正宗一脉,虽也承认谷梁氏也出于夏氏传授,但所得的“日月之例”、“灾变之说”终是皮相之谈。至于如“建五始”、“通三统”、“张三世”之类高深的“大旨”,是公羊氏的独家之秘,不是中人以下者随便可得与闻的。刘氏从《春秋》十二公中摘出一些事例,说明《公羊》之义为长,贬《谷梁》之义为短。道光年间,丹徒柳兴恩作《谷梁大义述》,于刘氏之说多有所辨正。柳氏沉潜此学达二十年之久,其说多有可观,此从略。
刘氏攻击《左传》的专书有《左氏春秋考证》和《箴膏肓评》二种。其要旨约有以下二端。
一、认为《左传》的名称应是《左氏春秋》,而不是《春秋左氏传》。此书性质犹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冒称《春秋左氏传》则是东汉以后人以讹传讹造成的。他还进一步指出:“太史公时名《左氏春秋》,盖与晏子、铎氏、虞氏、吕氏之书同名,非‘传’之体也。《左氏传》之名,盖始于刘歆《七略》。”[20]刘氏这一番话,不仅仅是简单的书名异辞问题,而是关系到《左传》的地位问题。如果说是《春秋》的“传”,那就意味着是解释孔门思想的书,倘非《春秋》的“传”,意味着与孔门无关,充其量不过是与《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之类等量齐观。前者属于神圣的“经”,后者不过是子部家者流。这个问题在我们今天看来殊属无谓之争,无论是经是子都不过是研究古代文化的史料而已,而在当时无疑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汉代今文博士反对《左传》立于学官,理由是“不传《春秋》”,目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禄之途。今刘氏釜底抽薪,其手法较汉代今文博士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所做的工作是以《春秋》还之《春秋》,《左氏》还之《左氏》,以及“删其书法凡例,及论断之谬于大义、孤章绝句之依附经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真”。既然《左氏》不是解《春秋》的《传》,自然谈不到有什么“书法”、“凡例”。他还突出《左传》的“良史之材”与“文辞赡逸”,表面上看是褒扬《左传》,实则贬在其中,明眼人一看便知,不妨抄录一段,以见其意。
《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多洽,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名为尊之,实则诬之,《左氏》不任咎也。观其文辞赡逸,史笔精严,才如迁、固,有所不逮。[21]
二、以为《左传》是刘歆伪造的。《左氏春秋考证》中举出许多事例,证明是刘歆“妄作”、“附益”。刘氏这一观点影响极大,后之康有为进一步坐实《左传》是刘歆从《国语》中析出一大部分材料比附而成,并附以解经之语迷惑后世。直至近人也仍有信奉此说的。但对刘氏之说持批评意见的人也大有人在,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即对《左氏春秋考证》下卷逐条进行驳斥。《驳箴膏肓评》对刘氏的《箴膏肓评》也作了逐项驳斥。章氏是古文经学大师,立场不同,间有意气用事的地方,然其立说大多可从。民国间钱穆先生有《刘向歆父子年谱》,所谓刘歆伪造之说,至此可以息讼。
总之,刘氏为扬《公羊》,必定要贬《左传》和《谷梁》,武断傅会之病在所不免,这也是历来经师的门户之见在作怪。关于《春秋》三传,平情而论各有长短,正如前人所说《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公》《谷》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因此三传各有存在的价值,完全不须抑此扬彼。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刘逢禄的《春秋》学特点是“申何难郑”,即尊信《公羊》,排斥《左传》、《谷梁传》。尊信《公羊》又偏主何氏一家。凡何氏之说必力为疏通证明之,何氏未及者又引而申之,可谓何氏功臣;谨守今文师说,不杂糅牵引他家之说,确成一家之言。然何氏误解《公羊传》处亦百计为之弥缝,乃至傅会曲说,不能不说有左袒何邵公之失。综观刘氏说经之得失利病,与历来经师相同。时贤著文谓其发明公羊学说中的“张三世”、“通三统”之义,有历史进化论思想;“黜周王鲁”有寄托于“新王”之意;且云刘氏身处鸦片战争前夜,面对当时西方列强凌辱中国的危局,故大力阐发“大一统”思想等等。刻意求深,未免陈义过高。刘氏的公羊学下启龚、魏、乃至康、梁。龚喜以公羊讥切时政,康摭拾公羊之义以为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这些都是事实。康氏援引古老的公羊学说,意不在春秋公羊学本身,而在维新变法,属于旧瓶装新酒性质。而刘氏纯属今文经学的经师,其春秋学研究仍属清代“汉学”研究范围内。只不过乾嘉以来朴学诸儒宗贾马许郑,究心于名物训诂之学。而常州诸贤不泥守章句,意在洞明经术,究极义理,学术宗旨与当时朴学家异趣而已。
原文参考文献:
[1] 赵尔巽.清史稿·宋翔凤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 刘逢禄.刘礼部集:卷十一末附[M].光绪十八年延晖承庆堂重刻本.
[3] 戴望.谪麟堂遗集:卷一[M].光绪元年赵氏刻本.
[4] 刘承宽.先府君行述[A].刘逢禄.刘礼部集:卷十一末附[M].
[5] 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叙[A].清经解[M].上海:上海书店影印,1988.
[6] 李兆洛.礼部刘君传[A].养一斋文集:卷十四[M].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7]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 章太炎.馗书·清儒[A].章太炎全集: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9] 刘逢禄.刘礼部集.卷三[M].
[10] 金景芳.孔子与六经[A].金景芳古史论集[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
[11] 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M] .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
[12] 杜预.春秋序[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3] 晋书·王接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4] 苏轼文集: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5] 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十[A].清经解续编[M].
[16] 孔颖达.春秋序正义[A].十三经注疏[M].
[17] 春秋三传:卷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8] 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序[A].章太炎全集:第二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9] 刘逢禄.谷梁废疾申何叙[A].清经解[M].
[20] 左氏春秋考证[A].清经解[M].
[21] 刘逢禄.春秋左秋考证[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