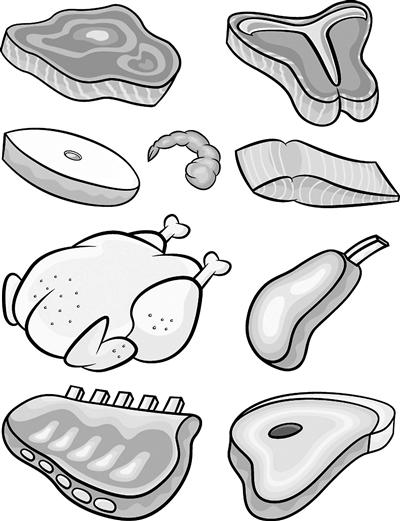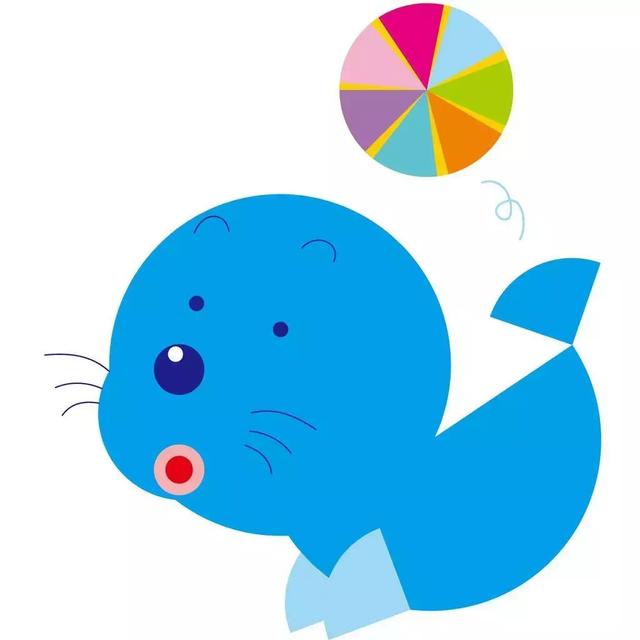很多学者都认为,“古代中国人在狩猎和畜牧活动中逐渐熟悉了动物对象,化敬畏为亲近,在各氏族融合的过程中,某些氏族崇拜的动物得到共同接受;又出于纪年的需要,选择那些适应于纪年、纪时的动物,使之化为‘生肖’的符号。经过长期选择与交融,淡忘了图腾,终于形成十二生肖。”[1]77人们不可能直接将奉为神灵的动物,直接转变为附属于人类、与人类结合的生肖动物,在动物崇拜的动物与生肖动物的选择间,一定还存在一个过渡环节。这个选择与交融的环节,受到了《山海经》的影响。《山海经》与十二生肖都是先民们受动物图腾崇拜所进行的创造,因为《山海经》动物崇拜的直觉思维更为原始,产生于十二生肖之前,十二生肖的形成过程也受到《山海经》的影响。

《山海经》里有众多动物,也有动物与动物相结合的奇珍异兽,但是明确提出为人面兽身神的动物却不多,而《山经》里的山神全为人兽合一,且为单一动物即一人一兽组合而成,这些分别与人类组合成为山神形体的动物,刚好属于十二生肖的十二个动物范围之内。《山海经》里的山神是人兽结合,生肖属相也是人兽结合,不过一个是形体的组合,一个是灵肉的结合,达到了更高的高度。从动物崇拜,到动物之间形体组合的灵物崇拜,从人与动物形体组合的山神崇拜,抽象到动物与人灵肉结合的生肖崇拜,这是一条人类逐渐认识自我的发展路程,也是生肖动物逐步确定的过程。
一、《山海经·山经》与十二生肖对《山海经》成书年代与作者的探讨,其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已成共识,目前“多数近代学者认为《山经》所记录的地理信息、自然产物来自于唐虞之际大禹治水之后的一次大规模国土资源考察活动。”[2]16该书出现和上古文化走向大一统的政治权利集中的现实需要相对应,为祭政合一的神权需求服务[3],实际上我国夏时就已经实现了统一的国家局面,或是古代巫师的口传而题为夏禹、伯益所作[4]。综合众说,《山经》至少在西周以前就已经在最早的知识分子巫师之中广为流传,早于分别成书于夏初、先商、西周或晚至春秋战国时期的《海外经》、《大荒经》、《海内经》,直至西汉时被合编。
生肖动物最早出现在先秦典籍中,从出土文物和文字记载来看,殷商甲骨卜辞、《易经》、《诗经》都有关于生肖动物的记述,但此时的生肖动物并未形成十二生肖,只是生肖符号。“支”最早见于西周之前,“用干支纪年最早文献始于春秋时代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5],上层文人用十二地支纪年,底层农民用十二生肖纪时,十二生肖的出现应该晚于十二地支,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墓出土的秦简下葬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这是目前十二生肖最早的记录,说明此时民间已出现了相对完整的生肖动物。两汉时期,从王充的《论衡》可以看到,十二动物的名称及其与地支相配的顺序逐步固定下来,即: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6]7-16北朝后期始将十二地支与十二生肖相结合[7]。十二生肖产生于春秋时期,与学界认同的“十二生肖的说法大约在战国时就已存在”[8]152的说法不相矛盾。
《山经》是《山海经》中成书最早的部分,在西汉刘歆父子编著《山海经》之前,《山海经·山经》及其他各部,已在民间散落多年,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于数略·形法类,视为卜史、巫祝所用的占卜之书,西晋郭璞称时人皆以其为“怪”书,可见《山海经》被认为是怪异之书是有历史传统的,《山海经·山经》因其对地理山川的记录,常被巫卜用来占卜,其对祭祀仪式和祭品的记载成为巫术的教科书,学者袁珂、孙致中等众多现代学者也认为《山海经》为“古之巫书”,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简书和甘肃天水放马秦墓发掘的简书,两批秦简关于十二生肖的记载,均见于战国后期的《日书》一一选择日子吉凶的民间用书。[9]125而商、周时代出现的干支和若干生肖动物的符号,也是在甲骨卜辞中。在全民皆巫、事事皆卜的时代,对农业生产的预测占卜巫术不可缺少,就已知的《山海经》和十二生肖发展历史来看,十二生肖受到《山海经》的影响是十分可能的。
《山海经》的山神信仰没有与十二生肖相联系,一是《山海经》内容驳杂庞大,是一个可以无穷探索的宝库,十二生肖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文化现象丰富,仅是本体研究就有足够的空间;二是历代学者们对《山海经》成书年代和十二生肖缘起年代一直略有争论,随着近年来不断的新的材料的发现和支撑,才得以大致确定;三是因为图书的分类问题。王充《论衡》、《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都将其归为史部地理类,唐代刘知几将其归类为“地理书类小说”,清乾隆年间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分类为“异闻类小说”。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说明《山海经》与十二生肖有联系,但是《山经》产生时间早于十二生肖,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山经》被当做巫书占卜的经历与甲骨卜辞中的生肖符号密切相关。
二、《山海经·山经》与十二生肖的动物选择《山海经》“全书记载了550座山望、300多条水系、473种动物、525种植物、673种矿物、130多个国家和部落,还有古神名200余个,涉及面积达几百万平方公里。”[10]1记载的动植物信息,“按照传统中药学分类:动物方面,包括虫类品种12个,鳞类品种41个,介类品种13个,禽类品种54个,兽类品种53个,禺类品种10个。”[2]139全书持有超然力量的神祗形态,人形出现55次,蛇形29次,龙形16次,鸟形12次,虎形9次,兽形8次,猪形6次,马形5次,豹形2次,牛形2次,羊形2次,麟形1次,犬形1次。这些神可以分为三类:引起天象变化的神、创造人类文明的神、制造与解决人世纷争的神,其中以第一类为众,并且这种超自然力量都集中在山林。《礼记·祭法》记载:“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此五代之所不变也。”“天象之变化为神,怪物亦为神;如此以山林多神祗,藏匿众多超然力量,乃初民之普遍想象。”[11]118这是初民的山神信仰的体现。
实用性是图腾崇拜的特点之一,《山海经》与十二生肖都是图腾崇拜的发展,《山海经·山经》鸟兽鱼虫的拼合,“实际上是一些原始群体经过数量简化的图腾徽号”,“每一个怪物都是一个部落级群体在神形方面纳众归一的诸神结构。”[12]60十二生肖原本是农民用来计时的,是农业生产规律性的产物,农业发展成熟,生肖动物的最终确定经历了长时间的选择过程,因为山神信仰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生肖动物在选择的过程中受到了山神动物的影响。
山神信仰出现很早,除了最早的山体信仰,还因为原始农业的发展还处在自然的掌控之中时,人们需要祈求超自然神灵降临福祉,农业生产与天气物候密切相关,古代人们认为风雨皆出自于山,所以对山神信仰有加。“十二生肖的产生是由于农牧社会生产与生活的需要。”[1]103民间用十二生肖来纪年计时,山神信仰和十二生肖在农业社会都承担了重要的作用。《山海经》其书,“《海外经》和《大荒经》中那些非我族类形象怪异的殊方异类,并非海外异域实有之族类,实为战国时期的作者基于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异域想象而对一幅古图的误读。”[16]3而“《山经》其书,无疑是一部以实证性的地理实录为主而偶或掺杂神怪内容的地理博物著作,这一点已基本定论。”[13]10既是地理实录,那么其中所记录的当时的山神及其信仰,便也是真实存在过,对后世有所影响也是可以想象的。
《山经》中的山神以半人半兽的形象出现,说明《山经》“人兽同形神是人类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智性思维有所提高后,意识到人的力量,意识到自然象人而不再是人象自然,这时先民们便在动物神祗中加入‘人’的形象,人兽同形便产生了。”[14]38《山海经》中与人类组成山神的动物,包括人类的敬畏对象与食用对象,既包罗万象,内部又有区分,对应了人类社会阶级分化,人们内部鱼龙混杂的状态。这样的山神组成符合农耕时代的社会现状,直接影响了十二生肖的发展。
1. 山神动物的种类《山经》记载了25个山系,441座山,25个山系中,19个山系的山神是群山神,没有神名,每个山系的山神形貌相同。《山经》共49个山神,身体部位出现人身8次,鸟身4次,龙身4次,马身4次,猪身4次,蛇身3次,兽身3次,牛身1次,羊身1次,虎身1次。其中人身山神出现动物元素龙首2次,羊角1次,蛇尾1次,虎尾1次,虎爪1次,豹文1次,手上拿蛇2次。“这些山神没有神名,形象多是动物或人与动物的简单组合体,除山主外,无其他职司或本领。群山山神之间彼此无统属关系,无等级大小之别,无统一首领或至上神,也不受其他天神管辖。”《山经》的山神崇拜产生较早,无论是群山神还是单个山神,都是原始的低级山岳崇拜,受原始农业的影响。
“在这个蒙昧的时代里,人与兽是平等无别的,甚至兽类某些生存的本能为人们所向往和欣羡,人们认为人与兽等多种力量之结合便是超然力量的最理想表现。”[11]190兽也可以成为山神,为什么要与人相结合,这就与后来人的生肖属相是同一个道理,人们相信人与这些动物相结合,会产生出超然的力量,增加人战胜自然的能力。“神话里‘变化’主题所反应的不仅是形体转换的异想奇思,更隐含了人类最原初的生命观,包括生死的概念、困境面对的态度,以及万物与己间之内在联系。”[11]191
相对于有神名的神祗和动物,或某座山具体的山神,《山经》的大多山神没有名字,一个山脉中各个山峰的山神形貌相同,毗邻山脉也有相近之处,如《中次十一经》翼望山至几山有彘身人首神,属于荆山山脉,《中次七经》也有一个豕身人面十六神,此神被崇信的地区,在苦山山脉自休与山至大騩山之间,在地望上,与荆山山脉相毗邻,故其山神形象相近。这一方面说明,山神信仰是在当时普遍的,人们认为一座山本来就有山神,对这些山神没有具体的说明,另一方面,不同山脉、不同地域的山神神貌却不同,说明这时的山神是既普遍又独特的。
相对于多种动物结合,《山经》的山神除十四神与彘身八足蛇尾神,龙首鸟身神与鸟首龙身神,其余皆是人与一种动物的结合,且与人结合成为山神的动物全部属于十二生肖范围内。这普遍而又独特的山神信仰表现了与十二生肖的联系。
2. 承上启下的选择途径动物崇拜是早期自然崇拜的主要内容之一,它以动物为崇拜对象,是早期人类狩猎时期社会意识的反映。“最初人们动物崇拜的对象就是他们的食用对象,诸如野牛、马、山羊、披毛犀、长毛象等食草动物,而且也都是人类能够制服的动物,是他们的食物来源。正因为人类的生存要依赖于这些动物,人们才产生了对它们的崇拜心理。”[15]11巴哈毛力沟岩画中即有大象、山羊、鹿、獐等动物的造型,内蒙古阴山岩画中有大角鹿、鸵鸟等图形。“从原始艺术史的资料来看,旧石器时代的人们动物崇拜的对象多是他们的食用对象。进入早期农业文明时代后,这种食物型的动物崇拜开始发生变化,逐步演化为力量与能力型的动物崇拜,如山中猛兽虎、熊、豹以及空中的飞禽、水中的游鱼、急速爬行的蛇、千年长寿的龟等,他们崇拜的是这些动物超人的能力与力量:一方面希望自己也能从中取到这种能力与力量;另一方面则是祈求求得到这些动物的庇护,这是这一时期动物崇拜的两个主要动因,与早期那种崇拜食用动物的习惯相比,是一个飞跃。所以,在这一时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许多虎豹、龙蛇、鹰鸮类形状的飞禽猛兽图案和器物。”[15]20
对生肖动物的崇拜由来已久,史前时代的原始先民,已会刻画龙、蛇、猪、羊、猴的形象。人们将这些动物形象制品作为饰物,可以说是生肖的濫觞。与《北山经》的山神多为人面蛇身,《东山经》的山神为人身龙首、人面兽身、或人身羊角不同,《中次二经》九山之山神,均为人面鸟身。此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此地族群的鸟信仰有关。汪绂注曰:“大抵南山神多象鸟,西山神象羊牛,北山神象蛇豕,东山神多象龙,中山神则或杂取,以各以其类也。”这是动物崇拜意识残留的表现。这些山神动物中,有的有超人的能力与力量,是人们崇拜的对象,有的是人们的重要食物来源,人们认为这些动物都具有神奇力量,由于先民对生肖动物的崇拜意识一直伴随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对人们的意识形态产生长久的影响,所以在种种动物中,《山海经·山经》选择了这些生肖动物,人们为了获得这些动物的力量,并不局限于动物崇拜,而是直接将它们与人类相组合,成为了拥有神力的山神。
《山海经·山经》对山神动物的选择,表现了先民们的自我意识,其记载的山神形象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山神动物的心理认同,经过了选择与统一;山神是农耕社会农业生产最常求助的神灵之一,人们希望山神保佑风调雨顺、农业丰收,人们对山神形象十分熟悉。人们在用十二生肖以计时农业活动时,不自觉的采用山神动物,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最终确定了生肖的十二个动物。
从山神信仰对后世的影响,《山海经》对山神动物的群体选取,山神动物与生肖动物匹配程度来看,足以说明山神动物有强有弱的选择,奠定了生肖动物选择的基础,直接影响生肖动物最后的确定。
三、《山海经·山经》与十二生肖的人兽组合《山海经》在西汉定型,十二生肖的内涵一直在发展丰富。显然十二生肖受到《山海经》的影响,吸取其内容后,还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发展,如将生肖动物扩展到十二个,与十二天干配合以纪年计时,运用到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才形成如今的样子。在发展过程中,生肖不再是简单的具象投射,而是融入人们的生命中。人们用十二生肖纪年,生肖动物以附属的形式与人相结合,成为人的属相,并衍发出丰富的生肖文化,如婚俗文化“蛇盘兔”、本命年禁忌,成为民俗意义上的十二生肖,这个过程也受到了《山海经》的影响。
相对于新石器时代动物与动物相结合组成的灵物,《山海经》山神的人兽结合,是一个大胆创新之举,重视人的作用,只有与人组合才能成为神灵,否则只是异物,这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而生肖动物与人的灵肉结合,又将人类的地位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台阶,生肖动物只是人的属相,是人类的附庸,这是人类自我意识的彻底觉醒,《山海经》人与动物的组合与生肖动物与人类的灵肉结合内部驱动原因何其相似。
1. 形体组合与灵肉结合阴山乌拉特后旗岩画蛇鸟图中,至少画了八只引颈伫立的蛇鸟;另外,还有人面马鹿和其他动物。这些是动物崇拜的表现,也是动物崇拜变异的开始。新石器时代先民在陶器上描画的动物形象表现了当时人们的意识形态,赵宝沟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约有五千年历史的尊形陶器,上面刻画有猪首蛇身和鸡首蛇身勾连云纹,这个形象被称为最早的“灵物纹样”之一,说明这时的人们已经有了动物相结合即为神异的意识。
“在初民心目中,超然力量一大半是为兽类所持有的,人类根本不是什么万物之灵。”[11]137但《山海经·山经》里的山神,除鸟身龙首神、龙身鸟首神、人身龙首神、十四神和彘身八足蛇尾神没有明确人面,其余皆说明为人面,说明人们在这时已经认识到人类自身的重要性,山神身体可以是其他动物或者某动物的某一部分,但是只能是人面,头部只能是人、龙、鸟。
十二生肖被用来纪岁,每一年都用一个动物来代表,这一年出生的人也就有了自己独特的属相。每个人都记得自己的生肖,但生肖对于人们而言,不能代表自己,它是人们所拥有的文化符号之一,生肖动物虽然也是神灵,但是人们不会因为具体的愿望刻意求助于生肖,更多的是借助于其美好的寓意,希望自己的生活有好的事情发生,如取乳名,或规避某些事情发生,如本命年禁忌。
从新石器时代,动物与动物的形象相结合成为灵物,到原始农业时代《山海经》人兽组合的山神,受人供拜,到农业成熟阶段与人类灵肉结合的十二生肖,伴随人们的日常生活,动物与人的组合方式,经历了从简单的形体组合,到抽象的灵肉结合的变迁。
2. 一脉相承的组合机制动物崇拜时代,动物是拥有神奇力量的神灵,是敬畏的对象,地位远高于人类自身,而生肖崇拜中的动物,是人类的属相,并非主导人类生活的神灵,人类占据主要地位,更注重人类自身的发展。这样的转变必定经历了一个动物崇拜走下神坛、抬高人类自身的过程。
《山海经》中人兽组合的山神,就是这个过程中的产物。“我们从《山海经》里可以发现,初民思考诸神之角度是特别的,全书只是选择性地略提了点诸神异能,但对于诸神形貌之记述却非常认真,甚至可以说资料丰富,描绘详尽;像这般着墨浓淡的区别,记述重心之排列,不啻宣言了初民对于外形之强烈重视;外形在此的意义,显然远胜于神祗之平日表现;换言之,初民以为超自然力量有极大程度是由外形所决定的,异能的存在源自于形体,并赖此而发挥及掌握。”[11]137对外形的重视,也表现了对人类自身的重视。
除了山神之外,《山经》里还有很多动物是人兽合一的,《南山经》人面鱼身的赤鱬,鸱身人手的鴸,人身彘鬣的猾裹,身人面、白首三足的瞿如;《西山经》人面枭身的顒,鹿身人手的犭婴如,鸱身人足的数斯,鸡身人面的凫徯,蜼身人面的人面鸮,人面马身、鸟翼蛇尾的孰湖;《北山经》人首豹身的诸犍;人面雉身的竦斯,人面牛身马足的窫窳、人面犬身的山犭军,人面羊身、人爪虎齿的狍鸮;《东山经》人面彘身的合窳;《中山经》人面豺身、鸟翼蛇行的化蛇,人面虎身的马腹,状如人而二首的骄虫。这些动物与山神的区别,其一、有名字;其二,对其有介绍,如马腹食人;其三,组成元素多于一个。虽然只是异兽,不足以称为神,但部分已有神异的力量,如见化蛇有大水,和山神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是人兽的形体组合。
不仅要和人类组合才能成为神祗,连拥有一点异能都要有人类的参与,这个时代,动物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中次十经》经文说到在堵山和騩山两个地点对冢和帝的不同祭献仪式和用牲,对山神龙身人面神的祭献规格相对较低,更是说明此时宗族崇拜已经较动物崇拜占据上风。这个阶段的神祗,人类占据一半元素,山神必有人面、人首,这是对人类智慧的尊崇。有了将动物与人相结合的突破,十二生肖将与人形体相结合的动物,转化为人类的附庸,成为与人类灵肉结合,就是再向前发展一步的事情。
《山海经》影响十二生肖的形成,《山海经》在西汉时被合编,形成如今的版本,在这之前《山海经·山经》已经在民间流传了几千年,其作为巫卜之书,与甲骨卜辞中的生肖动物符号不无联系,《山海经·山经》在生肖的生发时代扮演了启蒙者的作用。《山海经》山神信仰对动物的选择与十二生肖对动物的选择一脉相承,十二生肖在两汉才逐步固定,《山海经·山经》伴随着生肖动物确定的过程,为其选择奠定基础,山神信仰伴随人们的农业生产,《山经》山神对神异动物的选择是影响选择生肖动物的重要因素。
《山海经》伴随十二生肖的发展,十二生肖从单纯的纪时动物,到成为生肖神,成为人的属相的发展过程中,借鉴了《山经》中山神的组合方式,即动物与人类相结合。《山海经·山经》里的山神形象是人兽结合,生肖属相也是人兽结合,不过一个是形体的组合,一个是灵肉的结合,《山经》人与动物的组合方式,到生肖动物与人类的组合方式,是形体结合到灵肉结合的质的飞跃,是对《山经》简单形体组合的改造与升华,是人类自我意识的彻底觉醒。
无论是形成年代,还是动物的选择、人兽结合的方式,十二生肖的文化受到《山海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山海经》对十二生肖动物产生与发展的影响与伴生,值得重视和思考,可能可以为十二生肖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对先民的意识与选择研究做出新的思考,促进十二生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
参考文献[1]张皓.十二生肖[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2]刘滴川.山海经外传[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
[3]叶舒宪.《山海经》神话政治地理观[J].民族艺术,1999(3).
[4]袁珂.《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试探[J].社会科学研究,1985(6).
[5]耿法禹.破解十二生肖之谜[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2).
[6]沈壮志.图说十二生肖·兔[M].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2007.
[7]尹钊,刁海军,张继超.十二地支和十二生肖的演变研究[J].东方收藏,2014(4).
[8]李学勤.失落的文明[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9]吴裕平.生肖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0](战国)无名氏著,王海燕译注.山海经:彩图版[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11] 邱宜文.《山海经》的神话思维[M].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
[12]张岩.《山海经》与古代社会[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
[13]刘宗迪.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4]毛文志.《山海经》的神祗形象[J].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4).
[15]马新,贾艳红,李浩.中国古代民间信仰:远古-隋唐五代[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6]刘捷.驯服怪异:山海经接受史研究[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