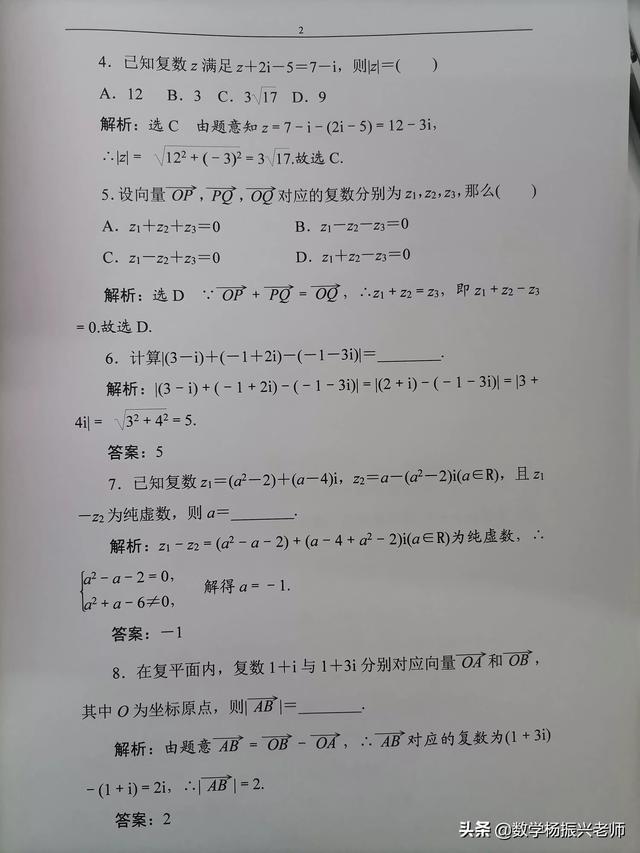2011年,一场由突尼斯爆发的反政府示威席卷埃及,冲垮了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政权,当代法老就此被“阿拉伯之春”的烈火焚身。综观穆巴拉克的人生轨迹,其先是发迹军旅,在44岁那年成了阿拉伯世界最年轻的空军司令,又经纬国政,于53岁正式问鼎埃及总统。在30年的统治生涯内,穆巴拉克虽有建树,却也一步步为自己的倒台埋下祸根,他曾是全国98%选票的心之所向,却也在万民唾弃中仓皇辞职,并于今年2月24日,正式从人生舞台谢幕。

穆巴拉克,图片来源:AP
于穆巴拉克而言,这场骚乱让自己由中东强人跌为历史罪人,最后再沦为无权老人;对埃及来说,“阿拉伯之春”是历史的浓重一笔,到头来却彷佛什么都没改变-军人执政依旧,经济常处低迷。改变的风沙在不变的金字塔上啸掠,碎裂的结构在失序的尼罗河中碰撞,这样的埃及,笔者曾经见过;对寓居埃及五年的何伟而言,想必更是刻骨铭心。
用看过中国的双眼凝视埃及
自打27岁(1996年)来到中国,何伟(Peter Hessler,彼得·海斯勒)似乎就不曾离开过。从四川涪陵的英文老师,到《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纽约客》驻北京记者,再成为四川大学的非虚构写作老师,何伟的中国路走了20多年。在这段期间,他先后出版被称为“中国三部曲”的《江城》、《甲骨文》与《寻路中国》,书中既有身处异域的抽离与冷眼,也有安居新乡的融入与情热,更侧写了当代中国的复杂与深邃。

何伟于2019年出版《埃及的革命考古学》
然而,在他与中国的漫长交流间,还有段出走埃及的小插曲。2011年,何伟以《纽约客》特派记者身份迁居开罗,据其所言,事前感觉自己要前往的是“历史悠久,语言丰富有趣,与中国很像”的地方。然而时值“阿拉伯之春”动乱,他与妻女的住所经常缺水断电,自己也因抗议活动折断脚骨,电脑与相机更差点失窃。最后何伟看着周遭旁人纷纷进监狱,终于在2016年离开了埃及。但这五年种种并非徒劳,何伟选择在2019年出版自己的埃及观察《埃及的革命考古学》(The Buried,台譯),既书写考古现场,也记录革命以来的政治运动。而过往的中国经验,也成了他丈量埃及的隐形圭臬。
例如谈及埃及的社会秩序时,何伟便不只一次将两国相较。其认为,与中国相比,埃及社会相对缺乏“系统”(نظام,nizam)。首先,埃及人普遍对数字不太在行,小贩们时常找错钱,且就算是小范围的数字计算,都还得用计算器;但由另一个角度观之,何伟认为这不失为一种放松,毕竟“中国对钱可以执着到令人厌烦的地步”,且或许正因如此,何伟发现埃及人的语言学习能力非常强大。虽说这其中也有殖民、埃及人爱交际等因素,但曾在中国执教的何伟还是感叹:“中国学生常用学数学的方式来学语言,也就是凭记忆力死背,加上反复练习”,但在埃及有许多平民根本没受过任何正式训练,却能在面对观光客时说上一口好英语。
此外,许多埃及人的生活日常毫无规律与秩序可言。何伟举例,赖床、不按时吃饭、社交到半夜可谓埃及常态,在阿拉伯语的埃及方言中,还有无数表达“迟到”的厘语短句;相比之下,中国的时间观非常严密,约好时间后迟到是例外,不比在埃及迟到是常态。
而这种“失序”,也体现在埃及自编的阿文课本中。何伟回忆,他当年学中文时,用的是《用中文读中国》,是中国自编教材,光是开头几课,就出现许多官方机构、政府组织的名字:“妇女协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总理”、“社会主义”等;但埃及自编的阿语教材,除了穆巴拉克总统外,就很少出现其他政府相关名词,甚至还暗藏对国家体系的不信任。例如有段对话如下:
父亲:“你的大学朋友都去哪了?”
马哈茂德:“去大公司工作了。”
父亲:“那你怎么不去?”
马哈茂德:“这要靠关系。”
这里的关系用的是“wasta(واسِطة)”这个字,在阿语中意指“走后门”或“裙带关系”。在读完这段带着淡淡哀伤感的对话后,何伟联想到了中文里的“关系”,在他看来,中国的“关系” 时而腐败时而弹性,而正因中国社会体系已充分发展,故“中国式的关系”可以培养、学习、操弄,只要有方法与常识,人人都可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关系”;但在埃及社会中,所谓“关系”却更像阶级,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人们当然还是可以经营自己的人际关系,但这些交情很难让自己跻身另一个社会高度。

图片来源:Mahmud Hams/AFP/Getty Images
除了比较埃及与中国社会外,何伟还特别用了一章的篇幅,来书写在上埃及闯出一片天的中国商。就意识形态版图来看,上埃及可谓全国最保守的地区,此处的穆斯林妇女不仅多包头巾,也常有黑衣蒙面装束,但在何伟打入当地温州商人圈后,却发现保守之下其实别有洞天。
一般而言,埃及妇女通常会准备三种服装,保守的在外穿,轻便的家中穿,性感的则有特殊作用。而或许正因上埃及妇女在外穿着普遍保守,故而物极必反,对的消费需求也相对巨大,受何伟采访的一位中国商人便表示,她的店每两个月就要从中国进一批新货。而依据埃及婚俗,每逢新人要共结连理,新郎往往负责置办房产和家具,新娘则出资采购小家电、厨具和衣物,故何伟也曾多次目睹所谓婚前性感内衣采购团:新娘由未婚夫、母亲、兄弟陪同,一伙人共同挑选胸罩、丝袜、丁字裤、各种睡衣睡裤。看完这幕,他不禁喟叹:在亚洲,就算是最有自信的妇女,也会因购买内衣时有父母、未婚夫与兄弟在场而感到尴尬,没想到这在埃及却如此稀松平常。
而在采购当下,中国店主常以特殊的埃及阿拉伯语招呼顾客,何伟称其为“内衣店方言”。这种方言起于温州商人圈,以何伟接触过的某些受访者为例,这些中国人刚到埃及时不仅一句阿语都不会说,甚至连英语也不大通晓,却能靠着日积月累模仿顾客,耳濡目染习得语言;然而由于店还是女顾客为多,故这些商人讲话都有一特征,那便是动词都以阴性结尾,故就算是男店主,也多以女性口吻招呼客人,颇有安能辨我是雄雌的错位感。
而这种错位,也像极了何伟眼中的埃及与中国。这两大文明古国在某些神髓上似曾相似,却又极其不同。而正如中国商人透过女顾客之口学习埃及阿拉伯语,何伟也透过自己的中国经验梳理埃及,进而反扣“阿拉伯之春”。
解构革命的时间与系统
在《埃及的革命考古学》中,“时间”是条再明晰不过的主线。而早在此前,何伟便曾于书写中国的《甲骨文》中探讨时间概念。身为一个现代人,我们已习惯用线性的方式理解时间,隐然接受了历史将不断进步的假设,进而强调逻辑、理性与个人主义的重要。但何伟认为,正是这种习以为常的思维,让我们淡忘了时间的循环性,容易视所在当下为“历史的关键时刻”,结果便在千年一隅中过度流连,错估“阿拉伯之春”的意义。
何伟在埃及时常与考古学家接触,因而知晓5000年前的古埃及时间观。在古埃及人的思维中,时间有两种:“Djet”与“Neheh”,Djet有静止之意,或可译为永恒; Neheh则是周期,喻指重复、更新的意像,例如太阳运转、季节流逝与尼罗河的周期性泛滥等。
而之所以存在双调的时间观,何伟认为这与埃及的两极地貌有关。对尼罗河谷地的居民来说,洪水年年降临,水患所经之处虽是一片狼藉,却也暗喻肥沃的生机与重生;但对沙漠中人而言,除了翰海黄沙与各色沙丘外,周遭环境就是一片死寂,没什么变化,因此他们的国度适用另一种时间。

埃及太阳神,图片来源:Images/Alamy
而藉此双调的时间概念,何伟进一步解构人们赋予“阿拉伯之春”的线性感与进步光环。在他看来,埃及近代史虽在无数政变、战争等“Neheh”中前进,但其本质是在中世纪与现代秩序间来回摆荡,埃及没有因萨达特(Anwar Sadat)遇刺换上穆巴拉克就更好,也没有因一场“阿拉伯之春”就成功民主化,这个国家一直走着自己的路线,其本质还是停留在某种“Djet”中。“阿拉伯之春”不过是众多Neheh之一,就像时间一到自然发生的尼罗河洪水。其颠覆性之脆弱,主因还是在于书中第二主线:“系统”。
“系统”是何伟在书中用以反思“阿拉伯之春”的另一主线。据何伟所述,他之所以会关注系统这个概念,也与自己的中国经验有关。他于90年代踏入中国,起初还不是个独立的作家,而是在地方单位工作。所谓单位,里面有领导、结构与规定,又挂靠国家,就像一部部小机器,可以自行运作,同时支持大型工厂产出。而当年许多中国人都在各种单位里谋生,故而整个国家可谓是各种系统的集合体。
然而当何伟迁居开罗后,便发现埃及社会有一根本问题:缺乏统一的系统。除了前段举出的中埃社会对比外,何伟还将此现象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例如在首都开罗,约有65%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违建中,但政府对此不仅睁只眼闭只眼,甚至根本不愿、也不能解决这件事;当人民被警察取缔,虽偶尔能以贿赂解决,却也有被活活打死的风险;庞大的官僚虽享受着相对高薪,却似乎什么计划都没在执行;国外援助源源不绝涌进,但政府彷佛都没将钱用在刀口上。
在埃及,政府看似专制,却只能掌控部分国家机器,无法在所有角落贯彻法度;但人民也算神通广大,总有一套本领能让自己在失序的国家中存活。笔者曾三度游学埃及,对此也是颇有感触。
以交通为例,出门搭公交车的路上,首先要过马路,这时看的必须是车而非交通号志;上公交车前也永远要问司机是否有停自己要去的站,因为在当地过站不停是常态;如果过站便是鼻子一摸乖乖走路,或是改搭名叫“أوتوبوس”(autobus)的小包车,但同样得每台都问价钱与停靠站,因为没有统一标准;如果搭出租车还得注意,司机常开到一半自行加价,而乘客除了假装凶狠外,往往别无选择。以上种种不过是生活失序的一隅,但适应之后便觉稀松平常,这时又会生出种“自己也算埃及人”的欣慰。在埃及,秩序与混乱间既有张力,又维持着某种平衡。对笔者来说,那是段既挫折又充满成就感的有趣岁月。
然而,何伟也好,笔者也罢,毕竟都是过客,可以在心灵上自由进出所谓“埃及人”的身份;但当地人却是终其一生要过这种日子,国家治理无能是真,腐败也是现实,人民久了自然要上街头,“阿拉伯之春”的火苗因而窜出;但这种治理障碍又已深入骨髓,区区革命不过让权力洗牌,政府上台后多仍萧规曹随,官僚颟顸腐败依旧,于是整个国家的治理问题继续存在。所谓示威与革命最后就成了人民与政府间的古巴飞弹危机,双方硬撑,最后看谁先松手,例如埃及在2019年又爆发了反政府示威,但在政府逮捕4000人后,人潮终究散去。
既考古埃及革命,又回望中国
在埃及这5年,何伟以时间为经,系统为纬,为我们留下一本精彩的埃及革命考古报告。然而,这何尝不是他对中国的隐晦回望?他曾询问埃及当地中国商人对“阿拉伯之春”的看法,对方回应如下:
“要是不把穆巴拉克赶下台,情况还会比现在好些。”
书中虽未针对此句直接给出评语或结论,但笔者曾读过他于《纽约客》上谈及此事的长文报导,何伟是这么认为的:
“我常听到中国企业主们发出这样的议论,在西方人看来,他们显得见利忘义,因为按照西方的设想,一切局外人都该乐于看到埃及改革。但也许中国人的看法更加清醒,因为他们看到了埃及实际的样子,而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样子,……,按照中国人的看法,埃及的根本问题不是政治,不是宗教,也不是军事,而是家庭。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在埃及,‘阿拉伯之春’丝毫没能改变他们之间的关系。家庭关系不变革,谈论革命就毫无意义。”
对何伟来说,他的埃及生活离不了中国经验;而他的某些中国观察,也往往要在出入异文化后,才会不经意迸出。如今穆巴拉克已逝,何伟也已回到中国,但这份角度殊异的革命考古报告,将会成为见证那段激情岁月的另一种脚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