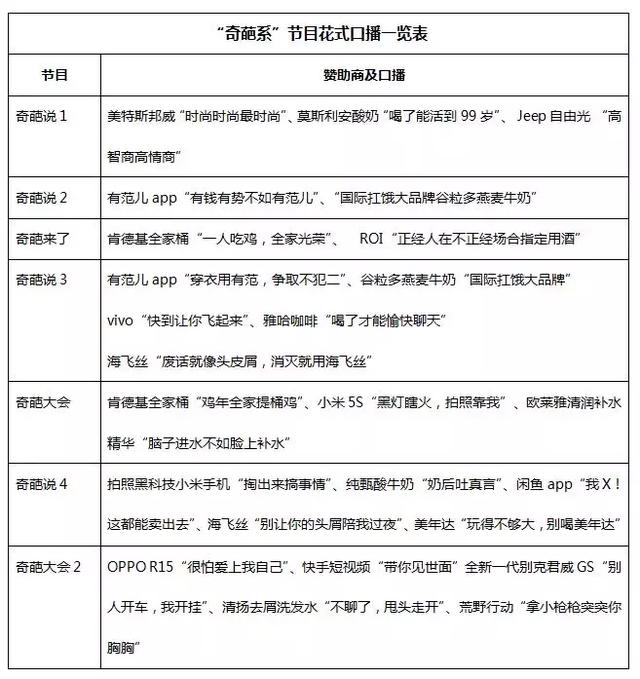▲《二十二》导演:郭柯
罗帏对卷秋风入,新插瓶花娇欲泣。
那知更有断肠人,血污罗裳归不得。
夜深宛转闻娇啼,清晓遗尸弃深谷。
仰天终日语喃喃,皮骨虽存神已死。
伶仃弱女何所依,瑟缩泥中血满衣。
被俘自分军前死,不信将军赐就医。
殷勤看护更相慰,折得花枝伴憔悴。
▲《三十二》 导演:郭柯
导演郭柯曾在2014年制作了一部关于日本性奴隶受害者韦绍兰的影片——《三十二》。摄影机游走在桂林青翠的山水和破旧昏暗的老宅间,勾勒出老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全景镜头下展现了她当下的生活,这个佝偻微显孱弱的身影穿过城镇熙攘的人群去领政府补贴,而她的常态是独自忙碌在灶台前、小溪边、田垄上,从此便与人群再无交集。
特写镜头下,关于过去她掩面、哽咽、泪流、叹息、倾诉、不语。其中韦绍兰沧桑的脸是唯一的着光对象,后景深邃的黑暗像无边的恐惧紧紧的包围着她。蒙太奇碰撞出她和儿子关于未来希冀的不同侧重,想要一声道歉,想要一笔赔偿。影片结尾字幕颜色在数字从200000转到32这一过程中逐渐由白色变成了红色——这是现存受害者的人数。
《二十二》是导演对处女作题材的某种意义上的继承,更是中国第一部获得公映许可的关于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的影片。然而这个第一却让人有一丝羞愧。从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主流媒体关于这些受害者的呈现,常年囿于民族主义的框架之下,她们的存在被集体化,或是作为战争压迫的指示器,或是作为国家之争的符码,在民族主义需要时开启,不需要时封存。而郭柯在同韦绍兰相处的过程中对她作为一个“个体”的觉知,令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创作。这也促使他决定放松对电影技巧的自觉,用一部影片更加冷静地呈现老人们的真实生活。

▲韦绍兰老人
“再见到韦绍兰,她依旧是笑呵呵的,我也不采访了,就把机器架在那儿,在老人和受害者两个身份中,老人是排在第一位的,我不是去拍受害者,而是去拍老人”。这一次镜头不再对痛苦的回忆步步紧逼,也不需要配乐的主观介入,这双机械的眼睛似乎一下子有了人性的灵魂。
影片中有大量的镜头使用门框或是窗框做前景结构画内空间,摄影机化身为有血有肉的形象,他站在门外,站在窗外,远远地深情凝视着老人们,进退维谷。仿佛也在担心自己跨进那道门槛听到她们说起从前,如芒刺在背。而小景别对老人侧脸、背影的拍摄仿佛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呵护。

▲《二十二》工作照
郭柯的镜头中出现了22位幸存老人,2位民间调查员,2位邻国志愿者,1位国内媒体工作者。我大体把他们分成五类,在每一个人物的呈现上,导演似乎都想要说点什么,却总是保持克制。
幸存的22位老人们。镜头主要聚焦在其中李美金、林爱兰、李爱连、毛银梅四位老人的身上,通过具有内在连接力的剪辑串联起其他老人的现状。尽管他们都在各自的生活里找到了一时的平衡,而在现实社会的大语境下昔日相同的伤痛在今天氤氲出相似的困境。
“我不想讲曾经人们是如何死去,我只想聊聊后来的人们是怎么活下来的”,这是郭柯的创作初衷。所以当老人们的回忆在苦难的闸口前止步时,他没有再去叩门。只有李美金老人,没有回避,主动说起了那段过去。摄影机的镜头长久的停留在黑暗中,仅存的一处光源折射出空气中起起伏伏的微粒。我们只能听到老人的声音,看不到老人的表情。诸如此类的空镜运用,其实是导演对观众的慈悲。无论她是否蹙着眉头,是否擎着满眼泪水,某种程度上我们也不忍心看。当老人话音落下后,一道强光刺穿了整个银幕,这一暗一明的强烈对比,像是从历史的深处射来一支箭刺在观众心上。
她们当时是怎样活下来的
要么逃走,如李美金。一路奔跑回到家,等待她的是母亲的怀抱,家人温暖的呵护。同样是逃跑,韦绍兰没那么幸运,这个家园等待她的是丈夫的鄙弃、女儿的夭折、产下日本人的后代,忍受贫困与孤独。要么被重金赎回,要么在濒死的边缘被敌人“丢弃”被家人“捡起”。

▲郭柯和林爱兰老人
林爱兰庆幸自己还有逃的机会还有跑的力气,作为战俘身份被带进慰安所,等待她的是无尽的蹂躏后以活靶子的身份走向死亡。尽管腿坏了,每一步都靠挪,但言语铿锵有力。她自豪自己曾是一名战士,她珍视国家发给她的勋章,这是对她生命意义的肯定。老人在说到母亲被日军杀害时掉下了眼泪,原本眼神里坚忍而倔强的光芒,一下子就消失殆尽了。在影片中呈现过数次老人们情绪的波动,关乎的不是仇恨而是呵护。
父权社会下的传统贞洁观,这些“失贞”的女子要么背井离乡隐姓埋名嫁为人妇;要么重新回归家庭获得丈夫的体谅;要么与早已结下婚约的男子组建家庭。夫妇之间彼此达成一种和解之后,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情感的温暖给她们受伤的心灵强大的慰藉。而林爱兰终身未婚,选择自梳的勇气背后是否藏着一种担心,即对往事成为一种软肋被对方拿捏的担忧。而在韦绍兰身上没有婚姻带来的温情,反倒是同性之间的关怀让她放弃了自杀。

▲毛银梅老人
虽然心灵的创伤可以隐藏的不露痕迹,可以用温情的累积将记忆封印。老人们身体的病痛却如影随形与日俱增。很多受害者在当时就失去了生育能力,通过收养子女获得了母性身份的完满。毛银梅原名朴车顺,她爱毛主席,改了姓;丈夫爱梅也护她,取花作名。现在和养女一家七口住在一起。她的房间里挂着朝鲜半岛的地图,那是她的家乡。
“很多事忘记了,记不得了,很多事有时候好像记得,有时候又记不得了”,毛银梅用手摸了摸头这样说道。那么记忆里还剩下些什么呢?摄影机和老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她背对着我们坐在床上。然后她突然跳下床欠身用日语细声细语地说出“欢迎光临”,“请坐”。窗户和门透进来的大面积日光让画面镀上一层幻梦的色彩,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个少女在“地狱”委屈求生的意志。摄影机用特写去倾听那饱经沧桑的歌声,一首《阿里郎》,一首《桔梗谣》,这是影片中唯一的音乐。朴车顺一生再没返回故土,毛银梅在这里安了家。
她们现在是怎么生活的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像毛银梅一样享天伦,住砖房。长久以来由于缺乏国家政策支持,地方政府也态度含糊,即使出于人道主义关怀给与一些保障帮助,资金也少的可怜,难以解决实质问题。而来自社会的慈善组织的援助几乎是缺席状态。摄影机多次通过对空间、物件的“打量”,细述老人们的生活起居:窑洞、土屋、柴火、蛛网、杂物,所有的陈设都是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存,小瓦数的灯泡驱不走房间内所有的阴暗。林爱兰从棚屋住进了村里开设的养老院,除了她有伤残退伍军人的政府补贴待遇,其他人来自政府的津贴项目只有高龄补助和五保户补贴,对于那些基本丧失了劳动力、疾病缠身的老人们来说,显得有些苍白。

▲李爱连老人
李爱连也有一处院子,镜头记录下的她宽厚而安详,这一点连猫咪都察觉得到。公开身份后,二十多年过去了,对日诉讼都没有带回捷报。
几十年后,要亲手在全球视野下撕开结痂的伤口,这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像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博,她们压上了整个余生,也打碎了好不容易才获得的平静。关于索赔,是一道叠加在旧伤口上的新疤痕,影片中做了“无声”的回应。
镜头远远地眺望着田地深处的一个村落。字幕向我们介绍了这位老人——刘风孩,唯一在镜头中缺席的受害者。这是一位曾经公开过身份,也接受过采访的老人。由于担心给子孙带来影响,放弃了表达。我们尊重刘风孩的选择,但是抛出来的理由却让我们轻松不起来。我推测她的子女可能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她的孙辈可能一边刷微一边戏谑地说过“大清早亡了”,然而男权文化体系中关于“贞洁”的片面孤立的判断,关于“女性”从属地位的执着,在一些人的心中根深蒂固,并理直气壮的随着家族的血脉得到传承。囚禁在这种语境中,又有多少受害者把这段委屈带进了坟墓。

片首片尾两位老人的葬礼把整个影片的时空缝合起来,死亡的气息穿插其中,像是倒计时的钟声,从22到8,滴答滴答。太行山上新立的坟茔转个年就被青草覆盖了。苏智良教授在采访中说,“他们都85岁以上了,留下的时光不多了”。
她们以后要怎么活
在导演的镜头里出现了三个不同国别的年轻人。从三种层面上作了设想。

▲米田麻衣
来自日本的志愿者。作为正视历史的代表,她的存在是一种纵向的延伸。米田麻衣第一次出现在视野中时,摄影机在房门口静静的站着,画框内是她得知老人故去后痛哭的背影。她曾在东京见过黄有良老人,老人说自己到日本来打官司是为了不让当代的女性再经历自己的遭遇,这深深地震动了米田麻衣。来到了中国,她也怀疑过自己这种身份的“闯入”,会不会给老人们造成一种困扰。然而在老人们心中对过去、现在、未来保持了理智的丈量。日本民众曾自发抗议判决的不公,然而并没有奏效。对日诉讼律师团长大森典子陪伴着老人们战斗了二十年了,还没有放弃。历史教师吉池俊子不畏右翼分子威胁,仍在致力于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历史的真相,这是希望的种子。
来自韩国的青年。作为有相同伤痛记忆的群体,他的存在是一种横向的对比。在本国对受害者经历的了解,让他们的关爱的视野更加宽泛。摄影师用镜头把老人珍藏在时间的永恒范畴里。志愿者在物质上给予了毛银梅老人很大的帮助,让她们的晚年尽量多一点温暖是我们必须去做的。1991年,韩国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金学顺,第一个开始公开身份进行控诉。1992年,韩国受害者及社会团体开始发起“周三集会”,二十五年的坚持她们从未放弃,社会的偏见越来越少,地方政府为她们上了医疗保险,并每月提供70万韩元的补助。受害者的诉求也提升到国家的层面上,积极敦促。
而中国幸存者不论是作为群体,还是作为个体,被关注的太少了,即使被关注也显得少了那么点人情味。李爱连老人想到记者,禁不住拍起炕来。人是一批一批的来,“可是每次问那些问题,都当着我的儿媳孙子的面,我怎么说得出口”。
媒体的导向作用非常重要,文章总是在压榨完悲伤之后戛然而止。她们是活生生的人,不是无偿提供记忆下载的资料库。影片中也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年轻的女记者,她背着身拿着纸笔,问罗善学是否有女子愿意嫁给他了,承诺给他找老婆的人兑现了吗。说话的语气很轻快,而画面中的韦绍兰被前景的记者、儿子挤压在中间。后景的她依然笑笑的,我想她心里有点涩涩的。在《三十二》中,老人感叹道活着是受罪,活着是孤独。是母性的本能让她不得不坚持下去,儿子的独孤不是轻快的笑谈,而是人母心上最大的挂牵。她在等,等得到道歉的那一天,那可能就有人愿意嫁给儿子了吧。

▲张双兵在首映式上讲话
影片的尾声张双兵垂手走过镜头前,“假如以前知道事情会是这个样子,那我不如不去惊动她们”,这一句话有点无奈、有点迷茫。
再回想影片开头葬礼上张双兵第一次出现在镜头前,他拿着悼文,脸上的表情很复杂,不是悲伤,更像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愧疚。作为最早开始民间工作的调查员,三十年来,他心里装着129个悲痛的故事,也是129份未兑现的承诺。道歉什么时候会来,至今没有启明星出现。海南民间调查员陈厚志在镜头前接了一个电话,镜头等着他接完电话,继续陈述。这就是生活,他们要为老人奔走,他们也要养家糊口。这份不仅无利可图,还备受非议的工作,他们不忍心丢下。他们更担忧的是,谁会接过他们这份沉甸甸的责任继续坚持。
1972年《中日联合宣言》中国政府放弃了国家战争赔偿,收入微薄的张双兵被学校被组织扣上了破坏国际关系的帽子。他看着邻居老人把报纸撕碎,恨恨地说,“抢了那么多东西,欺负了那么多人,就这么算了?”虽然中国政府现在一改当初对民间索赔“不鼓励、不介入、不反对”的态度,但除却外交方面支持之外,其他方面未有全面性的帮助,特别是在政治方面。民间力量依旧在孤军奋战。2016年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开馆,中韩和平少女像揭幕。

▲中韩和平少女像
米田麻衣问自己,到底可以为老人们做些什么,可能陪伴就是最合适的答案。导演用镜头带领我们完成了一次陪伴。影片中出现了大量的空镜头,一是,对空间环境的交代。带我们走进老人们的家园,搬个凳子坐下;二是,对时间的具象化表达。陪着她们看日升日落、云卷云舒、风吹雨打、白雪皑皑,挨过时光,一起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正片结束之后,没有人起身提前离场,大家看完了所有字幕,直到银幕上新一轮消防警示片出现。那些三三两两结伴而来的人,都没有交流只有脚步声向着门口而去。
后记
文中补充了很多关于日本性奴隶制度受害者的资料,影片中并未呈现。导演郭柯的镜头保持着克制,但笔者认为值得我们主动去思考更多。
参考资料:
1.宋少鹏 《媒体中的“慰安妇”话语——符号化的“慰安妇”和“慰安妇”叙事中的记忆/忘却机制》 开放时代 2015年5月
2.王学振 《抗战文学众的“慰安妇”题材》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12年12月 第4期
3.陈尚文 《“我想在活着时,听到日本的道歉”》 人民日报 2017年6月2日 第23版
4.赵青青《日军“慰安妇”幸存者生存状况调查与PTSD初步探究——以海南澄迈、临高两县受害者为中心》
5.黎若谷《中国“慰安妇”索赔问题研究》

文:点心妈
编辑:福尔魔歌、蒙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