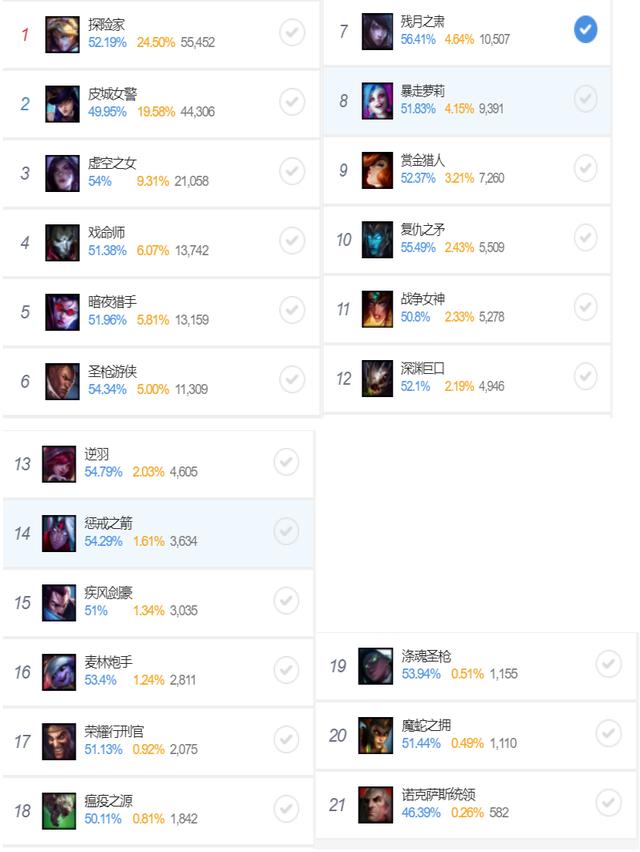深:

——《美国传统大辞典》第三版(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戏:在某个限度的时间和空间内,依序且按规则进行的活动,非属必要,亦不合功利。游戏的情绪是欣喜热烈的,并且配合神圣或欢乐的场合。随行动而来的是意气飞扬和紧张刺激。
——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荷兰历史学者) 《游戏的人》(Homo Ludens)
人人都明白什么叫游戏。徜徉公园之际,有小女孩邀我掷豆袋为戏,如果我迟缓笨拙,她可能就会觉得无趣——就像玩“捡回猎物”游戏的狗因无聊而另觅玩伴去了。但究竟为什么游戏?人类传奇故事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游戏。我们经由游戏演化,我们的文化借着游戏繁荣,例如,求偶的过程就包括游戏的高度的戏剧性、仪式性和礼节性;创意和点子就是心灵游戏的回响;语言原是文字的游戏,最后却能代表具体的事物,表达抽象的观念。
动物的游戏有许多功能,可能是成年生活的彩排,如幼小的哺乳动物玩追逐的游戏、战争的游戏、社交的游戏和运动技能游戏。幼小的海豹在碧波间打斗,小老虎飞扑玩伴你撕我咬,全是为了磨炼将来能救命的技巧。游戏远比人类的历史还久远,它和我们太熟稔,和我们的童年密不可分,因此我们视之为当然。但不妨想想:蚂蚁并不游戏,因为无此需要。它们天生就知道要做某些事情,自动自发,由出生开始。反复磨炼和发挥聪明才智,对它们而言毫无必要。越需要学习方能生存的动物,就越需要游戏;它拥有的闲暇越多,就可以玩得越久。某些高等生物——如海豚和黑猩猩——之所以和我们玩,是因为它们有幸生为拥有余暇的智慧生物,抑或是因为它们和小老虎一样活泼好玩?就我们所知,我们所称的“智慧”可能是灵长目独有的特色,或许未必是生物发展的顶峰,只是知的一种形式,是我们恰巧能掌握并且喜欢的形式。各种动物都会游戏,因为这有助于解决问题,让生物测试自己的极限,想出因应的策略。在千变万化的危险世界里,唯有灵巧活泼者方能生存,而闲散懒惰者只有遭淘汰的份儿。或许我们以为游戏是无关紧要的活动,其实它是演化的基础。没有游戏,人类和其他许多动物就会衰亡毁灭。
动物游戏的部分原因,是要保持活泼,以适应环境。灵长目动物的探索游戏让它们得以收集关于环境和食物来源的信息,马的奔逃游戏让它们随时为逃跑做好准备。社交游戏能够建立高下尊卑的等级,帮助求偶,必要时也促成合作。中枢神经系统需要定量的刺激,而游戏可能使动物的官能保持清明警醒。对精力充沛的生物而言,单调沉闷是难以忍受的。幼小的动物不知道何者为轻,孰者为重,它们缺少新奇的经验,官能急待新的刺激,又高度敏感,因此游戏影响深远。
甚至连乌鸦也会游戏。我骑车时,经常看见翼上戴着塑料标签的乌鸦,这是附近鸟类学实验室的学者为它们贴的。我不禁疑惑,这些色彩缤纷的标签是否使它们在乌鸦社群中拥有特别地位?至少这使得学者们容易研究乌鸦。学者们已经发现它们其实非常合群,而且全心奉献给家庭。五岁大的幼鸟,在繁殖期依然会在父母的巢附近帮忙,而当它们自己求偶时,也会选在靠近父母家处,和伴侣做一生一世的夫妻。它们会协助养育甥侄,也常成群出外觅食,还会玩各种各样的游戏。两只幼鸦会用树枝玩拉扯游戏,或者成群结队戏弄落单的猫。乌鸦会像猴子一样在树枝攀上爬下,或是戏耍细树枝——再向下疾飞衔住它。曾有学者见到乌鸦发明滚木游戏,在塑料杯上保持身体的平衡,一路滚下小坡,它的手足见到这样滑稽的把戏,也如法炮制。我的邻居有一天下午也惊见乌鸦站在她家天窗的架缘上,朝玻璃抛小石头,看石头四散为乐。
其他动物同样也有玩心。贝瑞(Wendell Berry)就曾如此描述鸟儿游戏的情况:
一个夏夜,我正端坐着,却见一只大苍鹭由山顶直降山谷,它以一种不慌不忙、从容的速度往下飞,雍容华贵一如平常,就像显要人物下楼一般...
对人类而言,游戏是脱离日常生活的避难所,是心灵的圣堂,让人免于人生的种种习惯、规律和裁判。游戏总在神圣的场地发生——某种形式的游乐场,通常都有清楚的界限,以便和现实的场所有所区别。这个场地或许是间教室,是座体育馆,是个舞台、法庭、珊瑚礁、车库里的长凳、教堂或庙宇或是一块众人可以在新月之下携手的场地。游戏有时间的限制,可能是一段热切却稍纵即逝的时间,如棒球赛可长可短的一局,或是一节心理治疗的固定时间。有时这时间的限制是预先安排好的,有时则唯有回顾才能辨识出来。游戏让你纵情丰富的世界,可以施诡计,可以试策略,可以任你改头换面。在自我封闭的游戏世界,没有渴欲,游戏的目的就是游戏本身,而它也以非常令人满意的方式达成。游戏有它自己的礼仪规范和绝对的规则。赫伊津哈在其研究游戏与文化的经典之作《游戏的人》中写道,游戏“创造了秩序,它就是秩序本身。在不完美的世界和一片混沌的人生中,它带来了暂时而有限度的完美。只要有一丁点儿的偏离,就会破坏游戏”。这是所有游戏形式的基本规则,不过游戏亦各有其独特的心理。
最重要的是,游戏需要自由。我们是出于自由意志,自行选择参加游戏的。游戏的规则或许是强制执行,但游戏本身却和人生其他的戏码不同,它发生在日常生活之外,必须自由。就算是出于本能而游戏的动物,它们也是因为能由此得到乐趣,乘兴之所至自发或获其他动物之邀加入游戏。只是仅仅自由未必能确保会有欢愉的结果;人虽自行选择工作,但并非人人都有幸视工作如游戏。游戏者喜欢揣想虚拟世界、更美好的结果、弥补现实不足的方法,或是自我的其他面貌。假装是游戏的核心,也是工作的核心。让我们假想自己可以把火箭发射到月球上。
许多形式的游戏都涉及以自己或他人为对手的竞争,借此来测验自己的技巧、才智或勇气。我们甚至可以说,所有的游戏都是某种形式的竞赛,对手或许是一座山、一台会下棋的计算机,或是恶魔的化身。游戏即冒险,冒险即游戏。其实“争斗”(fight)这个词,就是源自“游戏”(play)这个词。中世纪骑士的马上比赛是恪守严格规则的战斗仪式,角力、拳击和击剑赛亦然。暴力的仪式——在一个神圣的场地,穿着特别的服装,遵守时间的限制,依循规则,举行典礼,动作紧张刺激,而结果未知——是游戏的元素。
但若我们再朝更深处溯源,就会发现游戏的原义其实截然不同,是更急切而更抽象的活动。在印欧语系,“plegan”意思是冒险、尝试、孤注一掷。誓约(pledge)是游戏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就如危险(peril、plight是同根词)一样。游戏原始的目的,是冒个人生命危险向某人或某物立誓约。究竟某人是谁,或某物是什么呢?答案有各种可能,可能是某位亲人,是部族领袖、神明,或是拥有如荣誉、勇气等道德特性的人物。“plegan”基本上与道德或宗教价值密不可分,也包含了紧紧地束缚或深深地投入这样的想法。后来“plegan”就和进行神圣的行为或主持正义相关,而且经常出现在典礼之中。稍后我会再谈这些典礼的重要性。
不过并非所有和道德相关的游戏都需要冒险或赌运气。例如我认识的一位小学教师通过小区服务的方式教道德,启发学童们由行善中获得乐趣。十月底的一个阴天,她带了上百名学童及其父母到当地的救济院栽种球茎植物。先前孩子们已经知道救济院是什么样的机构,也谈论过这些花朵对救济院中的住客会有多大的意义,这可能是这些住客有生之年最后见到的花朵,因此孩子们明白自己行为的价值。他们欢欢喜喜地拔除了经霜枯死的大波斯菊和其他一年生草本植物,挖了2000个洞,耙梳土壤,种下光泽的球茎,还驱逐偶尔探出头来的土拨鼠。孩子们和泥土,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礼物?在那次栽培植物的计划中,老师和学生掌握的是plegan这个词较温和的含义。类似的机构,如人道之家,由善心人士担任义工为穷人建造房舍,同时享受户外辛勤工作和社交的乐趣,意义是相同的。
在各种语言中,最常和游戏相关的词语,往往和性爱有关。梵文中描述男女之欢的词是kridaratnam,翻译过来就是“游戏之宝”。而在德文中,Spielkind(字义为“游戏的孩子”)乃是私生子之意。英文也有用计吸引(make a play for)、试图引起他人注意以博取其好感(play up to)及沉迷于爱的游戏(indulge in love)等说法。英文词lechery(淫荡)源自leik这个词,是play一词的词根。在美洲原住民黑足族人中,koani这个词既代表儿童游戏,也意味着地下情。和play相关的词常会衍生出描述调情、战争或宗教仪式的词[如feast(宴乐)和festival(节庆),其词源都和“play”相关]。这些活动究竟有哪些共同处?它们全都需要胆大心细,甘冒风险,能够容忍不确定的后果,愿意遵从游戏规则,并且拥有超越平凡的欲望。这些活动的参与者都拥有神圣游戏的精神,不论儿童、诗人,还是野蛮人。
有时候我们正渴盼要做野蛮人——靠着聪明才智和直接的情感,配合大自然,保持官能的警觉,避开危险,因挑战而兴奋。马丁(Peter Martin)曾在《共同演化季刊》(Coevolution Quarterly)中写道:“有人说,托尔斯泰曾与哥萨克人共同生活,在赤贫如洗、艰困不堪的环境中,学习生命原始的力量。他们的生存严峻得如此纯粹,启发他的感官,而无疑地,在他稍后的生命中,当他想要抛却一切道德束缚之际,也有相同的成分在起作用。道德力量和面对生死之间,有一定的关联。”
面对试炼而战胜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善和恶的力量相抗衡之际。在这样高赌注的赌局中,运气当然举足轻重。许多神话都叙述神以人的性命为赌注,如梵文叙事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印度两大史诗之一,意即“伟大的婆罗多王后裔”,描写两族争夺王位的斗争)中,代表四时的人类借着掷金银色子来决定世界的气候和五谷的收成,但在运气或诸神的偏爱之外,人依然能够凭着自己的才智获胜。人为了获得赞美,为了争取他人肯定自己的价值而走的极端,实在教人惊异。弗洛伊德派的学者可以在此找到许多研讨的题目,演化心理学者亦然。究竟是什么使得我们产生公开接受赞美和表扬的需要?倘若这样的欲望是出于贪婪,牵涉到整个国家呢?名声威望是变幻莫测的,战士必须不断以勇武的行为证明自己的骁勇。如今不论战场是办公室或拳击擂台都无关紧要。毫无光彩荣耀地度过一天,就会令人坐立难安,因为地位可能不保,颜面可能尽失,资源可能消减,而意中人也可能却步。就算是表面明显的利他行为,都可能和功绩及荣誉相关。曾有一名飞行员把失控的飞机驶入山林而捐躯,虽然他原可幸运地降落在公路上而求生,但可能造成无辜的伤亡。于是人们赞美道:“他多么无私无我!”然而无疑地,他的动机之一是要表现出高尚的情操,因为若造成无辜伤亡,他将无颜苟活。若有人为他人而牺牲,我们或许会说他是舍己为人,但他真正的动机或许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无私;他或许只是很在意自己是否勇敢,也忧虑自己给人的观感。体魄的强健与否一直是测试个人是否高尚的标准,其他的准绳还包括勇气或财富。12世纪的佛罗伦萨,上流社会竞相筑高塔,一座比一座华美。这些美轮美奂的建筑表面上是作防御之用,后来被称为“吹嘘之塔”。不过在过去以及在许多文化中,竞赛通常包括知识和才智测验。古代的英雄必须解开神圣的谜题,答案错误,就意味着死亡。战士以侮辱和夸耀的言辞侮蔑对方,一如当今的街头顽童。在中国甚至举行礼貌比赛,谁能比对手更有礼貌就获胜。在法庭上,对手也常展开论战。O. J. 辛普森涉嫌谋杀案的审讯过程,已让无数的电视观众明白,要在法庭上胜诉其实与公理正义无关,而是取决于律师如何掌控这场比赛。所有的竞争者都要经受的磨炼,获得技巧皆与参与游戏相关。赫伊津哈说:
战争的法则,高尚生活的习惯,全都是依游戏的模式建立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文明在早期的阶段,是游戏塑造的,并不是如胎儿脱离子宫那般突然地发生,而是以游戏始,且本身就是游戏,并从未摆脱游戏本质。……就一公平游戏而言,过程中展现的诚实是最重要的,因此欺骗或扰乱游戏进行者就摧毁了文明本身。
我想他是对的。我们追缉且惩罚违法者,并不只是为了要防范他们再度犯法,而是因为他们在更基本的层面威胁我们。
我们总把游戏想成自我放纵,不负责任。“不要再玩闹了,认真一点!”总有人会这样说,仿佛这两者是相互冲突似的,然而游戏却是再认真不过的事了。在古罗马,所谓的“竞技”除了有嗜血的群众之外,还有让人毛骨悚然的死亡;它们有时候起于古怪难测的念头,例如让我们看看如果把人和熊或鳄鱼关在一起会怎么样。儿童对于游戏可能非常认真,他们的游戏虽然“有趣”,却未必是愚蠢或笑声不断的。
游戏的乐趣在于它本身的活动,是我们头脑最喜爱的学习和演练方式。由于我们把游戏视为认真严肃的对比,因此忽略了它其实掌控了社会的大半——政治游戏、婚姻游戏、金钱游戏、爱情游戏和广告游戏,这只不过是一些常见游戏巧计的例子。游戏的长处或各不相同,未必全都是充满奥秘、教人神魂颠倒,但就算是它最不教人心醉神迷的形式,依然能提供满足,让你全心投入。它拥有自己的规则和生命,同时赐你绝佳的挑战。游戏让我们有磨炼自己的机会,和我们密不可分,就像呼吸本能一般。人类生活中有许多部分,都是以游戏的面貌呈现的。
* * *
本书探讨的是人类传奇中让我着迷已久的一个成分:卓越的游戏(transcendent play),不只是如孩童那般游戏——因为天真烂漫而欢喜、团结合作,或是演练追求和社会的规则——而且是成人游戏中一个特别的层面,极度的人性化。当然,成人游戏的方式和原因经常和儿童相同:为求趣味而装疯卖傻;他们游戏以便交际,这也包括战胜对手,或是发展友谊。但还有更深层形式的游戏,让你心醉神驰、神魂颠倒,使人不独喜爱欣赏,而且感受到圆满(whole)。
感受圆满,这倒是个有趣的想法。人被束缚在皮肤之下,别无分身(除非是同卵双胞胎),如果他身体的甲胄被刺穿,五脏六腑就会流失。他既是自给自足的整体,又怎么会觉得不圆满?柏拉图的解释是,我们每一个人天生就只是半个人,因此必须要找到挚爱的另一半,才能圆满。不完整的感觉是自古就有的错觉,同样古老的是借着饮酒、嗑药、性、祈祷、符咒、运动、危险,和其他我们能想到的任何事物,暂时把头脑里絮絮叨叨的音量转低。借着摒除心灵的噪音,让我们同时感受到自由、安适和兴奋。
深戏正是达到狂喜的游戏形式,其间所有游戏的要素都清晰可见,而且臻至强烈和超越的高峰。因此深戏其实应以情绪而非活动来定义,它验证的是某事如何发生,而非发生了什么事。游戏未必能保证达到深戏的境界,但某些活动却很容易达到这样的境界:艺术、宗教、冒险,和某些运动——尤其是发生在较远、较安静和飘浮的环境,如水肺潜水、跳伞、滑翔、爬山等。
深戏常和神圣或宗教息息相关,有时隐身在最不可能发生或是最贫瘠的地点——在高耸入云的悬崖之上,蜷伏在室内昏暗灯光照映的书籍上,滑行在人造草皮上,附着在椰壳面具上。我们穷毕生之力,追求这种变化发生的时刻。澳大利亚原住民在荒野的旅途上追寻它,部族中的年轻男子独自步入人烟稀少、危险重重的内陆,求取力量和智慧。佛教的僧人和印度教的圣人也都几近全裸地旅行,在冰川高原的顶点祈祷。不同文化的人都曾到荒野中作性灵之旅,让危险、饥饿、痛苦、疲乏甚至自我折磨启发自己的视见。年轻的马塞族男子赴他们世界的神圣的中心——乞力马扎罗山上朝圣,这是他们入会仪式的一环。美洲原住民也经常以赛跑的仪式来衡量心灵的高度:霍皮族人每年都举行多次这样的比赛,包括化妆、斋戒和祈祷。克劳族人跑到精疲力竭,向神明证明他们值得被赋予好运。祖尼族人边踢圣棒边跑20至40英里。这些考验,表面上的目的或许是宗教,但生理上的目标是驱使入门者在必须靠才智和胆识方能生存的环境下,让自觉意识更上一层楼,启发他的心灵,开拓他的视野。
巫师和顶尖的运动员全都以近乎疯狂的感官狂热来追求深戏的状态:创造力、心理治疗和感官的淋漓尽致——这些全都是深戏最理想的游乐场。最近我在骑自行车之时,也常体验到这样的时刻,但过去我却往往得在骑马、驾驶轻型飞机、水肺潜水、在旷野中研究动物和赴极地探险时,才能有如此的体会。这些点点滴滴增强了我的梦想和渴望,启发了我写作的灵感,也构成我性灵的基础。下面我会稍稍引用横跨约十年的日记的内容,虽然当时我还不知晓深戏的观念,但却常常经历到它,而且不知不觉记下它的种种特色及其多种变化。深戏使得我的生命如此多姿多彩,也让这么多人的生活充满了活力。如今这些记录都可以在我探讨深戏的心灵栖息地时派上用场。
约有五年的时间,我很少旅行,也似乎罕有深戏的机会,不过当时我正从事心理治疗工作,如今回顾起来,那段经验也满足了我的一些需要。心理治疗怎么能和深戏扯上关系?所有的游戏都发生在特殊的心灵地点,有时间的限制和规则,超脱日常生活之外,它包含了变幻无常、幻觉、假装或绮想、容许人冒险,或探索新的角色。毕生以儿童研究为职志的精神分析学者温尼科特(D. W. Winnicott)就明白心理治疗这种独特游戏的价值:
心理治疗发生在两个游戏领域的交集中,一个是病人的,一个是心理治疗师的。心理治疗是两个人一起游戏……精神分析已经发展为高度专门的游戏形式,用来作为自我和他人的沟通。
我也是“生命线”的义工,这个工作充满了私密而紧张的戏剧。因此就几个方面来看,我的生命其实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之外,还有另一层的现实,强烈而专注,充满了冒险以及对其他事物的沉醉——这些全都是深戏最关键的要素。英国心理治疗师史基纳(Robin Skynner)就发现,他在工作上体会到困难重重的兴奋,和“二战”时他驾驶蚊式轰炸机的经验不相上下,有时他可以由精神治疗的工作中,辨识到“绝对专注、全神投入的感受,和当年要掷炸弹时相仿。两种情况下,我都面对着充满爆炸性的事物。在治疗时,我的目标是拆卸炸药的雷管,而不是逃避或被炸死。这非常危险,也非常有趣”。我怀疑他对每一个病人做治疗时,都会有如此强烈的危险情绪,但就专业的报酬而言,治疗的确让他有深戏的机会。
古人曾描写并歌咏深戏的要素,为深戏的某些情绪创造出描绘的名词。拜他们之赐,我们知道英文中的rapture(欢天喜地)或是ecstasy(心醉神迷),以及其他我曾在体会深戏经验时所用的用语。Rapture和ecstasy本身并非深戏,但它们确是深戏的要素。
就字面上来看,rapture意即“被力量攫获”,就像被捉的猎物。一旦被超凡狂喜的力量抓住,人就如同遭攫,飞升到不由得心悸的高处。古希腊人觉得,这种感受通常预示着凶兆和危险——同样掬饮狂喜源头的词包括rapacious(强夺)、rabid(猛烈的)、ravenous(狼吞虎咽的)、ravage(破坏)、rape(掠夺强暴)、usurp(篡夺)、surreptitious(暗中的)。常由空中直冲而下捕食猎物的鸟类,被称为raptors(猛禽)。被这样强大粗暴的力量攫住者,往往身不由己,只能任凭这股力量带他们高飞至终极。
ecstasy也意味着被热情攫住,但角度略有不同:rapture是垂直的,ecstasy则是平面的;前者是高高飞舞,后者则发生在平地上。不知为了什么,古希腊人对站立的象征非常着迷,以这个形象塑造了无数的观念、感觉和物体,因此今天有许多英文词都是表现事物站立的方法与姿态:stanchion(支柱)、status(地位)、stare(凝视)、staunch(坚强)、steadfast(坚定)、statute(雕像)和constant(持久不变)。另外还有上百种出乎意料的词,如stank(静止的水)、stallion(站在马厩里)、star(矗立在天空上)、restaurant(让流浪者得以站立歇脚的地方)、prostate(立于膀胱之前)等。在古希腊人眼里,ecstasy意即立于己身之外。这怎么办得到呢?透过存在的机巧(existential engineering)。阿基米德在公元前3世纪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地球。”借着ecstasy的杠杆,人便能跃出自己的心灵,摆脱平常的自我,立于另一地,矗立在身体、社会和理性的限制之上,注视着已知的世界逐渐朝远处缩小。在梦中飞翔的陶醉,或是在海洋里和海豚同游的渴盼,让我们心中充满了rapture。人能否同时感受到ecstasy和rapture?安普森在一首诗中思索在爱情中并存的限制和宏伟,“矗立的核心,就在于你不能飞翔”。这是逃离俗世的两种途径,两种赴深戏的途径,同样能解你之渴,同样神秘,其间只有微妙的差异。所有的路的确都通往罗马,但一条可能经过山林,另一条却可能行过沼地。
17世纪法国流行的情色文学,常有欢喜若狂到“欲仙欲死”、“灵魂出窍”的描述——这种如急症发作般狂乱的热情,虽有些许亵渎意味,却更让灵魂战栗。其实这样的词语原先是用来形容神秘主义者或极虔诚的教徒着迷宗教到脱离现世的地步。不管是狂热销魂也好,灵魂出窍也罢,如今都被视为可喜、渴盼甚至值得钦羡的状态。
不论用什么样的词语形容,欣喜若狂、心醉神迷都是“深戏”观念的基本要素,超验、冒险、着迷、喜悦、迷乱、超越时间和神圣的感觉亦然。多年来已经有不少作家描述人类和“深戏”相关的种种重要层面。20世纪之初,涂尔干(Emile Durkheim,法国实证主义社会学者,认为劳动分工为社会团结之基础,集体意志对社会有决定作用)曾提出过“集体欢腾”的观念,这是典礼仪式中以群体形式出现的“深戏”;透纳(Victor Turner)也描述过暂停扮演日常角色时产生的类似情绪;弗洛伊德提到婴儿渴望“汪洋般的感觉”,让自己能和所爱的人或环境融合。温尼科特把游戏当作摆脱日常生活的创作状态,布里尼(D. E. Berlyne)则认为生物并不追求完全的平和安静,反而需要最大的刺激才会觉得健康。齐克森米哈利(Mihalyi Csikszentmihalyi)写到“心流”(flow),他的实验对象常用这个词来描述自在享受的情绪。葛鲁斯(Karl Groos)和墨菲(G. Murphy)则提到把自己的身体和官能发挥到淋漓尽致时的欢愉感受。萨特、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尼采全都强调游戏时掌控和自由的魅力。荷兰人类学者赫伊津哈关于游戏和社会的文章多有启发,马斯洛则写道,“狂喜、心醉、极乐……的巅峰体验”;这种超验的经验还包括“敬畏、神秘、尽善尽美、谦逊、臣服和崇拜”。健全(自我实现)的人往往在发现自己的能力和极限时,感受到这些与生俱来的满足。
“深戏”的精神不但是每一个人生活的重心,对社会也有深远的影响,启发了视觉、音乐和语言艺术,驱使我们探险和发现,导致战争,产生法律和其他种种我们珍爱(或畏惧)的文化层面。陶醉在游戏最深沉状态中的人不但身心安定,创造力丰富,也能够集中心神。“深戏”是人类最让人着迷的印记;说明了我们必须寻觅某种特别的超验经验,怀抱追求刺激、发挥创造力和虔诚信教的热情。或许在表面上,宗教和游戏扯不上边,但若仔细观察宗教仪式和节庆,就可以发现所有游戏的要素和热烈的情感尽在其间。宗教仪式通常包括舞蹈、礼拜、音乐和装饰,它们吞没了时间,让人手舞足蹈、全心投入,也让人返老还童。祈祷(prayer)一词源自拉丁文precarius,含有不确定和冒险的意思。我们的恳求会得到应许吗?生死可能就在这一线间。既然举世皆有牺牲祈祷的仪式,赫伊津哈于是得出结论:
这种习俗必然根源于人类心灵非常基本、原始的层面……游戏的观念很自然地和神圣观念融合……因此原始的仪式就是神圣的游戏,是社群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充满宇宙性的洞见,攸关社会的进步发展,但也总是依据柏拉图的定义进行——是超越日常生活必要与严肃之外、自成一体的行动。
本书可以说是依据赫伊津哈的主题而衍生的幻想曲,把他的观念想法加以变化发展,追索它们的影响和细微巧妙的差异。不过“深戏”一词则源出“功利主义之父”边沁,他认为“深戏”是一种“赌注很高的活动,很少人愿意参与其间,因为即使赢,其边际效益也根本及不上万一输所造成的不安和痛苦”。这种说法的确不假,在我们读报纸时,往往因某处某人不计后果无论如何都要完成某事而惊讶莫名,剥开平淡无奇生活的外衣,你或许会见到对越野滑雪几近疯狂的热爱,或是如苦行僧般虔诚投入的集邮收藏,这一切都因为它包含了如基督徒追求圣徒遗物般的热忱。
边沁不以深戏为然的原因,恰是我和许多人热爱深戏的缘故。攀岩家安东尼(Mo Anthoine)曾说,他每年总得喂食心里的“老鼠”几次。他的意思是不停啮噬他心灵的“老鼠”要他面对挑战,参与结合了冒险、趣味、神奇、风险和考验的旅程。虽然我并不会攀岩,但深知这种心痒难搔的感受,也认为再也没有何事如深戏这般。冒险会刺激浪漫精神,而深戏正是靠着生命中的浪漫精神而存在。源源不绝的创意正是深戏的一种形式。心理学者葛林奈克(Phyllis Greenacre)多年来对儿童做临床研究,认为有艺术家倾向的孩子往往和照顾者未能建立依赖关系,而和世界“发展出情爱”。这种看法对深戏的观念有所启发。我赴南极洲时,曾在日志上写道:
今晚看不见月亮,就连黑暗也几乎消失。我们用家庭、例行公事和报纸架构起来的已知世界飘浮到地平线之外。到陌生的新景物中旅游就是一种浪漫,你强烈地感知到自己所在的世界,但同时却也把其他的世界抛诸脑后。就像爱一样,旅游使你再度天真烂漫。多少天来,我听到的唯一消息是大自然的讯息。明日,正当我们漂过格拉契海峡的冰山花园之时,我会开始工作——写散文。我的心灵将成为内在警醒的旋风,所有的细节会一个一个缓缓地呈现。我不知道该如何描述在“大自然”和“写作”时自己心中的感觉——那是一种欣喜若狂的经历,它经常发生,教我有所期盼。
我正站在伟大冒险的门槛之前,期待着明日一大早即将发生的欣喜之感,心知那将是内心极度警醒的旋风,等待我的是几近惊恐的状态,我将完全存在于紧张的眼前瞬间,体验到生命的精华。
这段日志说明了深戏的许多要素。我们进入了拥有独特规则、价值和期待的另一个现实,展开销魂体验的全新生活,而摆脱了自己的文化及其附带无数规则和道德的要求。我们总把“洗脑”想成负面的含义,认为是战争中掳走并隔离囚犯时所施的奇特伎俩,切断囚犯所有过去的关系,迫使他发展出一种不同的心理状态,和他先前所认同的价值观完全相反,因而可为敌人所利用。然而还有一种正面的“洗脑”,让我们能够摆脱先入为主的成见和陈腐老套的观念,刻意抹净心板,以明镜般的天真心灵面对整个世界,一如我们童稚时般。如果人因年龄增长,就会愤世嫉俗,那么随着这种情绪而来的,就是对天真的渴望。对儿童而言,天堂就是能够长大成人;而对成人而言,天堂就是重回童真。
情侣决定结为一对时,就热切期待甩脱世俗扰攘,只活在两人独自的小世界里,其实正是逃到爱情的神圣王国,在这个私密的世界中,自有其风俗、语言、价值和规则。爱是一种自愿投入的神秘主义,是两个人所建立的教派。情侣常互以娃娃语相称,用父母溺爱子女时所用的亲昵语词,他们往往一起嬉游,结为玩伴。情人就像起乩的巫师,在恍惚中能窥见恋人的心和灵魂。如果其中一人抛弃另一人,那么他们的私密世界瓦解了,现实粉碎了,负心的一方就像孩童嬉戏时破坏全局的罪魁祸首,拒绝认可游戏的现实、本质和吸引力,否定这些幻觉,游戏就只好结束。不去理睬流氓,他就丧失威胁的力量;忽视女妖,她就失去魅惑人的能力。“幻觉”这个词其实就意味着魔力,当爱的游戏停止,我们说“魔力消失了”,幻觉破灭了,我们再度回到俗世凡尘。
这种状态非仅情侣为然。举凡独自置身于紧张、戏剧化情况,诸如战争、探险、启蒙仪式、海上巡游、俱乐部等地点的人,都可能摆脱现实,置身浪漫而曼妙的世界里。有时候他们隐身面具、制服或服饰之后,有时候他们使用私密的语言,有时候他们共享神圣的秘密。王尔德说,浪漫的本质就是不确定,而还有什么会比危险更不确定的?许多学者发现,人往往在离家或面临生死关头,或兼具两者之时,会坠入爱河。危险把你的焦点移得更近更深,爱亦然,祈祷也是。当世界缩小为明亮狭小的空间之际,每一个念头和动作都关系着个人的救赎,于是四散的精力突然有了重心,唯有此刻,我们的官能开始警觉,所有的知觉都举足轻重,在此同时,其他的世界都淡出,我们暂时摆脱了人生的枷锁——家庭、工作和我们加诸己身的责任负担。我在1980年的飞行日志中写道:
并不是我觉得危险有什么了不起,也不是因为我非得寻求廉价的刺激以纾解日常生活的烦闷,而是因为我喜爱紧随危险和某些运动而来的浑然忘我的时刻。在那一刻,你为求安全,必须灵活动作,唯有临机应变,而无从分析推测。你摆脱多少世纪的包袱,发觉自己只剩下生物的一面。当然,你必须扫视、评估,不时做出快速的决定,但这和你平时以逻辑的方式来思考并不相同,取而代之的是掌握所有讯息的直觉。对爱思考的人来说,能够保持警觉,却摆脱所有的思想,就是一种欣喜……还有一种状态,是当知觉不再起作用,意识消失,而你也摆脱所有身心的限制,如此突然,让你根本不觉得自己自由自在,只是眼观四路,耳听八方,没有评断、历史或情感。这种超脱时空的感觉在许多运动中都是精华的一刻,在危险行为中往往也会经历到它,甚至上瘾。
在后来的岁月,赴特殊地点探险之际,我发现自己能够深入大自然的殿堂,让时间以新的方式颤动。短短一刻可能匍匐数小时之久,也可能倏然即逝,落入一张又一张独立分别的照片,或是堆在一起,或是像美丽的龙卷风一般不停回转。陷入深戏状态的人,时间感不再起于己身,这种时间感的变幻经常发生在和野生动物同处的人身上,尤其当他们出发去探索未知世界之时。
曾有一次,我赴遥远的日本小岛,寻觅最后几只残存在世上的短尾信天翁,结果不小心摔落悬崖,跌断三根肋骨,自此之后,旅程变得非常危险。在黄昏时刻,我们像僧侣一般结束沉默的观察,收起背包,思索要如何攀爬。我的左侧身体就像束着痛苦的紧身衣般,一动也不能动,但我们却又得回头爬上四百英尺的悬崖,再徒步越过火山,才能到达位于废弃驻军要塞的基地营,再设法找路离开岛上求医。
“虽然艰苦,但却是美好的一天,”当时我这么告诉同伴,而且的确心有所感,“若能由源头掬水而饮,又有谁会用杯子呢?”
这段故事强调的是深戏的另一面。我们希望实实在在地体验生活,把生命发挥得淋漓尽致,希望由源头掬饮。在深戏的宝贵时刻中,我们摆脱自我意识,让时间的流动中止,忽视苦痛,只静静地坐在绝对的现实中,凝视着宇宙间平凡的奇迹。心灵和智慧都停止作用,不再分析或解释,不再质疑逻辑,没有承诺,没有目标,没有人际关系,不再忧虑,完全敞开胸怀,准备接纳即将到来的各种戏码。我们带着天真的期待,思索人生的形形色色及其背景。我们感受到的是对整个创造大业情感洋溢的好奇心,不论造成这种情绪的是什么——是凝视信天翁求偶,或是壮丽翻腾的日落。当它发生之际,我们只觉得到启示和感谢,不需要多想,也毋庸多说,这样的凝视就是一种祈祷的形式。
这种深戏的时刻并非突如其来,可能有十数种路径引导你到那儿,“正常的”时间环绕着它。在发生之前往往有界限或门槛。这样的界限可以称为“沿岸时刻”,因为它们就像海岸上薄薄一层细沙,连接坚实的土地和流动的水波。在这边缘时刻中,你可以有种种的选择,或许找个恋人,或许不;或许陷入自我怀疑,或许不;或许一头栽进不同的文化,或许不;或许扬帆朝向未知而去,或许不;或许步上舞台,或许不。仅仅有那么一瞬你的未来架在深渊之上,这里就是十字路口。在那看不见的十字路口上,刻有下面这句话:赴此路者,必得放开执着。
放弃我独特的意志、自我——心甘情愿,仿佛圣徒一般虔诚,自有其吸引力。就好像把我的感官知觉借给别人一样,让他通过它说话,用和谐的语言分享他们的视界。我似乎化身为译者,努力想把所感所见形诸笔墨,表达出动物和风光景致的生命力,为它们代言。我细细回味大自然和人性华美丰富的细节,这和奉献一生在一本重要经书上的和尚又有什么不同?
一般的游戏和深戏究竟差别在哪里?一般的游戏有多种形式、多种目的,但只是为游戏而游戏;如果游戏成为你生命的重心,为你带来欣喜若狂的感受,那么它就成了深戏。生物演练面临强敌时的本能,如变色或逃跑,就是最基本的游戏,各种生物可以不假思索地做出形形色色的反应,而且充满了风险。动物练习长大后所需要的技巧,或是欢腾雀跃以保持头脑和肌肉的灵敏,是另一种形式的游戏,但却不是深戏。为了义务或威胁而做的反应亦非深戏。为了艰苦的工作而长时专心并非深戏。为了名利而奋力参加某种运动亦非深戏。复诵老掉牙的祷词或圣歌并非深戏。深戏未必总是正面,帮派分子有时也会说他们的暴行让自己也深感痛快。但在深戏时,你的心灵往往会觉得清明,受启发,接纳自我并有其他肯定生命的感受。
深戏中,总有让你觉得自己无敌、不朽,成为理想人物的时刻。篮球女运动员尼尔(Patsy Neal)曾描述比赛时登峰造极的体验,“她站在奇迹的门槛上,那一刻的力量使她的表现更添了宗教意味,不妨称之为恩典的状态、信心的行为,或是神迹。这个人被卷入她周遭的行动之中——几乎飘浮在这些表现里,汲取她先前从未感受过的体验。而在这些纯然狂喜的宝贵时刻中,我们又跑又跳,经历这全然游戏的过程,充满欢欣、喜悦、快乐和笑声;在这珍贵时刻中,我们领略到自己是唯一、是整体,甚至连痛苦都能忍受”。若以唱福音或绘画来取代尼尔描述的篮球体验,就会发现它们也同样真实。
探险家一次又一次地描述提高感官知觉和无所不能的综合感受。山友舒尔海兹(Rob Schultheis)在《骨戏》(Bone Games)书中,回想自己在摔得半死之后下山的感受,“我在那山上成了从没有过的好人,成了我原该做的模范生。没有遗憾,没有犹疑,没有虚伪。我相信自己可以用松针一下刺中蚊子,绝对不会失手,因为没有所谓的失手”。林白(Charles Lindberg)写到他有鬼魂为伴,横渡大西洋,而且赐他“日常生活中得不到的重要讯息”,让他成为名闻遐迩的人物。瑞士地质学者海姆(Albert von St. Gallen Heim)在1982年的专题论文《致命坠落斯言》(Remarks on Fatal Falls)中,访问了许多登山失足者,发现他们都有相似的经验:
没有焦虑,没有绝望,没有痛苦……心灵活动无限庞大,速度和强度都加快百倍。他们能够清明客观地看出因果,同时又以迅疾如电的速度行动。
舒尔海兹把超验的经验归因于“因焦虑引发的狂喜”,这正是人们追求的启发,也是巫师追求的境界。痛苦、疲乏、饥饿、压力、隔绝、冒险——这些都是巫师、追求极限的运动员、圣人等鞭策自己身体以达超我境界的手段。
神圣的游戏场或如大峡谷一般宏伟,或如海豚优游其间的海洋那般流动,或如喧闹的俱乐部那般拥挤,或如网络上的网络教会那般无形。深戏最极端的事例可能包括生死关头,而在其间的人只觉得平静。摩托车赛车手史密斯(Malcolm Smith)说:“你觉得全身非常平静,虽然你的神智明白自己正在灾难边缘。”挑战、发现、探索、新奇、超越极限、在行动中失去自我——这些深戏的要素在史密斯赛车时,都在他身上发生过。然而并非所有骑摩托车的人都能体验到同样的热忱。在有些人看来,赛车是工作;对另一些人而言,赛车是游戏;而在史密斯身上,赛车是深戏。
本书并非结论,而是一种探索,邀请你仔细观察人类传奇,思索它和游戏有多么密切的关联。基本的游戏,讲究的游戏,原始的游戏,世故的游戏,暴力的游戏,轻松的游戏。大多数的动物都游戏,演化本身就和“生物形式”游戏;整个文化随习俗、观念、信仰体系与时尚同戏。然而唯有特别的游戏——深戏,才能带引我们到达超验、创造力和神圣感的境界。正是深戏的热情,才使得我们成为如此让人迷惑奥妙的生物。巧的是,本书正是其主题的例证。它的写作包括了许多游戏的时光,其中有些比一般的更纯粹、更超验。我任这些时光翱翔,因为这超脱时间之外的一刻正是深戏的源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