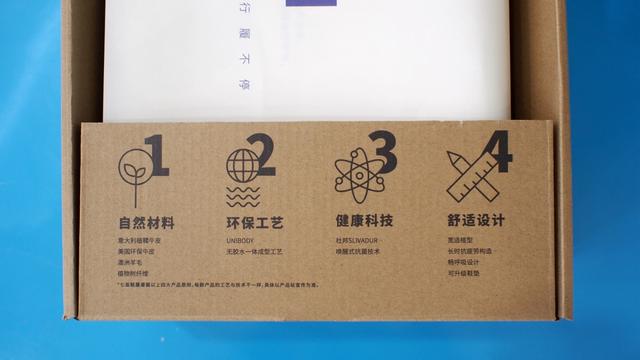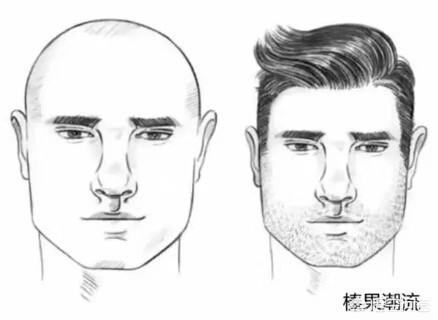充满危险的求美之路桂林生活网讯(桂林晚报记者沈青)三位爱美的女性,都梦想着留住年轻的容颜于是,当美容院声称可以为她们找到“快速有效”的解决方案时,她们就迫不及待地走了进去,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桂林美容养生基地?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桂林美容养生基地
充满危险的求美之路
桂林生活网讯(桂林晚报记者沈青)三位爱美的女性,都梦想着留住年轻的容颜。于是,当美容院声称可以为她们找到“快速有效”的解决方案时,她们就迫不及待地走了进去。
结果,所谓“国外进口”的最先进仪器、针剂,却在她们脸上留下了让她们记忆深刻的印迹,而随后美容院的巧舌如簧,让这些爱美的女性,在日后陷入了不胜其烦的维权困局。
事实上,在我们身边,通过一些美容机构进行医疗美容遭到失败的个案,远不止上述三位丽人。
当下,越来越多的美容院在私底下从事着医疗美容的业务,但无论是从药物来源、人员资质到操作使用再到监督管理,这都是个灰色的地带。
美容针还是毁容针?
望着自己发黄的面容,31岁的冰冰(化名)一再问自己:打了美白针,为何不美白?
一年前,通过市内一家美容院的极力推荐,冰冰预约到一位外地的整形医生。在被注射美白针一个疗程之后,“效果”开始显现,她满脸发黄、浑身乏力。
去年底,一则新闻更让冰冰冒冷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在其官网首页对美白针发出警告,市场上的美白针产品不仅可能无效,还潜藏着感染艾滋病、损害肾脏和神经系统等多种风险,并声明FDA至今未批准任何注射类的皮肤美白或祛斑药物。
冰冰回忆起,她注射的正是一种打着“FDA认证”的美白针。当她找到美容院提出质疑时,对方辨称只是提供了中介服务,而执行注射和提供药品的则是南宁一家整形医院的医生,“有问题应该找医生啊”。
后来她多次联系那位医生,却都没得到想要的答复,而南宁的那家整形医院却明确表示“无此医生”。所经历的一切,让冰冰意识到自己“中招”了。
这几年,相较于需要开刀且恢复慢的整容手术,微整形越来越受爱美女士们的青睐,注射类针剂则更是受到追捧。
琴琴(化名)是一位28岁的本地女性,前段时间她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一条链接,有朋友去市内的一家美容院预约美白针,听起来极为诱惑,“全身美白,无任何副作用,同时还可加速身体排毒……”
1月27日,记者跟随琴琴到了这家美容院,与该美容院请来的医生见了面。医生自称,他来自广州某整形医院,所采用的针剂产品是韩国进口,由静脉注射,一个疗程8000元。
当天,琴琴又到市内另外4家美容院进行了咨询,其中有2家也表示可以提供注射美白针的医疗整容服务,其运作模式与前一家如出一辙:都是先在美容院预约,由美容院帮请外面的“医生”来执行药物注射,针剂和注射仪器都由请来的“医生”提供。
除了美白针,有的美容院还推荐琴琴注射另一种很流行的美容针——— 水光针。其直接注射于脸部,主要药物是玻尿酸,根据个体需求差异,可以加入肉毒素和胶原蛋白。
在网络上和线下的美容实体店里,也都充斥着类似的美容和药物的推广广告,有些爱美者已经通过QQ、微信相约注射或者探讨注射效果。许多卖家则自称产品自国外进口,售价不菲,一个疗程少则两三千,多则数万元。
但无论是当下颇受女士们追捧的水光针,还是前两年就开始火爆市场的美白针,在医学界却都并未得到认可。
“医学上,不存在美白针这个概念。”市内一家大医院皮肤科一位医生介绍,至今还没有哪一款所谓的美白针得到国家食药监总局的许可。记者随后查询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并没有“美白针”作为药品和化妆品的注册备案。
另外就水光针注射来说,国内仅有一款注射设备通过了国家食药监总局批准。就注射物而言,国家食药监总局则在去年专门发布消费警示,玻尿酸属于风险最高的三类医疗器械之一,必须经相关部门批准才能销售使用。
而类似的美容产品如溶脂针、人胎素等等,国家食药监局则从未批准过。
从冰冰女士的例子也可以看出,一些据称有神奇功效的美容针剂,从药物来源到注射使用都存在显而易见的大风险。
生活美容还是医疗美容?
除了来源不明的药剂,在并不具备任何医疗美容资质的美容院做医疗美容,则让一些“白富美”们的美丽梦想变得充满危险。
去年12月31日,市民徐慧(应本人要求化名)从秀峰区人民法院拿到了一审判决书,判决市内一家美容院须赔偿她近25000元。
2012年至2014年,徐慧一直是这家美容院的老顾客,刚年过三十的她逐渐感到自己不再如以前那般光彩艳丽,觉得需要在自己脸上下点“功夫”了。
美容院开始为徐慧做净肤、破皮、提取等一系列祛斑美容项目,并多次采用了一种镭射祛斑仪为其进行祛斑美容服务,“老板说这是花了数万元从国外采购的,是当时最好的祛斑仪器。”徐慧说。但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花费了19800元进行了祛斑美容后,脸上的斑非但没有消退,反而出现了无法消除的疤痕。
法院审理此案认为,美容院所使用的具有侵入性、创伤性的方法进行祛斑美容项目,侵害了徐慧的身体权,过错明显,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据记者了解,这已不是这家美容院第一次因类似美容项目被告上法庭。2011年,一位女性消费者就曾因为在这家美容院做去除妊娠黄褐斑而“毁容”。
“当时,是朋友介绍我到这家美容院,说这里有一种超导雾化仪作祛斑效果很好。”这位消费者说,但在几次治疗之后,她的脸部皮肤开始渗血且凹凸不平,美容院还称是正常现象,只需要继续修复。
但当这位消费者坚持到医院就诊后,医生诊断其脸部已属于陈旧性创伤性瘢痕,后经司法鉴定已构成十级伤残。最终,法院判决美容院赔偿消费者6万多元。
据了解,这家屡次发生事故的美容院最早成立于2008年,曾在桂林业界颇有口碑。
但记者在卫生部门和工商部门查询到,这家美容院至去年底尚未取得医疗美容资质,经营范围仅为生活美容。而与其相关的两起案件,主审法院都依照证据认定,两位女消费者在这家美容院接受的都是创伤性的医疗美容,而非普通生活美容。
在国家卫生部颁布的《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第十六条中规定,实施医疗美容项目必须在相应的美容医疗机构或开设医疗美容科室的医疗机构中进行。
据工商部门不完全统计,市内已有上百家美容院和其他美容机构,而目前除了一些医院外,在我市工商部门注册的具有医疗美容这一经营内容的美容整形机构仅有三家。卫生部门则介绍,美容机构要从事医疗美容服务,必须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所有注射剂,以及其他侵入真皮的项目,美容院都不可以操作,即使有合格资质的专业医生坐诊也不合法。”一位法官告诉记者,上述两起案件涉及的美容院都缺乏安全卫生的医疗条件,安全性自然难以保障。
美容行业的“临时工”
今年1月21日,一则“模特美腿惨遭毁腿”的新闻见诸本地报端。
2013年7月,一位20来岁的女孩被市内一家医疗美容门诊部的瘦腿广告吸引,来到门诊部希望做医疗减肥。从当年7月至9月初,在该医疗美容门诊部进行了3次双腿穴位多层次埋羊肠线减肥术。
当年9月底,女孩的左小腿出现一处化脓感染,每天发烧不退,不能行走,经过这家门诊部和多家医院治疗,从2013年10月至12月,女孩前后经历7次全麻手术、多次局麻手术,双腿留下大小疤痕13处。
这位车展上漂亮的模特,如今甚至生活都不能自理,巨大的精神压力导致她多次产生轻生的念头。
记者从市卫计委对该美容机构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看到,这家机构虽然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但为女孩进行手术的医生却没有行医资质。
最终,这家美容机构被罚款3000元,女孩则通过法院起诉进行索赔,后经法官调解成功。
除了案件中受害人的遭遇令人震惊外,美容业从业人员的资质疑问也成为一些爱美人士的关注焦点。
在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聘用无行医资格的人员或许只是个例,而在多数通过美容院为媒介为顾客进行医疗美容服务的“医生”和所谓“专业人员”,则完全属于游走在灰色地带的“临时工”。
在市内不少美容院,老板都对顾客表示可以联系到整形医院的专业医生,为有需要的顾客提供注射美白针、瘦脸针等等医疗美容服务。
但这些“医生”的真实身份始终存疑。
1月28日,记者伴随一位要注射水光针的女顾客,通过市内一家美容院,与一位“王医生”取得了联系。这位医生说自己来自上海,曾在当地一家大型整容医院工作,后来出来“单干”。
“我全国各地跑,一年做手术至少100多次。”王医生说,自己使用的产品全部是韩国进口,保证不会出问题。但具体是什么产品,针剂里面的药物是什么,他拒绝透露,并表示:“打的时候就知道了。”
根据王医生留下的QQ号,记者多次与他交谈后,才勾勒出了这位“医生”的工作轨迹。他常年带着药、注射器具、笔记本电脑游走在全国各地,哪里的美容院联系到客户,他就到哪里去给人注射、手术,不过他无法提供执业医师的资质证明。在药物方面,“王医生”销售的肉毒毒素、玻尿酸、美白针等则应有尽有,只要你有需要。
除了这种临时工,在美容的“江湖”里,也有货真价实的医生以个人身份参与其中。但按照我国《执业医师法》,医师只能在执业注册的医疗机构行医,在注册地之外的医疗行为都属于非法行医。可是,在“外快”诱惑之下,一些医疗美容医生还是铤而走险,在医院之外甚至到外地开展这种医疗美容服务。
这些“江湖郎中”,与大大小小的美容院紧密结合,构成一条完整的医疗美容利益链条。
谁是沉默的羔羊?
于是,一条“灰色”的产业链浮出水面。
美容院提供需要做医疗美容的客户,从“医生”或整形机构里收取提成,仪器和药品全部由“医生”负责,“医生”再把病人带到宾馆或者整形机构接受手术,拿走提成外的费用。
手术后,那些非正规的医生会尽快“消失”,美容院一般都会表示自己只是提供中介服务,几乎能够撇清所有的责任。
而记者也从市工商部门和卫生部门了解到,这里很少接到医疗美容方面的投诉。但这并不表示接受非法医疗美容的受害者完全没有,只不过像冰冰女士或者徐慧这样愿意曝光自己受害经历的人实在太少。
一些受害者碍于面子,担心遭到非议或者产生家庭矛盾;还有一些受害者则因为已经与非法行医方达成“私了”协议,只要能得到治疗费用和赔偿,当然也不想再公开举报。对于美容机构来说,只要获得的利润足以承担事故赔偿的风险,自然也愿意用钱封住受害者的嘴。
非法医疗美容造成的感染往往病情复杂,受害者最后都不得不寻求正规医疗机构就医。因此,只有在大型医院的整形外科,非法医疗美容的受害者才可能浮出水面。除了寻求医院的帮助,这些受害者几乎不会向任何机构投诉。
在采访中,记者寻找非法美容受害者的过程也十分艰难,一位受害者就坚决拒绝与记者见面,她在电话里说:“如果让我老公知道了,他一定会跟我离婚。”
而记者找到的一位将非法行医美容院告上法庭的受害者,美容院已愿意向她支付赔偿金。但因为一部分赔偿款尚未到手,这位受害者不愿让案件曝光,担心会因此激怒美容院,导致无法得到完全赔偿。
即便是徐慧这样已经拿到判决书的维权者,在诉讼过程中也几次想放弃,“维权的过程就是不断回忆痛苦的过程。”但幸运的是,徐慧在被美容院侵权后留下了照片等一系列证据,并且说服了一位当时在美容院为她服务的工作人员作证,让她的维权路稍微顺利了一些。
秀峰区法院民事庭一位法官主审过一起美容侵权案,整整花了三年时间。这期间,美容院极不配合,“时间拖得越久,取证就越困难,就越难证明受害者是在美容院接受医疗美容而造成的恶果。”双方对证据的不断争论,不断举证,美容院甚至不承认受害者来接受过相关仪器服务,宣称导致受害者受伤的仪器根本不存在。后来,受害者找到了这家美容院多次在报纸上刊登的相关仪器的广告宣传,才让案件有了转机。
非法医疗美容的受害者,隐身在各个角落,数量无法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特别是最近十年,注射美容、微整形的兴起,非法医疗美容也发展成为成熟的产业链。此外,便捷的互联网,也让非法医疗美容的推销有了更便捷的途径,从购买注射药物,到联系“医生”,医疗美容“一条龙服务”可以全部在网络上获得,这样的操作模式几乎能够完全避开相关部门的监管。
2015年7月,国内一位年轻女性在微博直播自己在家自行注射美白针而成为网络红人,视频中的她使用未经消毒的设备,将针头戳进自己身体,其淡定的表情令网友毛骨悚然。
但即使如此,大量的医疗美容产品未获国家批准认可,风险依然巨大,在爱美者们的未来求美之路上,依然有着重重危险。因此,有关部门加强对美容机构的监管已经刻不容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