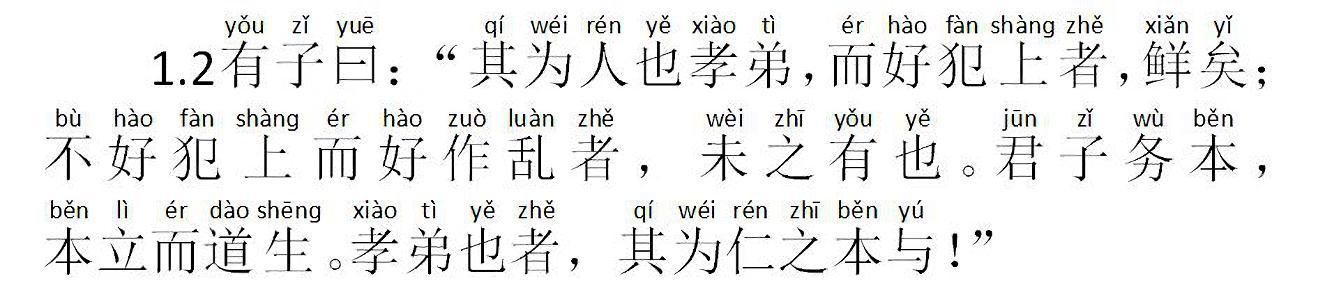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大寒前后,中国北方大地还笼罩在一片萧瑟、凛冽的深冬气氛中。此时,“聊赠一枝春”的江南最是风雅,在莽莽北原,踏雪寻梅也不失浪漫。梅花,这早春的信使,冰雪之中的女王,总是在最寒冷的时节慰藉着人们的心;它不仅被中国人视为“百花之首”,还在无数朝代的流转中,将她赋予了人格化的情思,她是君子之花,是高洁、坚强、忠贞的象征。
古人赏梅,不仅赞叹自然的造化、生命的坚韧,更是将梅视为知己旅伴,是人生中熨帖的际遇和相逢。曾在杭州寄身的白居易,“三年闷闷在余杭,曾与梅花醉几场”,梅花是他身世浮沉中的知己;“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欹窗前,寒梅著花未?”
王维的梅花,是人在异乡时的一段柔肠一份牵挂;人称“梅妻鹤子”的北宋处士林逋,更是深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隐逸情怀和寂静之心。
原产中国的梅花,栽培历史也有三千多年,在这三千多年的光阴里,它早已不是一株植物的形象在寒风之中独自绽放,而是一位高士、一位邻人、一位诤友,与追求高洁志趣的中国文人相伴相随。
宋代是中国梅花文化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宋朝人在赏梅、咏梅、画梅、与梅交游等方面都可谓登峰造极,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北宋咏梅第一人苏轼曾写下了四十二首关于梅花的诗;近代画家吴昌硕曾说自己“家传一本宋朝梅”,指的就是宋伯仁的《梅花谱》。有关梅花的著名典故、诗篇和绘画,多起源于宋朝。
这一时期,关于梅花的诗词、绘画作品数不胜数,梅花似乎成了宋人表情达意、抒发胸臆、感怀身世最体己最自然的载体,它就是美德、志趣、情操的化身。尤其是“崇文抑武”的北宋时期,梅花的淡泊清净暗合了此时人们所推崇的恬淡、稳健、不随波逐流的人生态度。
宋人笔下的梅花,有“疏疏淡淡,问阿谁、堪比天真颜色”(辛弃疾)的清寂、疏落之美;也有“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陆游)的卓尔不群。这是一个梅花人格化集大成的时期,特别是范成大关于“梅以韵胜,以格高,以横斜疏瘦与老枝怪奇者为贵”的“三贵”之说完全奠定了梅的风韵、风骨、风格三方面的至高标准。在宋代关于梅的绘画作品中这“三贵”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单说南宋李唐的《策杖探梅图》。画家描绘的是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一隅的赏梅图。一位淡定的闲者正策杖驻立于村口桥头,两棵虬曲、苍劲的老梅树从他的身前身后环抱而来,似乎要遮住他头顶的苍宇。树梢上梅花数点,应该还不到梅花最盛的时候,梅枝却已展示了它俊逸、疏朗的气势和风度。不知这位白衣人在这里站立了多久,是否已有梅瓣随风落入他的衣襟或是眼前的河流?他是否每日都会来此静立,探望这两位老朋友谈谈心问声好呢?这是江南情致的小桥流水,也是画下《采薇图》《万壑松风图》这样雄壮、阳刚画卷的李唐笔下的梅树。它们是秀丽的,也是坚定有骨的,它们的枝丫在高处形成了一个世界,那是人的精气神,也是梅的风韵和浙派山水内心的火光。
《策杖探梅图》所营造的空间感很特别,看似小桥流水通往更广阔的天地,两棵梅树的围拢之姿和左侧的密实村落又形成了一个向内的、相对封闭的空间。梅树之外的河流、天空、消失的小径则又增添了隐约的延伸感。这似乎对应着观梅人的心境,他在桥这头策杖而立,是否想要跨过桥去,走出梅树的风景?还是甘于终日与这两棵梅树相对,互诉衷肠呢?在静立中梅花含苞、绽放、翩然而落,多少时日,多少季轮回,生命的相互教诲和启示,皆在人心的盘桓和领悟中完成。这是中国古人的自我修炼之术,也是宋人寄情于山水花木的初心。
这也是写下“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的李煜的梅花,是飘零中故国的影踪,是离乱中痛楚的回望。那一点点,一株株,开过了世代的更迭,它曾是美人额头上的妆饰,也是持志如心痛的抱守和安慰。它在众人心上开落,直到今天,一不留神,我们也是那个策杖桥头痴痴看梅的宋人。
(本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