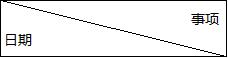某天朋友召集的聚会上,初见张永祎时我愣了一会儿,突然眼前就浮现出大片大片浓密的梧桐树,盛夏酷暑的南京中山路上,我捧着从邮局新买的杂志,沿着路牙子边闲散地走着边翻着我那时还是一个因为单纯而自信得敢于光脚穿凉鞋、清水洗脸、穿棉布裙子的职场新人那时的中山路多好啊,路上的自行车是慢的,站台上等车人的眼神宁静地望着车来的方向,路上没有悄无声息疾奔的电动车,无论妇孺皆人手一部手机在当时简直是个梦想所以,那时人们有很多时间用来等待,那时的人们习惯从书香里获得诗和远方,中山路金陵饭店边上的邮局里,永远有人在买邮票和信封,永远有人站在大号的浆糊瓶前用刷子往信封口轻轻抹着浆糊,邮局杂志柜台前也永远有人在翻着新到的杂志我就是买杂志人群中的一员张永祎的名字伴随着这些光影记忆沉淀在我曾经拥有过的时光里,他那时写影评,在我连续不断地买的《东方文化周刊》等刊物上频率出现得很高张永祎的影评写得鲜活,他的文字自带旋律,是会呼吸的生命,字里行间充满旖旎光彩,有着所有文科生都喜欢的那种充满浪漫情怀的腔调,对于读者,有着一种生生不息的吸引力,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秋思夜归人?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秋思夜归人
某天朋友召集的聚会上,初见张永祎时我愣了一会儿,突然眼前就浮现出大片大片浓密的梧桐树,盛夏酷暑的南京中山路上,我捧着从邮局新买的杂志,沿着路牙子边闲散地走着边翻着。我那时还是一个因为单纯而自信得敢于光脚穿凉鞋、清水洗脸、穿棉布裙子的职场新人。那时的中山路多好啊,路上的自行车是慢的,站台上等车人的眼神宁静地望着车来的方向,路上没有悄无声息疾奔的电动车,无论妇孺皆人手一部手机在当时简直是个梦想。所以,那时人们有很多时间用来等待,那时的人们习惯从书香里获得诗和远方,中山路金陵饭店边上的邮局里,永远有人在买邮票和信封,永远有人站在大号的浆糊瓶前用刷子往信封口轻轻抹着浆糊,邮局杂志柜台前也永远有人在翻着新到的杂志。我就是买杂志人群中的一员。张永祎的名字伴随着这些光影记忆沉淀在我曾经拥有过的时光里,他那时写影评,在我连续不断地买的《东方文化周刊》等刊物上频率出现得很高。张永祎的影评写得鲜活,他的文字自带旋律,是会呼吸的生命,字里行间充满旖旎光彩,有着所有文科生都喜欢的那种充满浪漫情怀的腔调,对于读者,有着一种生生不息的吸引力。
后来还发现,张永祎涉及的领域并非只是影评,他的兴趣非常广泛,视野非常开阔,古典的,现代的,文学的,艺术的,美学的,高大上,短平快,比比皆是,《天津社会科学》《青海社会科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新华日报》《南京日报》等多有他的作品。记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几乎成了《人民日报》的投稿“专业户”,隔三差五就会发表他的文艺评论,记得最清楚的是,1990年4月24日在文艺评论版头条刊登了他的大篇力作《文学在理念化倾向中的失落》,引起较大的震动;还有在《新华日报》发表的“《红高粱》未酿出醇香的酒”,也获得了强烈的反响。尽管后来他在报刊上重见率极高,特别是在《南京日报》上几乎周周见面,但我还是忘不了那.一棵棵枝繁叶茂粗壮的老梧桐树,工商银行那幢民国老楼朝西的墙壁上发白的阳光,邮局前绿色的邮筒,李顺昌洋服行,福昌饭店,还有散发着纸墨香的报刊,张永祎的名字与上述意象一起,成为南京城在某一个年轮中特有的符号,停留在我的记忆里。
所以等到离开上述场景若干年后,终于有机会见到真人时,他与记忆中的文字并没有什么违和,眼前的张永祎比他当年的文字更有亲和力,像是相处很久的邻居或者同事。他的笑容温和儒雅,让我想起校园里那些曾教过我的老师们。人的长相是先天的,但相貌上的表情一定是后天的,即所谓“相由心生”,张永祎的那种温儒里隐逸着他所经历的世事和所读过的书,此时的张永祎已不再是我记忆中单纯的一位喜欢文艺评论的业余作者,而是在文化评论特别是对江南小镇的研究方面的大家,甚至连专业人士都啧啧称赞,这令我不好意思喊他的职务,那样似乎太世俗了,还是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张老师”,这一喊,很契合那个从纯良年代走过来的历史况味和文人气质的典型风范。
等到有机会细细聊一些话题时,越发显示出学识对一个人胸怀和精神气度的拓展作用,谈及对江南文化的喜爱,他曾用乌兰图娅的歌词作譬:“如玉的模样,清水般的目光,一丝浅笑让我心发烫”,一见钟情,一往情深,一发不可收拾,近年来他在江南小镇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果。在面向海峡两岸发行的《东方潮》杂志上曾开设专栏,写了50个江南名镇,文辞华美、文理通达,深受港澳台等地的读者欢迎,杂志曾在台北召开读者见面会,他的江南名镇得到肯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曾因此在中央电视台的“文明之旅”栏目,做过一档“梦里水乡江南镇”的节目,与主持人刘芳菲有过近一个小时的电视访谈,通过形神情意的描述,对江南古镇和江南文化的历史轨迹和人文精神,进行了如数家珍的介绍和酣畅淋漓的诠释,有人看后评论说,他“把江南叙述得温婉而深情,杏花春雨,荷叶田田,美轮美奂,美不胜收”,而在他的家乡,那些发小们看到他在电视里侃侃而谈,挥洒自如,谈天说地,娓娓道来,当时就激动得潸然泪下。
某一天深夜,我打开视频回看了这档节目,发现他讲述的江南,讲述的小桥、流水、人家令人从内心升起一种“风景旧曾谙”的亲切感,他的演绎赋予灵性的江南更多了一份人性和生机,他的江南不仅是风景,还有站在桥上看风景的人,他的江南是周庄形如钥匙孔的双桥江南,是百姓们充满美好祈望的“心愿桥”江南,是陈逸飞的艺术江南,也是中美文化政治交流的友谊江南。他的江南是张继这样的落魄知识分子“江枫渔火对愁眠”的心灵江南,也是无锡钱氏、海宁金庸家族等文脉传家的旺族江南。张永祎之所以能将江南文化讲得如此通透,一是缘于他的博学,但凡江南经济、政治、历史、文化都能随手拈来,融会贯通;二是缘于他充满探究精神的治学态度,据说,他几乎跑遍了江南古镇,许多都是第一手资料,是他与当地居民聊天中获得的众多鲜活故事。但我认为,最重要还是他的精神品格中融合着显著的江南文化特质,他真正看透了江南,懂透了江南,悟透了江南,他的思想和他的妙笔生花就是行走在江南文化里的一道风景。他与江南,当是相互视作知音和难舍难分的伴侣。
江南,并不完全是一个地域概念。自古江南多才俊,江南是读书人的精神故乡。自古江南佳丽地,江南有着独特的审美意趣。江南多水,水体现了道家“利于万物而不争”的思想,也体现了儒家文化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情怀,而佛家思想中“珍惜现世”的“早晚复相逢”的三世观,令江南更多了一层情义与婉约。所以才有那么多的读书人奔赴江南,在江南的风里雨里、花开花落里寻找可以栖落心境的梦想。自吴王夫差起历代几任君主以举国之力开凿运河,江南的政治意义、文化意义和经济意义,更是不言自明。但江南其实也是悲情的,曾经是作为偏安文化的一个符号存在历史深处,岁月掩盖不了那声声长吁短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但张永祎更愿意发现和传播江南的柔情与美好,在他笔下徐徐展开的江南画卷,花团锦簇,绵丽不绝,“水是最灿烂的风花水月,超越了尘世的喧嚣,代表着古镇宁静的时光,几只小船停靠在岸边,是江南古镇从前以及将来最动人的风情。”他的这种认知和解读完全来自于独特的审美体察和感悟。苏州的九如巷、枫桥前的徘徊、小镇茶楼前的留连,这些都是他梦里的灵秀江南,只是这江南比他早年在电影《早春二月》里所看到的,更生活,更有温度,是可触摸和感知的江南。他所领悟到的江南,是一个紧贴时代、引领时代的江南,我读过他写江南临河边的“美人靠”,读过他写的周庄,越读心越静,读出了“水清鱼读月,花静鸟谈心 ” 的意境。他笔下的江南小镇是这个时代的一股清流,雅致地承载起了现代人的情感寄托。
张永祎身上充盈着满满的人文情怀。他崇尚中国传统文化人的精神操守,他说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人生观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他非常看重一个人的价值取向,他说许多人因为考虑物质过多,而失去了太多的机会。他既有入世的勤勉,也有出世的通达,大学毕业后,在单位的多个岗位上待过,他说每一项工作都是一种历练,都能丰富人的精神阅历和心灵层次,都能提升个人的综合素质,这些经历都值得他感念和感恩。他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思考、阅读和写作上,他说一年写十篇文章或许看不出来什么,但坚持十年会怎么样呢?那就是一百篇文章啊,重要的不是这个量,而是当你有了一百篇文章放在那里,你与那个只写了十篇文章的自己相比较,明显很不一样了,这不是十篇与一百篇文章的距离,而是在写这一百篇文章的过程中,你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和角度以及思维的深度是迥然不同的。张永祎对自己的本职工作研究很深,精益求精,毫不马虎,许多事情都希望做到极致,他非常崇尚“将心比心,以心换心”,他时常以理解人、帮助人来学做人为己任。听他这一席谈,只觉他是举重若轻,四两拨千斤,令我觉得若能做到善解人意原来也是很愉快的一件事。
许多大家都曾非常到位地评论过张永祎的写作,无论是他的文化评论,还是他的江南小镇随笔,都有一种气势和激情在其间游走,“可以将他的评论当作散文诗来读,因为那里面有一种让你也一同燃烧起来的力量!”张永祎说,他很崇尚恩师吴调公先生的写作风格,评论性的文字可以写得雍荣华贵、镂金错彩;他也非常崇拜红学家何永康教授的洒脱笔调,许多研究《红楼梦》的文字竟写得那样的气韵生动、虎虎有风!张永祎大学时读的是文学专业,而且特别喜欢中国古典美学,《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原诗》中的名句随口就来,写起文章也就不可避免地顺流而下,涌波绮丽。我曾读过他评论电视剧《琅琊榜》的文章,辞章美而不艳,如清莲浮于水上般动人心魄,隐喻美学、镜头美学等概念运用其间如同轻风吹江帆,令理性十足的文章灼灼其华、云蒸霞蔚。
有时我也会想,张永祎的思想、情感和写作的根基在哪里呢?他非常热爱阅读,从不拒绝知识,他认为到处都是学习,随时可以汲取,不管是传统阅读,还是网络阅读,只要阅读就是好事,他不认为网络阅读就是浅阅读,因为阅读的深浅,不取决于阅读的方式,而是在于阅读者本人态度和取值,一个人只要阅读时专心致志,心无旁骛,获得的感受一定不会是浮光掠影。我认为,张永祎能达到今天这个才情,跟他因阅读而获得的扎实牢固的基础不无关系,但似乎并不是全部,还有更深的原因。后来偶然读到一组他写故乡的文章,突然像一阵长风吹过,被深深惊到了。他写他故乡的亲人,写他的大姨三姨四姨,写他童年时校门口卖蚕豆的邰六爹,写他的那位名叫永莉的妹妹,写他要求严格的父亲,写在家乡照料生病的妈妈,写妻子写女儿,写他的那位总是把方便留给别人的表弟,写他小时候去过的乡上的粮管所、食品站,写他的同学聚会,写他故乡的用两块青石板搭成的老街......这一组文章,文字朴实,情感真挚,叙述冷静,并不回避人生的痛苦和世事的艰难,也没有忘记生活的健康和美好,他曾经的文辞华美依然还在,只是沉淀在字里行间的节奏里,幻化成遣词造句的稳扎、叙事的深情、人物的独特性和对故乡往昔时光的珍惜。我点着鼠标一字一句认真看完他写的故乡,我明白了,纵然世界再美艳动人,他这棵冠盖如云的大树其根仍深深扎在故乡的土壤里,他纵然写尽江南古镇的繁复的前世今生,但他却永远为故乡的哪怕一座桥哪怕一个春夏秋冬哪怕一草一木而牵扯,他永远走不出的故乡,是他写作和思想的情感来源。他温儒的笑容,他待人接物的谦和,他渴求新知的执著,他踏实勤奋的笔耕,都是源于融在血液里的故乡所给予他的一种禀赋,包容万物,信任秩序和规则,与人为善,这是土地的特质也是种子的特质更是生活在那方土地上的祖祖辈辈的特质,这些,才是他的精神底色,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底色。
任何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都不是偶然的,都有值得我们去探究的规律和学习的地方。张永祎人生之旅所显现出的读书人的智慧特别打动人,诚如曹雪芹所说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但因为他的精神底色来自于故乡与书香,因了这样的熏陶所以令他的这份“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没有圆滑与世故,仍有读书人内敛的棱角,散发出人文情怀的温馨芬芳。所以,感觉只要在脖子上围一条长长的灰色围巾,他完全就像是一位从民国走来的先生了,我的这种充满年代感的想像,可能是对往昔岁月的一种怀念,借此慰藉我们并非特别饱满的精神生活,如同我们人人都在心里藏着一个江南梦,以此抵挡光阴的侵蚀。(韩丽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