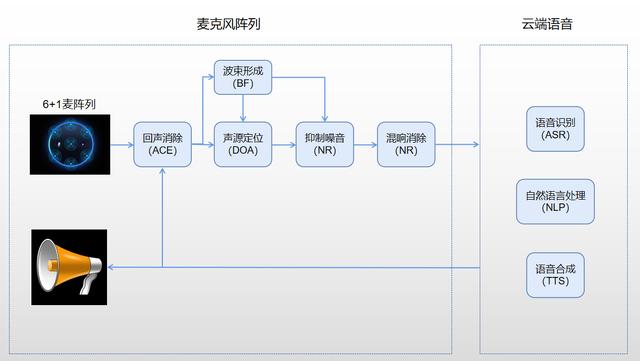所有基层剧团的演员都有一个梦想,去更大的舞台,被更多人欣赏。过去多年,这个大舞台指的是省城、北京或上海,是那里的大剧场。因为在县城,剧场并不景气,也不一定有人来。
但2022年,一些地方剧团突然找到了新的舞台。他们在抖音上拍视频,做直播,有时候几十万人同时共享这个新舞台。这不仅带来了流量,改变了很多演员的物质生活,也让地方戏重新走入大众的视野。
这其中,又以黄梅戏最为典型,也走得最远。

被遗忘的剧团
2022年的最后几天,整个潜山市都是雾霾天,显得这里很冷清。这是安徽省安庆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因为境内有5A级风景名胜区-天柱山,前两年就撤县设市了,这是一个年轻的城市。一年前,潜山市又通了高铁,来这里旅游和兴业的就更多了。
安庆是黄梅戏之乡,这跟下辖的所有县(市)都有黄梅戏剧团有很大的关系,其中,潜山市黄梅戏剧团在基层院团中当属佼佼者,因为他们曾代表安徽省去北京演出。
剧团的团长名叫汪卫国,他1995年就到了这里,此后再也没离开过。汪卫国看起来很严肃,言辞不多。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有忧患意识的人,言谈中,他说的最多的词语就是希望,希望能招到更多优秀的演员,希望有更多的戏曲从业者能坚守这块阵地,希望有更多的保障来支撑剧团稳步发展。

过去三年,潜山市的疫情一直控制得很好,2022年12月份之前,这里甚至没出现过一例新冠病毒感染者。
剧团原本计划在11月前往合肥保利大剧院演出大型原创剧目《榴花不开盼哥回》。但因为疫情防控,延期到12月底。意外的是,疫情防控突然放开,由于感染人数激增,演出最终还是被取消了。
这几乎是剧团这三年的生存缩影。2020年之后,剧团几乎没有接过商业演出,也没有走出潜山之外的地方。除了送戏下乡,他们也没有机会把好的剧目传递出去。如果是以前,剧团每年至少都有二、三十场的商演。
下乡演出其实还是蛮辛苦的,每天要演出两场。下午演出刚结束,就要赶往另一个村。收台、装台,男女演(职)员齐上阵。有时候,舞台刚搭建好,就碰到下雨,剧团又得匆匆收好设备,然后原路返回县城,或者等着雨停继续演出。团长说,这种演出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了,长时间都这样,累也就不累了。
但是最近几年,下乡演出时的观众也在越变越少。因为疫情防控,因为村里只剩留守老人和小孩,所以,没有观众的演出,对演员其实也是一种伤害。
在剧场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演员们的梦想还是未变,都希望挑大梁。汪卫国说,如果剧团招来了一个新演员,天天让他跑龙套,对方肯定也不舒服。但作为团长,想把最好的阵容展示给观众,也是非常明智的。年轻演员想迅速成长,也必须从龙套开始锻炼。
下乡久了,就想去大城市、大剧场演出,这种感觉特别强烈。因为简陋的舞台和稀疏的观众是很难让一个演员能全神贯注的投入表演。大舞台是所有演员的梦想。
团里的年轻演员们提议,要不试试在抖音直播?他们说,似乎也没有哪一个平台比抖音的传播力更强。换句话说,这会不会是一个新的舞台?

2022年5月,他们正式开始直播,随后整整三个月,潜山剧团一共直播了八十多场。人气最高的一次,几十万人次观看,同时在线有6000多人。看短视频的观众是越来越多,对剧团拍摄的小视频给予了赞许,同时也提出了不少宝贵的建议,因为这样,抖音直播一直开展得很顺利。
每年夏天都是剧团的演出淡季。由于天气太热,他们无法下乡进行演出。抖音直播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给演员们练了功,也增补了演员们的收入。通过直播,传播了黄梅戏,提升了潜山剧团的名气。
为了直播,他们可是下了血本,改造直播间,采购设备,他们花了近二十万元。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尤其是对于一个收入不怎么好的基层院团。
等待不再漫长
在潜山黄梅戏剧团,负责直播的是一个32岁的年轻人,名叫胡勇。
胡勇是个乐天、脾气好的人。他和妻子五年前才加入这个剧团。他说他虽然很早就入行了,但演技在团里并不是最拔尖的。不过,他对剧团的任何事都感兴趣,愿意琢磨。这可能是汪卫国让他负责运营抖音的原因。
对胡勇来说,抖音并不陌生,他常在上面看新闻,有时也会刷一些搞笑视频。工作上遇到不太懂的事情,例如一个文件该怎么排版,他也习惯打开抖音,搜索上面的实时教程。但对于做直播,胡勇却是陌生的。
他请教了剧团的几个年轻女演员。几年前,她们就做过个人直播,最早收入只有一百多块,但现在每一场也能收到几百块打赏。她们很高兴剧团也能做直播,如果剧团变得更知名,演员们也能跟着沾光。因此在剧团直播之前,他们先发了半个月的短视频,做预热。
5月1号早上八点半,胡勇和同事们开始准备,一块讨论表演哪些节目,之间怎么穿插,如何应对突发性情况。首场直播,进行了三个多小时。形式很简单,演员们在镜头前,以单唱或对唱的形式唱一些戏曲片段。
第一场直播结束,演员们看了后台的数据,很激动,结果远超他们的预期。胡勇用剧场来举例,他们表演过最大的剧场,观众坐满了也就一千多人。但是直播当晚,在线观看的人数就有1000多人。他说:“我们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几场直播之后,他们很快做了调整。如果用手机直播,演员要离镜头很近。但相机实现了焦段自由,可以呈现更多的画面,演员们有了专门的小舞台。他们不再需要提词板,电视上滚动着台词,还分成了三个屏幕,用来看实时表演状态、粉丝留言、最新数据。
夏天那段时间,胡勇和同事们每周都会拿出一天,专门来拍短视频。他们通常清晨出门,去有古街、古建筑的景区,等待好的光线。有时候,游客见他们拍短视频,拍出来的花絮发在抖音比正片还要火。一天下来,他们可以拍八个短视频,更多时候都是等待,等待一个好的光线,琢磨一个更好的构图。
胡勇很喜欢这样的集体生活。他是剧团为数不多的异乡人,来自邻近的湖北黄梅县。他和黄梅戏结缘,与其说是爱好,不如说是少年的叛逆。
胡勇的堂哥在黄梅县剧团工作。2004年,剧团不景气,团长决定带着演员们下海,组建一个民营班子去福建。胡勇那时14岁,不想读书了,虽然他并不了解黄梅戏,但很渴望早一点谋生,见见外面的世界。他和十多个同龄人集训了三个月,成为剧团学徒。最开始五年,他只能拿几百块生活费。19岁才算出道,每个月工资有两千多元,之后涨到四千,收入远高于其他的同龄人,也高于在国有剧团工作的演员。但好景不长,由于市场不景气和管理问题,剧团在2012年就解散了。
胡勇后来说,那时候很开心,虽然没存下什么钱,但他和一起进去的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那几年他们都在一起学习、上台演出、吃住,胡闹花钱。那时,剧团的工作很忙,常有村子的宗祠、庙会请他们演出。一行人坐着大巴车,请的专职厨师也跟着去,席地烧饭。有时候去的地方太远,当晚回不来,演员们就在舞台旁边,找个角落,打个地铺睡一宿。
这样的生活,看起来动荡,但又很封闭。在福建剧团里,胡勇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剧团解散后,两个人又去了一个景区当黄梅戏演员。直到2016年,孩子出生,胡勇回到了黄梅县。
很长一段时间,他不知道该找什么工作。他厌倦了很漂泊的日子,不再想继续这样。2018年,同在福建学黄梅戏的朋友联系他,说潜山剧团在招人,可以去面试一下。
现在,胡勇在潜山安了家,买了房。他说,每平米7000元的房价,要比湖北老家的县城贵不少。但他已经熟悉这个地方,跟这方水土建立了很深的情感。
胡勇得出一个结论:只要进了剧团,一辈子可能就在这个行当了。这些年轻人之所以留在县城,不去大城市生活,是因为心中有一种更大的渴望。他们考虑更多的是演员生涯,渴望上更大的舞台。演更重要的角色。即便离开县城,也是因为想去一个更好、更有艺术氛围的剧团。
一般来说,戏曲演员的黄金年龄从三十岁开始。这意味着要等很久,练习很多个日夜,等着上场的那一天。
但现在,抖音直播也许缩短了上场前的漫长等待。
胡勇说,在线下的舞台演出,一个演员即便演了很多场戏,也很可能不被观众熟知。但在直播、短视频里,演员的表演留下了影像,很有可能一句唱腔、一个不经意的表情,就被手机另一端的人捕捉到了。
舞台变了
年轻一代演员也许很难理解团长的焦虑,这很正常,因为没有换位思考。在演员们看来,汪团长是个低调、严谨、认真、较劲的人。他还是一个戏痴,常常一个人在办公室听戏、唱戏,跟同事们处得非常融洽。
但在抖音直播的那段时间,汪卫国常常担忧——如果直播休息几天,观众还会再来看吗?他有时会督促胡勇,希望直播不要停。
他其实一直鼓励演员们,多做个人戏曲直播。因为做团播的时候,要考虑到剧团形象,除了唱戏,你不能随便说话。但如果私播,可以更自由一些。
汪卫国的戏曲之路,可能跟很多戏曲工作者是一样的,环境和耳濡目染。
汪卫国出生在潜山市的一个农村。小时候,他记忆犹新,夏天纳凉的时候,村里人就聚集在一起,聊天、讲故事,唱黄梅戏。他父亲是村子里唱的最好的戏迷,农闲时,父老乡亲就围在父亲身旁,乐此不疲的享受着“精神大餐”,他父亲还收藏了不少油印、手抄的剧本,那个年代,这样的“戏痴”是很罕见的,从某种程度来说,对汪卫国走上艺术之路有直接的影响。
八十年代初,剧团下乡演出很少。人们获取黄梅戏途径更多的是半导体和露天电影。《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汪卫国说,父亲带他看了无数遍。当然,还有越剧的《追鱼》,豫剧的《穆桂英大战洪州》,曲剧的《卷席筒》,评剧的《花为媒》,可以说,戏曲电影在那个年代是高产,也是最受欢迎的。
初二那年,黄梅戏电视剧《严凤英》正热播。这是一部传记式电视剧,讲述了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的坎坷一生。这部剧的影响对汪卫国来说是很大的,懵懂的少年此时正热血澎湃,立志想成为一名黄梅戏演员,但农村地区消息闭塞,他抱着试试看的心里给黄梅戏学校寄去了一份信,不久就收到了招生简章,于是在90年,他圆梦了,被安徽黄梅戏学校表演班录取。
毕业进入剧团工作后,汪卫国才发现,剧团几乎无戏可演,每年就象征性演十多场。剧场的主营业务,变成了录像厅,卖电影票。每周,演员们都过来值班,当服务员,帮忙卖票和检票。第一个月工资,汪卫国拿了93块,当时团长也就拿130块。而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薪水大约有两、三百块,还能领到毛巾、肥皂这样的生活福利。
团长那时也不会安排新戏,因为做一个原创剧,意味着要请编剧、导演,制造布景、舞台美术、服装,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所有人都等着领财政工资,对于演员这个职业来说,这几乎是一种混日子的生活。
没戏可唱,为了生计,演员们只能靠副业来养活自己。有十几年时间,汪卫国干过很多营生。他开过宵夜摊,卖过衣服、也卖过鱼和茶叶。
2010年,剧团开始“转企改制”。按照企业进行运营,打破“大锅饭”制度,保障优秀的同志基本权益,剧团发展迎来曙光。
当然,改革是阵痛的,有过渡期。改革初的几年,同志们工资都拿的不多,团长为了规范管理,彻底断了大家搞副业的念头。直到2015年,剧团有了每年200场公益演出的任务,待遇才跟着慢慢变好。
汪卫国说,这个行业一直是“清水衙门”,福利保障很低。如果演员对钱很看重,就不要踏入这一行。
但汪卫国还是有很强的忧患意识。他说,黄梅戏过去很流行,除了旋律好听外,也和题材有关。黄梅戏不讲帝王将相,更多是唱儿女情长,来自茶楼酒肆、田间地头的故事,很接地气、富有生活气息。不过,现在电视台很少播黄梅戏,而且看电视的人也越来越少。

他很担忧黄梅戏的未来。但是,他也觉得抖音是一个机会,就像过去电视广播影响过他一样,直播与短视频,也可能会让更多年轻人了解黄梅戏,喜欢上黄梅戏。
汪卫国的微信名,叫做“戏说天下”。他说他一辈子都会留在剧团。他解释说,在基层剧团,虽说条件差一些,但可以获取更多演出大戏的机会,能磨炼自己。
另一种活法
2022年12月30日,潜山剧团正在排练《五女拜寿》。这又是个雾霾天,剧场显得空旷、灰暗,演员们从左侧的小巷进来。临街的售票厅已经关闭,承租给了手机维修、金银珠宝、桃酥大王等商铺。这里很久没有出现过观众,也没有过正式的演出。
这个剧场地处县城老城区最繁华的地段,在十字路口交汇处。东侧是一栋竣工于1995年的供电局生产大楼,对面的中天商厦也不再营业。几年前,剧场被认定为危房,不能对公众开放。
剧场曾有过辉煌的历史。1957年建成后,有两层楼,有长木靠椅1000多个。每到上演新戏,或是节假日时,总会满座。没买到票的人,只能等待着有谁来临时退票。
现在,汪卫国看着几乎废弃的剧场,说希望可以恢复剧场原貌,不一定要成为真的舞台,而是让人们来参观,这里也代表了潜山过去的历史。
剧场如今只保留了几十个座位,后排堆满了不少演出道具,那是剧团演出时要用的布景,老剧场,已然成了仓库和对演员临时排练的场所。

但作为团长,汪卫国考虑的东西更多。有人建议,剧团可以试试直播带货。但他总觉得不太可行,别人来看你直播,是来欣赏你的艺术,如果带货,戏迷们会不会远离你呢。
但他也觉得,卖票看演出,几乎成为了历史。在他年轻时,人们还会托关系去买一张黄梅戏演出票,但随着港台文化、VCD、电视、智能手机的冲击,很少有人再有兴趣进入剧场,花时间去听传统戏曲。
现在,这个剧场每年就象征性的演十几场戏,此后又处于空闲的状态。不只是潜山,整个安庆地区的小剧场可能都是如此。
也许这并不是剧场的新与旧、大与小的问题,而是人们的习惯改变了。
汪卫国说,别说卖票了,你免费送给别人,他也不一定愿意走进来。不只是黄梅戏,京剧、越剧等传统戏剧的舞台市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但最重要的是先活下来,这样文化才能继续传播。
直播,也许是活下来的一种方式。每个演员都有了自己展示的空间。每个人都有机会在镜头前,独唱自己拿手的戏曲选段。直播间的观众喜欢一个演员,不一定代表他的专业水平很高,有可能只是他演出的风格、神情,得到了青睐。
比起传统的舞台,在抖音上,每个人似乎都被放大了。这意味着无论你是剧团的主演,还是凤尾,你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观众。文/李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