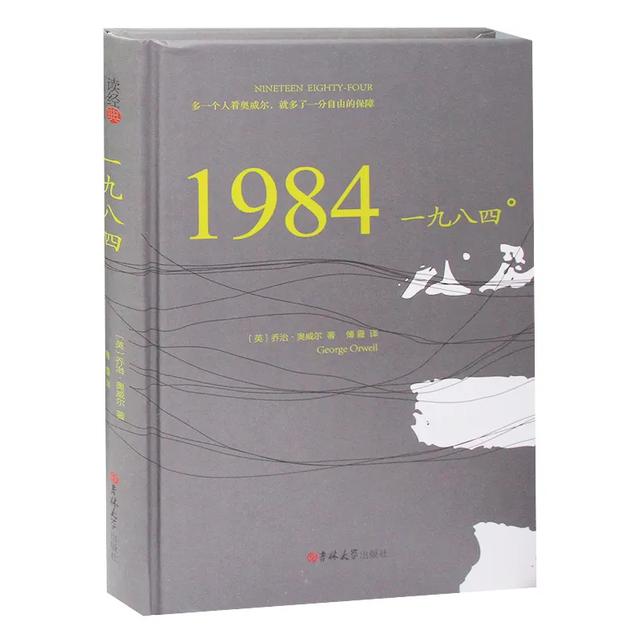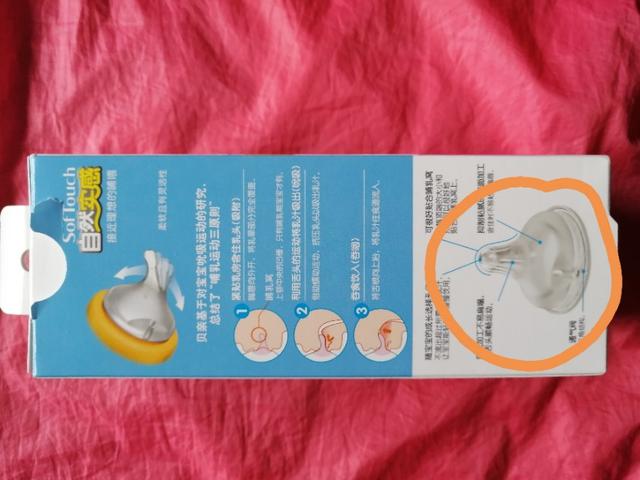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35期,原文标题《<奥威尔书信集>:道路的意义》,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伟大的作家常常反过来被自己的作品定义,奥威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九八四》让他永远留存于文学史,但我们却很少了解他真实生动的另一面。如果你读奥威尔的书信,就会发现他其实还是一个唠叨的杂货店主,一个细心的丈夫,他关心鸡蛋价格和公羊配种、土豆的收成,也关心饲料和厕纸品牌。
记者/张从志

乔治·奥威尔(视觉中国供图)
业余流浪汉
1920年8月,乔治·奥威尔给自己在伊顿公学的同学写了一封信,心情激动地讲述了自己“头一回做业余流浪汉”的经历。这次旅途是他从伊顿军官训练团训练结束后返回,错过了列车,而身上除去买车票的钱只剩7.5便士,这点钱只够住一晚旅馆或吃一顿饱饭,他选择了后者,夜里就只能睡到了农夫的庄稼地里。信的结尾,奥威尔写道:“我很为自己的这次历险而自豪,可是我再也不愿重温这种经历了。”
写信的时候,奥威尔17岁,他可能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不仅没有遵守信中的“诺言”,反而不断“重温”着流浪和冒险的经历。
奥威尔是通过奖学金进入伊顿公学这所英国最有名的贵族学校的,他是70个“国王的学者”之一,住在校本部。但毕业后,家庭经济条件不足以支持奥威尔去上大学,他只好去了缅甸,做了五年殖民警察。奥威尔不堪忍受这份让他心怀罪恶的工作,回国休假时决定了辞职。
奥威尔本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1903年出生于印度孟加拉邦,父亲是英国在印度殖民地的一个低级文官。奥威尔自称家庭属于“中产阶级偏下,即没有钱的中产家庭”。没钱,的确困扰了奥威尔一生,直到去世前几年,他才稍稍从经济压力中喘过气来。
1928年从缅甸回来后,奥威尔开始写作,也开始了另一种“流浪汉”的生活。从巴黎辗转伦敦,奥威尔混迹在社会底层,做过厨房的洗碗工,担任过家庭教师,还干过啤酒花采摘工、书店兼职店员。他穿着破烂的衣裳,在贫民窟居住,和工人、乞丐混在一起,还和流浪汉一同流浪。但因为操着一口伦敦上流阶层的口音,奥威尔很难真正融入底层的生活。据说,他曾经去挑衅警察以便进监狱跟穷人一起过圣诞节,但警察听出他的口音后放了他一马。
可奥威尔也无法进入上流社会的圈子。当他出身显赫的同学们纷纷开始进入文学和艺术的殿堂时,奥威尔还在给报纸杂志写着不入流的书评。1938年,在给伊顿时期的同学的信中,奥威尔如此写道:“在学校的时候你各个方面的表现都比我成功得多,我的地位是复杂的,实际上这是受我远不如我周围的那些同学有钱这一事实支配的。”
《道路、意义与生命:乔治·奥威尔书信集》(以下简称《书信集》)选译了近300篇书信,既有上面这种写给同学和朋友的,也有给亲人的,还有大量是和出版商、经纪人以及报刊编辑的通信。
在巴黎和伦敦流浪的经历后来被奥威尔写成了《巴黎伦敦落魄记》,1933年出版时,他首次使用乔治·奥威尔这个笔名。后来在给新结识的朋友和编辑的信中,他总会在信的末尾提醒对方,自己是用乔治·奥威尔这个笔名写作的。
唠叨的杂货店店主
在写作生涯的前八年里,奥威尔几乎每一年都出了一本书,还撰写了大量专栏和评论,但在平庸的写作和挣更多钱之间,奥威尔常常陷入矛盾。成名后的他曾承认,当年有不少作品都是卖文糊口的文字,“原本不应该出版的”。
即便这样,写作也无法保障他的生活来源,特别是在和爱琳结婚后,更加捉襟见肘。他们迁居到赫特福德郡一个叫沃灵顿的小村里,因为此处安静且租金低廉。奥威尔一边写作,一边开起了杂货店,卖些糖果和黄油之类的东西,每天下午营业,赚的钱不多,但可以付上房租。
在沃灵顿的杂货店里,奥威尔夫妇住了好几年。其间,奥威尔作为志愿军去西班牙参加内战时离开过一阵,但他在战场上被子弹射穿喉咙,没多久就回了英国。1938年,奥威尔的肺结核旧疾复发,寒冬到来前,他去了法属摩洛哥的马拉喀什疗养。在摩洛哥期间,奥威尔还总惦记着沃灵顿村的杂货店,隔一段时间就给帮他照理事务的好友杰克·考曼写信。在信里,奥威尔像个絮絮叨叨的小农民,计算着新养的母鸡什么时候下蛋、鸡蛋留到什么时候出售获利更多、买什么样的鸡饲料最合算,还有家里的公羊什么时候该配种了,甚至连厕所要用什么牌子的手纸,奥威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而谈完家长里短,他又会毫不突兀地论起时局,再痛批一番不讨他喜欢的政治家和媒体。
去摩洛哥疗养费用不菲,还是一个仰慕者通过奥威尔的好友匿名资助他的,300英镑,奥威尔一直把这笔钱当作借款,在后来给不同朋友的信里都提及过,但直到1946年,他才有能力给好友寄去150英镑作为第一笔还款。彼时,《动物农场》已经出版并风靡各国,给他带来了丰厚的版税,他的经济状况好转。在这封信里,奥威尔说,自己最遗憾的是,爱琳没能活着看到《动物农场》的出版,“她特别喜欢这本书,甚至还帮助我进行了策划”。
爱琳死在了头年的一场医疗事故当中,那原本是一台“被认为没什么危险”的手术。当时奥威尔正作为随军记者在法国采访,见证纳粹最后的溃败。奥威尔回去后,在爱琳的信件中发现了一封她去世前一个小时还在写的信,“很明显她是希望从手术中苏醒过来以后再接着写下去的”。
“我认为它说出来应该说的话”
奥威尔在1944年2月便完成了《动物农场》的手稿,但它的出版过程几经波折。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奥威尔的签约出版商,以及英美多家大出版社都拒绝出版这本以动物寓言形式来隐喻政治的小说。在给一个报纸编辑的信中,奥威尔对此意味深长地说:“我只有42岁,我能够记得过去说拥护俄国的话就像现在说反对俄国的话一样危险的年代。”
屡屡受挫后,奥威尔告诉自己的经纪人,如果实在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他就去找一个小出版社把书印出来——这意味着他可能不会有什么版税收入——“我认为它说出来应该说的话,尽管它不符合当下的潮流”。
等到1945年8月,“二战”临近尾声,世界局势悄然变化,《动物农场》终于合时宜了,才在英国得以出版。也是在这时,奥威尔开始动笔酝酿已久的那本小说——《一九八四》。写一本反乌托邦小说的念头,是奥威尔在1944年2月给一个俄裔学者的信里首次提到的,他还说,自己一直坚持做着相关的笔记。
在后来的一些信里,奥威尔讲述了写作《一九 八四》的动机,“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奥威尔几乎是在病床上完成的《一九八四》,到1947年,他的肺病恶化,开始长期住院,但只要恢复了体力,奥威尔就继续写作,直到1948年,小说完成。奥威尔把这个年份的后两位数字颠倒,给小说取名为《一九八四》。这本书几乎耗尽了奥威尔所有的生命力,第二年年初,奥威尔病情加重,转入了伦敦大学学院医院治疗。
在《书信集》收入的最后一封信里,奥威尔在病床上感谢友人寄来的蜜饯和茶叶,还说自己身体恢复得相当不错,胃口也比以前好多了。但两个多月后,1950年1月12日,奥威尔转院去瑞士疗养,登机前突然大量吐血,生命结束在了47岁。

《道路、意义与生命:乔治·奥威尔书信集》
作者:[英]乔治·奥威尔
译者:甘险峰
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