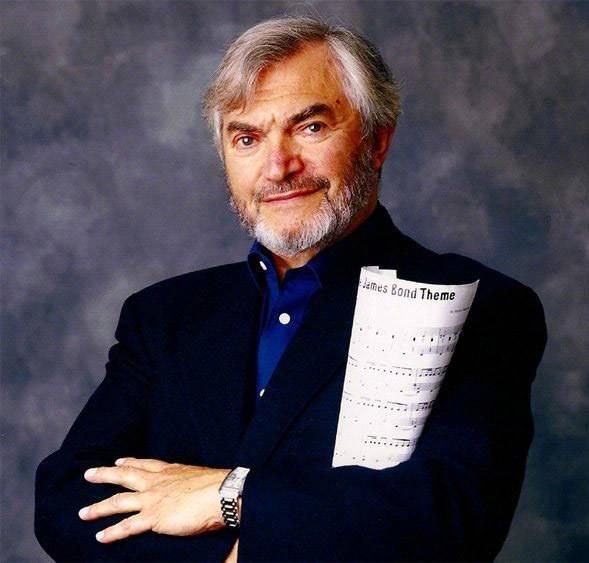第四章 我的天才梦(文学之梦)[65]
十二、艺术准备
我是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66]
在一个推崇谦恭自抑品德的国度里,上述这样的自我表白是很容易被视为狂妄的。而这段话出自张爱玲之口,人们却不会指责她为“狂妄”,因为人们都承认她是一个品位极高、文学创造力极强的才女。
天才并不一定是全才,很可能只是一个在某一方面超群的人。人与人有先天的不同,更有后天的不同。天才们把个人的志趣、才华和刻苦努力融为一体,专心致力于自己所感兴趣的和所擅长的,便可能获得非凡的成就。
现代中国的文坛艺海中星河灿烂,贝珠夺目,涌现过无数风流人物。由于时代风云变幻无穷,政治势力强弱多变,阅读对象庞杂不一,因此每一次浪潮都会淘没一些作家,涌现一批新人。有一些作家因生逢其时、时代感召而写出一时为人称道之作,但因先天不足,文学修养有限,终将被人们遗忘。针对这一现象,20世纪末一位杰出而早逝的作家曾深刻而犀利地指出:“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学秩序是彻底颠倒了的: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名声,一流的作品却默默无闻。最让人痛心的是,最好的作品并没有写出来。”[67]这是个令人感慨的表述,但我们不必为此感到尴尬。因为当代人评当代文学,偏见不可避免,何况一百年历史太短太短。中外文学史一再昭明,真正经得住历史考验的传世之作,必定出自成名前有坚实的生活准备和文学修养的优秀作家之手。张爱玲正是其中之一。因此,在我们介绍她童年少年的经历后还要专门谈谈她的文学准备。
天性聪颖、记忆敏捷、阅读广泛、勤于思考是优秀作家的必要条件。爱玲三岁的时候,就会背诵不少唐诗宋词。稍大一些,家里曾给她和弟弟请过私塾先生,她虽不甚喜欢,但从中获取了初步的阅读能力和粗浅的古典文学知识。表妹黄家瑞对她的评价是:“不爱说话,走路飘飘的,大伙儿在玩的时候,她面前不是一本书,就是一张画纸,给人画画哩!”[68]
在少年阶段求学求知的道路上,母亲是一个努力而持久的老师。作为中国较早的留学生,母亲的眼光是西式的,一心一意要把女儿培养为一个懂得美术和音乐的淑女。从形式上看,她没有获得太大的成功。这些东西没有成为张爱玲人生道路上的装饰点缀品。但从内容上来说,使她较早接触了西方文化艺术,丰富了她的心灵。但张爱玲认为母亲的教育是失败的,她自己并没有顺从地学过多长时间。对她来说,收获最大的是一种自娱式的学习方式。在没有家庭温暖的日子里,这是她的主要方式。它既是求知,又是逃避。
自娱的方式就是随心所欲的、毫无硬性的外部规定的学习,无论是看电影、听音乐,还是读书、习画,兴之所至,一切以兴趣为大,不太在乎读的是否是名著,听的是否是名曲。偶尔兴致大发,也画上几笔,唱上几句,写上几段。这种方式,培养不出科学家,但可能培养出文学家艺术家。从人才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相当有效的学习方式,尤其有益于成年之后从事文学艺术和哲学这些个性体验极强的精神劳动的人。现代心理学证明,人记忆最深的东西是他最感兴趣的东西。自娱式的优点正在这里。
有一段时期她迷上了绘画。她不攻山水,专画人物。简单的几笔勾勒,颇有神韵,富有个性。不同国籍和身份的人物,如中国人、欧洲人、美男子、洋太太、舞女、疯狂的艺术家、房东等,尽收笔底。不同性格的人物,如浅薄、做作、笨拙、横蛮、奴性、听话、刁泼、可怜等,栩栩如生。散文集《流言》中就收了部分画作当插页。她生平第一次赚钱,是中学时代的一幅漫画,投给上海的英文报纸《大美晚报》,得了五元稿费。母亲要她留着钞票做纪念,或者买本书,但她觉得钱就是钱,跑到商店买了支小号的唇膏。如果她后来不写小说,专攻绘画,也许会成为一个出色的人物画家。
艺术的门类是相通的。写小说与画人物同样需要作者对人物命运的深刻理解和对人生现实的精细观察。习画的过程同时也是培养观察能力的过程。如果绘画能力是未来小说家张爱玲的一只翅膀的话,那么对音乐的理解力是她的又一只有力的翅膀。
9岁的时候,看了一部描写穷困画家潦倒一生的影片以后,她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69]有一段时期,她学弹钢琴,母亲对她说,既然是一生一世的事,第一要知道怎样爱惜你的琴,叫她每天的第一个功课就是用绒布去擦拭琴上的灰尘。她很喜欢姑姑弹奏钢琴和母亲伴唱时的氛围和情调,多次羡慕地说:“真羡慕啊,我要弹得这么好就好了。”有一段时间,跟一个白俄女人学钢琴,每天有用人送她到老师家去学习,一周一次。老师夸奖她的时候蓝色的大眼睛充满泪水,抱着她的头吻她,张爱玲会客气地微笑,隔一会儿就悄悄地把老师的吻痕给擦掉。跟着这位钢琴老师学了几年后,父亲认为学费太贵,她的钢琴生涯就终止了。
也许有这个未完成态的学习生活,她声称不太喜欢音乐,口头上的理由是“一切音乐都是悲哀的”。[70]但她的音乐修养是第一流的。她曾有专文谈音乐,文中谈及外国名曲,如数家珍。对每一支曲子的感受别致新奇而又真切服人,恐怕专门的音乐工作者也要对其理解体悟音乐的能力赞叹不已甚至甘拜下风。比如她对不同乐器的描绘:水一般流着的小提琴,仿佛流去了人生紧贴着的一切东西;胡琴虽然苍凉,流去了又流回到人间;大规模的交响乐由于有一定的程序,犹如有计划的阴谋。对不同风格的音乐,她有着切实的把握:如火如荼的南美洲的曲子、夏威夷琤琤瑽瑽的吉他、干净的苏格兰民歌、像赌气的大鼓书、软性刺激的弹词。她喜欢老实恳切的申曲,平实单纯而又嘈杂仓皇,“至死也还是有人间味的”。[71]
“人间味”是她取舍艺术的标准,因此她对中外的通俗流行歌曲也爱听爱唱。她最喜欢的古典音乐家是德国的巴赫,也只为这可爱的人间味。巴赫的世界在她看来笨重凝固而又得心应手。她把巴赫的曲子幻化为一幅美丽的图画:小木屋墙上的挂钟嘀嗒作响,木碗里飘出羊奶的腥香,女人在牵着裙子请安,绿草原上有思想着的牛羊与没有思想的白云彩,那里的喜悦也是沉甸甸的。
爱玲的小说世界也是“笨重凝固而又得心应手”的世界,充满了苍凉和繁复,显然也得力于这种超凡的理解力。对于颜色、声音、气味她向来是敏感的。
爱玲还十分喜欢看电影。她当时订的杂志以电影方面为多,包括美国的Movie star、Screen play等。在她的床头,摆满了小说和电影杂志。三四十年代美国明星主演的电影,她都爱看。如主演过《大饭店》《安娜·卡列尼娜》《茶花女》的葛蕾泰·嘉宝,主演过《女人女人》《红衫泪痕》并获第八届、十一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蓓蒂·黛维丝,主演过《欲海情魔》等片并获第十八届奥斯卡奖的琼·克劳馥,因成功主演《一夜风流》而获第七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的克拉克·盖博,以及加利·古柏、秀兰·邓波儿、费雯·丽等奥斯卡明星,都是爱玲所喜爱的演员。在上海、香港期间,对他们的片子,她几乎是每片必看。她欣赏嘉宝的出色演技,也对她的神秘身世十分好奇。盖博和费雯·丽主演的《乱世佳人》更令她津津乐道。中国影星如阮玲玉、谈瑛、陈燕燕、顾兰君、上官云珠、蒋天流、石挥、蓝马、赵丹等的作品,她也很少漏过观赏的机会。弟弟张子静曾有一段生动回忆: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和她到杭州去玩,住在后母娘家的老宅里,亲戚朋友很多。刚到的第二天,她就从报纸广告看到谈瑛主演的电影正在上海某家电影院上映,立刻就说要赶回上海去看。一干亲戚朋友怎样拦也拦不住,我只好陪她坐火车回上海,直奔那家电影院,连看两场。迷电影迷到这样的程度,可说是很少见的。但这也说明我姊姊与常人不同的特殊性格。对于天才梦的追寻,她一向就是这样执着的。[72]
当然,对于文学她更为钟情。小时候她对外国童话和《西游记》爱不释手,稍大一些涉猎更广。她家有读书好文的家传。祖父张佩纶“少工骈俪文,才思敏捷,下笔千言”。赋闲后,大量购书读书,有文集印行。父亲虽未干什么伟业,但常泡在书房中消磨时光。张爱玲这样形容他:“我父亲一辈子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沉默着走了没两三丈远,又开始背另一篇。听不出是古文、时文还是奏折,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我听着觉得心酸,因为没有用处。”[73]他对古近代的历史有丰富的知识。爱玲常在他书房中找书来读。张廷重大约也是个“读书无禁区”论者,对涉世不深的女儿读《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等作品从不横加干涉。他曾经破例给女儿四块钱,让她去买多卷本的《醒世姻缘传》,让女儿在他的书桌前读《胡适文存》。有一次寒假,张爱玲模仿报纸副刊的样式,编了一张家庭副刊,内容是自家琐事杂闻,版面图文并茂,都出自一人之手,张廷重见了十分高兴,总将它展示给上门的亲友们看,得意地说道,这是小煐做的报纸副刊。他这种自由放任的态度,对张爱玲培养广博的阅读兴趣、独立思考、早熟早慧,肯定是有积极作用的。
黄逸梵订有不少小报,也购买了很多新文学书籍,长大成人后的爱玲还记得母亲当年坐在马桶上读老舍《二马》时放声大笑的趣态。张爱玲贪读知识的年纪,正是新文学诞生了十多年并取得较丰硕成就的时代,新文学不仅确立了自己的“正宗”地位,而且在各种文体内部涌现了大家,他们无疑也是张爱玲的文学泉源。对鲁迅、老舍、曹禺、穆时英、张恨水、沈从文这些名家的作品,她读得津津有味。对文人们不屑一顾的小报她也很有兴趣,她喜欢小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大众性。
她喜爱的古近代文学中,下列作家及作品是不得不提的:唐诗、李清照词、《金瓶梅》《红楼梦》《海上花列传》《歇浦潮》《老残游记》《醒世姻缘》《泪珠缘》《广陵潮》等。也许因为个人经历的关系,近代小说她读得特别多。而她最熟悉最推崇的是《红楼梦》,其次是《金瓶梅》。这两部作品对她后来的创作影响很大。
在天津的时候她就读过萧伯纳的《心碎的屋》,后来读过他的《圣女贞德》和林纾翻译的小说。上大学后,她对外国文学尤其是现代英国文学的兴趣增加了。如幽默多讽的伯纳德·萧、长于科幻故事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政治态度偏激的奥尔德斯·里奥纳德·赫胥黎(《天演论》作者之孙子)、擅长心理分析的德·赫·劳伦斯,都是她读得很多的作家,而她最喜爱的莫过于威廉·萨默塞特·毛姆[74]。毛姆对侨居他国的英格兰人的刻画,对中产阶级的讽刺,对异地风情的描绘使她感服崇拜,以至于在爱玲最初的香港故事中也有毛姆的风味。她后来还提到的作家有:狄更斯、王尔德、托尔斯泰、莎士比亚、拜仁、密契纳等。“张爱玲所接触的外国文学主要以英国和美国居多,此外还有俄国、法国、日本、挪威、比利时、爱尔兰等国的作家作品。这与‘五四’以后中国对外国文学的大量译介、张爱玲的家庭背景与教育经历、所学外语为英语、早年在教会学校就读后来在香港求学以及漂泊海外定居美国的人生历程相关。当然,更与张爱玲个人对外国作家作品的偏好密不可分。而在英国和美国文学中,张爱玲则又更多地倾向于前者,如果说,从整体上而言,张爱玲对美国文学的接触主要是通过翻译,如对爱默生、华盛顿·欧文、海明威等作家作品,那么张爱玲对英国文学的接触,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自觉的文学兴趣选择。”[75]
对各类艺术的良好修养,对中外文学的广闻博收,是一个优秀作家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这本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人们常常遗憾地发现,对于中国现代作家来说,并不是每个人都轻而易举地拥有这些条件的。张爱玲是一个富足的占有者、掘金者,惟其如此,她一登上文坛便出手不凡,才惊四座。
十三、“生来就会写小说”
张爱玲还有一个起笔甚早、时间甚长的试笔阶段,这对她后来正式以作家为职业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她自称生来就会写小说。七岁时便写下了第一篇作品,写了一个姓云的小康之家,媳妇叫月娥,小姑子叫凤娥。凤娥趁兄长外出之机设计陷害嫂子。七岁的故事便是一个世态炎凉的凡人悲剧,与同龄人在母爱、童真、自然美中沉溺正酣相比,她幼小的心灵是多么沉重,令人不忍多想。这是一篇未完成之作,写作的时候,遇到不会写的字,她就去问厨子。
八岁那年,她又构思过一篇题为“快乐村”的小说。快乐村的人是一个能征善战的高原民族,因征服苗人有功,受皇帝特许免征赋税,享有充分的自主权。这是张爱玲的理想社会、世外桃源。她做了精心设计:有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等,她还配备了好几幅图案。显然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小爱玲也无法想象什么是快乐的人间生活,终又作罢。
大约10岁的时候,张爱玲利用课余时间,用铅笔记在一个笔记本上,完成了一个女郎因失恋而专程从上海跑到杭州投湖自杀的故事,女主角因为表姐插足,造成三角爱悲剧。写成后在同学中传阅,得到大家的交口称赞。母亲看后不以为然,说如果她要自杀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但张爱玲坚持这个构思,因为西湖是美丽的,为爱殉情在她看来也是美丽的。这是美的毁灭的悲剧。
读小学期间,她开始有了一些较完整的习作。如“新文艺腔”浓厚的三角恋爱悲剧《理想中的理想村》。这大概是她先前构思并写成断片的《快乐村》的改写或续写。爱玲的“理想村”是美丽的——
在小山的顶上有一所精致的跳舞厅,吃饭后,乳白色的淡烟渐渐地退了,露出明朗的南国的蓝天。你可以听见悠扬的音乐,像一张桃色的网,笼罩着金山。——这里有的是活泼的青春,有的是热的火红的心,没有颓唐的小老人,只有健壮的老少年。银白的月踽踽地在空空洞洞的天上徘徊,她仿佛在垂泪,她恨自己的孤独……
爱玲十四岁时还尝试过一个长篇的鸳鸯蝴蝶派体的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她一生嗜读《红楼梦》,其启蒙老师是父亲。他的旧学根基较牢,也很欣赏爱玲爱看书爱涂鸦文字的性格。张廷重也有珍视温爱的父女情的时候。爱玲说过:“我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沓的大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76]爱玲所说的“寂寞的时候”,主要指的是张廷重从离婚到再婚的那几年间。她在父亲书房看书,与他讨论对小说的看法。爱玲最爱读的是《红楼梦》,张廷重详细地给她谈《红楼梦》的作者身世,分析书中主要人物。爱玲也谈到自己的观感,并有了“戏续”《红楼梦》为《摩登红楼梦》的念头。看到女儿有戏写《红楼梦》的冲动,张廷重雅兴大发,为她代拟了回目。
第一回:“沧桑变幻宝黛住层楼,维犬升仙贾琏膺景命”;
第二回:“弭讼端覆雨翻云,赛时装嗔惊叱燕”;
第三回:“收放心浪子别闺闱,假虔诚情郎参教典”;
第四回:“萍梗天涯有情成眷属,凄凉泉路同命作鸳鸯”;
第五回:“音问浮沉良朋空洒泪,波光骀荡情侣共嬉春”;
第六回:“陷阱设康衢娇娃蹈险,骊歌惊别梦游子伤怀”。
张爱玲的构思是新颖别致又大胆出奇的,取《红楼梦》中人物,改换其中故事,将背景搬到20世纪的上海洋场。内容有秦钟与智能儿坐火车私奔到杭州,自由恋爱结婚;贾母带着宝玉及众姐妹到西湖看水上运动会吃冰激凌;主席夫人贾元春主持新生活时装表演;宝玉要与黛玉一同出洋,家中不允便负气出走;贾琏当上铁道局长,等等。其人物描写、语言动作、心理刻画与《红楼梦》酷似,自然流畅,活灵活现。试看其中一段:
(贾琏当上铁道局长,凤姐置酒相庆)自己坐了主席,又望着平儿笑道:“你今天也来快活快活,别拘礼了,坐到一块儿来乐一乐罢!”……三人传杯递盏……贾琏道:“这两年不知闹了多少饥荒,如今可好了。”凤姐瞅了他一眼道:“钱留在手里要咬手的,快去多讨几个小老婆罢!”贾琏哈哈大笑道:“奶奶放心,有了你和平儿这两个美人坯子,我还讨什么小老婆呢?”凤姐冷笑道:“二爷过奖了!你自有你的心心念念睡里梦里都不忘记的心上人放在泌园村小公馆里,还装什么假惺惺呢?大家心里都是透亮的了。”……平儿见他俩话又岔到斜里去了,连忙打了个岔混过去了。
在《流言·存稿》中,张爱玲曾引用过少作的片断。跟不少作家“悔其少作”的做法不太一样的是,她是不悔的,甚至有些夸耀和得意。的确,从那些残简断片中,可以看出,其文笔之熟练老到,构思之奇异巧妙,远非同龄人所能比拟,读罢使人万难想到它们竟出自一个十岁上下的小女孩之手。才女文学之才,显露得出奇的早。
爱玲不仅喜欢写写画画,还很早就有发表欲。她第一次给报刊投稿时年方九岁,虽没被采用,但随稿寄给编辑的信的影印件现在还可以见到:
记者先生:我今年9岁,英文不够,所以还没有进学堂,现在先在家里补英文,明年大约可以考四年级了。前天我看见副刊编辑室的启事,我想起我在杭州的日记来,所以寄给你看,不知你可嫌它太长了。我常常喜欢书子。可是不像你们报上那天登的孙中山的儿子那一流的书子,是娃娃古装的人,喜欢填颜色,你如果要,我就寄给你看,祝你快乐![77]
九岁的孩子能写出那样流利的信已属不易,敢于投稿本身便是了不起的举动。
张爱玲的文章第一次变成铅字是她在十二岁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圣玛丽亚女校年刊《风藻》第12期(1932年号)刊载了她的小说《不幸的她》[78]。“她”和雍姊两个十来岁的女孩同在小学读书,亲密无间。后来雍姊远嫁成家,“她”这个“孤傲爱自由的人,几经风雨,仍然不幸着”。这个作品故事较粗疏,但已显现出张爱玲注意挖掘女性心理、关注女性命运的特色,文字也清新可喜。在《风藻》上,爱玲还发表了《迟暮》《秋雨》《心愿》《牧羊者素描》《论卡通画之前途》等散文。《迟暮》中可见张爱玲对青春和创造的人生价值的珍视,对时光和生命流程的警惕态度。“青春如流水一般地长逝之后,数十载风雨绵绵的灰色生活又将怎样度过?”这里跳动着一颗敏感的少女之心。
高中阶段,张爱玲在校刊《国光》上发表了两篇非常出色的小说:“《牛》和《霸王别姬》。前者取材于农村生活,后一篇是被作家写烂了的历史题材,这对于一个长期在公馆和校园中生活的涉世不深的女孩来说,她能轻松驾驭,写出特色,令人不得不佩服这是一块写小说的料——她有不凡的想象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对人性的体认。”在《牛》中,围绕着农民生计的命根子,禄兴娘子自家活蹦乱跳的牛被人硬生生牵走了,农忙时节好不容易借来的牛又害死了禄兴:
黄黄的月亮斜挂在烟囱,被炊烟熏得迷迷蒙蒙,牵牛花在乱坟堆里张开粉紫的小喇叭,狗尾草簌簌地摇着栗色的穗子。展开在禄兴娘子面前的生命就是一个漫漫长夜——缺少了吱吱咯咯的鸡声和禄兴的高大的在灯前晃来晃去的影子的晚上,该是多么寂寞的晚上啊!
爱玲不仅表现了农民的物质贫困,而且还注意他们的心灵创伤。在她的笔下,小说不只是故事,更要有人性的透析。这是她一开始就有意为之的。《霸王别姬》更是有别于一般的英雄美人故事的神来之笔。
作家和史家通常把虞姬处理成一个被欣赏者、被占有者,一个被动者。张爱玲却让虞姬的悲剧有了几分主动和清醒的意识,她开始怀疑十多年来以项王的苦乐为苦乐的价值,“她怀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无论项王的霸业成功与否,无论她有怎样的结局和“冠冕”,她要有一个明确的“自己”,“她不再反射他照在她身上的光辉”。当项王拼死做最后一搏时,她先结果了自己——
项羽冲过去抱住她的腰,她的手还紧握着那镶金的刀柄。项羽俯下他的含泪的火一般光明的大眼睛紧紧瞅着她。她张开她的眼,然后,仿佛受不住这样强烈的阳光似的,她又合上了它们。项羽把耳朵凑到她的颤动的唇边,他听见她在说一句他听不懂的话:
“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收梢”。
不做英雄的陪衬,不做敌人的俘虏,不再继续那不可摆脱的女人的命运,虞姬的收梢,因为有主动和自觉,是一个漂亮的“收梢”。
当语文老师汪宏声先生读到这篇作品,喜不自胜,他在课堂上给张爱玲很高评价,认为爱玲的《霸王别姬》比郭沫若先生的《楚霸王之死》有过之而无不及。只要爱玲继续努力,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从以上所引爱玲的少作,足可以看出,她是一个驾驭文字的高手,一个神童,一个少年天才。恐怕任何一个中小学语文教师见到这些习作都不会相信它们竟出自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之手吧?这就是张爱玲,不凡的张爱玲。
中学期间张爱玲还写过一些短小的文论,可见她那时就有品评作品臧否作家的能力。比如她说丁玲“是惹人爱的女作家”。对丁玲自传式的平铺直叙的《梦珂》,她认为“文笔散漫枯涩,主题很模糊,是没有成熟的作品”。而对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评价甚高,她说:“细腻的心理描写、强烈的个性、颓废美丽的生活,都写得极好。女主角莎菲那矛盾的浪漫个性,可以代表五四时期感到新旧思想冲突所带来的苦闷的一般女性们。作者特殊的、简练有力的风格,在这本书里得以成熟。”[79]应当说,这是一篇简洁准确的作家论,出自一个十六岁少女之手,值得佩服。这些习作的可贵不仅在于它们表明了张爱玲的惊人才华,而且在于它们清晰地展现了张爱玲的创作轨迹和艺术探索的道路。
上引各篇,以体裁论有小说、散文;
以题材论,有家庭纠纷、爱情故事、生命意识、历史演义;
以风格论,有《红楼梦》式的章回文言小说,亦有雅驯的白话创作。
可见她在正式冲向文坛之前,她有过各种尝试,各方探索。高眼光高起点高成就,是自小就奠定了基础的。成名后,在一次作家聚会上,有记者问张爱玲的写作经过,她答道:“我一直就想以写小说为职业。从初识字的时候起,尝试过各种不同体裁的小说,如今古奇观体、演义体、笔记体、鸳蝴派、正统的新文艺派等等。”[80]这话清晰地表明了两点:
1.张爱玲具有“为写作而写作”的职业作家意识;
2.与之相联系,作者具有相当强的文体意识。
现代史上的不少作家,经常宣称不是为了当作家而写作,而是以写作作为表达见解发泄愤怒的方式。他们关注的重心是见解,而非艺术性,他们对写什么(题材)的兴趣大于怎样写(技巧)。因此他们的作品的内容的进步性和题材的价值常常以粗糙的形式表现出来,呈现出社会认识价值与艺术审美价值的严重分离。这种现象固然有可以理解的历史限制,也表明了这些作者自身创作意识的匮乏。他们扮演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二流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的角色。
张爱玲视写作为生命存在的方式。她并不特别计较说教的意义,而是苦心探索艺术表达方式,寻找最能适合于自己的文体风格。因而品质纯正,技艺超群,终于形成雅俗共赏,中国传统味与西方现代味俱全的独特文体。
这,就是张爱玲早期试笔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以看出,张爱玲早年的文学梦甜美、纯净,不含杂质。
十四、才女怪癖
大一时期,张爱玲写的应征稿《我的天才梦》——一个多么不凡的题目!她实际上是在向文坛、向读者预告:一个文学天才即将诞生。这是在童年少年的辛勤耕耘培养之后,对不久后的收获的充分自信。在表露了自己的自信之后,也即本章开头所引的那句发展个人天才的“狂妄”之语后,张爱玲还谈到了个人的怪癖:
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退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张爱玲的确有许多“怪癖”,很多不及常人之处,以至于她到老了之后也是美籍华人圈子中的怪人,不与他人往来。当她最初在涂鸦文字的同时,她缺乏着起码的生活自理的能力:不会削苹果,不会补袜子,怕上理发店,怕见客,不会织毛衣,记不住家里汽车的号码。在一个房间里住了两年,始终不知电铃在何处。接连三个月坐黄包车去医院打针还是不认路……在待人接物方面有着惊人的愚笨。此外,她有很多特殊的小趣味。她喜欢雾的轻微的霉气、雨打湿的灰尘,喜欢汽油味、葱蒜味、牛奶的煳味、油漆味、陈油味等,确实有些怪。
“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81]张爱玲这样苛刻地评价自己,对于一般人而言,这自然是一个缺点,但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往往是充满艺术气质的体现。他们常常注重的是事物的意义而非结果,注重于情感体验而非操作程序。他们追求的是生命的趣味和价值,而非生活中的实际获取和需要。他们是理想的真正生活的憧憬者、追寻者,是实际的真实的生活的漠视者和低能儿。行为乖张、举止出格、思维反常,皆因他们沉溺于理想的诗意的应该如此的生活中。如同弗洛伊德所说,诗人、作家、艺术家往往与疯子怪人只有一纸之隔。
很多评论家和文学爱好者常常在这一点上发生误解。他们把作家视为完人、通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熟悉人间的各种生活。其实从来没有这样的作家。作家不是最高文凭的拥有者,不是高智商的被测试者,不是通万物的超人,不是特异功能的携带者、表演者。他们有着凡人共有或没有的缺点或局限,在很多日常事务方面他们常常令人大跌眼镜。只有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其他人和疯子不同——他们是人类生存价值的全力探求者,他们是人的生活状态和人性发展过程的特别关注者,他们是人的情爱意识的专门表现者。他们拥有的是性格鲜明的个体和整个人类!
他们的双眼里装有一架别人看不见的显微镜,一只别人看不见的放大镜。他们的心灵始终是人类人欲横流的漩涡和港岸。他们的脑海永远是人类斗智斗勇的宝地和战场。他们体悟所经历的、思索所观察的、表达所凝构的,写作之于他们,不是一种技能性的职业工种,而是生存方式,是内驱力的外泄;他们的作品也不单是一种种技巧的编织,而是激情冲动的符号,人性冲突的映现。
惟有顺着这样的思路,我们才可以理解张爱玲的怪僻和才华。读书和写作从幼时起就成为她生活的主要兴奋点和内驱力,她自然是有些怪了。
虽然尝试过不同的题材和体裁,但她一开始所关注和表现的就是人的内心世界、情欲冲突。姑嫂之争中有女人对女人的阴谋,美女的自杀中有美的毁灭的喟叹,妻妾对谈中有男性中心主义的强力,青春赞叹中有对时间老人的恐惧,农妇孤寂中有对穷人生命意义的感慨,霸王别姬中有对女性生命价值的思索……
这,就是张爱玲少作的过人之处,可贵之处。是哪一位天神赋予她特殊的才华、敏锐的心灵、早熟的智慧?
除了天赋,还有她童年的记忆。“童年记忆”对于成人尤其对于作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是评论家和心理学家的共识。童年是作家生活的摇篮、观察的起点、灵感的初源、天才的土壤。它蕴藏最初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氤氲着细微的观察视角和创作无意识。
生于富家、长于富家、死于富家,一辈子生活富裕的人多是没有出息的,他们不知忧愁,因而无以清醒无从奋起;生于贫穷、长于贫穷、死于贫穷,一辈子生活贫困的人也多是少有作为的,他们终生为起码的物质生活操劳,不可能有大贡献于社会。因为太穷会限制眼界,难以超越。只有那些随着大时代变幻个人家境也在变幻的一代人才多有可能成功。他们知道先前生活的无奈与精彩,更深切地感受到自身现在的无奈与外面世界的精彩,因此他们奋发有所为。现代中国文坛提供了无数这样的实例。
本书的传主,一代才女张爱玲,童年时代的她不是金色光环笼罩下的张公馆的小天使,不是在纯情母爱宠幸中的小公主,不是四邻夸耀的小宝贝,不是老师引为自傲的小精灵,她是一个没有父爱的名门千金,少有母爱的富家小姐。如果说贫困使人因皮肉之苦而发出对不公道世界的诅咒的话,那么无爱则使人备感生命的孤独和情感的扭曲。贫穷只能带来辛酸感,而优裕则可能会带来孤独感。冰冷的家庭使她产生无尽的恋家情结,优越的家境使她产生了优越的感伤。在她柔软的心灵中始终有一个巨大的落差。身心的重创,对于一般人是永远的重创。对于敏感多情的文艺家则是发酵的酵母、心灵的回流、掘金的宝矿。如同当铺药店之于少年鲁迅、屠杀流血之于巴黎的巴金、孤苦之于夏绿蒂、债务之于巴尔扎克……
张爱玲的童年经历,使她失去了儿童似的惯常的认知世界的金色眼光。她的童心世界没有单纯的明丽,而是繁复的苍凉。
不幸是作家的摇篮,痛苦是智慧的母亲。张爱玲正是在不幸和痛苦之中诞生的作家。她后来的作品直接间接地来自童年记忆:洋场和洋场阔少、公馆和公馆里的遗老、鸦片和吸鸦片的太太、古董和古董般的老婴孩、旧家具和随家具的老去而长成的女性、舞场和舞场上的调情、电车和电车中的邂逅,无不打上早年生活的印记。作品中某些人物的原型,也可在她家的生活环境中找到。《茉莉香片》中病态的聂传庆,不正是她那怯弱无能的弟弟的影子在游荡?作品中那些精巧的比喻、丰富的意象,难道不是她在那使人昏睡的洋房里没有昏睡而在自由遐想的记录?那一再出现而隐义每每不同的月亮意象也许因为她儿时的夜晚常常与月亮共享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