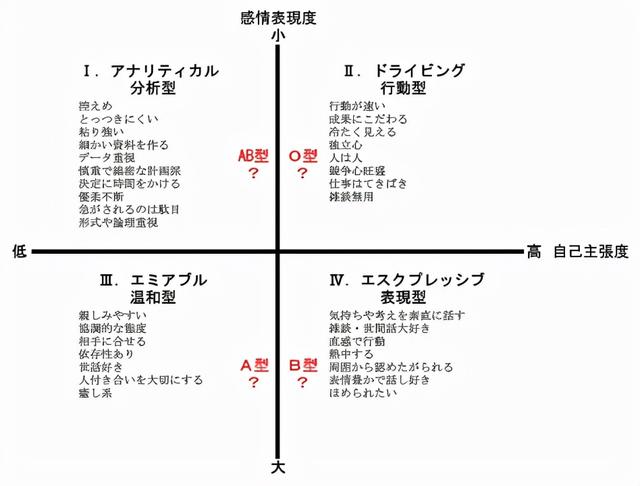寒露过后一早一晚天着实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早一晚更觉寒意浓浓这天早上人们正在熟睡,王老大家可忙开了,老婆将要临盆,捂着肚子叫疼“大妮,二妮赶紧的起,你娘要生了,赶紧推平车”王老大大声叫着女儿王老大忙着抱了两床被子放到平车上铺平,把老婆扶到车上躺下,王老大驾车就跑,大妮二妮推着左右车帮,不时給娘鼓劲,坚持住到公社医院有四里地,土疙瘩路虽凸凹不平,王老大低头找着平一点的路小心翼翼一路奔跑,一不注意就猛颠一下,只想老婆能快到医院,也没听到老婆不时得叫,王老大觉着老婆快生了肚子疼得厉害叫疼,实际叫疼是因为这一路太颠,到医院人颠的快散架了,也忘了肚子疼的事了到公社医院也就五点光景,值班刘医生和蔼可亲的赶紧安排王老大把平车推到产房,大人小孩一起用被子裹着王老大媳妇抬到产床,这时又来了一名护士,王老大爷三被赶了出来,在门口等了不到二十分钟,就听到孩子啼哭,刘医生告诉王老大是带把的,王老大嘴里念叨着“怎么又是带把的,唉”,这是王老大第六个孩子,俩妮四小,王老大点上一支一毛二一盒的“普滕”烟裹了裹褂子蹲在了产房门根,紧邹眉头一口接一口的痛苦的吸着,吸得好像不是烟,是毒药,是惆怅“王老大把平车推过来,母子平安,回家吧”刘医生安排道,王老大一动不动,“不想要咋地?咱换换,我女儿二个月了”“真的?”王老大来了精神,猛吸了最后一口烟,把烟屁股往地上用力的按了下站了起来,瞪得不算大的眼睛盯着刘医生刘医生这个女儿是第五个了,一直想要个男娃可就是生不出来,家里人早就想弄个男孩,也没少找神婆子,还是没有“真的,你去和你老婆商量一下”刘医生说“不行,我不换,我身上掉下来的谁都不给换”产房里传来女人气愤的埋怨声,“刘医生家庭条件好,孩子吃不了亏”“别说了,不行,你换我就死给你看”“大妮二妮推你娘回家”王老大粗声粗气喊着,大妮二妮慌地把被子铺到平车上,又赶紧扶着娘上车,女人一手捂肚子一手抱孩子步履维艰的上了车,一直紧紧抱着孩子不丢手,生怕别人抢走喽王老大说了声“我回家做饭去”就大步流星头也不抬的往家回,也不管她娘几个的事,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那些小时候一直搞不懂的事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那些小时候一直搞不懂的事情
寒露过后一早一晚天着实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早一晚更觉寒意浓浓。这天早上人们正在熟睡,王老大家可忙开了,老婆将要临盆,捂着肚子叫疼。“大妮,二妮赶紧的起,你娘要生了,赶紧推平车”王老大大声叫着女儿。王老大忙着抱了两床被子放到平车上铺平,把老婆扶到车上躺下,王老大驾车就跑,大妮二妮推着左右车帮,不时給娘鼓劲,坚持住。到公社医院有四里地,土疙瘩路虽凸凹不平,王老大低头找着平一点的路小心翼翼一路奔跑,一不注意就猛颠一下,只想老婆能快到医院,也没听到老婆不时得叫,王老大觉着老婆快生了肚子疼得厉害叫疼,实际叫疼是因为这一路太颠,到医院人颠的快散架了,也忘了肚子疼的事了。到公社医院也就五点光景,值班刘医生和蔼可亲的赶紧安排王老大把平车推到产房,大人小孩一起用被子裹着王老大媳妇抬到产床,这时又来了一名护士,王老大爷三被赶了出来,在门口等了不到二十分钟,就听到孩子啼哭,刘医生告诉王老大是带把的,王老大嘴里念叨着“怎么又是带把的,唉!”,这是王老大第六个孩子,俩妮四小,王老大点上一支一毛二一盒的“普滕”烟裹了裹褂子蹲在了产房门根,紧邹眉头一口接一口的痛苦的吸着,吸得好像不是烟,是毒药,是惆怅。“王老大把平车推过来,母子平安,回家吧”刘医生安排道,王老大一动不动,“不想要咋地?咱换换,我女儿二个月了”“真的?”王老大来了精神,猛吸了最后一口烟,把烟屁股往地上用力的按了下站了起来,瞪得不算大的眼睛盯着刘医生。刘医生这个女儿是第五个了,一直想要个男娃可就是生不出来,家里人早就想弄个男孩,也没少找神婆子,还是没有。“真的,你去和你老婆商量一下”刘医生说。“不行,我不换,我身上掉下来的谁都不给换”产房里传来女人气愤的埋怨声,“刘医生家庭条件好,孩子吃不了亏”“别说了,不行,你换我就死给你看”“大妮二妮推你娘回家”王老大粗声粗气喊着,大妮二妮慌地把被子铺到平车上,又赶紧扶着娘上车,女人一手捂肚子一手抱孩子步履维艰的上了车,一直紧紧抱着孩子不丢手,生怕别人抢走喽。王老大说了声“我回家做饭去”就大步流星头也不抬的往家回,也不管她娘几个的事。
王老大回到家叫醒大狗子让他去上学,然后开始做早饭,十分钟左右才听到平车的轱辘声,把娘扶到床上姊妹俩背着书包去上学了。早饭是面汤和红薯,有咸菜,还有就是爷爷的一块白面饼,只有长辈才能吃上,做好饭王老大喊二毛,三毛起床吃饭,爷爷早就起来在那看书,王老大把饭端给老父亲面前,“大嘞,吃饭吧”,老爷子摘下老花镜放下书捋了捋胡子端起碗来吃饭,学生也都回来了,一锅红薯一锅面水吃个精光。王老大又单给屋里人冲了一碗鸡蛋茶。吃完饭,各屋把各屋的尿盆倒在茅房集尿桶里,以便等生产队上门收。然后上学的上学,看书的看书,玩的玩,王老大就开始刷锅,刷锅水和草面喂猪喂羊。
左右邻居的妇女吃过饭知道王老大家又添新丁都过来看看,东边邻居曹二媳妇开玩笑说“大婶子,那么快就生了”,王老大屋里人说“这有啥,跟撒泡尿差不多功夫,又不是头胎”,女人们都哈哈大笑。又聊了几句,安抚女人好好养着,然后都拿着农具去生产队领活干。
去生产队干活哪个也不敢迟到,公分员要扣分的。生产队有活干时,一天十分,年终分粮,按人口和公分多少分粮食和粮票、肉票等等,劳动力多的分得多,王老大家人多,但劳动力少,分的就少。在农村孩子上个小学毕业一半的就下学了,十三四岁就开始跟大人下地干活,特别是女孩,有的小学上不完就跟大人下地干活,多少也给点公分。女孩的地位是比较低的,一样吃饭,养大就是人家的人了,干活给公分也少,多数父母就不待见。
孩子生了要送粽米,这是农村的风俗。男孩十二天,女孩九天,要摆喜酒,这几天里邻居送白糖、鸡蛋,娃的姥娘家送白糖、红糖、鸡蛋、娃的衣服等很多,橼子也是最大的。生娃的家里始终有红糖茶准备着,只要有人去就招呼喝红糖茶水,苏北很多地方管白开水也叫茶。到了日子门上贴个喜,亲戚邻居摆几桌,热热闹闹中午一顿大席饭。大席头几天就开始准备,请大老知和忙人,垒锅洞,借大锅开始蒸馒头,借桌子、凳子、锅碗瓢盆等等。喜事借的东西自己再还回去,忧事借的东西东家不还的,谁家的谁去取回来。生孩子一般邻居是不上桌的,饭后东家把染好的红鸡蛋根据关系查好个数放在亲戚的橼子里。红鸡蛋都是煮熟的用红纸包着,邻居一般回十个鸡蛋,亲戚一般回二十个鸡蛋,娃的姥姥回六十个鸡蛋。有的邻居虽没随礼,家里有小孩子的,东家也会送几个红鸡蛋过去,以示同喜,还有就是之前有点言差语错的矛盾的邻居也送几个鸡蛋以示和好。最后分剩下的大席菜,基本都是吃剩的,先送给本村年纪大的,然后是本姓的家,由最近的房份到远房,看菜多少分到哪就是哪,分完为止。王老大做的自然很好,毕竟他是本村有名的文化人,自家生孩子自然不会叫邻里说出“不”字来。
王老大高小毕业,属于村子里的文化人,因五十年代跟母亲河南逃荒终止了学业,现生产队农业专干,前几年干过二年小学教师,工资太低就回家挣公分啦,在邻里口碑很好,人送外号“小诸葛”。
孩子生在文革期间,王老大就给孩子起名叫文革,人说天下的父母疼小儿,小文革倍受父母宠爱,特别是母亲,有点好吃的经常偷偷留给小文革吃。那时也没多少什么好吃的,也就是糖,水果,一块糖也舍不得自己吃,留着也要给文革。当时吃的不怎么好但能吃饱,就是没衣服穿,衣服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上学前夏天文革基本不穿衣服,村子里不上学的男孩、女孩基本上都是光腚猴。就是冬天也没有棉衣,那时很少能看到几个穿不带补丁的衣服,最好笑的是屁股上补丁与裤子颜色差的太多的,有的针线活不好还露腚呢,衣服一般老大不能穿了给老二,老二不能穿给老三,有的衣服小的裹在身上,袖子接了再接,有的袖子短的只有到胳膊肘,有的小孩拾大人的,穿的踢里踏拉,反正有衣服穿就行,男孩说媳妇借衣服借手表借自行车,包括粮食、家具也借,没谁笑话谁。麦忙季节,太阳能把人晒熟晒干,男女老少在场里打场都光着膀子,头上系个毛巾,女人也不觉羞,袒胸露乳正常的,只有新媳妇羞羞答答不好意思,生了孩子,一开始孩子拱到娘的怀里吃奶,后来皮实了,就敞着怀让孩子拽着奶吃,可能这样都畅快,也没有奶罩,穿个小背心就不错啦,其实就是因为当时衣服少。
逢年过节每家都会熬一大锅猪肉海带干豆角菜,煮点咸花生一盆。王老大家也不例外,也早早的准备年货、年饭。年二十三就开始蒸馒头,有时几家合伙蒸,有馒头,有黄团子,有菜包子,有糖馒头,有的把钱包里面,有的把麦麸子包里面,都预示着来年有个好兆头。蒸的馒头有的吃到出正月,发了霉就结掉皮吃。
过了年初一就该走亲戚,姑舅姨等等都要走动,也就是大锅菜、咸花生招待,条件好的也就加一个菜。吃饭时女人、孩子不能上桌,只有他们吃完饭才能围桌上吃饭,有时老爷们聊的投机,多喝两杯,学生等不及就随便吃点赶着去学校。过年孩子们最高兴的是能穿新衣服,有压岁钱,一般父母会把压岁钱换成新的一分、二分、五分、一毛、两毛、五毛的,再大点的就很少给,小孩拿着也不舍得花,用纸叠个钱夹留起来用,真花钱时也是找旧一点的,咬着牙的不舍。过年时杂耍的、说书的、唱大戏的包括要饭的就多了起来,知道大人小孩手里都有几个钱,就都来了。不论说书的、杂耍的、唱戏的,一天的,一般在演着时有人掖你口袋里一张纸条,有纸条就给他们钱,这是不成文的规矩,老农民实在都会给。若是演的时间长,好多天,就会上门要粮食以当收入。老红军死后房子空着,要饭的老严就恳求曹兵的爹住一阵子,闲着用不到就借给他了,老严把那当成自己的点,每天要的馒头有大有小还有半个的,半个的最多,然后卖给村里,一天的收入颇丰,比庄家人强的多。后来每年过年他都来,再后来就不来了,说是去有钱的地方要去了,要的发了大财。
一般大人去生产队干活,小文革就和三毛还有同龄的小朋友到处跑着玩。大人闲暇时经常到队场里踢足球,有时约外村人比赛,特别一到年底没啥活时更是天天踢,村后的张秃子踢球最厉害,个不高跑得快,带球灵活,几个人都拦不住他,脚法准、狠。老红军的儿子曹兵的爹大高个,把球门最棒,再刁钻的球他都能抱住或者拦在门外;大人再有就是玩打柆子,柆子,直径二三公分,十公分左右长,用粗树枝做的,两头用刀削尖。柆子棍也是用树枝做成,四十五公分左右长,粗细和柆子差不多,会玩的一下能把柆子打几十米,规则也不太复杂,大人小孩都喜欢,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后来玩的就少了;大人们再就是比赛翻辘滚(轧场用具)。
那时小孩玩爬树、游泳、沿墙头、打坷垃仗、打柆子、玩沙包、玻璃球、纸壳、掏鸟窝、爬生产队的瓜、打邻居家的杏、枣、野地里烤红薯、豆子、花生、跳红薯秧、玩瓦片、踢毽子、藏马猴(捉迷藏)、玩积极灵扛大刀、锥子插心、对拐角力等等太多啦。爬树文革最厉害,当时也就七、八岁,基本上都能爬到树梢,肚皮扯得一天到晚就没好过。那年曹七他爸给他做了个风筝,被曹七放到了树上,当时就请的文革,树猴跟走闲路一样几下就到了树顶,取下风筝,得了一颗糖的酬劳。小文革还有一个厉害的杀手锏,就是几个小男孩比尿尿,三毛、曹七、张永等等都不是文革的对手,小文革号称“迎风一丈”,尿的又高又远。一次曹二记功员当裁判,几个小子站在地里堰埂子上,曹二喊比赛开始,小子们都捏着自己的鸡鸡往前送,成弓状,用力的往前尿,最后还是文革赢了,当时曹二感慨道“人家是迎风一丈,咱是顺风一鞋”。
小孩有时跑集上听戏、听评书,看玩把戏的(有玩猴的,有打拳的),看画书(小人书)。听戏听书有时正听得起劲时,锣鼓点子急促敲几下就停下托着盘子开始要钱,大人小孩一到要钱就跑,过一会再回来听,也有个别的捧场给点。夏天赶集渴啦可以去吃打瓜,黄瓤,不甜,瓜仁要吐给摊主,不要钱,随便吃,最起码解渴。没人玩时有时学大人背毛主席语录,大人经常说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他们也跟着说,学唱《东方红》《绣红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南泥湾》。当时看小人书是孩子们的最爱,文革二哥二毛就有好几本小人书,看一本一天一分钱,在集上摆摊的小人书抢手的三分一天,新的一般二分,旧点的一分。
玩的最出格的是曹七,他真是人才。有天夜里,曹七正靠着母亲睡觉,床晃得厉害,母亲急促的呼吸声把他惊醒,迷迷糊糊地看到他爹曹八斤在她母亲身上一丝不挂哼哼唧唧的喘着粗气,母亲好像享受的样子,曹七没敢吱声,也不知大人玩的什么,一会就又睡着啦。过了几天,曹七和邻居曹臭妮子玩,问臭妮子见没见过爹娘玩配对,臭妮说见过,她俩一拍即合就搞了一把,两个小孩光着身子也学爹娘的动作,但他们只看到表面,实质的不懂,两小孩也没感觉有啥好玩的,但不巧被邻居老妖精太太看到告诉了她们的爹娘,都被狠狠地揍了一顿。
老妖精满头白发,但精神抖擞,干净利落,穿戴与人不同,农村人打扮这样,就有人给她起了外号“老妖精”。这位老太太其实没过门当闺女时是地主家的大家闺秀,穿着谈吐和一般人当然不一样,就是批斗她,她也是穿戴的漂漂亮亮。就是说话和老百姓不一样,古怪得很。
“文革,看狗吊秧子去”曹七大声喊着,在村子中间已有很多人,一群孩子都往这个方向跑。两条狗屁股对着屁股在很多人的注视下惊恐万分,像是偷情逮个正着,调皮的小孩用小坷垃头投向惊恐的那一对,最让人心疼的是,有两个大孩子用木棍插在狗尾巴下把两条狗抬起来,两条狗大声惨叫,特别是公狗叫的更是凄惨,有时会被挑断阳物血流不止,直到两条狗分开夹着尾巴逃跑,大家才哈哈大笑散去。有时如果谁家的母狗被别家的公狗上了,就会打公狗,骂公狗不要脸,不让人打母狗。有时自家的公狗上了人家的母狗就感觉赚了便宜,也不让人打。因为打狗的事两个小孩会打架,都不想别人打自己家的狗,都说别家的狗勾引的自家的狗,有时大人也会吵两句。
到了八一年,交了八毛五的学费,王文革跟着三毛一起去上学啦,规定八岁入学,差一岁、半岁跟校长说说也能上,校长、老师基本上都是本村的,没一个是正式学校毕业的,上学了文革就很少玩啦,每天搬着凳子上学放学,别的孩子都有书包,都是自家娘夜里点着煤油灯给缝的,有的女孩书包花花绿绿非常好看。文革没有书包,就用腋窝夹着书,用手攥着铅笔头,早上、中午、下午一直如此,每天早上六点多去学校,冬天跑操,夏天做广播操,然后晨读、上课一节,八点放学,回家吃饭,九点就得上中午课三节,下午两节课就放学,五年级是毕业班加一节课,一般四点半学生就放学了。老师布置的作业很少,数学也就四道题左右,语文写生字、生词、造句子等,也就半小时就解决了,有的在学校就写完啦,下面的时间就可尽情的玩。玩纸壳、丢杏核、捉迷藏等还有知道玩法不知道名字的,想玩什么几个小朋友一商量就玩起来,直到满头大汗。
王文革刚上一年级不久,就听同学叫杨玲“老母猪”,这位女同学听到有人叫就会大骂。这位女生不是因为胖也不是丑,听说她同桌经常见她捉虱子,大虱子都叫它“老母猪”,可能虱子长的像猪吧。那时人人都有虱子,虱子的蛹都叫几,几是白色的,叫几是因为小而繁多,人们都是用两个大拇指盖挤它,听着啪啪的响,就叫它几啦。以前人到热天才能去河里洗澡,总的来说卫生是非常差的,所以每家都有梳子、篦子,特别是篦子排得比较密“虱子”“几”都能梳下来。经常看到老太太用篦子梳虱子,有的人直接用牙顺着衣缝“嗝吱嗝吱”地咬。冬天靠着柴火垛晒着太阳逮虱子是常看到的。有的虱子会肆无忌惮的在你头上,在你衣服上爬行,王文革就见过校长给他们上数学课时屁股靠着他的课桌认真的讲课,一个很大的虱子就在校长身上爬来爬去,那一课王文革什么也没听进去,仔细的观察虱子的一举一动,几次差一点从校长的衣服上掉下来。还有个小男孩个子太小就有人叫他“小几”。那时起外号也不觉什么对不对,老师都有外号,大人们常说:没有外号不发家,也不知真假。
在学校里王文革的游戏就是踢毽子、丢沙包、玩玻璃球、打纸壳等。毽子都是自制的,缝衣服的下脚料,抽线头,找两个铜钱,穿起来系成圆形就行。穿布鞋特别是条绒鞋最好踢。我们一般玩五按十打的,从一踢到五时毽子要稳稳地停在脚背上,如果不稳可以用另一只脚踩实,使毽子容易再次踢起,踢到十时要跳起用另一只脚后踢毽子,然后继续踢。失误就算一次,一人一次最后按个数多少计胜负,在规定数字的情况下谁先到谁胜。这是女生的长项,村东的邓梅花就是高手,一口气就能踢一百。三毛就不行,一次就踢一个,跳起后打更挨不着边。但丢沙包三毛最厉害,他有劲,丢的还快,一般人接不住,天冷时我们就双手敞着外衣去接沙包。玩玻璃球王文革是高手,别看人瘦小,弹玻璃球非常准,总能第一个进老虎洞,赢了不少玻璃球,不管怎么玩他都很少输,三四年级的大孩他也赢。
打纸壳是王文革最爱玩的,他一般用自己写了檫,檫了再写的确实不能用的纸叠纸壳,赢回来的好点的拆了用针线再缝成本子写作业。有一个同学叫张永,家里条件好,就总爱挑战他,一直不服输,王文革就要求他用好的,不然不与他玩,张永像着迷一样,就用好纸也要和他论输赢。可以说王文革的一年级作业本基本上由张永负责的。
王文革到了上二年级时流行玩枪,叫洋火枪。制作简单,用硬铁条握一个枪架,握扳机、撞钉,几节自行车链条,四五个橡皮套,链条最前面用一根火柴堵住,带药的留在链条洞里,然后把火柴头的火药挤进链条洞里,尽量把药挤结实,撞钉一定能撞到药才行,一切准备好,扣动扳机,撞钉在皮筋的拉扯下撞击链条内的火药,啪的一声,青烟升起,煞是威风。有时别在腰间,威风凛凛。
王文革大哥狗子也做了一个,非常漂亮,文革只能看,不让玩。文革就拿自己的木枪,闭着一只眼,整个脸扭到一个方向地瞄着目标,嘴里发出“啪啪啪啾啾啾吐吐吐”的声音,有时拿着枪在土堆后面趴着探头探脑用嘴发出枪声,有时还匍匐前行,左右侧翻身,跟电影里差不多,每天都是一身泥。
大狗子学习也不好,就喜欢瞎修理,很多东西他一看便会,手电筒他不光会修还会做,很神奇,后来每家都按小广播,谁家的坏了,他摆弄几下就好了,再后来有电视,他也能修理,也是个人才。但因为学习没少被王老大用绳吊在梁头上打。
说起和文革玩纸壳的张永,听说他妈是转亲来的,是他姑姑转到别人家去,三家转的,他爸兄弟多不好说对象,才要他姑转亲的。村西头刘光贵的媳妇还是童养媳。有钱的也可以偷偷地买外地的媳妇,八九时年代可以说一阵风,一个村少说也得几十上百,云、贵、川居多,小的女孩十三四岁,大的女的四五十岁,一千块左右,也是多年的积蓄,后来国家严查拐卖妇女儿童慢慢的就少了。
王文革的叔叔也是外地媳妇,本地娶不上的原因是成分孬,说来是上辈子的事,王文革爷爷有点文化,当过保长,教过黑学,也有点地,之前跟共产党、国民党都干过,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逮啦,经查没干过坏事,蹲了几年就放了。划成分时还有点地,成分化为中农,贫农好找媳妇,又红又专的吃香也好找,成分孬的长得好歹也没人要,有能耐也没人敢要。成分孬的女孩婆家也看不起,在婆家一直抬不起头来。成分不好也是文革的批斗对象。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多年后这些人还是不敢多说话的。王文革的爷爷例外,大家都尊重他,他有文化,人家看书他唱书,双手能写梅花篆字,全村每年的门联几乎都是他写的,写对联从年二十五就开始排队,老爷子一年要搭上几瓶墨汁,包括全村的喜庆忧事老爷子是笔杆子。老爷子象棋下的也好,所以大家都非常尊敬他,见到他都及早打招呼。
八十年代国家急需人才,王文革的父亲王老大被村支书提名去县里学习农业技术。王老大非常高兴,但没想到第二天在村部,小队长曹老红军就找到村支书并痛批一顿,村支书想辩解说王老大有文化有经验也是可塑之才。老红军资格老,老党员,老红军就问支书,王老大什么成分你不知道吗?也不调查就胡乱安排。最后派了一个上过二年级的人去的,最后这人转成了吃皇粮的啦。王老大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几年后还说这事可惜啦。
八十年代初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都分了土地,还分了马、牛、驴,还有平车、锄头、铁锹等工具,每个人干劲十足,大集体装病的病也好了,也不需要照顾了,每年除去交的公粮,自家都有了存粮,好收成时条囤子、洋灰缸、折子圈的都满满的,也都能吃上白面馍馍啦,有点头脑的也可以做点生意,人们像解了束缚的一样,掩饰不住挂在脸上的喜悦。王老大用分的牛换了一头驴,找木工做了一辆大点的平车,打算去山东做粮食生意,干了一年生意不太理想,然后把驴卖了买了一辆大架长征自行车,打算倒腾鸡蛋,折腾几年也没发财,就不又回到土地打算农业致富,种西瓜,毕竟是农业技术员,一年下来也落几个。
李连杰饰演的《少林寺》红遍了全国,光头小子就多了起来,有的女孩也剃了光头。三毛、文革、张永、曹七、曹臭妮都拜了师傅,学习少林拳,当时师傅不要钱,学拳脚的轮流管师傅吃饭,文革练了有二年,因为串庄去表演,需自行车,家里就一辆还得做生意,武术就放弃啦。看到对越自卫反击战和抗美援朝的电影,文革觉着解放军很威风,歌曲《十五的月亮》《望星空》《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学习雷锋好榜样》文革天天唱,文革就想去当解放军,老师说只有好好学习才能去当解放军,做有出息的人,然后他就好好学习了。
二毛不爱学习,是个拧紧头,捣蛋一个,经常在教室大声放屁,捣乱。放屁时神态夸张,把右手臂伸直,右手成枪状,大声喊着“注意啦,噹噹”,上下齐声,一周的同学就开始捂鼻子,用手煽。有时没屁也这样恶作剧,用手势枪瞄着女生打,吓得女生乱跑。曹老红军的孙子曹兵也和二毛一班,语文老师是他大姐曹红,曹红很严厉,学生都怕他,曹兵更怕,学习不好在家在学校经常被曹红打。这天曹红上课,快下课时,曹红在曹兵后面辅导学生,曹兵没看到,觉着姐姐回办公室啦,就把手一举成枪状,大声喊道“注意啦,噹噹”又放了一个长长的响屁,寂静的教室反响很大,曹红二话不说,扭着曹兵的耳朵走了,屙屎逮着拔橛里,该他倒霉。
小学学校就几口房子,没有墙头院,一片两敞,操场很大,放电影都在这儿,两棵大树就够了。王文革二姐有性子,每次学校操场放电影她占得地方最大,用树枝画个很大的地盘,都是C位,划好的地盘谁都不能占,大人说好话也不好使,想叫谁坐里边她当家,骂架厉害,打架也不怯场。所以看电影总会有空一片一片的,有的人去的晚就看背面,字是反的。那时电影有夹片,开始放无声的多数农业种植类的,还有跑片,这个村放完和其他村再换,有时等很长时间,有时放着放着就吃胶片,电影“吱吱扭扭”就停了,有的电影胶片曾截取过,很多内容就不知道。有时谣言说晚上学校有电影,人们赶紧吃晚饭,到了一看没有,失望的回来,有人问看的啥电影,说是《抬头望天》。那时《傲蕾一兰》《戴手铐的旅客》等都看十几遍。后来公社供销社有了电视,比电影好看,大人小孩都去看,学生不回家,背着书包直接跑去,晚了没地方站,看完电视回家零馒头吃算是晚饭。一看就是三四个小时,《射雕英雄传》《霍元甲》《陈真》多了去啦。王二妮也能给文革占地方,一放学她飞也似的往供销社跑,她把凳子一放,坐下后把腿伸直岔开,就等文革带凳子来找到她时才收回腿,把弟弟揽在怀里看电视。
寒暑假,王老大为孩子们准备了粪箕子,每天都要出去拾,茅房里挖了四个差不多的坑,比一比看谁先拾满。拾粪也有学问,到食品站收猪的地方,到牲口市场。马、骡、驴、牛爱干净,用粪箕子往它鼻子一放,立马就会拉大便,所以赶车拉脚的最怕拾粪的。天冷时,拾粪的沟边河沿、草垛遛着拾,一般是狗粪,下雪时用粪靶子搂着找,木头块也往家拾,草垛边一天会被拾粪的扒好几遍。
现在小孩上学都带水杯或者饮料,那时候也带,大人有的把凉白开灌进酒瓶里带着,一般的孩子带井水。村子两头有两口土井,全村就靠这两口井,大人用水挑子挑几水桶倒进自家水缸里能用好多天,一般是天天挑。
说起打水和挑水也有技巧,打水时用带钩子的绳子勾住水捎(提水桶的铁棍),当水桶贴近水面时,用手左右摇绳然后用力下方绳子,水桶会顺势沉入水里,提上满满的一桶。挑水走路不能死板,硬邦邦的,那样又累又洒水,必须走路顺着扁担的劲扭起来才能又稳又不洒水,当然扭的动作也很优美,桶人合一,既轻巧又稳健。王文革家的水都是他娘挑的,他娘是干活能手,家里外边都是他。
一天用破衣服滥套子换东西的来了,都叫他货郎鼓子,王文革在家里找了破布、旧鞋底换了一根二尺的塑料吸管和糖精,每天就可以拿着自制的高级饮料瓶去上学,上课也可以趁老师不注意偷吸两口。
在学校里有一个下放知青当老师,就住学校里,他家里打了一个压水井,学生经常去他家灌水,井头经常磨断。这位女老师姓丁,和蔼可亲,跟村子里的人都很熟,小孩子都喜欢她,有时去她家灌水把她家的煤饼子踩碎她也不生气,总是说,别急,有水。有次冬天的早晨,王文革口袋里揣着娘昨天蒸的卷子馍,馍凉特硬,下课吃了两口,没水送,噎的文革翻白眼,最后丁老师跑回家倒了半碗茶水才咽下去的。早晨起得早,到八点才放早学,所以很多孩子都揣着馍,也经常找丁老师要水喝。
随着孩子的长大,王老大家房子就有点紧张。王老大就开始着手挑新房,码坯,坯框架是木质长四十公分,宽有三十五公分,用钉子镶的框。和好泥填进去用泥抹子弄实抹平,然后把坯框慢慢取下做下一个土坯。这里和泥要不能太稀也不能太硬,泥稀去了框容易变形,土坯不能用,太硬土坯晒干容易裂,所以要不软不硬,和泥时可以加些麦壳或者碎草掺进去,这样会更结实。土坯打好要晾几天,这几天就要把石头、梁、门窗找木工做,用苇箔和用苇子扎把子备用。还有丁、扒锯子、绳都应备齐,准备几块砖,看好日子,放鞭炮,就可以动工。
这天王老大一大早把篱笆子拔了,用铁锨把屋底子铲平,王老二拿着木橛子、锤子、线开始放线定点,定好点后兄弟两找了一块大点的石头用绳子捆四个一米左右的木棍开始行夯,口里“一二”喊着号子,一起一落的沿画好的线夯,一早上就过去了。中午铺基石,基石是技术活,王老二当仁不让,铺的平整有样,知道哪里必须用大石块,哪里可以用下脚料,三间房到第二天下午才铺好。镶上门框开始上土坯,垒好一层要覆一细层土,直到把土坯用完,没有土坯就和泥用泥直接挑,把麦壳与泥和均匀,王老二在墙上接,老大在下面和泥往上挑,一挑一接配合有默契,两三天就把框架弄好。上梁、上脊是就在找两个人,这时要放鞭炮,然后把之前准备的砖、梁、脊轮、苇箔几个人配合着安放在房顶,最后用麦秸用水澌一下整齐地铺在屋顶,脊顶用脊瓦压住,以用房萡子把房子隔开几间。
没有十天半个月是弄不好的,忙了半个多月总算弄好了,王老大又把篱笆子用玉米秸和棉材围好,大门用两个粗的长树枝插上,中间留出二米的门,门是草苫子的,用细铁丝当锁缠到门框上就行。没有小偷,也没啥偷得,可以说夜不闭户。
农村喜事忧事都喜欢请喇叭班,晚上还唱戏,有钱的主就唱好多天,演员们化妆穿戏袍马靴。听戏是大人的最爱,吃过晚饭就会及早的到地方,大人听得入迷,有的小孩骑在大人脖子上,抱着大人的头就睡着啦,有的抱着孩子听戏,累了就放自己脚边,有的小孩不知啥时候就在脚边爬到外边去了,锣鼓家伙震耳欲聋,孩子在外面哭也听不见。特别《老包砸美》那黑头唱的声嘶力竭,秦香莲的凄苦连连听的人挪不开步子,早把孩子忘了,只有到结束才想起孩子来,听吧,小狗小猫小五小八的找孩子。
听戏一般翻来覆去就这些,《喝面叶》《打金枝》《秦香莲告状》等。有时在地里干活回家的路上也能听到有人唱几句,村后的王大头就喜欢唱黑头,还有模有样,唱的也不赖,他说有时累啦嚎几嗓子就会轻松很多。曹七的娘唱《喝面叶》中的女角“哎呦,哎呦”叫的着实让人怜惜,听说当闺女时学过几天,有时干活时队长让她唱两句,给大家放松一下。
生活就这样,逝去的都是美好的,回忆都是满满的,仔细想想很多都是屁大点事,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感觉有很多事做得不到位有好多遗憾。其实时代一直在进步,人的欲望和追求也在变化,就像现在的人白面馒头吃腻了又想吃玉米面啦,肉吃腻了想吃青菜啦,这不是后退,而是人们的品味高了,知道吃什么对身体好了,衣服露屁股的是流行的啦,露的越多越流行越时尚,这品味一般欣赏不了,可能是追求回归自然吧,原始人就不穿衣服。孩子们手机在手比亲爹还亲,门都不愿出,别说和小朋友玩游戏,一般的体育运动都不行,有的还戴着俩饼好像知识多渊博似的胖的路都走不成个。现代化的社会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和精神追求也发生变化,过去的只能相传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们口中,毕竟那是落后的时代,但想起来还是美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