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石岸书】
对于最新上映的《异形:契约》来说,我们走进电影院,是去看什么?
废话,当然是去消费。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异形》系列电影既是科幻片,也是恐怖片。类型片总是与一定的消费群体和消费口味对应起来的,《异形:契约》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满足了这两种类型片爱好者的消费期待。去消费,绝对值。

不过八十多岁的导演雷德利·斯科特,绝不会仅仅因为要满足世界人民的消费欲而去折腾自己的晚年,这一点毫无疑问。他有更大的野心。这个野心简单来说就是,他要回应万千表情包的玩家们常提的搞笑追问:我是谁,我从哪来,我要到哪去?
当然了,最令人感兴趣的,还是电影里的“异形”形象,追溯异形的历史,或许会有助于我们理解这部最新科幻力作。
外星生物大规模入侵电影屏幕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冷战初期的1950年代,冷战的对立、妖魔化的意识形态,以及这种对立和妖魔化所渗透的恐惧,被成功地转化到对不明生物的想象之中,于是这些丑陋恶心恐怖的不明生物,某种程度上暗含着美国主流文化抹黑共产主义的意图,例如《来自宇宙的危险》(It Came from Outer Space,1953)和《块团物》(The Blob,1958)等。
当然了,对人与非人的分类,在西方殖民主义的文明论话语中就已经被无数次实践过了。曾经,欧洲人认为非洲人和美洲人(甚至也包括亚洲人)不是“人”,例如,一个16世纪的英国探险家竟然恐怖地把南美洲的印第安人黑化成“眼睛长在肩膀上,嘴巴在胸脯中间。”总之,冷战意识形态和殖民意识形态叠加在一起,构成了我们理解这些荧幕异形的坐标。
1979年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的《异形》(Alien)第一部的诞生也要放置在这样的谱系之中来参照。但是,稍微不同的是,到了1970年代后期,由于冷战的缓和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推展,“异形”所涂抹的这些意识形态色彩也不那么显然了,有时,“异形”变得可爱搞笑了,代表性的作品当然要数1977年上映的《星球大战》(Star Wars)。
这部电影里有一个场景:在一个酒吧里,来自各个星球的各种各样异形聚集在那里,稀奇古怪丑陋不堪,但却新奇有趣毫不可怕。在全球化想象中,异形被奇观化,或者说被后现代化了,这一点延续至今。某种程度上,这种影像暗示着,经由这种全球化叙事,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也被裹挟其中,通过奇观化的方式消融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异质性。而这种变化,与1970年代后期所展开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成功地把社会主义阵营裹挟其中进而击垮苏联的世界史进程隐秘呼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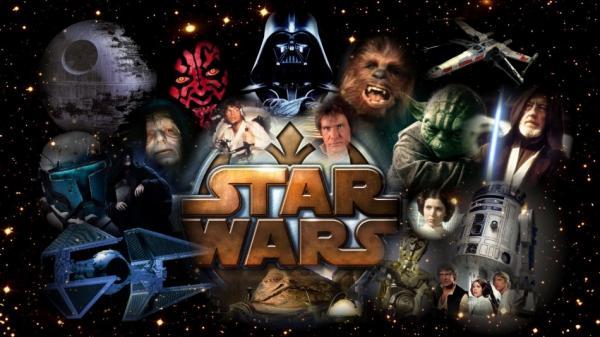
《星球大战》系列与《异形》系列关系密切。1977年的《星球大战》里有三类角色:异形、人类和机器人。但三者关系相当融洽,机器人R2和C-3PO都呆萌可爱,忠诚于人类,而异形则与人类“大杂居小聚居”,互相之间习以为常。
1979年的《异形》则故意反其道而行之,机器人看似忠诚于人类,实则包藏祸心,相当“反人类”,而异形则延续了冷战中的意识形态化的形象特质,极其恐怖,以人类为食,但异形必须寄生人体才能孕育,机器人又是人类的造物;总之,三者之间相爱相杀,这种复杂关系一下子把《星球大战》中的圆满自足的幻想颠覆了,从而开创了迥异的影像风格。
这种独特的影像风格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异形》暗含着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批判意味。电影里最大的幕后黑手是维兰德公司,这是一家资本极其雄厚的跨国垄断巨头,为了公司利益,它不惜以人类生命为代价来保护异形。“异形”的恐怖食人的形象隐喻着资本主义本身。
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马克思主义的“异化”(Alienation)理论:资本主义使一切都异化了,经济、政治、文化各个层面都处在日益加剧的自我异化之中。于是,异形这个“漂浮的能指”有了双向含义:一方面异形的影像谱系包含着黑化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异形又用来批判资本主义本身。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想象中,外部批判逐渐消失,一切批判都逐渐转变成为自我批判。
《异形2》(1986)、《异形3》(1992)和《异形4》(1997)都并非雷德利·斯科特所执导,且本质上并没有新的开拓。反倒是1982年斯科特执导的《银翼杀手》(Blade Runner),与他在2012年推出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和如今上映的《异形:契约》(Alien:Covenant)关系更为密切。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初潮与新兴的计算机/网络工程、生物遗传工程等新科学携手同行,此时冷战结构及其意识形态已经松弛而乏味,资本主义阵营曙光在前、胜利在望。《银翼杀手》的诞生与此密切相关。这部电影讲的是,在全球化和高新技术已经高度发达的未来,人类杀手德克追杀仿生人的故事,最后发现,德克自己也是仿生人。电影中一个关键情节,是人如何甄别仿生人,但讽刺的是,甄别者自己其实就是仿生人,这暗示着人与仿生人之间的复杂模糊的关系,于是,“什么是人,如何定义人”诸如此类的形而上问题,就成为这部电影的内核。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后人类”的问题,这个“后人类”的问题30年后成了我们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核心问题。而当斯科特把具有复杂意识形态含义的“异形”和“后人类”问题组合起来的时候,激发了更多可能的想象。
2012年的《普罗米修斯》是异形前传,讲述维兰德公司派遣的科研飞船去宇宙追寻人类的起源,结果发现人类的造物者试图用“黑水”(一种能改变基因创造异形的感染源)来毁灭人类,事实上,人类就是造物者利用“黑水”创造出来的。最终人类反抗,造物者被人类诱入异形的魔爪,异形强行寄生于造物者,并孕育出新的异形,即《异形》第一部中的异形形象。而《异形:契约》则又是在《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发生之后,科研飞船来到造物者的星球,但造物者的星球早就被黑水所感染,造物者的族类被灭绝,科研飞船的到来,只是又一次狼入虎口的旅途。

《普罗米修斯》中的异型
整个故事有着宏大的世界观,值得细细发掘。关键点之一是异形、人类和仿生人的复杂关系。由于将《银翼杀手》的问题意识引入到异形系列之中,《普罗米修斯》和《异形:契约》不但试图质询人与仿生人的边界,也试图质询人与异形的边界,从而彻底动摇我们作为“人”的坚定信念。
两部电影里都有一个智慧超群、永不衰朽的仿生人大卫(迈克尔·法斯宾德饰),他逐渐生成了独立意识,并且认为人类是注定要被淘汰的物种;他借助黑水的力量,从被造物者一跃而成为造物者,他要创造新物种,并不惜以人类和人类的造物者的灭绝为代价;他成了“超人”,他也着迷于创造“超人”,将此视为唯一有意义的事业。大卫是站在造物者的角度来审视人类和异形的,在他眼里,人类和异形都是“黑水”的造物,他们非但平等,而且异形要优越于人类。
如果说《异形》前4部的主角都是人类女性,而《银翼杀手》尽管是讲述人与仿生人的关系,但主角仍然一度被设定/误解为人,因而故事仍是围绕着人类男性和他的视角所展开的故事,那么到《异形:契约》中,真正主角则成了仿生人大卫,大卫的视角,有力地促进了整个叙事的推进和主题的深化。
主角的转移,是视角的转移,也是一种权力关系的转移,还是一种世界观的转移。如果说,《异形》前4部在于暗示人类女性象征的感性、爱是人类之所是的区别性特质,从而高于异形和仿生人,那么《银翼杀手》则颠覆了这种判断,因为仿生人与人类在这一点上并无区别,而到了《异形:契约》里,人类、仿生人与异形,都被放置在一个平行乃至颠倒的序列中了。
现在,我们可以了解《异形:契约》的“后人类”主题是如何从冷战意识形态的符码游戏中一步步发展出来的。冷战结构及其意识形态孕育了异形,并赋予异形以复杂的内涵,而随着资本主义1970年代后期以来在经济、科技和文化上的新的革命,冷战结构日益松弛并最终瓦解,“异形”形象被成功地置换到新的历史条件下,并被赋予新的内涵。使冷战终结的力量,某种程度上也是使“后人类”问题获得尖锐性的力量。
我们或许会幻想,如果我们把《异形:契约》从“后人类”的问题语境中抽离,移置回冷战前期,这部电影能否获得新的阐释的可能,并激发新的政治想象?那时的人们是否会因为异形与人类的奇特并置而重新思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历史不能假设。况且,在今天,还有什么是不能消费的?这让我不禁想起,《异形》系列以女性为主角可以说是彼时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的成果,而今天,一则豆瓣评论戏谑地说:“我已经不记得上一次看主角团这么蠢且女主角这么丑的片子是什么时候了……”这则评论获得了全部评论第五多的“赞”。
多说一句,上文提到的1950年代的电影里,《来自宇宙的危险》中的恐怖的独眼外星人,成了《怪物公司》(2001)里的小可爱,《块团物》中通过食人而不断膨胀的恐怖的肉球,而今已经成了“球球大作战”游戏里的主角,小朋友和青年人在稚嫩的喊叫和粗鄙的叫骂声中玩的不亦乐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