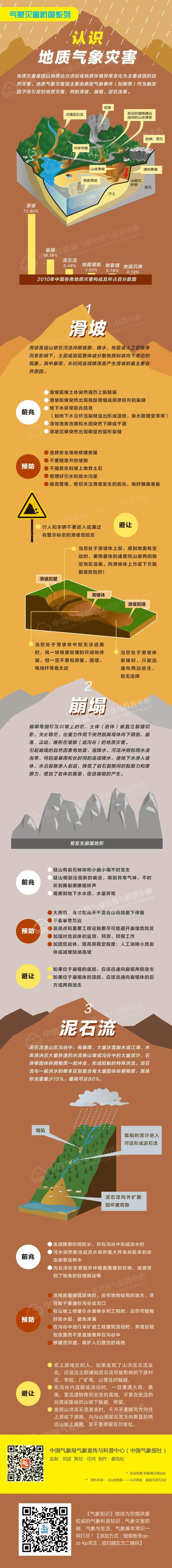多年来,人们孜孜不倦地研究驱使价格波动的逻辑,用一个个数学模型搭建成了精巧庞大的现代金融大厦。
20世纪上半叶,巴舍利耶在默默无闻中以十足原创性的眼光,观察到自然界的热扩散与金融价格波动之间的相似性,他的债券价格概率方程式与爱因斯坦在布朗运动基础上发展的等式存在奇妙的关联。以价格遵循随机游走、公平博弈的观点作为中介,高斯的正态分布曲线开始被用于金融市场分析,进一步发展便是尤金·法玛的有效市场假说。
马科维茨将方差和标准差纳入风险和收益的表征。夏普致力于衡量市场整体和个股的贝塔值和资本成本,并据此简化了马科维茨的投资组合,还有包括林特纳、莫辛在内的经济学家各自独立研究了类似的思想,后来成了被广泛运用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
风险既然可以计算,便可以用来套利。在布莱克、斯科尔斯、默顿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人们将德尔塔、隐含波动等术语纳入金融市场研究的日常语言。根据他们的公式建立了自动套利模型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一度如日中天,却在9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成为刻进教科书的惨败案例。
这座现代金融大厦看似精巧,却时现各种漏洞,人们不停地在事件发生后发展新的模型来查缺补漏。曼德尔布罗特干脆推倒了这座大厦的根基,人们一定是理性的,只以变得富有为目的吗?同样的赔率和胜率,换一种表述,人可是会做出不同选择的耶。无论在上升趋势还是下跌趋势中,理由从来不缺,有不同投资目的的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价格自然不是连续变化的,基于各种理由的各种跳空都很常见,好像也不完全服从布朗运动,因为用标准差表示的道指变化明显比用标准差表示的布朗运动要狂野——存在更多偏离幅度更大的极值。这意味着莫名其妙的大涨或大跌出现的频率比我们想象得要更高。
理论上,我们可以假设这些少量的不规则异常值不足以摧毁学者们的系统工作,现实却是极端异常值暴露的系统性缺陷,让无数投资者死无葬身之地。考虑到人类基于习惯和便利的懒惰性,错误、旧秩序的持久性往往会超出人们的估计。
如此狂野的价格波动简直是门玄学,放到大自然的视角则并不那么突兀。在数学的诠释介入之前,达·芬奇便在笔记里写下河流的狂暴能量带来的巨大破坏,遍布世界各地的洪水神话更说明人类不得不以身家性命直面着自然界无以言表的极端异常值。

△ 转引自《市场的(错误)行为》
正如洪水来了又去了,大的灾难总是会得到修复,市场的灾难也是如此,当然人们不会把泡沫当成灾难,但是超常的涨幅与跌幅一样会得到修复。市场、人类社会与大自然,都自有其基本趋势。具体形势千变万化,但是狂野变动与基本趋势总是存在的,面对现代金融大厦,曼德尔布罗特的分形结构另起地基,第一次将人们在理论中试图忽略的令人讨厌的不完美、不规则与粗糙度纳入体系中。
在充斥着异端与异象,极值随时可能出现的日常中,作为个体,我们没有一定能确保自己登上方舟见到来日晨曦的方法,毕竟时也命也,外在条件很多时候并不受大部分人控制,当下的环境足以令我们深以为然。
我们可以做的,不过是在可选择的范围内,尽量避免作死而已,用投资的术语来讲,就是风险第一。从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到波普尔的可证伪性,再到芒格所言,通过避免过不幸的生活来接近幸福,这种一脉相承的否定性智慧,不恰恰都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广阔世界里,真诚地承认人类的不完备性吗?

△ 《瓦尔登湖》
时刻警惕风险第一。价格狂野无匹,市场波动无常,盈亏分布极其不均衡,巨大的盈亏集中在较小时间内,甚至市场内的时间是可变的,你很难判定一天的风险比一年更大还是更小,分形的概念不恰恰是每一小部分重复着整体的结构吗?从这个角度看,任何一个标的与任何一个时间也许都是相同的,事前都具有十足的不确定性,事后都呈现出十足的基本趋势。
如果市场注定不确定,那么极端泡沫与极端熊市反倒都是必然的,这使预测变得危险。如果狂野价格造成了估值在巨大区间波动,那么价值这个概念反倒有其局限性,一不小心便令自秉谨慎人士掉进估值陷阱里。面对顶或底的断言,市场有一万种打脸的方式,当你看到十倍机会的时候,搞不好是阿鼻地狱。
价格狂野作妖时,我们以何面对?以沉默,以眼泪。开玩笑的(不是)。一方面,比起对价格的预测,判断波动在上升或降低的概率或许是一种更合理的工作,如若长假期间美债和汇率企稳,短期股权市场继续大幅单边波动的风险是降低的。
另一方面,前提中的前提,只要规避了全军覆没的极致风险,资产的波动是我们参与其中时本应面对的。假期还是要快乐,无论是什么名义的假期,无论是否夹缝中的快乐。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