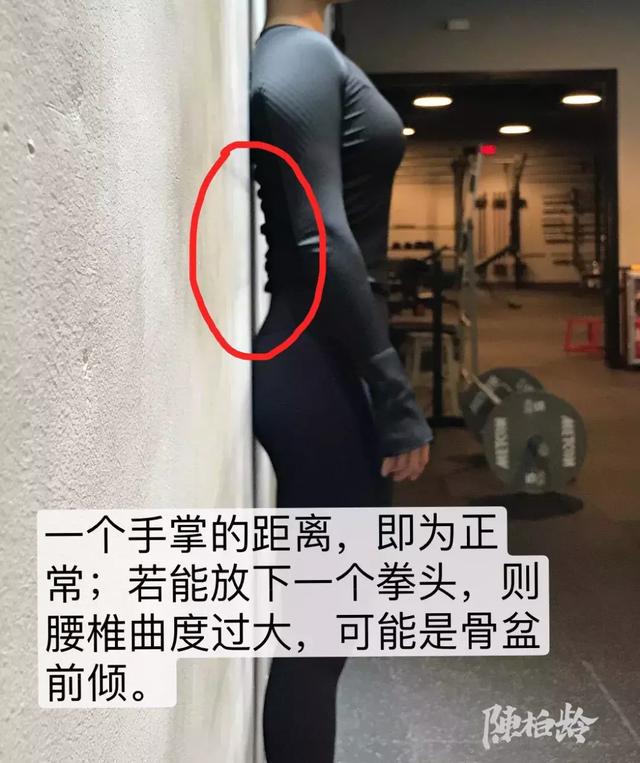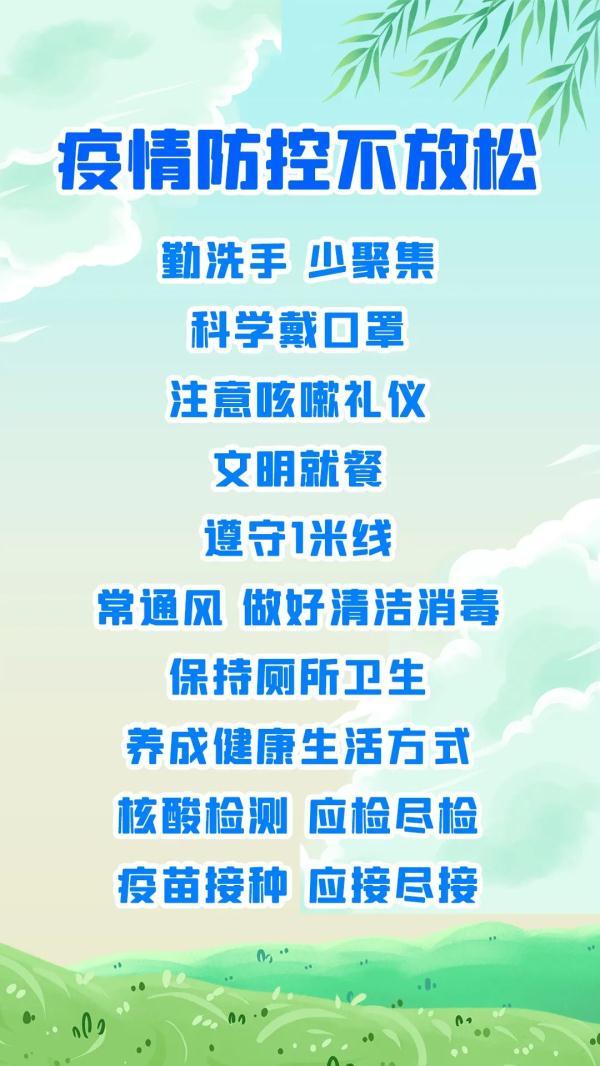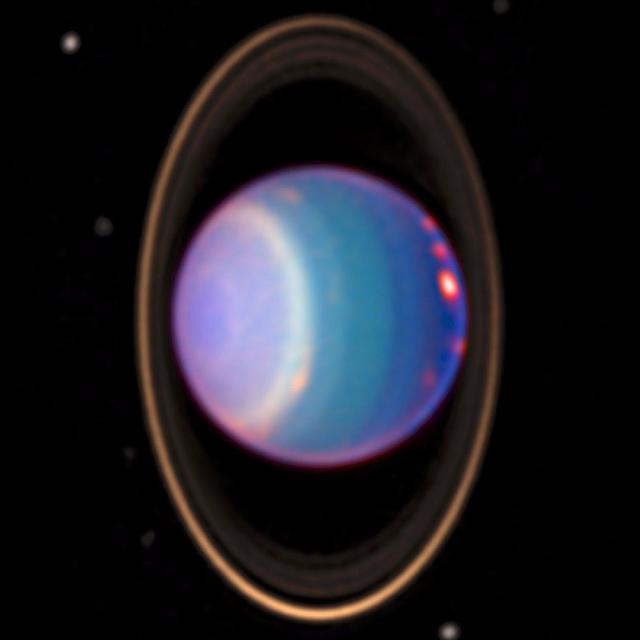就世界各敦煌遗书收藏单位的收藏而言,原中央图书馆收藏的这批遗书始终在人们的关注中。早在一九六○年代初,由王重民先生主持编纂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在其第四部分:「敦煌遗书散录」中共收入散藏敦煌遗书目录十九种,排在第一位的,赫然就是《前中央图书馆藏卷目》。该《前中央图书馆藏卷目》据《中央图书馆甲库善本书目录》,共著录敦煌遗书六六号。因其中一号下有包含两卷、三卷或者附有残叶者,故实际共计著录敦煌遗书七三号并附残叶两纸。
《中央图书馆甲库善本书目录》完成以后,该馆所藏敦煌遗书续有增加。一九六七年,潘重规先生对馆藏「敦煌写本百五十余卷」逐一审核、著录、编目,发表在《新亚学报》第八卷第二期。接着,又于一九七五年对原目录作了较大的修订,即「依书目(指《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增订本〕——引者注)次第,重编〈题记〉,增载吴君(指吴其昱先生——引者注)之说,并采馆方记录,添注卷子幅度。写定刊布"。潘重规先生把这一修订稿命名为〈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题记〉,发表在一九七五年《敦煌学》第二辑。该《题记》共计著录馆藏敦煌遗书一四四号(其中含日本古写经三号四件)。与《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对每号遗书仅有寥寥数语之介绍不同,《题记》对每号遗书的经名、卷次、译作者、抄写时代、纸张、纸数、行款、界栏、框高、内容起讫及其与《大正藏》本的对照、避讳字与武周新字,乃至该遗书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的编号等各种相关信息,均作了较为详尽的著录。如前潘重规先生自述,该《题记》还著录了馆藏对某些遗书的一些信息(包括来源信息与庋藏信息),著录了吴其昱先生对某些卷子的相关意见。长期以来,潘重规先生的《题记》成为人们了解馆藏敦煌遗书的主要依据,成为敦煌学研究者利用这批敦煌遗书的导航。
《敦煌学》第二辑还刊登了吴其昱先生的〈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敦煌蕃文写本佛经四卷考〉,石田干之助先生撰、邱棨镕先生译的〈台北图书馆所藏敦煌古钞目录〉,牧田谛亮先生着、杨钟基译〈台北中央图书馆之敦煌经〉等,使《敦煌学》第二辑成为馆藏敦煌遗书的研究专辑。此后,不少先生又在《敦煌学》及其他著作、刊物中,发表有关馆藏敦煌遗书的新的研究成果,有关资料可以参见郑阿财、朱凤玉两位先生,及其他诸位先生编著的各种敦煌遗书研究论著目录,此不赘述。
我这次编目,不同程度地利用了王重民先生、潘重规先生以及其他诸位先生的研究成果。在此特向诸位先生的辛勤劳动表示深深的敬意。
一、遗书编号与叙录体例
此次承馆方邀请,依据原件对馆藏敦煌遗书及日本古写经再次鉴定并重新编目,纂为叙录。在此先介绍该语录的编号与体例:
(一)遗书编号
馆藏敦煌遗书,除了前述《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给的「总目号」外,尚有馆方所给的「登记号」与「索书号」,此外还有潘重规先生〈题记〉所给的「潘目号」,共计四种。
此次编目,为了既便于读者查阅、又便于馆方管理;同时考虑到原有四种编号中的「总目号」、「潘目号」、「登记号」等三种都未能将馆藏敦煌遗书全部纳入,唯有该馆目前用来对馆藏敦煌遗书重新给号,以与其他收藏单位的敦煌遗书及该馆前此的四种编号相区别。
「台号」从「台○○一」起,到「台一四二」止,将馆藏敦煌遗书共编为一四二号。又,此次编目按照馆方的意见,将馆藏七件日本古写经作为附录一并纳入。为与馆藏敦煌遗书相区别,故以字头「台附」为标志,从「台附○一」到「台附○七」,共计七号。本文把上述以「台」、「台附」为字头的编号,称为「主编号」。如上所述,此次共计著录主编号一四九号。
为了体现敦煌遗书的文物特征,也为了便于馆方管理,著录时需要把每件独立的遗书单独编为一号。但由于种种原因,收藏单位有时会在一个编号下纳入几件形态相互独立的遗书,该馆也不例外。遇到这种情况,编目时为了既不打乱馆藏原编号次序,又能将各自独立的遗书梳理清楚,一般采用在主编号后附加「A、B、C......」等字母的方式,为各独立件分别给号。我把由此形成的编号称为文物号。根据馆藏遗书的不同情况,文物号有两种表现形态:一种是馆藏一个主编号中只有一件遗书,此时文物号形态与主编号相同;一种是馆藏一个主编号中包含几件形态各自独立的遗书,此时在主编号后面附加「A、B、C......」等字母,故此时文物号的形态为「主编号A、主编号B、主编号C⋯⋯」等。如前所述,馆藏敦煌遗书共有一四九个主编号,此次共编为170个文物号。亦即馆藏的敦煌遗书与日本古写经,共有170个独立件。其中敦煌遗书的独立件为一六二件,日本古写经的独立件为八件。
一件敦煌遗书上往往抄写多个不同的文献。这些文献或分别抄写在正、反面;或在正面、反面各抄写若干个文献。为了体现敦煌遗书的这一特征,梳理清楚此批敦煌遗书共计抄写了多少文献,我采用《文献号》来区别并著录某遗书上抄写的不同文献。所谓「文献号」,系在文物号后附加「1、2、3⋯⋯」或「背1、背2、背3⋯⋯」等,以表示该文献抄写在遗书的哪一面、及它在遗书正面或背面所抄诸文献中的排列次序。故《文献号》有三种表现形态:如果一件遗书上仅抄写一种文献,此时文献号形态与主编号相同。如果一件遗书的正、背面各抄写一个文献,抄写在正面的文献号形态与主编号相同,抄写在背面的文献号形态则写作「主编号背」。如果一件遗书正面、背面各抄写若干个文献,则按照这些文献在遗书上的先后次序,依次把它们的文献号编为「主编号1、主编号2、主编号3、⋯⋯」,乃至「主编号背1、主编号背2、主编号背3、⋯⋯」等,以此类推。馆藏的170件敦煌遗书与日本古写经,共抄有215个文献。其中162件敦煌遗书共抄写了207个文献,8件日本古写经共抄写了8个文献。故共计编为二一五个文献号。
(二)叙录体例
为便于把有关遗书的各项数据输入《敦煌遗书数据库》,此次编目的初稿,按照我设计的《条记目录》格式编纂。有关"条记目录"的著录规则,可参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 馆藏目录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一六年三月)或大型图录《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一一年九月)末尾所附「条记目录」的有关说明。为避文繁,此不赘述。但本目录正式定稿时,按照馆方要求,将《条记目录》改为《叙录》体。两种目录的文体形式虽有不同,著录内容基本对应。
按照馆方要求,对每个文献撰写一条相应的叙录。故本目录共包括二一五条叙录。诸叙录按照主编号→文物号→文献号这一次序排列。
二、学术价值
在〈谈散藏敦煌遗书〉一文中,我依据敦煌遗书流散史及目前收藏形式的不同,把敦煌遗书分为三类:
第一类,从敦煌出土后,未经过中间环节,直接被收藏单位收藏。
第二类,从敦煌出土后,曾经过中间环节,其后被收藏单位收藏。
第三类,从敦煌出土后,在民间流传,至今依然由私人收藏家收藏。
并将上述第二类、第三类称为「散藏敦煌遗书」。本叙录所著录的无疑为第二类,属于「散藏敦煌遗书」。
我认为,敦煌遗书包含文物、文献、文字等三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因此,评价某一批敦煌遗书,包括散藏敦煌遗书时,应该从上述三个方面作综合的讨论。
(一)文物研究价值
如何评定敦煌遗书的文物价值,不同的研究者可以有不同的观点。我认为,文物价值以敦煌遗书的断代为主要依据,并考察其制作方式、品相、纸张(或其他载体)特点、保存数量、装帧、装潢、栏格、裱补、古代裱补纸、书写主体、题记、印章、现代装裱、收藏题跋印章、附加物,予以综合评价。」 以下参照上述标准,简单谈一下对馆藏一四二号、一六二件敦煌遗书文物价值的看法。
1、抄写年代分布及其占收藏单位总数的比例
中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是世界上收藏敦煌遗书最多的两个单位,共计收藏敦煌遗书的文物号达三一四三四号,馆藏则为一四二号、一六二件。我们可以把上述两个单位所藏敦煌遗书之不同年代的写本数量的分布及其占据总数的比例,与馆藏同类写本的相关数据作一个对比。
两相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东晋写经,馆藏占比约为○. 六%,后两个收藏单位同类写经的占比约为○. 三%;南北朝写经,馆藏占比约为一八. 五%,后两个单位同类写经的占比约为八. 六%;隋代写经,馆藏占比约为二. 五%,后两个馆同类写经的占比约为○. 八%。亦即唐以前写经,馆藏约占据全部藏品的二一. 六%,超过五分之一。而后两个馆同类写经的占比约为九. 七%,不足十分之一。亦即馆藏高古写经所占总数的比例要比后两个单位高出一倍。
2、首尾残况
敦煌遗书大部分残破不全,其中有些甚小的残片。编目实践中,我一般对残片不著录其首尾的保存情况,仅著录为「残片」或「小残片」。而对其他遗书则根据「全」(即保存完整)、「残」(即已经不规则残缺)、「脱」(从两纸黏接处脱落)、「断」(被后人剪断)四种情况,著录其首尾的保存情况。中国国家图书馆与英国国家图书馆的残片、小残片共达一万多号,故下表仅统计其余19441号的首尾保存情况,而馆藏的162件中,亦除去残片、小残片4件,故下表所列仅为158件。
从上述表格中数字的比较,我们可以了解馆藏敦煌遗书的首尾存况也远远优于另外两个单位收藏的敦煌遗书。
3、长度
据统计,不计八件日本古写经,馆藏的一六二件敦煌遗书中,包含大小纸张一五一八张,合计总长度约为六五一. 八米,合计总面积约为170平方米,正反面总计抄写38300余行,合计总字数约72万字。如将八件日本古写经也加入,则上述统计数字为:总计古写经一七○件,包含大小纸张一八六○张,合计总长度约为七三六. 九米,合计总面积约为193平方米,正反面总计约抄写42000行,合计总字数约77万字。
如果仅计算每件敦煌遗书的平均长度,则因馆藏一六二件敦煌遗书的总长度为六五一. 八米。故其每件敦煌遗书的平均长度约为四. 02米。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总长度为三四六○七. 0九米,编为17337个文物号。故其每件遗书的平均长度约为2米。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长度为二四○二一. 四九公尺,目前编为一五一三四个文物号,故其每件遗书的平均长度约为一. 五九米。
4、长度达八公尺(含八公尺)以上的遗书及其占总数的百分比
在编制敦煌遗书定级国家标准的过程中,通过调查研究,我们认为将每个独立件的长度定为八米,作为敦煌遗书定级的参考指标之一,是比较适宜的。
按照这一指标,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七三三七件敦煌遗书中,八公尺以上写卷共有1032件,约占写卷总数的六. ○%。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五一三四件敦煌遗书中,八公尺以上写卷共有八三五件,约占写卷的五. 五%。馆藏的一六二件敦煌遗书中,八公尺以上写卷共有二四件,约占写卷总数的一四. 八%。
在《谈散藏敦煌遗书》中,我总结了散藏敦煌遗书的若干特点,其中之一为:一般来说,散藏敦煌遗书的长度较长,保存状态较好。馆藏的敦煌遗书也符合这一特点。这主要是由于敦遗书是古代寺院的弃藏,绝大部分遗书断头残尾。散藏敦煌遗书大都是人们从这些残破遗书中挑选出来的。虽然这种挑选,实际不过是矮子里拔将军,所以绝大部分散藏敦煌遗书依然是残破卷子。但散藏敦煌遗书毕竟是矮子里拔出的将军,它们的长度、保存状态都要比第一类没有经过中间环节直接进入收藏单位的遗书为好。
散藏敦煌遗书的另一特点是往往经过现代装裱,有现代人收藏鉴赏题跋、印章等。馆藏敦煌遗书,有的曾经袁克文、许承尧、魏忍槎等著名收藏家收藏,有的且有若干名人题跋,殊为珍贵。特别值得提出的是:
台○二七号,为《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八。卷首下有一枚枣红色方形阳文印章,二. 五×二. 五公分,印文难以辨认。但卷面有正方形阳文硃印共六枚:其中三枚七. 五×七. 五公分,印文为「觉皇宝/坛大法/司印/」。另三枚八×八公分,印文第一行上为星状符印,下有「斩邪」二字;第二行为符印;第三行上为符印,下有「田田田」三字。这一印章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亦有发现,疑或曾被道士王园禄用来作为做法事之道具。
台○九六号,为《十地经论》卷一。扉页有六行题跋:「六朝人书《十地不动论》卷子。/敦煌莫高窟所出六朝隋唐人书伙矣。/古籍固罕,若经论、经疏亦鲜于写经。/此《十地不动论》确为北朝人书。卷末有/'一姣(校)'二字,殆书者之名也。据此以校大/藏,胜于经典远矣。乙丑(一九二五)冬月,克文。/」跋前上下有二枚印章:(1) 一. 二×一. 七公分,印文为洹上寒云。(2) 一. ○×一. 0公分,印文为「双爰庵」。故知该卷曾为袁克文珍藏。该卷现代已修整,接出绸面护首,特别是卷尾后配细长白玉轴。此种白玉轴因极易断裂,故制作困难,极为珍稀。本人虽已经考察过数千号流散敦煌遗书,此类细白玉轴,至今仅此一见。
如前所述,敦煌遗书的文物特征体现在诸多方面。虽然馆藏敦煌遗书的数量不多,但年代涵盖了从东晋到北宋初年,基本体现了敦煌遗书已有的各时代的主要纸张乃至题记、印章、杂写的多种表现形态。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可以让我们从小见大,大体把握敦煌遗书的总貌。其历经文人墨客、社会名流珍藏的历史,又为它们增色不少。限于篇幅,本文对这批遗书的文物特征的进一步解说暂且从略。
需要指出的是,馆藏敦煌遗书,除了台一一九号尾部题记可疑外,未发现伪卷、伪题记。我们知道,散藏敦煌遗书中经常可以发现涉伪卷子,包括通卷作伪、部分作伪、在真卷子上添写伪题跋、将真卷子截头去尾相互拼接等等。从这一点讲。馆藏的敦煌遗书在诸散藏敦煌遗书特藏中可称翘楚。据有关资料,当年收购这批敦煌遗书时,大多经过徐森玉、赵万里两位先生把关。从馆藏遗书现状可知,两位先生的鉴定工作对这批遗书的质量保证起到极大的作用。
(二)文献研究价值
所谓文献价值,首先考察这些敦煌遗书上所抄写的文献,哪些有传世本,哪些前此不为人们所知。其中,那些前此不为人们所知的文献,自然具有更高的研究价值。但即使已有传世本者,如果敦煌遗书写本与传世本文字有不同,则亦有一定的校勘价值。
馆藏一四二号敦煌遗书,共抄写二○七个文献,今编为二○七个文献号。大体情况如下:
1、一二○号文献有传世本,已经保存在古代大藏经中,约占文献号总数的五八%。
2、二五号文献虽未被古代大藏经收入,但敦煌出土后,被日本《大正藏》录文,收入第一九卷、第二一卷、第八五卷等卷,约占文献号总数的一二. 一%。
以上两类,共计文献一四五号,现均可在《大正藏》中查到相应的文本,约占馆藏敦煌遗书文献号总数的七○%。经过初步考察,上述一四五号中,馆藏文本有四六号均与《大正藏》本有差异,或为异卷、或为异本、或行文有差异,可供校勘。这部分文本约占《大正藏》所收文献号总数的三一. 七%。
3、虽无传世文本,但前此研究者已有录文、整理者,计四号,分别发表在《藏外佛教文献》、《敦煌佛教经录辑校》、《七寺古逸经典研究丛书》中,约占文献号总数的一. 九%。
4、无传世文本,前此亦从来无人录文、整理,但被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推出的《电子佛典集成(二○一六版)》收入者,计二五号。约占文献号总数的一二. 一%。唯这一批录文尚为初稿,还需修订。
5、道教文献三号,已收入《中华道藏》。约占文献号总数的一. 四%。
6、此次编目,共重新录文三十号,约占文献号总数的一四. 五%。但其中《电子佛典集成(二○一六版)》已有录文者一八号,《敦煌佛教经录辑校》、《大正藏》已有录文者各一号,完全属于新录文者仅一一号,新录文约占文献号总数的五. 三%。
7、无传世文本,至今仍未录文、研究者,尚有一九号,约占文献号总数的九. 二%。
综上所述,馆藏207号敦煌文献中,有传世本者为120号,约占文献号总数的58%,无传世本者为87号,约占文献号总数的42%。如前所述,在有传世本的一二○号文献中,尚有四六号可据敦煌遗书校勘;而另外的八七号文献,则全部是敦煌遗书提供给我们的新资料。这八七号文献,不少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并作了初步研究,亦有部分至今未为研究者所关注。已经作了初步研究的文献,依然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所以,馆藏敦煌遗书是值得研究者进一步发掘的宝藏。
此处仅就编目所及,介绍几件重要的遗书。
台一二七号,《遗教法律三昧经》卷下
该首残尾全。现存一一纸,六行。有尾题惟教三昧下卷。因历代经录中并无与此对应的经名,故前此有研究者将尾题中的「教」字读为「务」,认为该经或为历代经录著录的《惟务三昧经》。
按:《惟务三昧经》,最早见录于《出三藏记集》卷五,作:「《惟务三昧经》,一卷。(或作《惟无三昧》。)」属于道安著录的二六部伪经之一。后隋《法经录》把它归入真伪难辨的「疑经」。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则将它作为失译经,直接收归入藏。《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则继承道安的著录,将它判为伪经,故此经此后失传。但馆藏此文献并非《惟务三昧经》,实为「《遗教法律三昧经》」,又称「《遗教三昧经》」,台一二七号尾题中之「惟」,实乃「遗」字之误。后唐景霄纂《四分律钞简正记》卷十五称:「《遗教法律经》等者,行古引经,许着五大色之失。亦名《遗教法律三昧经》。〈文〉此经明五部,各着一色。」 宋允堪述《四分律拾毗尼义钞辅要记》卷一称:「⋯⋯《遗教法律三昧经》,古师引此经,便许着五大色衣。」 台一二七号正有五大部「着五大色衣」的内容。可证它实际是失传已久的《遗教法律三昧经》。
《遗教法律三昧经》,最早见录于隋《法经录》,列为众律疑惑。其后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六著录,谓「见《始兴录》」。并称:
西晋惠帝世,沙门释法炬出。初炬共法立同出。立死,炬又自出。多出大部。与立所出,每相参合,广略异耳。《僧祐录》全不载。既见《旧》、《别》诸录,依聚继之。庶知有据,以考正伪焉。
隋彦琮《众经目录》亦仿照《法经录》列为「疑惑」。但《大唐内典录》接受费长房的观点,把它作为法炬翻译。《大周录》继承这一观点。《开元释教录》在卷二「法炬译经录」中著录了这部经典,但在卷十八的「伪妄乱真录」中又称:
《遗教法律三昧经》,二卷
右按长房等代录及失译录,俱有此经。既并无本,诠定实难。且各存其目。(撰录者曰:「此经余虽不者见全本,见所引者,多是人造。」 )
也就是说,唐智升当年已经未能见到该经的全本,他所见到的,只有其他典籍中的引文,他据那些引文对该经进行真伪判定,认为「多是人造」。但智升的观点,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同。如前所述,后唐、宋代的律宗僧人,均有继续引用该经的。
今天,我们有幸看到馆藏的该六世纪写本,且下卷基本完整,甚为可贵。从内容看,该文献虽然被命名为「经」,但论述的是戒律。所以《法经录》把它列入「众律」是正确的。按照《历代三宝记》的记载,该文献为西晋所译。这也反映了中国早期佛典翻译,未能正确辨析经律论的历史事实。此外,我们现在看到的台一二七号的文字,的确甚为质朴,呈现的也是早期译经的形态;从其内容察看,该文献的不少内容完全属于对印度佛教的叙述,恐非初传期中国佛教信徒所能杜撰。所以,智升在没有得到原本的情况下,仅依据引文便将本文献判为「伪妄乱真」,恐怕有点草率。
不管怎样,台一二七号的出现,为我们研究印度部派佛教、部派佛教戒律、中国早期佛教戒律、早期译经、中国人的疑伪经观都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值得深入研究。
台○九七号1,《论佛性如来藏义》(拟)
这是一件三阶教经典残卷。原卷虽首脱尾全,但无尾题,故该文献原名不清,在古代三阶教经典目录《人集录都目》中是否已有著录,亦尚需考订。叙录所著录为拟题。该文献最早由日本学者西本照真发现,录文后发表在他的《三阶教の研究》中。此次依据原卷再次录文。
三阶教是隋信行创立的佛教宗派,历史上曾经屡次遭到镇压,但屡踣屡起,最终约消亡在「会昌废佛」的浪潮中,该教的典籍也由此损亡殆尽。所幸的是,敦煌遗书与日本古写经中保存了一批三阶教典籍,它们证明古代三阶教曾在敦煌流传,也为我们今天研究三阶教这一已经消亡的佛教派别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台○九七号1的主题是论佛性如来藏,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从竺道生之后,除了法相唯识等个别佛教派别,「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理论可说已经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追究其原因,我认为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人之初、性本善」,以及中国儒家提倡的「人皆可为尧舜」不无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该文献在论述佛性及其作用时,采用了「体」、「相」等范畴,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否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似乎可以进一步探讨。特别是在中国佛教主体性受到挑战的今天,印度佛教到底是怎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逐步演化为中国佛教的?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有什么相同,又有什么不同?中国佛教有无自己独立于印度佛教的主体性?如果有,我们应该如何定义与描述这种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又是如何形成的?如此等等,台○九七号1都可以成为我们探讨的对象。近些年,我比较关注禅宗研究。禅宗的源头,固然追溯到达摩东来,但禅宗的发展与其他派别互有交流。其中禅宗在理论与行法两方面,与三阶教是否也存在一定的交流,就是一个颇有兴味的问题。
禅宗向来被人们认为是佛教诸派别中,中国化程度最深、最有代表性的佛教派别,也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宗密的《禅源诸诠集都序》作为对早期禅宗的总论性著作,一直为研究者所重视。台一三一号1就是《禅源诸诠集都序(二卷本)》的一个抄本,虽然属于兑废稿,依然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前此,冉云华先生曾对该号做过研究,现在看来依然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此外,台一三一号2之《大乘禅门要录》是目前所知的有关宗密的论著目录,对宗密研究具有相当大的价值。关于宗密的《禅源诸诠集》及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大量早期禅宗资料,我曾经有专门文章论述,主张宗密所编的《禅藏》可能传到敦煌,其若干残余,可能保存在敦煌遗书中。这也是一个可以再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馆藏敦煌遗书还包括了经钞、经论疏释、净土信仰、密教、佛教戒律、歌赞、礼文、讲经文、押座文、设难文、木捺佛像、白画、乃至多种疑伪经,此外还有道教经典、官文书、私文书等等,真可谓美不胜收。我相信,随着这批文献的公布,学术界对馆藏敦煌遗书的研究会大大向前推进,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
(三)文字研究价值
如前所述,这批敦煌遗书的年代跨度从东晋到宋初。本图录的出版,能够清楚地反映出这一时间段中国文字形态的演化历史。其中的古字、异体字、武周新字等,文献中出现的各种修订符号等,可以丰富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文字、文献的知识,并提供从事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总之,图录本身会用最直观的方式将上述种种告诉读者,故无需笔者再加饶舌。
(四)关于日本写经
本图录收入日本写经七号八件。其中《史记》卷二、《文选集注》卷九八均有重要文献价值。《八大童子秘要法品》(拟)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因首题不清,故本文献是否为我国或日本历代经录所著录,有待考证。文献中多处提到「圣无动尊决秘要义」,故本文献或即《圣无动尊一字出生八大童子秘要法品》,但引文尚不能完全对应。又,《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卷一著录有《金刚手光明灌顶经最胜立印圣无动尊大威怒王念诵仪轨法品》一卷,即现大正一一九九号。从日本入唐僧诸目录可知,该经也传入日本,本文献与该经或亦有某种联系。关于本文献,尚需进一步研究。
总之,这批日本写经也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值得研究者注意。
三、结语
在文章的结尾,想对这批遗书的来源略作探讨。
潘重规先生在前述《题记》一文中,对这批遗书的来历有所记载:「询之馆长屈翼鹏教授暨前馆长蒋慰堂先生,知多为抗战时及胜利后,购自李木斋之女暨叶誉虎所藏。」 现馆藏敦煌遗书,有些附有纸签,上有《战时沪购》、《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五月十日京购等标注,或可谓上述记载之注。
上文李木斋,即李盛铎(一八五九),字义樵,又字椒微。号木斋。江西德化(今九江市)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收藏家。当年李盛铎等人曾偷盗自敦煌押运进京之敦煌遗书,经过大略如下:
一九○九年,北京诸学者从伯希和处得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尚保存有若干劫余敦煌遗书,经多方酝酿,由清政府学部出面,委托正要前往新疆赴任的何彦升(一八六○─一九一○)将这批敦煌遗书悉数押运北京。何彦升将此事交给外甥傅宝华执行。傅宝华将十八箱敦煌遗书运抵北京后,不是直接送缴学部,而是先拉到何彦升之子何鬯威家。何阄威通知岳丈李盛铎及刘廷琛(一八六七─一九三二)、方尔谦(一八七二─一九三六)等亲朋好友,诸人大肆偷盗,并不惜以撕裂大卷子为数段的方式充数,以掩盖偷盗恶行。
馆藏部分敦煌遗书购自李木斋之女。承北京大学图书馆沈乃文来信教示:「李盛铎共十房太太和姨太太,育有九子五女,男为家淮、家江、家溎、家淞、家浵、家淦、家浦、家浈、家滂。女为家璇、家瑞、家琪、家瑚、家珩。因为没有系统的资料,上述子女名字的用字或有改变,有些或在李盛铎生前去世,以至于和流传的一些说法对不起来。家瑞是嫁给了何震彝。」 何震彝即何鬯威。我们知道,李盛铎所得敦煌遗书的主体部分,其后由其子李滂(即李家滂),经日本京都大学羽田亨鉴定后,售给日本武田财团,今存日本大阪杏雨书屋。则所谓购自李木斋之女,很可能是当年何阄威所得的部分。当然,罗振玉一九二二年左右曾从何阄威手中得到一批敦煌遗书,罗氏钤有「抱残翁壬戌岁所得敦煌古籍」收藏印的敦煌遗书,大抵即为一九二二年从何鬯威处所得。当年何鬯威到底偷盗了多少?除了卖给罗振玉外,手头还有多少留存?这些问题,目前都不清楚。如沈乃文先生来信所示,李盛铎有五女。李家瑞嫁给了何鬯威,如馆藏敦煌遗书为从李家瑞手中流出,自然应视为原何阄威所藏。但如果从李盛铎的其他女儿手中卖出,则未必是何阅威所得部分,也可能是李盛铎所得,后因赠送或析产为其他女儿所得。然而,李盛铎所得敦煌遗书是否曾因赠送或析产在子女中剖分,依然需要考订。
上文「叶誉虎」,即叶恭绰(一八八一─一九六八),字裕甫(玉甫、玉虎、玉父),又字誉虎,号遐庵。著名书画家、收藏家、政治活动家。据庄惠茹女史告知,馆藏史料已发现有关抗战时期叶恭绰在香港购买敦煌遗书的报告及一九四七年叶恭绰先生将那批敦煌遗书交给馆方的记事。也发现一些在北京购买敦煌遗书的信息。亲眼目睹庄惠茹女史寄来的叶恭绰书敦煌遗书清单手迹,感慨系之。前辈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为保存民族文化殚精竭虑,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屡踣屡起,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批承担着民族文化的脊梁。目前庄惠茹女史正在进一步爬梳史料,以厘清这批敦煌遗书入馆的具体情况。衷心期待庄惠茹女史的成果早日问世。
此次为了考察这批敦煌遗书(包括叙录及本文的写作),曾多次前往台湾,整个过程得到俞小明前主任、阮静玲女史、庄惠茹女史及该馆特藏组、善本书室诸多先生、女史的大力支持与各种帮助,在此特表示衷心的感激。此外,还要感谢中研院史语所刘淑芬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李玉珉教授给予的大力支持。
本叙录与本文如有不当之处,还望博雅君子不吝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