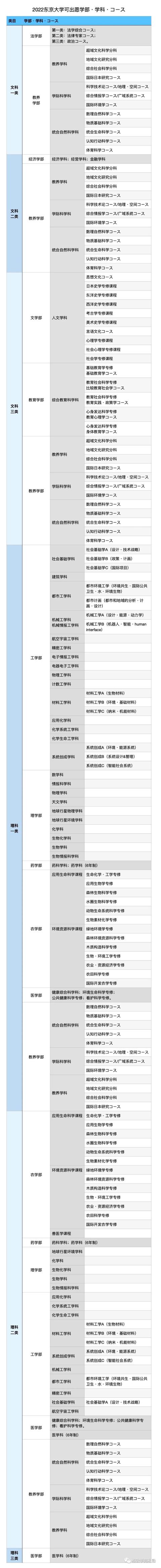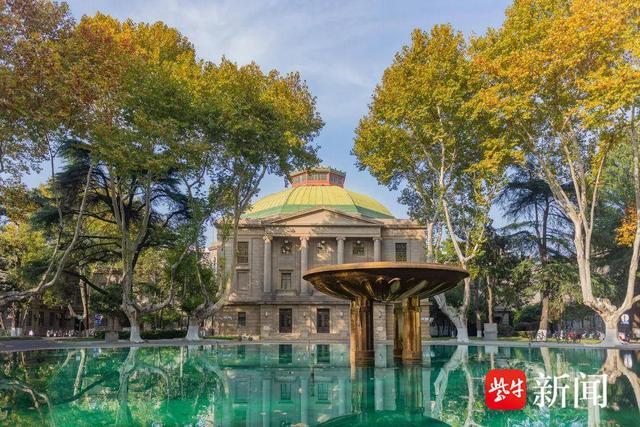原文题目:《抗战时期东北大学的省籍问题:以1944年壁报风潮为中心》

王春林
历史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奉系军阀史,著有《地域与使命:民国时期东北大学的创办与流亡》。
内容提要: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的东北大学始终以东北籍师生为主体,为收复 和建设东北培养人才。抗战爆发后,内迁到四川的东北大学东北籍学生逐渐减少,四川等省籍学生逐渐增加,东北籍师生的主导地位与办学主旨随之受到质疑。这种省籍矛盾在1944年冬的壁报风潮中集中爆发,中共、国民党以及其他党派的学生亦乘机鼓动风潮。风潮最后以部分教职员的去职而告结束,学校当局深受打击,而省籍问题以及党派纠葛却有增无减。东北大学的省籍问题反映了这一地域观念浓厚的内迁高校在生源上的尴尬处境,也折射了教育部、学校当局与校内师生对学校办学主旨的认识差异以及利益考量。
关键词:抗战时期;东北大学;省籍;党派;臧启芳
1923年,奉系军阀在奉天(即沈阳)创办了东北大学(简称“东大”),该校在地方势力支持下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流亡北平,学校仍以收容东北学生为主,并以复土还乡为宗旨。这一时期的东北大学牵涉到很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纠葛,最终在西安事变后为国民党CC系所接收。抗战兴起后,重新整合的东北流亡势力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相对温和,因而围绕东北大学的纷争主要以校内为主。近年来,学界对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以及国民党各派系在大学校园的纷争已有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侧重于考察西南联大、中央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校国共两党的党组织以及斗争,另一方面则侧重于探讨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近期学界开始关注内迁大学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但对于校内层面的地域观念或省籍问题似乎关注较少。因此,笔者拟以省籍观念较为浓厚的东北大学为个案,透过对该校东北籍师生比重的变化以及1944年风潮的考察,体察东北籍学校当局的地域观念与办学主旨,剖析风潮中东北籍与非东北籍师生的不同诉求,进而探讨党派势力与省籍观念在风潮中的复杂影响。
一、内迁后东北大学省籍问题的突显抗战爆发前,东北大学当局一度将校址迁往西安,但1938年初日军威胁潼关,东大遂于是年三四月间迁至四川省三台县。三台乃成为抗战时期东北人的聚居地之一。1938—1946年间东北大学一直在三台办学。与北平、西安相比,位于川北的三台不免有些偏僻。但在战时却是个理想的办学地点。“民风淳朴,物资富饶,当地的文风也相当的高,没有官僚气,也没有市侩气,”“亦非军事要地,”“堪称福地”。
在东北籍校当局与全体教职员共同努力下,东北大学的校务与教学很快步入正轨。校长臧启芳和教务长李光忠“两人全力投入学校的规划和建设中,中年教师以下大体是他们的学生,老年教师是他们原在东北大学的旧友,所以大家同心同德”。以校园为例,旧庙很快被改造成很实用的大学。教员住宅亦渐次成形,蒋天枢等教员都住进了新建的楼房中。同时,东大借助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资助充实教员与设备,先后聘请黄方刚、萧一山为文理学院院长,设立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后改研究所),院系也逐渐扩充和恢复。
战时东北大学仍以接收和培养东北学生为主,东大当局对该校的使命感也十分强烈。臧启芳曾表示东大负有开发、建设东北之特殊使命,战后必须迁回沈阳。时任文学院长的金毓黻也告诫东北学生:“应知东大所负之特殊使命,即如何收复东北”。这种使命感在东北教育界中是有相当共识的,车向忱认为:这“完全是一种打回老家去的教育。这种教育是极端重要的,它关系到东北的未来,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的未来。”
因为负有收复和建设东北的特殊使命,东北流亡势力和国民政府对东北大学甚为重视。彼时东大与东北流亡势力间的往还仍很密切。臧启芳等教职员经常往来于重庆、成都、三台等地,频繁地与东北要人会晤、聚餐。东北各界名流多聚居在重庆南山。“那时来自前方或由各省返渝述职的东北人士,每至重庆亦多上山小聚”。1943年6月28—7月3日,东北籍官员刘尚清、高惜冰等还前来视察东大。1942年1月18—20日,教育部长陈立夫亦来视察东大。陈立夫“对于校中所有设备,教学精神,以及学生体育军训,皆颇嘉许,认为在迁到后方各大学中比较以东大为最佳。”蒋介石为此 “奖励七万元给学生制备制服。”1945年抗战胜利仅数日,蒋介石又致电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请其研究东大迁回东北之事。
但与使命感相对应,东大当局在选人、用人上却不免有些省籍藩篱。臧启芳在中央训练团的报告中列举了校内人才,除李光忠外,陈克孚、白世昌、金毓黻皆为东北籍。而东北籍教员的小团体意识也甚为浓厚,时任东大秘书的苍宝忠表示其最好的朋友是陈克孚和白世昌。金毓黻道破了其中的关窍:“居今日以溯畴昔,应知所谓东北集团者,惟有吾东北大学在耳”。“此千余人之衣食住悉赖臧校长一人为之领导支撑,”“是知此一人之责任何等重大,而吾侪所应为之维系辅助者,又何敢有一息之忽懈。”金言语之间既有乡党情谊,也不无维护东北团体之地域观念。在这种观念影响下,这一时期东北大学的教职员多数为东北籍。这难免使非东北籍人士有所不满。但非东北籍教职员对东北籍教员在校内的强势却不无意见。1942—1943年间,萧一山、蓝文徵等人与东大当局矛盾激化,萧一山等人先后出走。1944年3月,教员丁山初到东大,即表示东大应以一般研究为主,而将“建设东北使命”寓于其中。
抗战初期,东北大学教职员及学生以东北籍为主,学校也弥漫着复土还乡的氛围。教员陈述表示:“大家都盼着早日胜利,”返回家乡。学生“毅生”也在一篇文章中4次谈到复土还乡的志愿。而最初非东北籍学生对该校的东北文化及诉求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1941年入学的郭秉箴希望能从东北流亡青年身上吸取抗日的力量。1944年入学的柏杨对东大的认识也是“以收容东北流亡学生为主的大学”。
但因为战区阻隔、僻处川北等因素,东北大学东北籍学生的比重逐渐下降。1939年6月在校的285人中,辽宁籍152人,四川籍39人,黑龙江、吉林、热河三省合计27人。东北籍仍为主体,但四川籍已成为第二大省籍。至1940年4月,该校之东北籍学生比重已进一步下降,“除一二年级外大多数为东北籍同学”。与之相对应,四川籍学生人数则逐年增加。至1943年上半年,东大在校生共651人。该校最大生源地已经是四川省,计有学生241人;其次方为辽宁,计141人;东北四省合计仅175人。再根据1946年东大的《四川籍同学录》,是时四川籍学生264人。
随着四川等省籍学生的激增以及东北籍学生的比重下降,东大省籍问题逐渐突显。1939年底,东大少数学生曾以“东北籍学生越来越少”为由驱逐臧启芳。1938年入学的吴标元认为内迁带来的学生省籍变化是自然之事。但吴在校时省籍问题或许尚未形成气候,因此不免轻描淡写。事实上,省籍比重牵涉到东北籍师生的主体地位以及办学主旨。1941年底入学的李季若证实:彼时“学生中非东北籍超过东北籍,出现改换东北大学校牌之说”。
共同的流亡背景更容易强化东北师生的省籍观念。东大当局多为东北籍,他们自然会对东北学生有所照顾。进步学生对此是很赞赏的:“应该像东北大学行政那样,创造机会帮助较差的东北同学学习,以考核的办法检验学习的成果,以利他们的继续深造。”东大毕业生、中共党员高而公也认为臧启芳对东北籍学生很宽容。教员高亨也曾在生活、学业上帮助过东北学生,他表示:“这些学生都是不愿当亡国奴,才流亡到此;若考试不及格,就会失去助学金,甚至要被迫退学,生活都会成问题,所以,应当尽量给一点照顾。”但此种照顾必为逐渐增多的非东北籍学生所不满,因为这似乎赋予了东北学生以“特权”。这种省籍矛盾在1944年的风潮中集中爆发。
二、从壁报事件到风潮起落内迁初期,中共在东北大学并无正式组织,整个三台、绵阳、中江地区都是由中共川康特委“派干部去做流动领导”。他们甚至在提到东大党员人数时也前后矛盾,起初说有3人,稍后又表示“我们只有四个同志,工作平常”。受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共高潮的影响,东大地下党员一度与地方党组织失掉联系,进步学生的活动也出现停顿。在“长期潜伏、积蓄力量”方针指导下,中共1943年在东北大学设置了“据点”,仍没有正式的组织。据1943—1945年工作于南方局青年组的张黎群回忆:他们“是通过在重庆的两个人,一个是(主要的)高而公;一个是赵家石。经由他们向东大进步学生传达党的指示。”然后以进步学生“为核心再以公开的团体组织学运”。至1944年,东大校内的中共党员及其影响的进步学生已经有了较大发展。是时张黎群负责动员进步学生去解放区工作,“1944年春夏和1945年春去的人最多。”而校内最为强势的当属国民党CC系。中共川康特委认定:东北大学被CC系“收买统治了。”臧启芳也颇为自得地表示:“教职员入党是我从廿七年起,开始酝酿陆续加入,到廿八年秋大家全成了国民党同志。”在倾向中共的学生眼中,“东大校当局从校长到教务处、训导长都是国民党CC派,少数三青团学生为其耳目”。
1944年下半年,中共在同国民党谈判中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实行联合政府。中共在国统区发动的民主运动有力地策应了谈判。在这种背景下,1944年11月20日,东北大学因壁报问题发生风潮。据国民党三台特务机关报告:
本月十九日因铎声社壁报刊载前毕业一同学栾成勋之贪污情形,旋经其弟栾成津(法四学生,辽宁人)发现,将上项刊载撕毁。铎声社人隆元亨、郭秉箴认为此次刊载经训导处核准,其撕毁有违出版自由之原则,要求学校处理,学校认为此项刊载及撕毁均失当,对隆元亨及栾成津各记过一次。铎声社遂于二十日午后发起壁报联合会并刊出不满撕毁及校方处理言论。训导长杨炳炎、法学院长左仍彦、教务长代校长白世昌会同亲往撕毁上项刊载。壁联及铎声社人士于晚间发动部分同学前往训导处咨询杨、白、左三人,并请求处理撕毁刊物之栾某,后以校方答复不满,当场转移题目,大哄杨、白、左三人,并限五分钟提出辞职书,要求当场承认组织学生自治会,开除栾某,并群呼撕打,白、杨、左见群情难犯,翻窗潜逃。该请愿学生遂齐集大礼堂召集全体大会,推选萧盈光为大会主席,王隆章为书记,商讨组织学生自治会及驱逐白世昌等问题,出席人数约五百,情绪至为极烈。后以萧盈光不能把握会场,另选陈乔为大会主席,陈某从中操纵刺激,通过以各班级长及壁联代表为自治会筹备委员,并将该会通过之一切案件付诸筹备委员会执行,筹备会另在教授预备室同时开会,起草简章,并办理大会通过之案件,对于赶走白世昌问题则通过由筹备会调查白世昌罪行,草拟宣言,向各教授接洽罢课,并由大会通过标语多件,由筹备会写就,于二十一日午前五时前张贴于三台市街及学校,并通过于二十一日午前八时学生自治会于大礼堂开会成立,当场不记名捐宣言标语经费,于三分钟共捐三千余元,会议遂毕。本日(廿一日)晨,一切标语均张贴完竣,罢课之事实现。
最初风潮的对立双方只是支持“铎声社”的学生与主持校务的白世昌、左仍彦、杨丙炎三人。特务认为萧盈光、郭秉箴是中共份子,事件是他们鼓动的。进步学生李一清证实了这一判断。萧盈光据理力争,但是“白世昌听不进”,“仍然不理。”萧盈光的陈述有理有据,却与前述报告中学生的激烈反应相去甚远,他显然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学生的不当言行,而夸大了白的傲慢。据臧启芳事后了解,学生们“包围训导处,人越聚越多,自下午五点到夜里九点还未散,白训导长不得已从后门走了。”白世昌自知有些理亏,但又不愿屈从于学生的要求。当久怀不满的学生围攻他时,他不得不一面敷衍,一面逃走。但白世昌的逃避更加激怒了学生。
白世昌此时是代理校长,又曾长期压制校内民主,自治会遂将攻击的对象转而集中到白世昌个人。在21日张贴的16条标语中,直接攻击白世昌的有11条,要求民主自由的4条,欢呼自治会成立的1条;而23日的16条标语中,保留了21日攻击白世昌的9条和欢呼自治会成立的1条,又增加了攻击白世昌的2条,以及欢呼国民党、民国、蒋介石、东大万岁的4条。此外,进步学生只希望在壁报方面获得更多的自由。特务对风潮前景也很乐观,“只要校长返校,应对得宜,学潮即行终止。”
但白世昌仍试图通过手腕和强权镇压风潮。21日,他一方面指使东北籍同学在自治会中进行扰乱分化,“并扩大反对杨、左二人,”甚至“武力强迫复课”;另一方面又召集全体教务会议,以全体教职员名义劝说学生复课。但这些伎俩难以持续奏效,自治会很快即采取措施排除了东北籍学生的干扰。而校内特务也指出了学校当局的措置失当以及地域观念。
在白世昌等人的挑动下,风潮很快扩大为东北籍与非东北籍师生间的对抗。东北籍教员吴希庸、陈克孚等认为必须维持东北人与江浙人平衡,若驱逐白世昌,杨、左二人也必须离校。23日,东北籍师生更使出激烈手段,“助教学生多人往打左某,以先得耗逃避未获,后移驻校长家。”这种做法也激怒了非东北籍教员。24日,他们决定支持左仍彦。
11月23日,文学院长金毓黻自重庆回到三台。但他对风潮也一筹莫展,此时白世昌等东北籍教职员仍态度强硬,金毓黻的劝说毫无作用。而学生方面更加任性使气。11月30日,金毓黻感叹:“今日目所触者,多为不衷礼法之人,”身心俱疲的金打算辞去文学院长而专心读书。但是时风潮已殃及到他本人。陈乔攻击金毓黻在重庆办的东北文物展览“有为伪满宣传之嫌,”“要求伊引咎辞职”。金毓黻“闻之大愤”,遂决意离开东大。
这时,相关方面已向最高当局及教育部进行报告。三台地方当局于11月21日致电蒋介石,报告东大发生风潮,事态严重,蒋23日令教育部设法处理。11月23日,白世昌亦致电陈立夫,报告东大发生风潮。11月23日,自治会亦致电教育部报告风潮情况。11月25,自治会又致电新任教育部长朱家骅,指责白世昌,并请派员彻查。
11月27日,臧启芳自重庆归来,当事各方纷纷进言。白世昌投诉左仍彦鼓动风潮,左则尽力自证清白。29日,自治会要求驱除白世昌,宽恕闹事学生;东北籍学生则要求驱逐杨、左,白世昌仍任教职。自治会的要求事实上确实是他们的真正要求,此时若处置白世昌,风潮当能迎刃而解。但臧启芳认为风潮系中共份子发动,他不愿意被牵着鼻子走,还想按部就班地处理。相关当局对风潮甚为重视。11月30日,陈立夫复电白世昌,询问臧启芳是否已返校,及风潮情形如何。12月2日,蒋介石也亲自致电朱家骅,令其查明实情,妥为处理。此时,臧启芳和陈立夫都有些掉以轻心。12月4日,甫卸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致函朱家骅,对风潮前景感到乐观,他转述了臧启芳的来电:“原因既较单纯,或不致另生枝节”。陈立夫还向陈布雷转述了臧启芳的判断。
但个别教员及自治会都将矛头指向东大当局。12月1日,教员丁山致函朱家骅报告风潮态势,他将东大当局分为臧启芳校长、东大出身派(校友派)、元老派与客籍4部分。他指责校友派把持校政,排斥非东北籍师生,还批评元老派和校友派“东北至上”。丁山的信函当能反映东大当局之地域观念,但也不乏夸大之词。而同仁中颇有卑鄙丁山为人者,傅斯年曾建议朱家骅“似可明说弟深鄙其为人,(此人不仅狂妄抑且下流)”,“弟殊不介意得罪他也。”孔德也表示:“丁之喜怒无常,人多厌之。”此次又“鼓动学生打倒金静庵,拥之做院长”。12月3日,曾霖在自治会上报告了2日校务会议的情形:苍宝忠欲担任训导长,并“主张开除自治会全体代表、壁联代表五六十人,辞聘杨、左”。赵鸿翥主张:“为东北人之救济,下届招生迳可不收外籍学生”。陈乔还攻击道:“陈克孚才学不及白某,而阴险过之,苍为白之爪牙”。两人的话难免有夸大之嫌,但却极富煽动性。丁山与自治会的言说相互呼应,双方似乎不无勾连。
东大当局逐渐失去了对风潮的控制力。12月3日,学校当局决定开除当事之白世昌、左仍彦及两名学生陈乔、陈祖翼。自治会对校方的命令进行了抵制,并希望学校收回成命。臧启芳起初有接受之意,最后还是表示拒绝。但学校的决定亦无法贯彻。当日,臧启芳感到事态严峻,电请教育部派员前来主持。7日,自治会散发驱逐臧启芳的宣言,胪列臧罪行6项。其中,“任用私人”、“滥收学生”、“强调地域观念”三项皆指向臧的地域观念,可谓切中要害。同日,东大教员表态支持臧启芳,但姿态已颇低:“本月三日之牌示,实系忍痛处理,诸同学果能破除成见,捐弃猜嫌,将来善后处理,亦未尝无变通之余地也。”12月8日,臧启芳再次致电朱家骅,表示教员与地方当局正竭力劝导,但仍希望教育部派人前来。12月11、13日两天,臧启芳又连电朱家骅。电报频传,可见臧启芳压力之大。
此时丁山的言行竟与自治会完全一致,事实上丁山即鼓动风潮最力之非东北籍教员。他一方面极力为左仍彦鸣冤,另一方面又提出更换校长:“继任人选,为国家统一前途计,宜绝对避免东北人。”而各种反臧势力亦有合流之趋向。孔德认为凤潮完全为张澜与中共份子所利用,驱逐东大当局后,将由丁山等人长校。但此时风潮也完全超出了中共份子的预想:“几乎把这场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变成了四川籍学生同东北籍学生的斗争。”彼时诬蔑、抹黑东大当局的传闻甚多,当系丁山及自治会刻意散布。与丁山的略嫌偏激不同,非东北籍教员孙文明的观察当更为客观,他认为省籍问题是东大风潮的症结,风潮的远因、近因,乃至扩大,皆源自东北籍与非东北籍学生间的矛盾。特分会亦认为省籍矛盾远多于党派鼓动因素。“最初稍寓有政治作用,然以地域观念之争为最,直至现在,整个空气,为地域观念所环绕”。
此时“撤换校长”的呼声很高,但对继任者的省籍争议甚大。特分会认为“新校长如籍非东北,东北人必大加反对,而自治会方面,则极端拥护欢迎。”时任西北大学文学院长的萧一山也力主任命外省籍者长校,其对臧启芳等人也攻击甚力。但教育部方面却绝无此意。教育部参事刘英士认为“非至万不得已,臧哲先不可去。原为‘东北’而维持此大学,校长必须东北人,”朱家骅也批示“安定第一”。12月14日,丁山或许接获上层消息,竟又发来赞赏臧启芳的信函,刘英士阅后颇觉怪异。
12月15日,教育部督学钟道赞和四川省教育厅长郭有守到校处理风潮。他们承诺将学生的要求带回教育部,并保证在两周内返回三台,给学生以答复。12月18日,学校复课。这时白世昌与左仍彦已离校,杨丙炎亦辞训导长兼职。
三、风潮的平息及余波
虽然实现了复课,但风潮的根本问题并未解决。尽管朱家骅希望丁山“秉公协助”,但丁山似乎有所保留。而自治会也只是暂时妥协,因为教育部没有按期回复,罢课之议再起。1945年1月5日,自治会虽然未就罢课达成一致意见,但仍派遣陈乔、郭秉箴等人往重庆、成都活动各方舆论。这时特务认为必须撤换东大当局,方能彻底解决风潮。风潮旷日持久,臧启芳也萌生去意,经朱家骅挽留一度打消了念头。但因风潮不见好转,臧启芳遂于1月5日再上辞呈,而朱家骅仍然决定慰留。
1月11日,东北大学风潮再起。是时自治会明确要求驱除东北籍学校当局,而东北学生因为臧启芳不能维护东北教员,也“赞成罢课赶走校长”。因此,特务认为学校当局很难再保全。教员杨向奎也觉得臧启芳难以继续长校。此时外界已有觊觎东大校长职位者。国民党CC系的萧铮、齐世英致电傅斯年,请其向朱家骅推荐同属CC的李锡恩继任。傅斯年即遵命推荐,然朱家骅似主张坚定,萧铮等又来电请求缓发推荐函电。萧铮等人似乎深恐东大落入朱家骅亲信手中,因此采取较为婉转的方式推荐李锡恩。但朱家骅并无更换臧启芳之意,萧铮等人也乐得维持现状。
此时臧启芳的去意颇为坚决:“我看闹的太不像了,下决心辞职,到重庆把辞呈送到部里,便跑到重庆郊外朋友家里住下,对东大事一概不愿再问,朱部长把辞呈退回,托人交我,并找我谈话,一连三次我不肯往见,最后见了面,我坚持不回东大,依然未获允准。”臧启芳所言不虚,报纸也提到他“曾两度向教部坚请辞职未准”。但朱家骅仍坚持由臧启芳继续长校,他斩钉截铁地表示:“部里派人调查回来真想大致明了,必须解聘三位教授,开除几名学生,盼你立即回校执行部令。”
东北大学风潮恰值教育部易长。这加剧了本就紧张的CC系和朱家骅系之间的斗争,组织部、教育部以及部分大学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人事更迭。但这种斗争是潜在的,双方还是要照顾大局。一方面,豫湘桂战役后,战区的教育机构破坏严重,大量师生流离失所,这成为上任后朱家骅的“第一任务”。另一方面,大后方的师生生活困难,对政府普遍存在不满情绪。12月5日,朱家骅向记者谈及当下教育部面临的首要工作,“在于使教育事业安定发展,各级学校师生生活安定,一切教育计划始有进行之可能。”朱家骅迟至12月7日方到教育部视事。12月11日,朱家骅再次重申教育部将着重“安定教职员及学生的生活”。1945年2月9日,朱家骅在国民参政会又作了类似的表示。这种“安定至上”的方针决定了朱家骅不可能对教育人事做出大范围的更动。因此,朱家骅支持出身CC系的臧启芳继续长校,应当主要是为了安定东北大学。否则,朱家骅大可顺水推舟,让自己的亲信取代臧启芳。事实上臧启芳固为CC系,但他作为校内国民党的主要干部与朱家骅亦不乏联系。1943年4月,臧启芳还曾与众多大学校长到中央训练团受训,朱家骅亦参与其间。并且臧启芳是东北教育界的代表人物,白世昌、陈克孚、吴希庸等皆是臧的学生。战后东北教育事业的接收与发展方面,朱家骅都要倚重臧启芳等人。
1945 年1月18日,臧启芳与教育部督学钟道赞、程宽正等人抵达三台。钟、程两人声明教育部全力支持臧启芳长校,“在维护臧校长前提下,一切要求保证有圆满结果,否则执行教部命令,以强制力解决。”而教育部对于东大之处置预案更为强硬,包括复课,惩罚学生,勒令陈克孚、苍宝忠离校,改革校政等。自治会对教育部之处置不无抵触,其中惩罚学生以及改革校政等问题商讨最久,后经当地驻军及丁山、孙文明等人调停方接受。
东北流亡势力也积极参与了风潮的处理。1944年12月5日,金毓黻致函莫德惠、高惜冰,“告以东大事已横决。”朱家骅也曾请高惜冰帮助平息风潮,高惜冰亦颇为尽力。后期高惜冰等人还随同教育部官员前往三台平息风潮。“东北籍参政员高惜冰,前工学院院长王文华同来。”而当东北籍教员派人赴重庆散发反对臧启芳的传单时,也遭到乡贤的责备而未敢散布。高惜冰等抵达三台后,即分头拜访东北籍教授,希望他们协助复课,并劝陈克孚、苍宝忠辞职。
在教育部的强硬表态以及各方配合下,风潮急转直下。1月23日,东大复课。24日,臧启芳到校办公。丁山等在劝说学生时曾暗示学校不会严惩。而校方最后对学生的处置确实甚轻,“罢除名之令,改为大过二次者四人,一次者十二人”。教员方面,“校友派”4人全部去职。“白世昌、左仍彦离职后,继有陈克孚、苍宝忠离校去渝”,吴希庸从军。大多数师生对复课都是持欢迎态度的。
对于中共学生接受命令这一结果,特务认为他们乃见机而作。实际上,他们也得到了中共南方局的指示。高而公安排了郭秉箴等人与南方局青年组刘光的会面。刘光分析道:“既然臧启芳还不像国民党嫡系党棍那样极端反动,若赶走了臧启芳,换来一个国民党党棍当校长,对学生更不利,那就应该在这次斗争中取得校方若干让步之后,就适可而止,不要坚持赶走臧启芳。这是符合‘有理有利有节’原则的。”郭秉箴等人回去后,自治会决定在“同意白世昌等人离校、取消壁报审查”等条件下拥护臧启芳校继续长校。此外,赵纪彬也将中共组织的意见传达到进步学生中。这个意见与南方局的意见相近,也是主张由臧启芳继续长校。
此次风潮对东大当局打击甚大。除白世昌等人去职外,臧启芳也心灰意冷。他曾作诗遣怀,金毓黻认为“颇能透露衷心之苦”。风潮使臧启芳的威望大大降低。臧启芳曾在1939年和1942年连续两次当选东北大学区党部执行委员。截至1943年初,臧启芳在东大党团方面都担任着负责人或指导者的角色。但到1945年3月区党部改选时,“应出席九十六人,除因故未到四十五人外,实到五十一人。”臧启芳仅“得八票,当选为候补监察委员。”显然国民党籍的反臧师生仍在消极抵制臧启芳长校。金毓黻也去意坚决。1944年12月20日,金毓黻向臧启芳“表明去校之决心”,其后即一直埋头读书,不问风潮。1945年3月底,金毓黻返回中央大学授课;7月,正式致函臧启芳辞职。
尽管风潮平息了,各方矛盾却仍在发酵。1945年1月20、22日,一些学生以自治会“极进派”的名义散发传单,攻击配合平息风潮的丁山、陆侃如、梅一略以及自治会委员等人。东北籍师生对臧启芳也不满已极。他们“均认为校长只求位置稳当,出卖东北人”。而丁山仍然敌视东北教员,他认为东大当局的地域观念并未消除:“在同乡会精神支配下,‘不学有术’者居上位,决难言提高学术水准,更难言彻底改革以实现部令指示各节。”而学生之言行则更为嚣张。壁报团体已全部恢复,学校对学生活动及言论亦无法控制。
这一时期,东北籍师生的比重仍呈下降趋势。1938—1943年间,教职员、在校学生与毕业学生人数都呈逐年递增之趋势。但其中毕业者必然以东北籍为主,而新生则应当以四川等省籍为主。同时,东北籍学生的招致始终是难题。1944年9月,东大《校刊》报道:“本校今年分渝、蓉、西安、三台四处招生,”“四处报考学生共三千八百余人。”东大招生地点以四川为主、陕西为辅,生源自然当以四川等南方籍为主。到1946年5月,“东北大学学生约计五百人,东北籍学生仅一百余人,其他均为川籍。”这一尴尬的省籍问题在战后复员时才得到缓解。当东大当局决定迁回沈阳时,“不愿到东北去的纷纷转到四川大学或其他大学,也有的转到自己家乡的大学”。
四、余论
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势力对国民政府已不构成威胁,东北大学也完全被纳入国民政府管辖范围。这期间东北大学虽已改组为国立大学,但仍负有收复和建设东北的使命。但与此前不同的是,是时东北流亡势力的地域观念已大为削弱,而主要是一种国家观念下的地方关怀。但其间省籍观念仍有很大的存在空间,在该校教职员与学生的各自纠葛中,利益之争往往与省籍矛盾互为表里。这期间,东北大学学生省籍的变化本为平常之事,但东北、四川等省籍学生的消长却激化了不同省籍师生之间的矛盾。透过东大风潮可以发现,省籍矛盾与政治关联甚深,党派纷争已深刻左右省籍矛盾。彼时的省籍观念本就十分浓厚,体制上的国立并不能消灭地域观念。“省籍”成为国共各党派斗争的重要媒介,也是影响学校安定的现实问题。
臧启芳认为中共份子是东北大学风潮的主要鼓动者。但事实上中共份子并不能操控一切,他们仅是自治会中的一部分。彼时“出现了所谓东北派、南方派、中央派,都各以不同面目进行争夺群众、控制学潮的紧张活动。”郭秉箴也“感到局面难以驾驭”。而自治会内还有某些青年党成员,他们对中共份子“得势反而忌恨,暗中斗争”。所以,此次风潮实为多种矛盾合力的结果,一方面中共份子确实是重要的鼓动者,另一方面各种反臧派别亦乘机推波助澜。丁山就宣称:“东大最大势力,现在山等把握中,诚不愿即此以送C.C.厚礼也。”彼时丁山所影响的人应主要是自治会和朱家骅系,但他们的目标却不尽一致。在中共份子眼中,其他反臧派别的活动“是国民党派系矛盾和各地方势力之间矛盾的公开化,他们企图把争取民主的斗争,变成驱逐东北籍的学校当权派的斗争。”1945年1月3日,特务机关呈报了一份35人的“东大学潮演变过程中活动最甚及主张激烈分子”名单,并认为其中多数为中共份子。而在这35人中,33人籍贯可查得,其中东北籍仅7人,四川籍16人。这表明非东北籍学生是发动风潮的主力。因此,党派对立与省籍矛盾似乎发生了叠加效应,结果导致东大当局成为众矢之的。
抗战时期,东北大学的省籍问题对于东大当局与教育部都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一方面,战区远隔使得东北籍学生的招致异常困难,但又须尽力维持东北籍师生的主导地位及其办学方向。另一方面,四川等省籍学生的递增使他们自然要求获得主导地位,并在办学方向上具有发言权。教育部为维持东大的安定,不得不对东大“校友派”开刀,但为了筹备即将到来的接收东北的工作,又须对他们做些安抚工作。东北流亡势力自然亦希望维持东大当局,但相对弱势的他们只能做些协调和安抚工作。这一因抗战爆发带来的省籍问题,最终只能在抗战胜利和学校复员东北后才彻底得到解决。
【注】文章原载于《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责编:李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