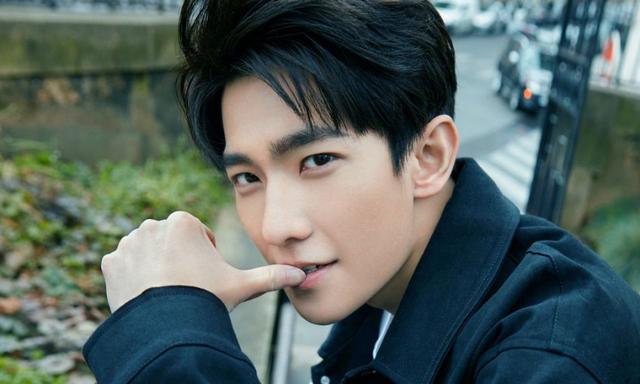卢旺达,那场引颈就戮的屠杀
文/云也退
发于2020.8.17总第960期《中国新闻周刊》
本文经“中国新闻周刊”公众号授权转载
1994年4月6日,卢旺达的胡图族独裁者哈比亚利马纳在首都基加利遇刺身亡。他统治卢旺达已逾21年,正在设法寻求同国内另一大族群——图西族的和解。但事发后仅仅几小时,一群极端的胡图族军人便占领总统府,领头发起了对图西族的大屠杀。一时间,从士兵、警察,到普通市民,甚至牧师,胡图族人都疯了一样地拿起了枪支和屠刀。之后的三个多月,有近100万图西族人和胡图族反对派被杀,而且死状极惨,大多受到从东亚进口的砍刀的残忍重创。
《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美国记者菲利普·古雷维奇1995年到1998年期间在卢旺达住了9个月,走访了多位大屠杀目击者,在《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一书中以令人信服的证据,揭露了暴力之源。
他在书中谴责了西方媒体的偏见和冷漠,以及西方观察家的傲慢。这种冷漠和傲慢背后,是对蕞尔小国卢旺达以至非洲大多数国家的轻蔑,让非洲进一步遭到遗忘和曲解——它成了地球上一个不可理喻的地方,有理性的人应该敬而远之。两个族群残忍地互相灭绝,除了证明那里都是些原始部落,愚昧冷血,还能说明什么呢?西方媒体更是灌输给大众一个概念,叫“非洲狂热”。但在古雷维奇看来,这绝非独属于非洲的病狂。
胡图族和图西族从建国一开始就是混合的,哪怕最敏锐的民族志研究者都无法将它们区分为两个迥然不同的族群。两族之间的确发生过不少政治性暴力,1990年代以来图西族里还出现了反政府武装力量,但即使是在哈比亚利马纳担任总统的最后几个月,国内的政治声音依然是较为温和的。那时无论谁都不会想到,这个国家会发生一场早已注定、无可避免的种族屠杀。
此外,两族人的民族认同长期以来也是混合的。像“胡图力量”这种极端组织里就有图西族人。也就是说,族群身份这个东西,在卢旺达大屠杀中,更多地取决于一个人的政治立场,而不是种族本身。
但是,非洲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即它们从过去到现在都活在殖民和后殖民的影响之下。比利时和法国是介入中非最深的殖民势力,即使卢旺达早已获得了独立,它们留下的阴郁遗产——从族群关系、资源利用、教育,到渗透在民间的各种集体记忆——都一直在引燃政治斗争。而一旦遇到经济滑坡,或领导人不明智地执行种族区分政策,这斗争就会激化。
量变的积累会达到质变。古雷维奇认为,到1990年代初,胡图族人的意识中普遍扎下了“图西族都是蟑螂,必须被消灭”的观念。在后来爆发的灭绝事件中,最可怕的不是杀戮本身,而是这种虚假事实被不假思索地传播。所以,作者一上来就提出了问题:为什么他所了解到的图西族人都如此镇定地接受了自己即将被屠杀的事实?为什么当近邻突然拿起刀枪,图西族人竟像在面对一种不出所料的命运?
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呼唤人道主义、口吐悲悯之声,也没有泛泛地责难当事人,只是列举了一桩桩让人开眼的事实。邻居对邻居下杀手,同事把同事干掉,基督教牧师挂在嘴边的“爱邻人”毫无障碍地转为了反面,更为骇人的是医生杀害病人,老师杀害学生。
这的确是种族灭绝,但这里没有什么“乌合之众”现象,也不关无政府主义什么事。古雷维奇认为,种族灭绝并不是秩序崩溃的结果,相反,它是秩序的产物。之前的20年,卢旺达推行政治上的绝对主义,管理既有效又全面细致。在屠杀中,施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默契”与其说是撕裂了共同体,不如说是在就建设一个新的共同体做出尝试。
这论断惊世骇俗,可是古雷维奇是看过了多少具残缺可怕的尸体、收集了多少令人毛骨悚然的真实故事,才相信了这场灾难事件有它自己的逻辑。安理会仅仅做出了一些绵软无力的动作,法国可耻地给“胡图力量”提供武器和外交上的支持,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以及克林顿政府也都缺乏必要的想象力,只能把新事物套入一些成见来理解。
古雷维奇用这样一件事来结束全书:在一所学校里,几个女学生坚称自己是卢旺达人,而不属于胡图族或图西族中的任何一方,结果被极端分子枪杀。依然是杀戮,可是在杀戮中,我们却看到了一星希望。这种拒绝标签、超越站队的态度,能否最终遏制新的屠杀?本书还期待更多的后续报道。
▼
将卢旺达大屠杀带回人们视线的第一手记录
一场并非久远、惨烈异常、不应忽视的历史悲剧
见证一个个危难与离散的时刻,
以及人类历史的黑暗一页
揭露种族灭绝背后的扭曲神话、政治操纵
和国际社会的无所作为
▼

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
——卢旺达大屠杀纪事
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Tomorrow We Will be Killed With Our Families: Stories from Rwanda
(点击书封即可购买)
[美]菲利普·古雷维奇 (Philip Gourevitch)著
李磊 译
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7月
1994年,卢旺达境内人口占多数的胡图族对作为少数民族的图西族展开全面屠杀,100天里至少有80万人遇害——大部分是用砍刀完成的。卢旺达大屠杀的累积死亡率几乎是死于大屠杀中犹太人的三倍,这也是自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以来死亡率最高的大规模屠杀。
本书作者菲利普·古雷维奇自1994年开始跟踪报道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先后6次前往卢旺达及其邻国,试图探究这场人道灾难的成因,倾听幸存者的讲述,并报道其余波。借由对各方当事人——幸存者、国际组织成员、包括现任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在内的高级政要——的采访,古雷维奇以一种极具推进感的叙事,重构了卢旺达种族冲突的起源、恐怖和混乱而尴尬的劫后现实——大量的人口迁徙,复仇的诱惑和对正义的要求,人满为患的监狱和难民营。
这是一个好人和坏人之间的故事还是一个只有坏人的故事?国际社会对此负有多大程度的责任?一个多半由行凶者和受害者构成的国家能够成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民族社会吗?这些内驱于这部见证文学的问题,使它成为一份绝无仅有的关于卢旺达大屠杀的深刻剖析。
编辑:草尉雨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