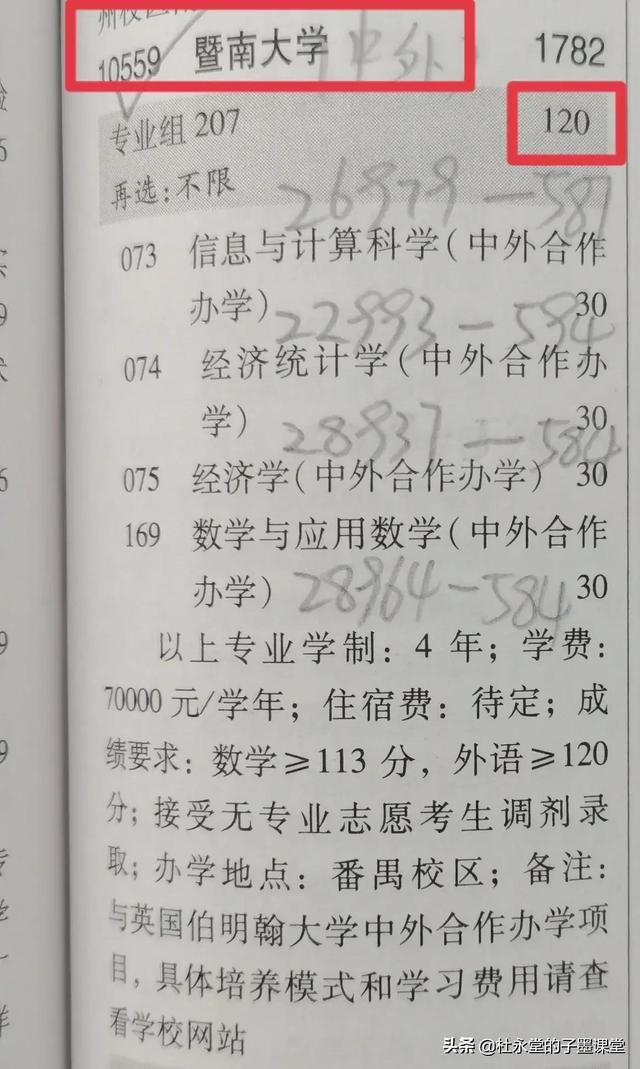北京海运仓胡同3号,朝阳大学旧址。 (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图)
在冯玉军12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堆放着几摞近两米高的书籍,原本就不宽敞的房间显得愈发逼仄。
冯玉军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2010年前后,随着法学院在职人员越来越多,一些比较“边缘”的研究中心的办公室使用权被收回,其中就包括他担任负责人的朝阳法学研究中心,相关书籍只能搬到自己的办公室。
朝阳法学研究中心的成立,与一所已停办七十多年的大学有关,那就是中国第一所法科高等院校——朝阳大学。
如今并不怎么为人所知的朝阳大学,成立于1912年11月23日,1913年正式招生,与东吴大学一道成为民国时期法学教育的金字招牌,在当时有“南东吴,北朝阳”的赞誉。1949年,朝阳大学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今天的中国政法大学由北京政法学院更名而来,两校只是同名,并无渊源),又在1950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这所只存在37年的学校,被称为中国的“法学摇篮”,培养了五千余名法科毕业生,包括新中国劳动法学奠基人关怀、现代刑侦学奠基人周应德、婚姻法学科奠基人巫昌祯、新中国第一代律师张思之和苏东问题研究权威学者徐葵等,新中国法理学主要奠基人孙国华也毕业于朝阳大学。
孙国华是冯玉军的博士生导师,有了这层关系,冯玉军认为自己和朝阳大学“搭”上关系,算是传承了导师的志业。比起朝阳法学研究中心负责人这个身份,他更愿意用“志愿者”来描述。
2022年是朝阳大学建校110周年。让冯玉军遗憾的是,疫情打乱了很多计划,纪念活动没能办成。当然,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随着老校友们陆续离世,即便是能举办,也快“没人了”。
不过,一些现代法学教育的精髓还是传承下来了。1929年,在世界法学会海牙会议上,朝阳大学被肯定为“中国最优秀之法律学校”。今天,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已成为引领法学教育的重镇,这似乎是那个遥远时代的回响。
选校址,引发“民告官”第一案
海运仓胡同3号,也就是如今的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内,有一处不起眼的平房区,部分房屋被改建成了医学院的行政办公室,有些还是住宅,屋顶瓦片上的荒草长出了两尺高。居住在此的老人,不知道那里曾是一所高校。
不同于眼下的萧条景象,在朝阳学子秦绶章的回忆中,那里曾是乱世里的“桃花源”——校门前竖立一座巍峨的照墙,照墙左右各斜铺两条石板行人道,大门口高悬着红底黑字“朝阳大学”的横额,由大门沿甬道往前,左边是教务处,右边是事务处,中间则是一座校长室和教授休息室。礼堂、教室、男女同学宿舍和学生自治会建筑,则由校长室向左右后侧延伸。
校园林木繁茂,中有大道通图书馆道,大道左右为荷花池。到了冬天,池水结冰,又成了天然的溜冰场,“男女同学,淡妆浓抹,翱翔其中,在隆冬里闪耀着青春气息,好一派北风景象”。
学校成立之初,选定校址时,还出现过一个颇具法科院校特色的插曲。
原本,朝阳大学被批准使用清朝最高文化机构翰林院的房屋为校舍,但因工商部已入住,不同意让出房屋,朝阳大学首任校长汪有龄为此将工商部起诉到法院,这成了民国时期著名的“民告官”第一案。最后还是民国政府出面调解,风波才平息。
能让朝阳大学有底气和政府部门叫板,离不开它的“硬背景”。朝阳大学建校时,汪有龄是国民政府司法部次长,江庸为大理院推事。此后长期担任学校董事长的居正,则是武昌起义的指挥者之一、南京临时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
这所名为私立的大学,其官方背景实际远超一般的公立法政学堂。在民国时担任过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的王宠惠、最高法院院长的夏勤、立法院院长的孙科、行政法院院长的张知本等人都曾是朝阳大学校董或任课教师。
再把时间线向前延伸,这所创办于民国元年的高等学府,建校背景可以追溯到清末的法制改革。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1902年,清廷设立修订法律馆,任命沈家本、伍廷芳为修律大臣,着手编纂近代法典,建立现代法律体系。1906年,在沈、伍二人的推动下,京师法律学堂创办,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官办法律专门学校。汪有龄、江庸等人,就在京师法律学堂和修订法律馆任职。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沈厚铎是沈家本的四世孙,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京师法律学堂培养了上千名学员,彼时,如果随着清政府退位、民国政府建立而使得学堂无法延续,沈家本也觉得遗憾。1910年,在沈家本的资助和支持之下,汪有龄和京师法律学堂学员熊煜、王克忠等人发起成立北京法学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法学会。
北京法学会创办之初,汪有龄等人就有意创办专门的法政学校,培养司法人才。191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专门学校令》,允许私人设立专门学校,朝阳大学成了最早的法科高等学校。北京法学会研究所,实际上在后来成了朝阳大学师资的主要来源。
虽然学校的性质发生着变化,但沈家本和汪有龄这些精英人物,实际上有着跨越时代更迭的传承。在研究中国近现代法律史的西北政法大学法学教授王健看来,朝阳大学的办学者和教师都是中国现代法律塑造过程中的主流人物,代表了中国法律演变的主脉。

中国人民大学已故教授孙国华(右三)毕业于朝阳大学。图为2005年2月8日,孙国华在家中为寒假留校学生即兴演奏小提琴曲《新春乐》。 (新华社/图)
“无朝不成院”
不仅在主流社会,朝阳大学在民间也受到很高的认可,这甚至体现在戏剧《杨三姐告状》中。剧中交代,那个为杨三姐辩护的律师,正是朝阳大学的毕业生。不过,在朝阳大学,律师还不是主流的择业方向。在一份朝阳大学对1947届法律系和司法组141名毕业生服务志愿的调查中,有75%的同学在首选志愿栏中填写的是与法院相关的职务。
这也是朝阳大学和东吴大学两所学校的不同之处。东吴大学位于商业氛围浓厚的上海。在法律领域,由于领事裁判权制度的存在,法律本土化需求并不迫切,相反对英美法律制度的学习更加紧要。因此,东吴大学法学院教学具有浓厚的英美法系特色,以培训执业律师著称。根据美国学者康雅信的研究,1918-1935年,东吴法学院的毕业生约有41%专职从事律师业,另有8%兼职。
而朝阳大学法科崇尚大陆法系,因处政治中心北京,又是由位居司法高层的京派法学家筹资创建,受传统士大夫“学而优则仕”情结影响,学生多以司法官为职业志向。
法学家熊先觉回忆当年就读于朝阳大学时的一段经历:1947年,时任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长的邓哲熙是朝阳大学教授,得知汉奸川岛芳子由河北省高院审理,他给朝阳大学的学生“通风报信”,让他们去旁听。去了审判现场,大家发现,包括审判长、推事、检察官、被告人的律师在内的诉讼参与人几乎全是清一色的朝阳大学校友或者老师。
在民间,当时也流传着“无朝(阳)不成(法)院”的说法。取得这样的成绩,光靠创办者的背景也行不通。在朝阳大学的教学管理中,严格实行学分制和考试制。一年级各系读共同必修的基础课;从二年级开始,各系设专业课,又分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种,各计学分。成绩低劣、三门不及格的,取消补考资格,予以淘汰,有的班毕业人数不及入学人数的1/2。
民国时期,形成了以宪法、行政法、民(商)法、刑法、民诉法、刑诉法六个支柱法律为主的现代法律体系,通称为六法体系。而朝阳大学的教学特色,便是把握住了中国本土法律的脉搏,围绕六法体系教学。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改革教育体制,因朝阳大学不足三个学院,改称朝阳学院,但一直沿用朝阳大学校印,在民间也一直惯称为朝阳大学。
冯玉军最早知道朝阳大学,还是在兰州大学法学院读硕士时。那是1995年,他已经树立了从事法学教学研究的志向,担任年过八旬的罗马法学泰斗吴文翰的助理。吴文翰是朝阳学子,1930年到1936年在朝阳大学本科学习,他曾向冯玉军讲起,在当时,同学们间流传着一本精简版的“小六法”,就像本小字典,人手一本装在兜里,随身携带,一有空闲就掏出来背诵,他就把一本“小六法”全背会了。
冯玉军记得吴文翰说起,同学们没什么娱乐活动,一心读书,总觉得能等到不打仗的时候,“我们就成了治国的能手”。
1933年1月,司法行政部的一份嘉奖令指出,朝大毕业生在全国法官考试中,录取率占全国参加考试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直到1948年,当局最后一次全国法官考试录取的第一名仍是朝阳大学应届毕业生古治民。
如同今天各名校教师授课的视频在互联网上传播一样,朝阳大学的口碑,也让各科老师上课时编写的讲义一时洛阳纸贵。学习法学的人在案头一般都有这套《朝大讲义》。参加法官或文官考试的人,更把《朝大讲义》作为必读资料。
在当时,甚至出现了有些“名人”“达官”们动脑筋,设法在朝阳大学发表学术演讲,以此作为沽名的手段。

1997年10月30日,朝阳大学校友会在北京召开。 (资料图 /图)
最后的校友
朝阳大学创办25年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高校陆续向内地迁移,朝阳大学也进入了四处迁徙阶段。
在西北政法大学教授王健看来,教育需要时间的积累,否则就无法体现出价值。民国时期不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法科院校又迅速消失,而朝阳大学,正是民国时期法学教育延续时间最长的学校。
学校先是迁到湖北沙市(现荆州市沙市区)张知本的家宅继续上课。当时,随校迁去的学生只有数十人。
1941年暑假,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命令朝阳大学迁往陪都重庆附近的巴县兴隆场。自1941年迁校重庆至1946年北平复校,5年间,朝阳大学班次逐年增加,在校同学人数,接近战前的两千多人。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朝阳大学在北京海运仓复校。出生于1927年的张思之在接受《中国改革》杂志记者采访时回忆,他原本准备去南京上外语系,他父亲一个朋友是朝阳大学毕业,说那是所非常好的学校,“无论如何也要上”。于是,他父亲把学费寄到北平,要求他“必须上朝阳大学”。他在1947年入学后,“基本上没接触什么专业课”。他原本决心埋头苦读,不料,第一学期还没修满,就“飞快地演变成一个彻底的‘地下工作者’”,成了候补党员。
后来成为新中国婚姻法学科奠基人的巫昌祯比张思之晚一年入学,是朝阳大学最后一届学生。这一届学生经历了3所不同名称的学校。
1949年北平解放,华北人民政府接管朝阳大学后,成立了干部培训班性质的学习队,巫昌祯在革命队伍中接受教育。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朝阳大学基础上,一所新的学校——中国政法大学诞生,“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被任命为校长,巫昌祯被保送到这所大学学习。1950年,原中国政法大学和华北大学等革命学校合并组建了中国人民大学,巫昌祯又变成人大学生。
和巫昌祯同一届入读朝阳大学的还有庚以泰,毕业后同样在法学领域耕耘,是中央民族大学法律系第一任系主任,二人后来成了夫妻。
参与过“八二宪法”起草工作的宪法学家廉希圣在1949年入学当时的中国政法大学,在学校合并后,他进入人大学习。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他还在上学时,1946年入读朝阳大学的孙国华就已经是人大法理学的教师了。那时,人大缺乏师资,就从同学中选拔了一批人,作为学校不同教研室的研究生,让苏联专家培养他们当老师。
这一时期,朝阳大学的师生也面临着留守与赴台的选择。
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原本还计划在台湾重建朝阳大学,不过,1951年,他在家中洗澡时意外中风身亡,朝阳大学复校计划也由此搁浅。同样赴台的东吴大学却在台湾顺利复校,成为台湾一所著名的私立大学。
1951年,旅台朝阳校友会成立时,正式登记为校友的有四百多人。他们中除了吴文翰的同班同学、“司法院”首席大法官林纪东以外,各凤翔、范魁书、管欧、梁恒昌、陈鉴波、吕有文、石明江、王瑞林、聂文等朝阳校友也在台湾地区法律界、法学界卓有建树。
留在大陆的朝阳学子中,不少人都成为了新中国的法学栋梁之才。除了孙国华、关怀、巫昌祯、庚以泰、周应德、徐葵,法理学家陈守一、李景禧,原司法部顾问贾潜,民商法学家赵中孚,刑事诉讼法学家陈逸云,刑事侦查学家周惠博以及曾任上海社科院法学所所长的齐乃宽等,都曾就读于朝阳大学。
重新被关注
在中国人民大学官网上查找学校介绍,会发现,人大的前身被认定为1937年诞生于抗日战争中的陕北公学,以及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并不包括朝阳大学。
王健在一篇论文中提到,人大法学院教授韩大元告诉他,2010年时,为筹备人大法学院60年院庆编纂院史时,对于朝阳大学是否为人大法律系前身,意见出现了一些分歧,那时正担任法学院院长的韩大元提出折中方案,采用朝阳“并入”人大法律系这样的表述。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所由国民党元老创立的学校一直处于“隐身”状态。朝阳大学重新被关注,是随着两岸关系缓和发生的。
1988年11月,台湾正式开放大陆同胞赴台探亲,此后两岸往来日趋密切。在教育研究逐渐开放和对台统战工作的背景下,两岸的朝阳大学校友才有了联络。
孙国华成了组织两岸校友的牵头人,除了他当时在人大法学院任教外,多少也同他的名气有关。1986年,孙国华在中南海给时任中共中央胡耀邦等中央领导讲授法制课。那时,中央领导集体学习制度尚未形成,这次法律讲座是中南海“第一课”,孙国华因此被称为“中南海讲课第一人”。
1997年10月30日这天,阳光明媚,正值北京气候最舒适的秋季,一群年逾古稀的老人站在人大新图书馆报告厅楼前合影。他们衣着正式,大多穿着西装或风衣,似乎是来参加一场盛大的典礼。
这是朝阳大学校友会成立的日子,到场的校友们大多已经半个世纪没见面了。九十多岁的法学家、中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倪征燠也担任过朝阳大学教师。他正好在住院,说好要从医院请假出来,可是因医生安排在这天给他做检查,结果未能如愿。
有两三位旅居台湾的老人原本也考虑赴京,后得知中国北方在10月底可能会出现零下3度的天气,这些都是80岁上下的高龄老人,因难以适应低温环境而却步。
即便如此,还是有两百多人聚到了一起。在校友会成立大会上,朝阳大学教师,后来担任过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校长的关世雄作为代表发言。这位朝阳大学最年轻的老师,当时也已经75岁了。他在发言中说,参加校友会,要“有所忘有所不忘”:个人或党派之间的恩怨得失可以忘,民族国家的利益不可忘;进一步扩大民主政治,健全法制建设不可忘。
为了联络校友,从1997年开始,每年都会出版一期《朝阳校友通讯》,成了大家分享法律观点、日常感悟的“朋友圈”。
2011年出版的第14期厚达280页,是一份校友生活的“大杂烩”,其中收录了媒体对校友的采访文章,还介绍了校友发表的专著。这期校友通讯里,还统计了2001年以来逝世的校友名录。
2015年,作为朝阳校友会首任会长,90岁的孙国华接受媒体采访时有显得有些落寞,“我可能是最后一任校友会会长,即便再改选也没人了”。两年后,孙国华逝世。
2022年,赵中孚、张思之、陈逸云等人相继离世。除了92岁的庚以泰外,数位研究过朝阳大学的学者表示,他们也不清楚是否还有其他朝阳大学校友在世了。

北京海运仓胡同3号,朝阳大学旧址。 (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图)
舍不下的“闲项”
老人们陆续故去,但还有些东西在延续。
20世纪80年代,两岸同学刚恢复联系时,大陆校友感到吃惊的一个消息是,虽然没能在台湾复校,但朝阳大学校刊《法律评论》仍在出版。
这本创刊于1923年的杂志,它的诞生与领事裁判权有关。曾任民国最高法院院长的夏勤在《法律评论》出版十周年时发表的文章里回顾,1921年7月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王宠惠、顾维钧等代表中国提出撤废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等8项要求,列强原则上表示赞同,却借口对中国司法状态还有不明了的地方,决定组成调查中国法权委员会,调查后再作决定。为了呈现出中国司法的进步,《法律评论》也应运而生。梁启超为它撰写了发刊词,“吾深冀法律评论之出,能增长司法界之朝气,使益磅礴,以待后之来者,刮目视之”。
《法律评论》在台湾的出版坚持到了2004年。这时距最后一届朝阳大学学生毕业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人员精力、资金都遇到了困难。正是同一年,大陆的朝阳法学研究中心在人大成立。2009年,在校友、香港实业家吕振万捐助人民币100多万元的支持下,这本有九十多年历史的杂志在大陆复刊,冯玉军担任主编,孙国华是名誉主编。
在原本的计划里,《朝阳法律评论》是半年刊。不过,13年过去了,目前只出版了15期左右,冯玉军也无奈,“进不了法学核心期刊,谁给你投稿?”为了凑齐文章数量,有时还得“拉下老脸”找人赐稿。
严格意义上,《朝阳法律评论》甚至不能被称为刊物。由于没有申请下刊号,这本杂志只能用以书代刊的形式出版。也就意味着,对法学研究者们来说,在上面发表文章,并不能在学术成果的考核中转化为量化指标。随着老先生们陆续离去,这项工作变得愈发困难。
出刊之外,冯玉军还主持了朝阳大学先贤文集的点校工作。2013年,这一项目成为人大年度重大基础研究项目,获得支持经费60万元。冯玉军带着人大法学院的多位中青年老师和博士生,重新出版了17位朝阳大学教师的讲义、文章,还完成了一本关于朝阳大学的综述集,《百年朝阳:历史的纪念与仰望》。
参与点校工作的法学院教师娜鹤雅主要做法制史研究。她发现,近些年,学院里民法、刑法等部门法的老师也开始看起了民国法学学者的文章。一位刑法学学者回答她其中缘由,这是因为目前一些学科的基础性问题,还没有得到完整的解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在中国语境下,无法照搬西方的理论,还是得回溯到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法制观念。
娜鹤雅负责点校冈田朝太郎的文集。清末修律时,这位日本法学家在1906年接受沈家本的聘请,来华参与清律修订工作。之后,他又在朝阳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东方文明如何吸收西方的法律制度?中国成了冈田朝太郎的试验场。
如今的学者和百年前的先贤们虽然身处不同的年代,但如何将西方制度和中国传统融合,是两者共同面对的一个命题。在娜鹤雅看来,这是研究民国学者的论著价值所在。
而对冯玉军来说,自己接手导师孙国华对朝阳大学的研究,除了其中的学术和文化价值,也有客观原因:2000年他进入人民大学读博后,就开始跟随孙国华参与朝阳校友会的工作。留校任教后,朝阳大学研究这一棒也自然传承到他的手中。
“朝阳大学是个‘闲项’,它更多代表着近代法学教育和法律文化的传承,大家看不到它的直接效用”,缺人、缺经费,又难以在学术评价体系中获得认可,“志愿者”冯玉军也多次想搁置研究朝阳大学的项目,不过总还是“舍不得”。
面对这项工作遇到的困难,冯玉军还是怀着一些期待,“等我干到退休,总能克服了吧?”
(本文参考书籍:《法学摇篮——朝阳大学》作者:薛君度、熊先觉、徐葵;《百年朝阳:历史的纪念与仰望》 作者:冯玉军、闫桂梅、冉令标)
感谢中国律师博物馆对采访提供的帮助。
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