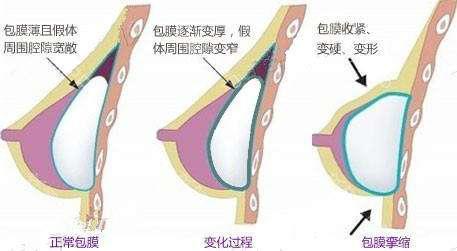图为电影《盲流》剧照
大家怀里揣的脸上挂的都是满满的幸福。提着牛肉匆匆赶回家,把这鲜嫩的牛肉“啪”的一声放在砧板上,在女人和孩子们的惊愕与喜悦面前,久违的满足感才能涌上心头!
生产队杀牛是临时的决定,好多人家根本就不知道。现在一块肥美的牛肉突然从天而降,就摆在砧板上,还真不知该怎么吃!我们知青大部分都是回家包饺子。我妈妈包的饺子真香,香的不行!但后来我才知道,好些社员家却连饺子都没有吃上。有的家剁好了饺子馅,却发现没有面粉。拿着面盆出去借,可女人兴奋地走了几家也没借到面粉,大好的情绪便一下低落下来。
这是有故事的人发表的第844个作品
作者:暴 志 强 . 鬼 谷 子
✤
小时候,时常有人上门查户口。现在是早已没有了。来人按照户口簿逐个与你的家人对号。对于外来人员,一定是要严加盘查的。如果遇到拉家带口的外地人,甚至要带回去审查。极有可能被收容和遣返。那时管那些人叫“盲流子”。这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那个年代它对于一些人是十分可怖的梦魇。
据记载,1953年4月,国务院发出了《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首次提出了“盲流”的概念。1956年、1957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国家连续颁发四个限制和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文件。1959年3月,由于极左路线盛行,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这份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产生问题较多地区的外逃饥饿农民,被地方政府以“盲流”名义堵截、收容,部分人员饿死在收容站。这应该是时代的无奈国家的悲哀。
但人总是要生存下去的。“文革”期间,在山村小镇免渡河西北角三公里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盲流子们竟聚成了一个散落、荒芜的村落。一群衣衫褴褛的人、一群乞讨者,在这里掘地而居。在陋如蚁丘般的一地窨子里落地生根,就此结束了漂泊羁旅。于是又呼亲唤友,仿佛找到了天堂之所。
这就是“红道山”脚下的盲流屯——后来的免西大队。一片肥美的草地上,一盘盘掘地如丘的地窨子。
大兴安岭,峰峦如积,绵延千里,林木葳蕤,相互轩邈;山下砥原远隰,奔腾不息的免渡河犹如玉带蜿蜒向西,划开那片雨露丰沛而肥沃的草场,与滨洲线铁路交叠在桌山脚下。得耳布尔的模范场,麦浪滚滚.......在那个年代,无论山上山下,这里都是遍地黄金。
“盲流屯”就这么突然凭空飘来!这里居住的都是“盲流子!”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也有孩子。他们来自全国十一个省。他们每个人都有一首苍凉、悲悯的歌。这歌让人动容、让人心酸、让人思量......
(一)
那年,我对未来信心满满,毫不犹豫地报名下乡,去了盲流屯。我坚信,是雄鹰就要翱翔在篮天上。那一年我十七岁,我刚刚把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读完。
青春的热血在沸腾,理想就仿佛炉火中的钢花璀璨而美丽。上大学、去当兵、去工厂当工人的远大前程就在盲流屯的终南捷径上。它顺理成章,光明耀眼.......那时对理想的憧憬热切、纯真而美好。理想又总能插上想象的翅膀。
两驾戴了大红花的马车,把我们二十四个知青从动员大会上直接拉到了盲流屯。在乡土气息浓郁的队部里,我们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一张张朴实憨厚的笑脸、一声声南腔北调的声音,处处表现出对我们的亲热。
大队部是一栋坐西向东而建的土坯房。里屋是大队主任、会计、出纳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盘有一铺大火炕(这是为了冬季取暖而建)。队部房前是一片菜地。房后是水园子,再往后是马号和仓库。周围散落的便是几栋低矮的土房,混杂其间是星罗棋布的地窨子。有的屋顶仅仅高出地面几十公分,抬腿就可以迈上屋顶。在和地平线一齐的地方勉强安装了一小块玻璃。初生的太阳就把那缕光线,象奢侈品一样投进屋里。
那时,路线教育工作队还在,生产队里的事都由路教队做主。路教队的队长陆家常是旗里文化馆的馆长。一个温文儒雅、和蔼善良的小老头。但盲流屯里的刺儿头们却有些怵他,暗地里盼着他们早点撤离。也有些人希望路教队能长期留在免西。
大队书记张生年,是一个面庞黝黑、精力充沛又有些驼背的车轴汉子。社员们背地里叫他张黑子。他常自嘲自己是黑三郎。当时正评《水浒》批宋江。盲流屯里党员极少,他是路教队培养起来的年轻人。他是个好人,只是软了些,有点胆小怕事。人们都说他撑不起这么大个家!
好在路教队还在!会计邢海四十多岁,瘦高个儿白净脸儿,梳分头,冬天戴一顶很好看的狐狸皮帽子,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我去过他家,他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他媳妇中等身材白净脸,一只眼睛有点斜。说话很明事理的样子。
他家土房低矮,没有什么家具,但屋里屋外拾掇得利利索索,屋里虽然是土地但没有一点杂物和纸屑。书记张生年不太喜欢他,背地里对我说邢海是只老狐狸。我看看他的样子,没有看出来那里像狐狸;但我也就渐渐不喜欢他了。后来,有人把他漂亮的二女儿介绍给我当对象,我当然也就没有同意。
出纳员王燕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小女人,脸上有少许的麻子,人挺和善的。她的丈夫焦凤祥和她形成很大的反差。焦凤祥中等身材,大脑袋,大眼睛,大嘴岔,说话声音也大。张张罗罗地办事,总带些夸张的声音和表情!他是辽西人,据说还是被铁路部门开除的干部。具体原因人们都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英雄不问出处,这里忌讳打听别人的底细。但是路教队没有重用他。
代理农业队长的是张国华,一个五十多岁瘦高个子的老头,说话慢条斯理,风趣幽默,有时柔中带刚绵里藏针。他梧桐色的脸上满是褶皱,我以为他是标准的贫下中农。为提拔他当队长,路教队的副队长和一名知青去做他的外调。结果却查出他上学时参加了三青团。我们在心里上立刻对他有了提防。形象也就都变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不容置疑地把他列入到农村坏人的行列中,开始讨厌他那斯斯文文的声音和他傲慢的尖笑。三青团的事,本来已经明白确凿。可不久事情却来了一个大逆转。路教队还是任命张国华当了队长。这很出乎我们的意料。为什么路教队一定要任命一个三青团员当队长呢?这对于我们一直是个谜。而去外调的知青却失去了路教队的信任。据说是提前泄露了调查结果。反正盲流屯的事云波诡谲暗流汹涌,我们这帮小毛孩根本摸不着龙潭的深浅。
“盲流屯”里有形形色色的人,他们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使我不能忘记的有失意的"大学生"唐云,人称唐麻子。他是不是真的上过大学,我们不得而知。他孤身一人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那男孩一脸雀斑。唐云神神秘秘地偷偷給人看相、批八字。他说自己谙熟《易经》,通晓三教九流,医卜星相,甚至他懂得置蛊。我们听得云里雾里,但终究弄不懂他这么精明的人自己缘何沦落至此?
在盲流屯里,很多人话里话外还都仰慕一个邋邋遢遢的逍遥人,这人就是赌王袁大苟(袁大狗)。他大高个、大长脸,驼背腰。自从落户在这里就真龙见首不见尾,但他在这里的名气好大好响的。他妻子死了,唯一的女儿嫁给了地主家的儿子宋宝山。女儿当家,一家过得还算和睦。他便无牵无挂,常年在外四处游荡,他善赌,不缺钱又逍遥,在屯子里让人羡慕。
还有会做买卖的生意人韩枫、还有讲故事唱二人转的张绪良两口子以及他家截去半只胳膊的漂亮女孩、还有那个大名鼎鼎(大明顶顶)的张秃子.....他们有那么多的传奇和神秘。有些人和事,直到今天仍然是个谜......
(二)
我们刚下乡那阵正是伏天,天天铲地。三伏天铲地真是一个要命的活。当天两只手上就都打满了血泡,腰也像要折了一样酸疼难忍。打头的(也就是领我们铲地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妇女主任陈桂香。浓眉大眼,中等身材,壮实的农村妇女。她比我们大概能大个四五岁的样子。她苗红根正,爸爸是饲养员老陈头。她干农活真是一把好手!刚一下地,就手起锄落,板结的土地瞬间翻出了浪花。龙背垄沟、苗间苗根、眼到锄到寸草不留,斩草除根。而且一下地就嗖、嗖、嗖地窜出十几米,我们这些知青,都看傻了。怎么赶也是跟不上呀。
炎热的天气也和我们作对,太阳早早地就挂在天上,火辣辣地显示着威力,汗水顺着脸颊流向脖子。嗓子眼儿一阵阵发紧,口中干渴难耐。望着一眼望不到头的长垄心里生出无尽的茫然和惆怅。被农民伯伯推荐上大学、进工厂、当兵的理想是那么丰满,现实让它变得骨感而渺茫。
妇女主任陈桂香一会就从前面绕到我们的身后。她扯着嗓门大喊大叫:“看看这是谁铲的,这草都没锄下来,还在喊救命呢!这还带草帽呢!(指苗根部周围的土和草没有被铲到)哎呀,哎呀!看看这是谁铲的,把苗都铲掉了!可别怪我晚上扣工分!”真是让人难堪。
我咬紧牙关向前冲,心里想着“跟上、跟上”但还是被远远地落在后面。后来在我前面不远处,经常有五六米、五六米的地方被人铲过。这一下减轻了我的压力,使我有了喘息一下的机会,而且也避免了落在后面的丢脸与尴尬。
后来我看到。一个个子不高,身材单薄,长着圆圆脸颊的小姑娘在帮着我。她的脸同样被太阳晒得红红的挂着汗珠。那一刻我心存感激,深感羞愧。后来我有意避开了这个小姑娘,不和它相邻。此时此刻难为情!我的自尊让我离开她的帮助。
另一个打头的便是唐云唐大学。背地里人们都叫他唐麻子。一个中等身材,黝黑的脸膛上长有很多麻点和黑症子的中年人,他是盲流屯的文化人之一。路教队长陆家常对文化人惺惺相惜,特别关照,所以唐云在盲流屯是被另眼相看的。据说唐麻子在东北读过大学,不知道是真是假。但当面大家都叫他唐大学!他嘿嘿笑着,得体的答应。
和唐云在一起铲地,就轻松了许多。他不会把你拉下一大截,他也不会在你的后面大喊大叫地检查。用他的话说是压住阵脚。他不准别人超越他,这是规矩。每到地头大家去喝水,他便席地而坐,抽一颗卷烟。那时社员们都抽自己卷的旱烟,每到地头便卷一支抽。知青抽烟的不多,但为了多休息一会,男生后来渐渐的就都学会了吸烟。
唐云爱听人们的奉承,也爱表现自己。因为在地头讲过故事,那段时间每到地头,我们便围上他,殷勤地递烟、递水,摆出要听他讲故事的架势。他就笑眯眯的点上烟,然后开讲。讲着讲着往往就超时了,这也是我们所盼着的。有时他把烟往地上一捻说道:“来,再干一会儿”,往往还没赶到地头,太阳就下山了。
那时最爱看的是即将落山的那轮又大又红的太阳,它代表着一天的劳作即将结束!它标志着可以毛毛草草的铲地,栖栖遑遑地奔到地头收工回家。后来到了秋季,唐云就不当打头的了。那时几乎所有的领导都来参加秋收。在北方广袤的土地上劳作一天,全身仿佛要散了架子般的疲乏。
回家的路上我们还能打打闹闹,二十几个知青,好大的一帮,疲劳伴着快乐,跳过那条时常干涸的小溪,走上那条废弃的铁路线,回到小镇的家里!第二天便又精神饱满地出现在这片“盲流屯”的大地上!
在屯里,每次去社员的家,大都要下地窨子。低矮的柴门你要低头猫腰,阴暗潮湿的屋子你要睁大眼睛。在那门槛前的斜坡处爬上爬下,雨雪天气尤为困难。晴好天气,屋顶的塑料薄膜上便凝结了细密的水珠。
室内那难于表述的怪味让人不由自主屏住呼吸,眯起双眼。角落里堆满了土豆、青菜,旁边的木板上放着半袋口粮。一盘火炕占去了绝大部分的空间,火炕上散乱的堆放着难以分变颜色的被子。火炕前连接着一个大大的炉灶,灶上的大铁锅里放着吃剩下的土豆和几块玉米面饼子。或是锅里总是要剩下些玉米面土豆糊糊。这里维系着几近最古老、最原始的生存方式。
那时,我们的生活都十分艰难。但面对"盲流屯”里的人们,我对生活似乎有了更新的认识。在生存恶劣的环境下,这里的人们是何等的坚韧,强烈的生存欲望,驱使人们直面于生活中的一切艰辛。走进他们,你可以体会他们、体会那笑声和哭泣声,体会那豪爽的高声大气和悭吝抠门的小心思......这就是我们的盲流屯了!
(三)
那年秋天,一件事在屯子里炸开了锅。
事情的经过大抵是这样的,那会儿,秋菜被盗的事儿经常发生。白天好好的一片菜地,一晚上就被盗得一片狼藉。
一场秋雨一场寒,北方漫长的冬季就要来了。“他们眼睛都红了”这是陆队长说的。是说那些连社员都不是的新盲流子的话。他们的眼睛真都会红的。他们必须在这个季节里捡麦子、捡土豆、捡一切秋季能捡到的东西!只有储备了足够的食物他们才能熬过整个漫长的冬春季节。
队里派出去好多人在夜里护秋。张秃子被分在红道山西面看土豆地。张秃子的大号叫张宝德,四十来岁的车轴汉子。只是头上一根头发也不长,平时总是戴顶瘪塌塌的帽子,尽量的遮住脑袋的四周。他特爱出汗,搞得帽子四周总是挂着白刷刷的汗渍,煞是难看。有时他不得不摘下他的帽子,光光亮亮缀满汗珠的脑袋便一下暴露在朗朗乾坤之下了。于是大家开他的玩笑叫他大名鼎鼎的张保德。
这天,半夜里张生年带着我、唐云及另外两个年轻的社员去查岗。月色朦胧中,我们看到从地头慌张起身的两个人,其中一个小个子的女人,飞也似的向黑暗中跑去。张保德慌里慌张地迎上来。笑嘻嘻地喊着书记,递上卷烟。而地头那白花花的土豆和已经扎好了口的袋子,让我们好像明白了什么。
张生年一下打飞了张秃子递上来的烟。一把拽住张秃子的衣领,用脚一绊,顺势便把张秃子撂倒在地。他喊了一声“按住!”几个人一拥而上。张秃子只有“哎吆、哎吆”哀求的份。我想还要捆起来吗?当我疑惑之时,我愕然地看到,他们三下五除二就扒掉了张秃子的裤子,几只手电筒一起射向了张保德黑白分明的私处,给他做了现场检查.......然后我们便笑翻了一地。
唐云笑着喊道:“龙涎四溢”啊!那种兴奋劲难以表述。突然有人提出截住回村的路,抓住那个女的。张生年一下犹豫了,黑着脸沉吟着说:“抽颗烟,抽颗烟”.......张秃子一边提着裤子一边“嘎嘎”笑着,讨好地把大半合香烟塞在张生年的手里。张生年毫不客气地一把撕碎烟合,把烟卷发给大家,每人一颗地抽了起来。唐云他们仨急得猴窜狗跳的,可张生年就是没动。
这次查岗其他的地里都没出事,我们单单查到了张秃子,却放跑了那个女人!
第二天,张生年把这事汇报给了路教队长陆家常。唐云当着很多人,把整个事件添枝加叶的烘托、渲染了一番,这件事就一下子传遍了盲流屯!张保德用队里的土豆换XX、张保德“龙涎四溢”,甚至那个女的身材苗条、相貌娇艳、平时她和张保德关系如何都传得绘声绘色。众多的揣度引起好事者无尽的联想。
还有更多的人等着看后头的好戏呢!可陆家常却不知对张生年说了什么,事情戛然而止被难以置信的压了下去,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这又引起了好多的猜测。有的说,现在知青刚到,弄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影响太坏,有损贫下中农形象!有的说,张生年知道了那个女的是谁,但他不敢说了。
也有的说,路教队要走了,陆家常不想把事情闹大。唐云则说:“草蛇灰灰,千里之外,今朝有恩,来日必报。”反正这件事杳无声息了,张秃子则像一根针掉进了大海一下子就消失了!而我朦胧中似乎还没搞清“龙涎四溢”的含义!
(四)
整个秋天,每天都忙得不行、累得不行。终于熬到秋收将完,可以喘一口气了。
那天早晨,艳阳初照,天高云淡。社员们聚在马号围栏前议论着什么,大家一脸的严肃。
原来,是队里的那头黑色的小牤子把卢俊卿差点顶死,好危险!要不是饲养员老陈头及时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平时我们都很怕这头小公牛,它膘肥体壮,黑黝黝的皮毛发着油亮的光,两只大大的眼睛总是虎视眈眈地瞪着每一个从它身边经过的人。今天它把卢俊卿顶翻在牛舍里,他连叫喊的机会都没有,只要他想爬起来,它就立马低下头将他再次掀翻。它并没有凶狠地摇头,否则它那锋利的犄角就会轻易地刺穿他的胸腹。看着它浑圆怒视的眼睛,让卢俊卿恐惧得浑身战栗。它那黑缎子般柔滑并打满褶皱的皮肤从肥硕的脖子上披下来,让这个庄稼人感到了深深的绝望。
是老陈头偶然发现了异常。老陈头不愧是老饲养员。他本来没看见倒在地上的卢俊卿。牛舍的地面由于清粪挖的比外面的地面矮了有半米深,卢俊卿就倒在那土坎下。但当他看见那头牛的神情时便立刻警觉起来,他抄起一根柳条棍子就跑了过去,结果赶跑了那头牤牛,救了卢俊卿。卢俊卿后来接替王贵当了副业队的队长,这是后话。
上工的社员来得越来越多,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说这头牛小的时候十分可爱,萌萌的,人们总是愿意逗它玩,摸索它刚刚冒出的犄角,和它推来顶去的玩。时间长了它一见到有人过来便主动梗着脖子等,惹得人们十分的爱怜和喜欢。
就这样它一天天长大,人们开始敬而远之地避开它,而它却时刻期待着再次玩那童年的游戏!它对和人们的顶撞乐此不疲,它绝想不到今天因为顶撞而闹出的危险。
有人说:“它今天顶了老卢,被老陈及时的看见了。好在没什么大事,但明天如果顶了别人,跟前又没人,那可就惨了!”唐云接着说:“是啊,说不定哪天顶着个小青年儿,可不是闹着玩的,特别是那些女孩子!”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
书记张生年的脸色立刻凝重起来:“老陈,放牧回来后必须把牛圈进牛舍,不能让它们再乱跑”。老陈答应着:“哎,不是想让它们在外面捡点儿卜留克樱子吃吗,再说那牛圈也该好好修修了.....”“可不是,谁能保证天天看得过来?......”“好了,好了,大家干活去吧!”
中午,就在菜园子的空地上,老陈头牵来了那头小牤牛。早有老老少少的人们围了上来。瘦猴李振华将一根大绳挽了一个活扣放在地上。老陈头就把那头牛牵过来,那牛的两条后蹄子刚一踏进那个活扣的时候,他猛地向上一提,牛的两条后腿便被套住。人们一起用力拉紧绳子,牛的两条后腿再也分不开。但它还满不在意,凭了浑身的蛮力企图向前猛窜。
它一蹦老高,把拽绳子的人甩倒一大片。大家起哄聒噪,但毫无放过牤牛的意思。匆忙爬起来,继续拽紧大绳。这时唐云喊道:“快把前腿也绊上,李振华拿绳子绊前腿......”于是李振华就用另一条绳子,放在了地上。那牛不知是计,踏上了那条要命的大绳圈,于是人们拉紧绳子。绳子的两端绕着牛腿转了一圈又一圈,四条牛腿终于被几乎缠到了一起。
那牛瞪着眼睛,鼻孔喷着湿漉漉的粗气,不甘心地轰然倒地。它不明白今天人们到底想和它玩怎样的把戏。人们围上来,首先将它的一个犄角深深地插在刚收获完的土地里,它的头连摇动一下的机会都没有。我们扭过头去,不忍看那残忍的一幕,只听见它有些绝望的叫声,“哞.....!”
仅仅几十分钟后,它便成了一块块鲜嫩诱人的牛肉。按着社员和知青的人数一共做了六十几个阄。张国华分割牛肉的公平犹如当年大汉丞相陈平。盲流屯的人们说不上有多久没有尝到肉的滋味了。
张绪良家弄了好大一锅土豆炖牛肉。唐云家满脸雀斑的儿子当即就在炉盘的铁圈上烤起牛肉来。牛肉吱吱啦啦的响,冒出的油滋润了炉圈,炉圈上就冒着淡淡的蓝烟。烤牛肉的香味和说不清的怪味裹在一起弥漫在地窨子里。那种味道多少天都不肯散去。
没有面粉的人家很多。有的用牛肉汆丸子,也有的抖落面袋子,又加了许多玉米面勉强包了混合面的蒸饺。队长张国华家人口少,老伴用一半肉包了饺子,另一半用朔料布裹好,用一根细铁丝拴上,慢慢地顺到房后的那口井里,悬吊在水面上,几天后拿上来还有些舍不得吃。那头牛可真的让我们盲流屯幸福了好一阵子。
责编:笑笑
本文版权归属有故事的人,转载请与后台联系
阅读更多故事,请关注有故事的人,ID:ifengstory
扫描或长按二维码识别关注
人人都有故事
有 | 故 | 事 | 的 | 人
投稿邮箱:istory2016@163
合作邮箱:story@ifeng
主编:严彬(微信 larf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