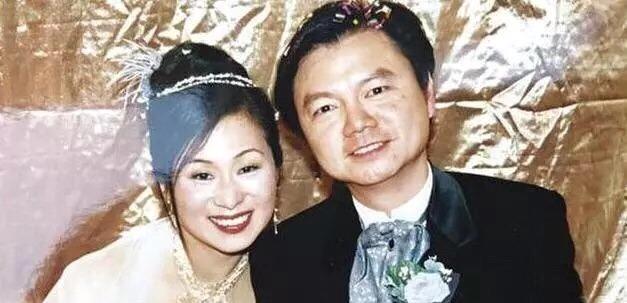多年来,陈丹青跟我提过好几次徐岩,说是新世纪初书店偶遇,徐岩请他评画,多为老北京的速写。我当时听后有点不以为然,对这些画没什么兴趣。上周,偶然路过中国油画院陈列馆,看到展览“徐岩的北京”正在布展,只见丹青俯身一件一件地摆布,又亲眼见到徐岩的老北京速写,意外的同时,心里泛起一阵之前对他不以为然的歉意。
01
难怪陈丹青将北京的徐岩比作巴黎的阿杰特和郁特里罗:
“1900年前后,阿杰特直觉到旧巴黎的灵光行将黯灭,沿着大街小巷拍摄了数百张银版大照片,然后死去了。奔向新世纪的人们不在乎他的照片。七十多年后,摄影界有心人公布了这批作品,新一代欧洲人这才明白,阿杰特预先留存了十九世纪巴黎的经典肖像。

画家郁特里罗同样迷恋旧巴黎。他跟着画家母亲瓦拉东在蒙巴纳斯长大,根据当年的彩色明信片,画出无数动人的油画,每个角落停着童年记忆。名胜、乡村、都市、街巷,是风景画家逗留不去的主题,但一往情深凝视自己的城邦,画了又画,毕竟是少数个例——并非每个城市的记忆都会托付给艺术,除非有位痴心的人,譬如阿杰特或郁特里罗。”
同样的痴心,差别是,在我们这里,没有人知道徐岩。

徐岩自画像
徐岩是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的侄孙,出身名门。“文治总统”徐世昌不仅善书画,亦对中国美术教育做出深远贡献。徐岩从小受家人影响习画,大学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他的字是“延宗”,所以签名用这个名字。然而这样显赫的家世,经不起历史的转折,毕业后辗转到宁夏,将其一生青春派给京剧团。

1947年徐岩与弟妹们合影,左一为徐岩

1963年徐岩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
他家北京曾经的宅子充公了,退休回京已然没有希望。然而,他父亲的好友夫妇年迈无后,生病无人照料,这才使徐岩回到北京,一边得以落脚,一边有机会提着画板凳子,满胡同画速写。但因为他经济上的拮据,速写和油画都是画在广告纸背面,或薄薄的鞋盒裁片上。可是,他的画里没有很多所谓贫穷艺术家作品中的“穷意”。
02
徐岩的速写勾起了我美院附中时的记忆,到我们迁校后这几届,这种北京胡同的速写已经很少了,有的话也不过是为了交作业,除了磨炼才能,没有如此特殊的情感。今天美院附中的孩子是不太愿意去画的,物理距离太远,心理距离更远,画不到这个意思。而美院本科以上的速写传统,我想已经灭绝。人们都不约而同地看不起自己的传统——在“创新”这么笼统的号召下。

徐岩给我的亲切感,恰恰相反,不是“创新”,而是一种“归回”。陈丹青对此评价说:“这是一批再朴素不过的素描,无可救药的诚恳。稍经训练的画手都会画几笔街巷写生,但没有哪位画家能画出徐岩赋予素描的哀婉,绝望,挚爱,处处投射诀别的目光。”

虽说整个展览七八个厅,其实总共叠起来不过一摞论文纸那么厚,但这些速写稀释在展厅空间时,却有一种浓厚的诚意和命运感扑面而来。请问,今天会有谁在北京胡同里不厌其烦地画速写?拍照片不是更方便吗?是什么理由催促着一个老人按照老苏联素描的传统,画下一片片北京胡同?
03
陈丹青在展览的序言里这样形容道:“徐岩以苏式的笔法与印象派色彩,画油画,也画老老实实的素描。新世纪初我认识他,他已年届花甲,积攒了数百幅纸本小油画和大尺寸素描写生。一年四季,除非雨雪,徐岩每天带着画夹子,幽灵般走遍全城,描绘旧京经已拆除、将要拆除的老街巷。

他在北海、紫禁城、团城、京郊描绘的油画写生,明丽而多情,街巷素描写生却像是低吟的挽歌,所有旧楼与门墙藏着记忆,每幅素描的边上,写满题记:这里曾是何处,谁曾是楼宇的主人——前清的恭王府,北洋时期的官邸,占领年间的刑警处,民国文人的旧寓——如今它们沦为大杂院,破败不堪,有如历史的残骸。”

大概是回忆,是感慨,是充实。
徐岩的速写都配着文字,记录并回忆着老北京的点滴,因此,这些画是城市历史的见证。不是我们印象中都市的高楼大厦,人流涌动的繁华,而是与喧闹比邻的胡同院墙:有的是历史故事的发生地,有的曾经住过达官显贵,大多曾经辉煌,如今破败或业已消失。
我把其中一些画推荐给一位远在英伦的朋友看后,她说:“这是残躯画残骸。”
看他的速写,得读这些文字,因为速写不仅是徐岩绘画的操练,更是他的历史记忆输出。慢慢,形成一部北京内城人文历史的个人图画注。“他用毛笔题写的文字、年份、印章,破坏了这些——我以为是一流的——素描,但在徐岩,这是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在为记忆作注。”陈丹青这样说道。

“寥寂尚有诗书伴,何妨重返寅辉关(注:颐和园后山一城关)”,不仅有注,还有诗。特别是他写了附在自画像旁边的那些,读起来不那么得志,像是他在劝自己放下,劝自己洒脱。比如:“秃首苦战桑拿天,依稀拙眼辨真颜。千涂万描应无术,留取颓影记残年。”生活的周遭,外形的枯槁,内心的煎熬,绘画艺术的追求和结果,都在诗和画里了,令人读罢随他一同叹息。

有时候读者会读出共鸣:古人来者,皆为过客。渺小浮生,何处是依归?他写道:“人世虚情胜雪寒,拼将余力探秋山。日暮途穷觉岁晚,头昏眼花感画难。”他大概就依归于这些速写,而这些速写,又附于徐岩的命运和记忆,情感的所托,而徐岩这默默无闻的一生,又附于历史的跌宕,家国命运的洪流之中。
04
曾经我们与徐岩同在北京,如今我们还在,他不在了。他凝视过的北京城,留在广告纸的背面,我们透过他的凝视,些许会品味到一种诀别之情。

正如他的一组自画像。晚年时,徐岩出门少了,如许多落魄中的画家,开始了自画像的创作。陈丹青说:“这也是他和他的作品的自尊。信守清贫、孤寂、无闻……他开始一幅接一幅画自画像,在纸端下方写一首诗。当他画遍旧京,当旧京变得无法辨认,他回首凝视自己的垂老,直到谢世。
这批自画像和他的街巷写生一样,无可救药的诚恳。在不同角度,不同光影中,徐岩的目光分明显得无助、哀矜、固执——令我想起晚年珂罗惠支,甚至,伦勃朗——这样的自画像无关乎艺术与技术,而仅仅是凝视。”

不仅是诚恳,也是一种尊严,他渴望认可,但不主动追求认可。徐岩曾说:“尊严不是虚荣,不是权势,不是威风,不是地位,不是摆架子,是在这些并非尊严的面前所坚持、拥有的平等的尊严。如果没有这种尊严,就用自己的成功去争取,或者绝不屈服、苟且,不同流合污。”他的画里透露出来的,正是这样一副傲骨。除了傲骨,还有正气,分得清主次:“人往往最容易丢失最重要的东西,为了利而丢失德,为了恨而丢失爱,为了情而丢失理,为了气而丢失智。”徐岩的日志中,这类的格言比比皆是,有些话一读,觉乃警世良言。
最后一个单元展示了他的风景色彩,都是巴掌大的尺寸,遵循着印象派——特定时刻、特定光色调子的原则,红墙黄瓦,白塔绿水,在他的笔触下有了新的色彩定义。


我多少会有点遗憾,如果早认识徐岩,给他拿去些画材,不止在这方寸中拮据,或许更有一番天地,更有一番作为?也可能正是这种匮乏,使得徐岩的艺术饱满。他这样定义艺术和艺术家:“艺术是能力(技术功力)加修养(素质思想)。光有能力没有修养是匠人,光有修养没有能力是眼高手低的空头艺术家。”这也是他一生诗书画一齐修为,笔耕不辍的写照。

这恐怕是当下最不“当代”的展览。徐岩生前没有观众,没有展览,没有市场。但我无法拒绝,有人用俯仰一生来描绘我所陌生的北京胡同,倾注所有情感和耐心。
叫人一眼扫去,两行落泪。
徐岩
(1942-2019)
字延宗 北京人
祖籍浙江宁波鄞县绕湖桥村
北洋政府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之侄孙
194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省重庆市
1945年随家迁居北京
1948年-1954年 就读于北京东华门小学
1954年-1957年 就读于北京二十五中学
1957年-1960年 就读于北京二十二中学
1960年-1965年 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
1965年毕业后分配到宁夏任舞台美术设计
1995年因病退休回京
2019年5月15日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七岁
展讯
展览:徐岩的北京
学术主持:陈丹青 杨飞云
展期:2020年8月8日-9月10日
地点:中国艺术研究院油画院陈列馆
文/尤勇
编辑/史祎
供图/中国艺术研究院油画院陈列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