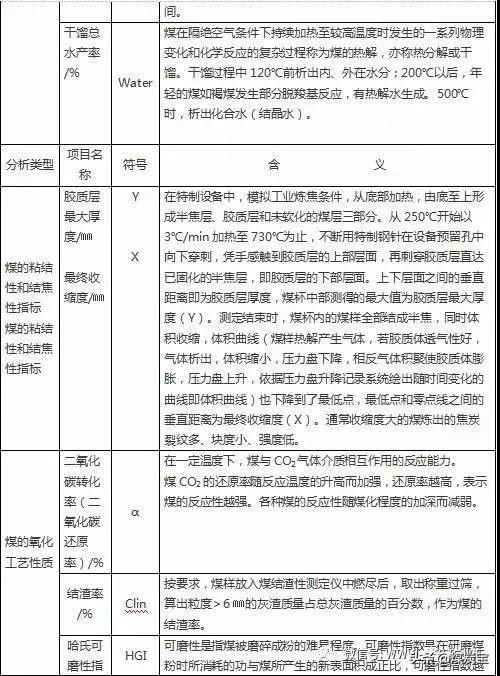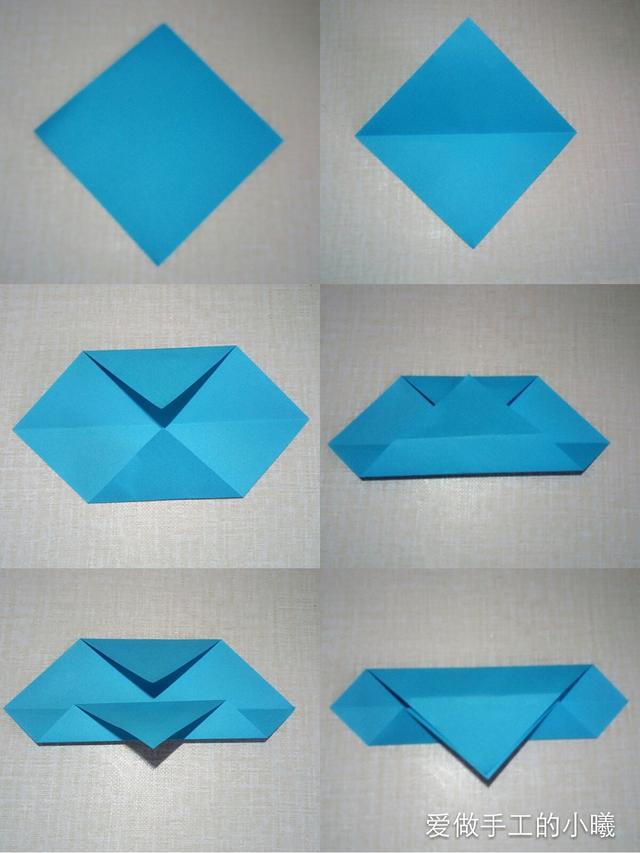看苏东坡《柳子厚诞妄》一文,说到柳子厚撰写文章,赞颂好友吕温在道州、衡州为官,死去之后,二州百姓为之哭泣超过一个月,客人到永州见到柳宗元还会大哭。东坡以为就算是春秋时期郑国的名相子产去世也不能如此让百姓悲伤,小小吕温凭什么能够?对柳宗元称吕温的弟弟吕恭“贤豪绝人”,也很不以为然。苏东坡看来,吕恭娶的是奸臣裴延龄的女儿,任何一个君子又怎么会和裴家谈婚论嫁呢?文词之中,对柳宗元多有贬斥。在《柳子厚论伊尹》等其他文字中,也同样表达了对柳宗元不满。
儒家本来就讲究恕道,何况苏东坡本是一个比较旷达,比较宽容的人。对于同样是文坛大家的柳宗元,苏东坡为何如此吝啬自己的赞美呢?
先看看吕温是怎么样的人,原来吕温和柳宗元一样,同样是王叔文集团中的核心人物,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永贞革新”,却一直立场鲜明,和柳宗元等人互通声息,在政治上力主改革弊政,推行新法。琐碎的介绍就不多说了,看吕温的一首诗《刘郎浦》:
吴蜀成婚此水浔,明珠步障幄黄金。
这首咏史诗是吕温经过刘郎浦时,听说此地是三国时刘备到东吴迎亲的地方,有所感触而写的。作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吕温对事情的看法入木三分。首二句点明孙刘成婚时候的地点和环境,用“明珠步障幄黄金 ”来指代迎亲场面的奢华,和双方对这场政治联姻的重视。后两句则表明自己的看法,作为东吴一方,孙权、周瑜本希望用孙夫人来笼络刘备,进而收取荆州,可哪里知道,刘备志在天下,岂会因一女子而动摇自己夺取天下的大志?
其实,这首诗既是吟咏古迹,也是抒发自己的怀抱。刘备不会因为孙夫人而改变自己夺取天下的大志,而吕温也不会因为各种挫折、诱惑而改变自己改革朝政,推行法治的理想。
尤其可贵的是,吕温不但是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一位开明法家,更是坚定的法治实践者。对于政治,他有着自己明确的理论依据,比如“德主刑辅”,一方面要看重法治,打击豪强,即便是一些功勋也不能凭功抵过;但同时法律也应该服务于德,用道德来进行引导,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犯罪的发生。对于一向推行德政,注重教化,施政以“礼”为核心的传统儒家执政思想,是不小的冲击。对于如何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认为“修诚”、“任智”、“立威”很重要,只有将领导的个人品德、智慧、威信三者相结合,才能做好一个执政者。即便是在现在,也颇有借鉴意义。
作为中唐另一位大家刘禹锡如此描述吕温:“年益壮,志益大,遂拔去文字,与隽贤交,重气概,核名实,歆然以致君及物为大欲。每与其徒讲疑考要,皇王霸强之术、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间,诋诃角逐,叠发连注。”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胸怀天下,平等待人,思想开阔的优秀的官员形象。有这样志向、抱负的官员,是地方之福、百姓之福。别说是古代的官员,就算是现在也绝对是稀有品种了,也就难怪吕温在道州一年,流民就纷纷来归。离任之际,百姓痛哭流涕。

而裴延龄其人,在历史上确实是一个对下严苛,对上谄媚的小人,甚至有人称其为“唐朝第一弄臣”。只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不但是裴延龄本人的责任,更是当时最高领导人德宗皇帝的责任。在裴延龄去世之后,满朝大臣拍手称快,只有德宗感叹唏嘘。而吕恭777年出生,裴延龄796年去世,吕恭当时22岁,不知道是否已经和裴家联姻,然即便联姻,在吕恭的仕途上,人生上,个人操守上,裴延龄对吕恭更多是负面影响。而三十岁之后才是吕恭为官作宰的主要时期,东坡以其岳父人品低劣,而轻易否认吕恭贤豪,未免意气用事。
苏东坡之所以如此,只因柳宗元也好,吕温也好,都是王叔文一党。作为改革家的王叔文,竟然被等同于奸佞小人裴延龄。那王叔文是何等人?
王叔文在德宗朝本担任太子侍读,经常和太子谈论朝政,深得太子信任,德宗驾崩之后太子即位,是为顺宗皇帝,年号永贞,重用王叔文,开始新政。新政主要有个方面。一是罢黜宫市、五坊小儿,打击宦官势力。白居易的《卖炭翁》就生动的记载了宫中太监仰仗权势,欺压百姓,“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而所谓“五坊小儿”本是为皇帝抓捕鸟雀的宦官,借口为皇家供奉,欺压良善。他们甚至把罗网张在人家门前不许进出,张在井上不让人打水,谁要是接近,就说惊吓了供奉鸟雀,甚至痛打百姓,直到人家拿出财物来才罢休。二是遏制地方藩镇势力,中唐以来,一些地方节度使都自行任命官职,去世之后也由自己的儿子承袭官爵,中央多无力干涉。而王叔文强硬地抵制这一现象。而变法最重要的部分是取得兵权。在玄宗以来,唐朝京畿地区的兵权多由宦官掌握,从玄宗时期的高力士,肃宗时期的鱼朝恩,到德宗时期的俱文珍,都一手掌控兵权。如果说,罢黜宫市,五坊使危害了宦官集团的经济利益,还勉强可以忍耐,王叔文任朝臣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节度使,以图逐步收夺宦官的兵权却危及宦官集团的存亡。于是俱文珍联合朝中保守势力,地方藩镇集团,联手打击王叔文集团。于是作为领袖的王叔文被杀,大后台顺宗皇帝被废,柳宗元,刘禹锡在内的八位新贵被贬偏远州郡担任司马。一场轰轰烈烈的永贞革新,在宦官势力,藩镇势力,朝中元老大臣联合围剿下如秋风落叶,短短三个月不到,就烟消云散了。

改革也好,朋党也好,永远都是利益之争。就像德宗年间,卢龙节度使朱泚举兵造反,唐德宗被迫逃离京兆,而之后各地藩镇也对中央权力虎视眈眈,十个月之后,叛乱平息,可得利最大的竟然是宦官势力。因平叛、护驾有功,窦文场、霍仙鸣被封为为神策中尉,使宦官集团掌握神策军成为定制。真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
但是,一些人被称为改革家,受到后世赞赏,另一些被称为政客,受到后世唾弃,最大的区别就是对利益的取向不同。这个世界上或许没有不图利益的政治家,但在追寻自己集团的利益的同时,兼顾国家的利益,百姓的利益,这种人就足以被后人称颂。王叔文等人就是如此。罢黜宫市,维护了京畿百姓的利益;打击藩镇,维护的唐朝中央的权威;夺取兵权,有利于消除宦官专权。可是面对两个盘根错节,遍布天下的利益集团,王叔文仅仅是凭借皇帝个人对自己的宠信,就想一扫乾坤,实在是螳臂当车。历史上无数为国为民者,被保守派、被一些奸佞打击迫害,不能不让人有“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之叹。
那么,为什么苏轼会对这样一位为国为民的政治家有如此错误的评判?
估计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原因是,历史永远是由胜利者来书写。唐顺宗即位之初,俱文珍就联合朝臣,册立李纯为太子。在几个月之后就合谋废黜唐顺宗,拥立李纯即位,是为唐宪宗。唐宪宗本是历史上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君主,他利用朝臣之间的矛盾,互相牵制,比较成功的进行了大规模的削藩,一时之间,天下一片中兴气象,甚至被后人认为能够和太宗、玄宗并列。
那为什么他不为自己的父亲翻案?
只因为宪宗之所以能够即位,正是建立在自己父亲的错误、王叔文集团的覆灭的基础上。为了自己的地位稳固,形象高大,王叔文等人,甚至是自己的父亲,也只能是一直充当反面角色。于是即便是名臣韩愈,也多出言诋毁永贞新政,宪宗年间编纂的《顺宗实录》也大都记载新政集团的种种劣迹。而后世编修顺宗年间历史,只能是参考《顺宗实录》,于是对王叔文集团的污蔑,诽谤也就一直延续下去。
第二个原因是,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本来这个典故说的是孔融取笑曹操让自己的儿子曹丕,收纳袁绍儿媳甄宓,以为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而苏轼对王安石倡导的新政也非常反感,对同样宣扬变法的王叔文和柳宗元乃至吕温,自然没什么好印象。
在文学上,苏轼确实是宋朝继往开来的一位大宗师,可是在政治上,他是一个保守派。当然,不单是他,包括其师欧阳修,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其友黄庭坚、曾巩,都是保守党。
在两宋以来的漫长的岁月里,大多数人都认为北宋衰弱以至于灭亡的主要原因,是王安石乱政。可是现在我们却认为,王安石是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前后荣辱,判若云泥,为什么?
现在的历史课本当然是认为,王安石新政之所以失败是遭受到太后为首的大地主大官僚集团的一致反对,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严厉打击新党,取缔一切新法。可是为什么王安石同时代的那么多优秀的政治家、文人都集体站到了对立面?新法就没有问题吗?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王安石变法之初,朝廷上下,无论是皇帝,还是朝中一些权臣都大力支持,其中包括后来新法坚定的反对者韩琦、富弼、文彦博等人,大家都对新法抱有很大的期望。而在变法之初,确实也使北宋朝廷上下风气一新,可是渐渐的,渐渐的,王安石的变法变味了。
多年的宰相生涯,使得王安石听不进负面的意见,固执的认为一切对新法的意见都是对改革的抨击,对自己的诽谤。对于那些反对者,王安石采取强硬的打压政策,将那些人纷纷撵出中央。苏轼也遭遇“乌台诗案”,被贬黄州。那几年,是苏轼一生最苦难,最彷徨的岁月。这一切虽然未必是王安石直接指使,但作为改革的最高领导人,王安石难辞其责。苏轼将自己的怨恨施加在王安石等改革派身上,完全可以理解。为了巩固新法,王安石大力启用新人,于是一些投机分子也纷纷打着维护新法的名义排除异己,扩充实力,收敛钱财。哲宗朝的“奸相”章淳、徽宗朝“六贼”之首的蔡京,都是凭借新党身份,踩着旧党鲜血爬上高位的。
不知不觉,王安石变法,演变成宋朝开国以来最恶劣的朋党之争。新党上台,旧党靠边,旧党上台,新党滚蛋。眼里都不再有什么是非,只剩下党同伐异。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真相与假象,道义与利益,口号与目的,法治与人治,是是非非一时之间难分辨,或许这就是历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