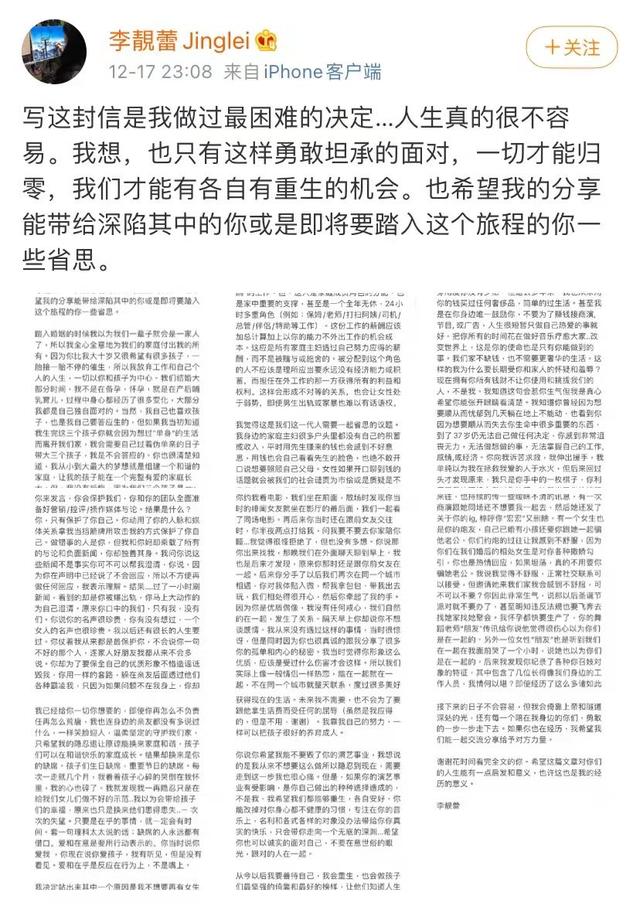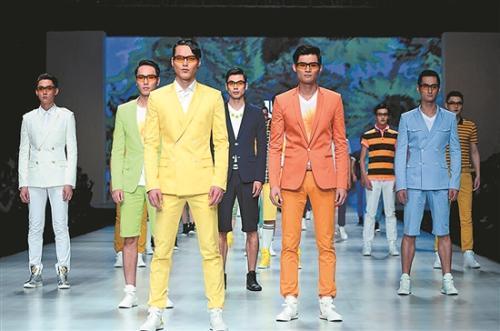1936年5月,背部剧痛、高烧一直未退的鲁迅先生接受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
斯诺问道:“当今中国文坛上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有哪些?”出乎众人的意料,鲁迅并没有推荐冰心、丁玲、庐隐这些成名已久的女作家,而是极力称赞了年仅24岁、作品数量还不多的萧红,他肯定地说道:“萧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

萧红
此时,鲁迅认识萧红不过一年半时间,却为萧红帮了很多忙,自己拿钱帮她出版了中篇小说《生死场》,亲自为萧红写序,让弟子胡风写后记,令萧红从一个与萧军合用笔名、合写小说的无名作者成为享誉一时的女作家,引人注目。

在接受这次采访的五个月后,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
不久,萧红与萧军的关系,也因萧军的多次出轨和家暴走到了尽头,1938年5月,萧红与萧军的好友端木蕻良在武汉结婚,后来在香港因肺结核去世。
萧红一生情史坎坷,先后有过两任同居男友和两任丈夫,并与其中两任生过孩子,而这四位伴侣先后都抛弃了她,最终,她死在相识不久的流亡作家骆宾基怀中,遗言希望他能把自己的骨灰交给许广平,以后安葬在上海虹口的鲁迅墓旁。
不过,由于当时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萧红的遗愿没能实现,只得暂时安葬在香港浅水湾的荒滩,后来迁往广州银河公墓安葬。
萧红临终时,曾发出了林黛玉式的感叹:“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在她漂泊无定的一生中,唯有年长三十岁的鲁迅给过她最大的欣赏与关爱,不但极力推许其文学才华、让她名扬天下,还有超乎寻常的怜惜与关心,让萧红感觉“像祖父一样”,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命若游丝的萧丝渴望能安葬于鲁迅身旁。
1、文学才华惊人的萧红,一生遇尽渣男论情路坎坷,民国女作家中,萧红绝对可以拿第一。
张爱玲也曾与到处觅艳、多次出轨的胡兰成结婚,但她平生只碰到这么一个渣男,而且,胡兰成对张爱玲的才华还是非常倾倒的,为她写过不少点评文章,用尽溢美之辞。
萧红却先后被四个男人无情抛弃,萧军与她同居期间,两次出轨、长期动手毒打萧红,对萧红的文章更是多有贬低。
萧军认为萧红的小说、散文笔力平平,没有结构,读起来絮絮叨叨,一如小女孩坐在外婆家的门槛上喃喃自语,而这一写作特点却是深受鲁迅先生欣赏的“意识流”写作,后人评价认为萧红与伍尔芙的写作技巧不谋而合,均有内心独白、视角跳跃、自由联想、形象切割等特色,有场景式的文章结构。可萧军顽固地认为,萧红写作功力很平常,是她与鲁迅有“不一般的关系”,才让萧红获得了鲁迅的赏识,直到故人均化烟云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萧军还一再向牛汉强调过这种观点。

电影《黄金时代》中,萧红与萧军同去鲁迅家中做客
萧红的相貌和个性,远不如她的文学才华出众,按丁玲在《风雨中忆萧红》的描述,萧红最大的短板,是“少于世故”、“幻想”、“稚嫩和软弱”。
丁玲回忆:
“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
萧红这种爱幻想、“稚嫩和软弱”的性格,用于对自己爱情婚姻的处理中,便有了多次草草收场的情事。
1928年,在叔父张廷献的张罗下,17岁的萧红与当地大地主汪家的小儿子汪恩甲订婚,汪恩甲在哈尔滨三育学校当老师,比萧红大两岁,相貌英俊,萧红为他织过毛衣,还以未过门儿媳妇的身份参加了汪恩甲父亲的葬礼。两年后,汪恩甲进了哈尔滨法政大学预科班读书,两家催着给二人办婚事,萧红却用家里给的嫁妆钱到裁缝店订做了新大衣,与从法政大学退学的表哥陆哲舜一起私奔去了北平。
陆哲舜早有家室,萧红也有未婚夫,可二人却不管不顾地爱上了,1930年4月,陆哲舜入读二龙路的中国大学,萧红在辟才胡同的女师大附中读书,为了不引起外人猜疑,他们对外宣称是甥舅关系,租了二龙坑西巷的一座小院子,雇了当地人耿妈照料生活,那段时间,萧红的生活是甜蜜的、她处处都感到新鲜。
深受打击的陆家和张家(萧红原名张秀环)拒付俩人的生活费,逃婚出来的二人逐渐感受到巨大的生活压力,北平冬天很冷、米贵,样样都要花钱,陆哲舜的感情慢慢冷却下来,甚至生出悔意,他与萧红的浪漫史就这样结束了,1931年1月,寒假期间,两人各回各家,再也没有联系过。

萧红
1931年2月,萧红重返北平,未婚夫汪恩甲也追赶而至,把萧红带回哈尔滨,可汪恩甲的二哥、哈尔滨道外区滨江小学校长汪大澄认为萧红已经名声狼籍,强行替弟弟解除了婚约,萧红深感不满,还去法院起诉汪大澄,软弱的汪恩甲为了哥哥的声誉,违心地承认解除婚约是自己的主张。
这年11月,流浪街头一个多月的萧红找到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读书的汪恩甲,他们在东兴顺旅馆里同居,萧红怀上了身孕,1932年6月,由于没有足够的钱交旅馆费,汪恩甲丢下即将临产的萧红,不辞而别、下落成谜,萧红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裴馨园派萧军去给她送书,二人就这样相识了。

萧红与萧军
萧军是萧红的文学带路人,相识之初,他对柔弱的萧红伸出了慷慨相助之手,先是帮萧红乘船逃离了欠费的旅馆,把她送入医院待产,出院后,二人在道里新城大街的欧罗巴旅馆开始了新的同居生活,不久搬到道里商市街25号的房子,靠微薄的稿费和借债度日,萧红新生的孩子因无力抚养被送走,后来不知下落,也有人说孩子夭折了,萧红对这第一个孩子怀念不已,还在遗嘱中一再叮嘱端木蕻良找到这个孩子的下落。
1934年底,萧军与萧红因创作进步文学遭到迫害,经青岛来到上海,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鲁迅先生,萧红的文学才华倍受上海文艺界的推崇,而她却高兴不起来,她曾经的爱侣萧军与一位在东北认识的有夫之妇陈涓展开了新的恋情,让她陷入痛苦之中。
1936年7月,萧红在鲁迅的建议下,离开萧军,东渡日本,几个月后,她得知鲁迅的死讯,回国祭奠,又回到了萧军身边,而这一次,萧军出轨了她的闺蜜、另一个有夫之妇许粤华,让许粤华怀上了身孕。
1938年1月,萧红跟着萧军离开武汉、前往山西和西安一带从事革命文艺创作,但时间并不长,5月,她与萧军的好友端木蕻良返回武汉并举办婚礼,此时,萧红的腹中又有了萧军的孩子,而萧军却根本没有娶她为妻的打算。

萧红与端木蕻良
1938年底,萧红在重庆江津生下孩子,孩子生下三天就夭折了,她与端木蕻良在1940年1月前往香港,萧红肺病日渐加重,1942年1月22日在玛丽医院去世。
在她离世前一个多月,端木蕻良不见了,只有相识不久的流亡作家骆宾基在旁陪伴照顾,萧红告诉骆宾基:““端木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

骆宾基
据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修订版自序》中回忆:
“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开始爆发的次日夜晚,由作者护送萧红先生进入香港思豪大酒家五楼以后,原属萧红的同居者对我来说是不告而别。从此以后,直到逝世为止,萧红再也没有什么所谓可称‘终身伴侣’的人在身边了。而与病者同生同死共患难的护理责任,就转移到作为友人的作者的肩上,再也不得脱身了。”
就这样,历经四任男友与丈夫的萧红,孤独地在医院里去世了,其临终的凄凉绝望心境,与林黛玉极为相似,因此,失声的萧红在纸下写下:“我将与长天碧水共处,留得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在这种心境下,她深深怀念平生给过她最大善意与欣赏的鲁迅先生,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2、萧红的柔弱与鲁迅的怜弱萧红脆弱的性格与她冷静的文笔形成一定反差,她与丁玲都擅长描写苦闷与苦难,而丁玲的生命力却要强悍得多,如沈从文所言:“她要人家待她如一个男子。”丁玲活泼、坚韧、开朗、无畏,有着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敢于斗争,不依赖他人,而萧红却不是,她内心的自我定位是个无助的柔弱女子,她倾诉苦难不是为了变革或者爆发,只是在寻找救赎。
为了离开哈尔滨,离开曾吸食鸦片的未婚夫,去北平寻找新生活,她求助于已婚的表哥陆哲舜,正在法政大学读书的陆哲舜也乐于相助,他为萧红抛弃了家庭、从大学退学,带着萧红不声不响去了北平,帮萧红进入女师大附中读书。
那段时间里,萧红是心情愉快的,她在信中向好友描述北平秋天的宁静风景,觉得样样新鲜。
而陆哲舜却渐渐感到吃力,19岁的萧红只是一昧的天真,像一个没长大的孩子,从精神到经济上都要依靠他,而无法与他共同面对风雨,陆哲舜开始后悔,借寒假返回哈尔滨的时机,他彻底离开了萧红。
此时的萧红没有选择独自生活,而是回到了未婚夫汪恩甲的身边,仿佛再次找到了依靠,同居八个月后,萧红临产前夕,汪恩甲同样选择了不辞而别。
旅馆老板不让萧红走,威胁她还上4百元的欠费,否则就把她卖到妓院。
怀有身孕的萧红只能到处求助,命运将萧军送到了她的身边,最开始,自顾不暇的萧军没打算管她,可山东籍东北汉子的萧军有着强烈的侠义心肠,他被萧红的柔弱激起了十足的同情心,萧军回忆初见萧红:
“半长的头发敞散地披挂在肩头前后,一张近于圆形的苍白的脸幅嵌在头发中间,有一双特大的闪亮眼睛直直地盯视着我,声音显得受了惊愕似的微微有些颤抖地问着:‘你找谁?’”
在收到萧军的三首情诗后,他们住在了一起。

萧红与萧军
困境之中,他们相爱了,萧军发现了萧红的文学才华,1933年,萧红以“悄吟”为笔名发表了小说《弃儿》,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之路。
而萧红的极度依赖渐渐也让萧军不耐烦,他曾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他认为萧红没有“妻性”,在萧军眼里,“妻性”应该是互相扶持,而不只是单方面的依赖。
经历萧军出轨和家暴后,萧红却仍然没有放开他的手。
即使在1936年7月,她听了鲁迅的话远渡日本,与萧军暂时分开,还是不断给萧军写信,要他寄书、买枕头和日用品,鲁迅去世后,1937年初,萧红归国,她得知萧军再次出轨密友的妻子许粤华,还让许粤华“珠胎暗结”,而萧红依然没有离开这个不折不扣的渣男,她一边与萧军争执不休,一边回到他身边,怀上了萧军的孩子,而萧军却根本不打算娶她。

端木蕻良
深感自尊心已经扫地的萧红,得到萧军朋友端木蕻良的安慰,便开始不断向他倾诉内心的沮丧,端木蕻良身材瘦高、穿着洋气、说话和气,看起来文质彬彬,很是通情达理,与暴躁易怒的萧军是两种人,在萧军与萧红发生争执时常站在萧红一边,也很认可萧红的文学才华,作为资深《红楼梦》迷,端木蕻良认为萧红就是他眼中的林妹妹,这一人物定位与萧红的自我认知不谋而合。
此后,萧红常主动去找他谈创作,还在纸上写下“恨不相逢未嫁时”的诗句,向他展示。
1938年4月,怀着萧军孩子的萧红跟着端木蕻良回到武汉,并在那里举办了婚礼,这也是她人生中唯一的一场婚礼,她期待自己的婚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而端木蕻良却不是个可以给她依靠的人,他出身乡绅家庭,是家中的宠儿,生活能力差,不会照顾人,向来依赖他人的萧红,对新婚丈夫深深失望,她生孩子的时候,端木蕻良为了逃离日军正在进攻的武汉,一个人先跑去了重庆,萧红好不容易才又买到一张来重庆的船票,而正在沙坪坝忙着编刊物的端木蕻良却根本没管她,把即将临产的萧红安置在远房亲戚家里,萧红只得一个人去医院生了孩子,孩子生下三天后就夭折了,她对好友白朗感叹道:“我会幸福吗?未来的远景已摆在我的面前了,我将寂寞忧悒以终生!”

萧红
果然,1942年,萧红垂危之际,端木蕻良再次扔下她一个人逃难去了,住在香港玛丽医院的萧红失望已极,她生怕身边唯一的朋友骆宾基也会离开,拉着他说道:“对现在的灾难,我需要的就是友情的慷慨!你不要以为我会在这个时候死,我会好起来的,我有自信!……送我到许广平先生那里,就算是给我很大的恩惠,我不会忘记,我会健健康康地出来。我还有《呼兰河传》第二部要写。”

萧军、萧红、许广平、周海婴在鲁迅墓前
她记得鲁迅与许广平对她的慷慨相助,鲁迅先生已经不在了,那么,许广平是她唯一的指望,而她不知道的是,许广平此时已经从上海租界房子里被抓走,正在日本宪兵队经受毒打和审讯。
她甚至还想念起了萧军,认为萧军如果知道了她的处境,一定会来香港救她,而远在延安的萧军听到萧红的死讯后,却一滴泪也没掉,还声称:“我并没有什么‘遗憾’之情!”在日记中,他抱怨道:“在这社会上,她们总是重重地压在你的肩上,使你精疲力竭,而她们并不企求上进!”
对于萧红的柔弱、爱依赖人,甚至连许广平也是有些厌烦的,她在回忆鲁迅临终前的那半年时光,写道:“这时过从很密,差不多鲁迅先生也时常生病,身体本来不大好。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的耽搁在我们寓里。为了减轻鲁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不得不由我独自和她在客室谈话,因而对鲁迅先生的照料就不能兼顾,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
敏感的萧红,认为她一生“尽遭白眼冷遇”,这感受并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
而令她感动的是,年长三十岁的鲁迅对她有无尽的包容和理解,他从来没有厌烦过萧红,萧红可以随便登堂入室、进入他的生活,在家里安排晚饭,可以在鲁迅面前展示自己的穿着求点评,甚至,在鲁迅自己发烧不退、病入膏肓的时候,还充满怜惜地说萧红太瘦了。
后来,在别人说鲁迅对待萧红像一个父亲时,萧红说道:“不,哪有那么好的父亲,应该说是像祖父一样的。”她自己的父亲,的确是没那么疼爱女儿。
萧红的这种殊遇,后来常被误会成她与鲁迅有几分男女之情。
其实,鲁迅何尝只资助过她一个人出书,同乡姑娘许羡苏来北京投奔他,不但在鲁迅家先后住了几年,她哥哥许钦文也由鲁迅资助并亲自选校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故乡》,从此名声鹊起;柔石被人引见给鲁迅后,两部长篇小说受到鲁迅赏识,很快被推荐发表,还开始负责鲁迅的《语丝》杂志,因来往频繁,被认为与鲁迅亲如父子;瞿秋白被介绍给鲁迅后,鲁迅称“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为身无分文的瞿秋白租房、出版文集,瞿秋白就义后,鲁迅临终前几天抱病促成了《瞿秋白文集》的出版;只听过鲁迅几节课的许广平因女师大风波写信向鲁迅求助,鲁迅把她安置在家中,写了二十几篇文章力挺女师大的学生复校,因此被教育部开除……
文笔犀利、临终也说着绝不宽恕的鲁迅,却有着最怜惜弱小的慷慨之心,他从小丧父,多年来担负着一家老小的生计,为人乐于奉献,平生帮扶过的人无数,萧红只是其中之一,只不过,善感的萧红,在孤独漂泊多年后,突然遇见这种罕见而巨大的善良,既感激又依赖,以自己精致细腻的文笔进行了深度刻画,才使这段忘年交更加广为人知。
而在她此后的人生中,再也没有遇见过同样的热忱与接纳,让她至死难以忘怀。
鲁迅身后被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没有和任何人合葬。
1947年,鲁迅的原配妻子朱安去世后,曾向许广平遗言想与鲁迅合葬,也未能如愿。1956年10月,鲁迅逝世20周年之际,迁往虹口鲁迅公园安葬。1968年3月,许广平去世后,遗言不留骨灰,后来经周总理批示,将她的部分骨灰撒在了鲁迅墓前的小树林中,充分肯定了她在鲁迅人生中的地位与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