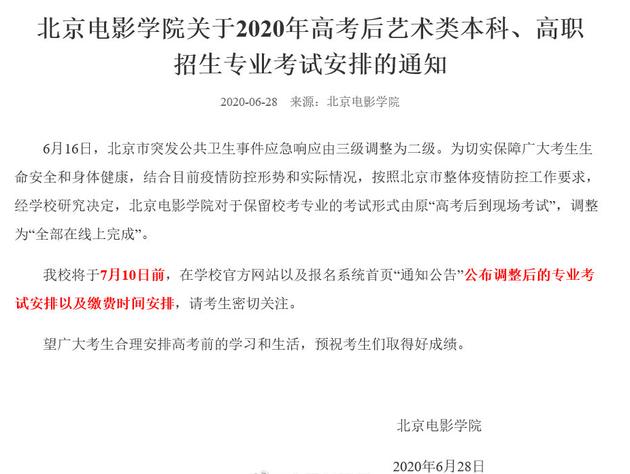哪里有移民群体生活的炊烟,哪里就有民间民俗艺术的亮点。浦东在南北朝时还处于浅海之中,直到唐开元元年修筑一条旧捍海堤岸,于是逐渐有了人口的聚集。宋元时代战乱频繁,宋朝迁都到临安(杭州),兵荒马乱中许多中原大户人家、难民、巫师、僧侣、道士、民间艺人纷纷来到浦东,与当地古吴越人生活在一起。由于黄浦江屏障阻隔的特殊环境,浦东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有一千二百余平方公里的广阔田野从荒芜逐渐到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使得古老历史跨度久远的说唱艺术像“活化石”留存在浦东。在“熬波煮盐”的浦东,佛教“唱导”衍变而成的“说(唱)因果”,成为传承民间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农村没有娱乐,除了到庙里去烧香拜佛祈求神秘的幻想之外,就是去吃茶听书消遣,浦东说书是适合农民文化娱乐的需求。

首先,说书艺人不仅依照坊间流传的刻本《水浒传》话本小说进行演唱,而且是根据代代相传的口头创作,口传心传,更重要的是还依靠自己的摸索与尝试,收集本土文化、民风民俗、当代新闻,进行再创作,在结构设置、情节安排、人物性格刻画及其连续性的保持和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等等大致不走样的情况下插叙内容越来越丰富,在不断说书实践中以诉诸听觉为手段、为娱乐农民听众为目的,每到一个新的书场演出都不会简单地重复或抛弃,而是经过仔细琢磨咀嚼,又根据说书艺人对生活的感受和认识,经过精心揣摩、构思、反复说唱和锤炼,将以往丰富的积累转化为自己特色的传统节目。例如施春年版水浒,不同于沈飞熊版水浒,因为他们的细节描写和插叙内容并不完全相同。
其次,说书艺人插叙的内容可以根据农民对象和书场变化“移花接木”。笔者听施春年打虎情节可以安排到《霍元甲·打虎》《林海雪原·上山打虎》等不同书目中。至于“外插花”的知识性、趣味性、“肉里噱”、新闻性情节都可以安排到其它书目中,在选定的条件下进行再创作,因为话本小说《水浒传》几百年来无论是城市平民、农民、妇女、孺子,几乎人人都知道的人物和故事已经相当普及。浦东农民到茶坊听书听的是说书艺人改讲的丰富细节描写来比较艺人说书水平的好坏,在插叙中获得更多知识,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国家大事、上海和浦东新鲜事,听书是农民共同喜爱的一种娱乐方式。
再次说书艺人将讲唱“话本小说”为谋生手段。
姜南《芙塘诗话》卷二《洗砚新录·演小说》曾经写道:
世之瞽者,或男或女,有学弹琵琶,演说古今小说,以觅衣食。北方最多,京师特盛,南京、杭州亦有之。
浦东说书艺人从清末民初“唱导”法师美丽转身而来逐渐消失,是民间艺人移民来到浦东,随着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艺人以说唱为谋生增多。《水浒传》在明代通俗小说基本上都是供民间流传阅读创作的,说书艺人将说书抄本给自己秘藏的称之谓“话本”,将平时演唱内容丰富的脚本只传给子弟或徒弟,例如一本《水浒·武十回》可以讲唱半个月到一个月,又可根据与书场老板合同时间可长可短,说书艺人的话本手抄本与《水浒传》有较大的差异,说书艺人“欲知后事,听客明日请早”是一种谋求生存的最好方式。
第四,说书艺人对善恶标准不一。例如,武松醉打蒋门神是因为施恩对武松施了恩,武松成了施恩的打手,梁山好汉能够“仗义疏财”。施恩和蒋门神都是因为看好快活林是块肥肉,快活林是山东、河北客商们都来做买卖,有百十处大店,三二十处赌坊、兑坊,有过路妓女之人,是十分赚钱的地方。施恩和蒋门神不是善与恶矛盾,而是黑吃黑的内讧,是弱肉强食,武松对此善恶并不关心,武松只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说书先生很少去分析这种善与恶的关系,只是热闹地说唱江湖上的义气或交情,不是讲是与非,农民听众只是同情武松和施恩梁山好汉,狠的是蒋门神和被武松无故杀害平民百姓的酒保。
第五,说书艺人插叙不用考证,尽可自由杜撰和发挥,例如,炊饼如何做,小说没有交代,只有一句武松出差前对哥哥大郎讲:“假如你每日卖十扇笼炊饼,你从明天为始,只做五扇笼出去卖。”大郎炊饼用笼屉蒸出来的面食,应该类似今天的馒头。为什么将蒸的馒头叫炊饼,有人考证在宋仁宗时,因为宋仁宗叫赵祯,“祯”与“蒸”谐音,为了避讳,宋代人将“蒸饼”改叫“炊饼”。
第六,说书艺人选择热闹的情节来演出,有比武、打虎、打擂台、婚丧、吃酒等,例如:《水浒》中出现虎有四处,洪太尉遇到过虎,此虎对人咆哮一阵,往后山坡跳下去不见踪影;武松在景阳岗遇虎,是几天没有吃人的饿虎;李逵遇到的是饱虎,李逵连杀四只虎,解珍解宝打的是受伤之虎。说书艺人插叙浦东之虎,在以上四处都可以用,这要求艺人对插叙“量”的分配,和观众是否已经听过进行合理“组装”的艺术效果而定。
第七,说书艺人在演出时常常会讲佛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一到,全部报销”和随缘济世,其内容有:与人为善;爱敬存心;成人之美;劝人为善;救人危急;兴建大利;舍财作福;护持正法;敬重尊长;爱惜物命。善行无穷,难以尽述,由此十条推广开去,那可以齐备了。
第八,说书艺人对巫释儒道的理解也可以自由发挥,武松也曾入过佛门,又愤然离开。水浒中写了许多和尚,有名的是鲁智深,他喝酒吃肉,放火杀人,大闹五合山,鲁智深蔑视践踏佛门。水浒中描写道士,如飞天蜈蚣王道人霸占妇女。水浒是市民文学,对宗教态度有褒有贬,说书艺人只是经常地说唱让农民娱乐。何况水浒本身也是艺术虚构,这种虚构是为了使故事情节曲折生动、丰富多彩的市井画面。墨子在《墨子·天志》中说:“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贱,必得罚。”
文化求根,也求变,忌讳老套与复制,模仿与抄袭,没有创新,就会失去文化的生命。
水浒这部现实主义杰作,经过一代一代说书艺人的再创作,在话本小说《水浒传》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整理,同时不忘记对本土文化历史、生活风貌、地方特色和民俗风情相融合,所以才会有更多本地听众的欢迎和不同版本的话本说唱。
一位美国人类学家说过:“乡村音乐被描述为一种特殊的区域性的丑文化,它与一种特殊的地理和社会体验,即南部和中西部农村生活的那种特殊体验息息相关。”同样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为浦东农民服务为农民欣赏适宜享用,具备拥有和消受的条件,曲艺本土化是重要的规律之一,也是延续民族民俗的重要载体。浦东农民依海而居,择水而生,浦东本土文化就是在定居年代里生成相对稳定的形态,浦东文化同时又在迁徒岁月中发生流变与融合,浦东文化同时又在相对稳定中积淀,在融合中嬗变,在作息的劳动过程中生成和升华,产生了许多民间传说和故事。说唱艺术视浦东本土文化是活水源头,农民听众的参与,是浦东说书创造、创新、传承的前提。
《水浒传》是经典作品,草根水浒同样需要呵护。浦东说书版水浒,插叙浦东大量信息,体现出浦东移民文化迁移、文化渗透、文化认同的深刻内涵,满足移民到浦东在不同时空中的情感诉求,实现了休闲文化的日常需求与族群的文化记忆之间交流与互补,同时也让移民群体和本土吴越农民的喜爱和享用。因为任何曲艺都是特定地域和人群所用的语言语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且与特定的乡土文化紧密相联系的,一方水土培育一方艺术,而且要为那里的人群接受服务,浦东说书水浒插叙浦东的乡土文化为农民喜闻乐见才能更好地传承和传播喜闻乐见的精品节目。

总之,浦东说书曲目维护伦理道德、塑造群体性格和杰出英雄人物,固守民族的价值观念,不断地插叙巫释儒道的格言、思维方式、民风民俗,往往是讽喻朝政,愉悦领导,上达民意,高台教化,匡正时弊。《水浒传》宣传了一种游民“造反有理”的思想,由于佞幸传权,武官受压,吏人没有出路,正义不能伸张,官场腐败,社会黑暗,所以肯定逼上梁山聚众造反的合理性。但是作为正统的儒家思想是维护社会稳定,孔子反对犯上作乱,佛家、道家都是主张应该各安其位“教人为善”。无论是正宗的《水浒传》还是浦东说书水浒,承载着民间艺人的深情和激情,凝聚着天下老百姓的希望和寄托,栩栩如生的一百零八将成了刚正之骨,浩然正气楷模,让听众津津乐道,宋江等人起义的故事并未随着北宋王朝的灭亡而消失,而是在大江南北,城市乡村各地流传,特别是引起社会下层人民群众极大关注和兴趣。胡适先生曾说过:“在500年中,流行最广、势力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书,并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理性语录,而是几部白话小说,《水浒传》就是其中一部奇书,是我国文学的正宗。”笔者认为民间曲艺水浒也是我国民间文学瑰宝的其中一部。(作者:严世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