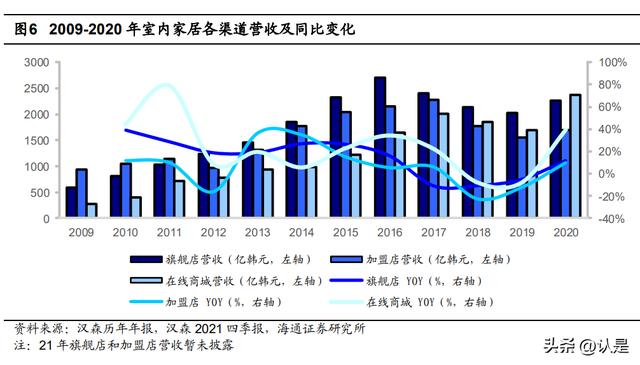从《社戏》到《故乡》
——鲁迅所要“呐喊”的是什么
突发奇想,大脑中蓦地蹦出一个念头:《社戏》和《故乡》都出自鲁迅先生的小说集《呐喊》,它们均被选入了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从教材选入的部分来看,《社戏》描绘的是清末江南水乡的情形,《故乡》则讲得是1920年前后发生在江浙一带的琐事,从《社戏》到《故乡》时间跨度近三十年,鲁迅先生要从这两篇文章中“呐喊”什么呢?
自知能力有限,才疏学浅,难以对其博大精深的文章评价,恰巧在搜狐网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清末老照片:江南原生态的水乡美景》有这样几句话引起了我的关注,就暂且说一说,以抛砖引玉:
1900年前后,北方因为有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乱频繁,社会不安定。但是江南一带有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与列强合作,搞起了“东南互保”,社会局势比较稳定。
清朝时期,江南一带不仅风景优美,更是朝廷财赋和漕米的重地。这里历来是鱼米之乡,盛产大米,无须多说。晚清时期,江南的开埠城市较多,国际贸易繁盛,各类商业发达,是朝廷筹措经费的最重要的地域。
钱理群先生的《周作人传》中也这样说到:“尽管时代的大气候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周作人故乡的小气候,却暂时风平浪静,维持着封建末世的太平景象。”这就应该是《社戏》所描述的和平富庶安定的清末江南水乡,民风淳朴善良,老百姓安居乐业。只可惜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末日大清王朝的内忧外患之中,这种暂时的宁静并没有得到长久的维持,很快辛亥革命爆发,大清王朝被推翻。国家并没有得到安定和进步,反而陷入了军阀混战之中,各方势力,你方唱吧我登场。封建旧势力,民国新军阀,再加帝国主义列强,搅在一起,乱在一起,中国将何去何从?让当世人迷茫而踯躅。先知先觉的文人志士,在北大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的主将在运动中,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当时鲁迅正在北京,并参与其中,这也是后来写作《故乡》的背景,国家已经凌乱不堪,民不聊生,却让人又充满着希望。
《社戏》中双喜聪明睿智,阿发淳朴善良,六一公公和蔼可亲,景色也十分优美,“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作为有文学救国情怀的人,鲁迅先生写这篇文章,是要先树一个标的,所希望在农村生活就是这样。虽然戏并没有什么特色,但在我来说却是无比的好,无比的难忘,正因为是山好水好人更好,才使戏显得更好,以至于使自己终生难忘。
什么是悲剧呢?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事物毁给人看。“我冒着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看到的却是,“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于是“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二十年后再回故乡,看到的却是“物是人非事事休”,闰土变得麻木不仁,是将希望寄托于神佛,只是对烛台和香炉非常感兴趣“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豆腐西施杨二嫂变得尖酸刻薄,肆意妄为污蔑别人。这些转变跟北洋军阀的混战是难脱干系,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等无数仁人志士,通过艰难奋争得来的中华民国,在袁世凯去世后,竟为了争权夺利,乱做一团,大好河山变成这样,岂不是悲剧?怎能不使求强图存的有志之士心生愤恨?
鲁迅先生心怀天下,渴望国家富强,不再受列强欺凌,于是弃医从文,想在精神上唤醒民众,但在现实中,经过多次失败,他意识到,“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因此感到无比寂寞,在《呐喊》自序中说,“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在老朋友的盛情邀请之下,他又重拾信心,去打破那“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他相信铁屋子是一定会被打破的,“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在“五四”科学、民主、自由精神的感召下学生和工人在运动中取得了一个个胜利,更使鲁迅先生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虽然那时他还未对未来社会的模样没有一个很好的蓝图,他对未来的社会充满了信心,他理想中的社会比《社戏》中的社会更要好,他因此要为之“呐喊”,于是他在《故乡》的结尾写这样道:
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以上只是一点粗浅的想法,敬请各位大家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