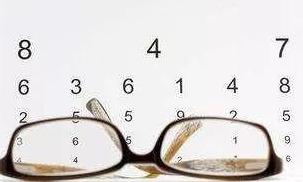一夜之间“伞兵”成了敏感词,源于网络谐音的梗,冒犯了这个词本身所具有的“象征着英雄气和胜战魂,代表着光荣和勇气”的内涵,这让包括笔者在内的正常人都难以接受。
反对正常词汇污名化,反对网络造梗无底线,是一个国家语言保持纯洁性、严肃性和尊严的必要之举,所以对“伞兵”的封杀屏蔽,具有正当性,也反映出网络语言的变化创新不能偏离主流民意。不过,抱着知其所以然的态度,一个不文明词汇“shabi”为什么要谐音“伞兵”,现象本身也值得深思,不是一句“扭曲公序良俗”的价值批判就可以了之的。一位网友感慨说:

他将“伞兵”谐音梗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楚了,不过我感兴趣的是最后一句:脏话本来是一种刚需。这句可谓世界所有语言中的规律性“真理”其实揭开了人类所共有的文化心理:这个世界太操蛋,无以言表,只好用更操蛋的语言来表达对它的认知、情感和价值判断。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言“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脏话乃是我们透过语言对这个世界的禁忌规范、不公不义、黑暗混乱,乃至美好伟大,表达出的愤怒、憎恶、怨恨、烦恼、嫉妒、报复、赌誓,甚至舒服、玩笑等等。人潜意识里有力比多的冲动,情绪里有喜怒哀乐的动荡,认知里有歧视侮辱的偏执,文化里有“骑驴诗客骂先行”的积习,注定了面对世界的种种不可理解、不可认同、不可思议、不可把控,争辩无用,动手无胆,只好詈骂随之,嘴炮先行,用心理学的话说,骂是人们由于心理上的压抑而产生的应激反应,而采取的发泄方式。受压机制是骂的创造机制,这也可能是古今中外脏话仍然大行其道的原因。
二
像“shabi”之类涉及性的骂人话,是所有骂人话里的最大一类。原因很简单,在非理性世界里,性的能量最强大;在理性世界里,性的禁忌最强烈,所以,用“性”去侮辱去谩骂,成了最直接、最有效的宣泄方式。只要社会还存在人性压抑、道德保守和精神禁忌,不方便谈及性,那么,涉及性的骂人话就永远是欲望对冲、意识对抗的首选利器。今天在网络上骂一句“shabi”,其实和《红楼梦》中贾府焦大灌满黄汤后“任意洒落洒落”本质是一样的——这让人想起鲁迅在《言论自由的界限》里说的:“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能做文章,就以文字发牢骚;不能做文章,就以语言骂翻天。牢骚和骂背后的心理动机是一样的:忍不住“shabi”地骂一句,只是因为那个称为“shabi”的人或事压迫着自己无从改变它,无法漠视它,怀揣着石头放不下,只好以骂来纾解自己的心理压力。从这个角度说,骂出来的“shabi”,如飞去来器,射人反射己,其实是自我“shabi”的写照。这是语言“双刃剑”的一个很好的例证:语言的平等性,使得使用者以其伤害别人的同时也是对自己的贬低和伤害。
但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有历时性的功能转变。骂,语言学上也叫詈语、詈辞。放到远古社会,它有“咒”的功能,所谓巫灵的语言魔力;放到近古社会,它有“辱”的功能,所谓不求伤害性极大但求侮辱性极强的语言歧视;放到现代社会,科学昌明,“咒”谈不上,众生平等,“辱”也减等弱化,更多的其实是“谩”(轻视、缺乏教养),所谓伤害侮辱都谈不上的纯粹表明态度的语言惯性而已。一句“shabi”,用以骂“人”不过百无一用的瞎比比,用以骂“事”不过无可奈何的随口一叹,无关痛痒,难着痕迹,更像是“妈的、丫的、奶奶的、妈了个巴子、娘希匹”之类的大众习语、口头禅,除了口齿留“脏”之外,没有什么意义。甚至久而久之,如鲁迅所谑称的,国骂“他妈的”一词可以说已经醇化为“我的亲爱的”,马季在相声里也将“他妈的”等同于“wonderful”,“shabi”已然进化为等同哎呀、哦豁、诶嘿之类的感叹词、语气词,那更是脏话无力无用之余的唾面自干,娱乐精神的转型成功。(有研究指出,《金瓶梅》就中近1/3的骂詈之语并非为了咒骂、辱骂等目的,而是笑骂、戏骂,常常以戏谑为目的,打情骂俏,打牙犯嘴,以骂取乐,消愁解纷。这从《红楼梦》里也可以看到。说明骂从侮辱功能转向调笑、亲和等其他文化功能,也是一个很久远的现象。)
无论好坏美丑,无论虚实真假,无论表情表意,都需要詈语脏话,这就是其“刚需”意义之所在。
三
和雅言一样,詈语也反映出一种语言的长度、厚度、广度,越伟大丰富的语言,詈语肯定也花样百出——据统计,仅在《汉语大词典》中的詈词就有近1000条,这还是因为载诸典籍而收录进大雅之堂的,还有更多的口语、方言中的大量詈词,没法收录——就像研究者所言,无论是詈语,还是雅言,从语言自身而言本无所谓高低贵贱,都是人与世界一切关系的表现形式,都是我们所赖以了解和认识世界的工具。好几位研究者不约而同引用了何新《我走入黑社会》里的一段话:“各个民族在骂的语言中,提炼、集中了一批最洗炼最形象的语言。骂人话,又是一种丰富的世界,当你最初面对它时,会感到肮脏而不知所措。但一旦了解了它,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自有它存在的道理、它的逻辑、它的实用性、它的美学和价值观。”
汉语博大精深,詈语也丰富多彩,是自然且当然的逻辑,有研究者专门整理了从古至今汉语詈语的总体变迁,发现可以分为春秋战国至三国两晋时期(古代)、宋朝至五四以前(近代)、五四时期至今(现代)三各阶段。古代人喜欢骂一些“役夫、畜产、废物、老奴、狢子、死狗、蛮子、祆贼”之类的话,注重维护纲常人伦,严防人物夷夏之别,体现了当时社会价值伦理规范,可谓骂人的宗法伦理时期;近代人喜欢骂一些“贱人、淫妇、死囚、光棍、小蹄子、三寸货、贼野狗”之类的话,偏向维护社会禁忌,严防身份地位之别,体现了当时充满市民气象的社会心理,可谓骂人的民间立场时期;现代骂人就不必多列举了,杂糅古今中外,体现了语言高雅文明观之下的亚文化风俗功能,可谓骂人的“粗俗、不文明”时期。
无论哪一个时期,雅言和詈语从来相伴相随、相辅相成,如同语言的阴阳二气,纠缠难分,共同成就了汉语的丰富性、多样性、文学性和特质性,也像我们表明,汉语从来不是一种纯洁、高尚的语言,从来不是一种道德感极强、道学气极浓的语言,相反,驳杂不纯、雅俗共赏更像它的本来面貌。如同研究者所言,“在每个社会中,几乎所有人在其一生中都或多或少地使用过詈语,且不说市井平民,即若贵为皇帝的最高统治者、德贤具备的命妇、深居高阁的千金小姐,也免不了骂人。在古代中国,汉高祖刘邦骂人是骂出了名的,诗祖屈原的姐姐平时温文“蝉媛”,到关键时刻竟也“申申其詈予”;曹雪芹心目中的少女偶像林黛玉,嘴里也曾吐出“促狭鬼”、“蠢才”的字眼。可见,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骂人或使用詈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就提醒我们,还原詈语之类“语言杂质”“文字渣滓”的真实功能和文化意蕴时,一定要跳出文明/不文明、俗/雅、洁/不洁的二元对立的“二极管”思维,既要认知詈语的文化价值,也要明白单纯地堵、屏蔽、封杀,是没有办法“净化”语言的,也没有可能“净化”网络的。就算禁得了一个,它也可能以拆字、谐音、外文字母、缩写等等其他方式多个形态变形重生,“伞兵”就是最好的例子。
这时我们该怎么办?社会道德有底线,不容语言无序突破,在两者的拉锯中,疏导还是更有效的手段。语言学上将这种疏导称为“洗白”,如同招安梁山好汉,语言通过其化俗为雅、去俗就雅的机制,将一些充满戾气的脏话“招安”成规训有加的净语。比如,和“shabi”并"美"的“我肏”一词,“肏”本是骂人用的下流话,“我肏”带有詈骂的意思。但经过“wo擦”“卧 槽”“WC”“我去”等一系列变体,其意义离本来的詈骂意义越来越远,辱骂程度也越来越轻,逐渐实现“洗白”。“我去”一词甚至还出现在春晚的小品中。再比如,和“shabi”类似的“泥马”“玛丽隔壁”“魂淡”等谐音詈语,都是使用两个不相关的字词组合成新语,字面上不容易和詈骂联系起来,以无意义联系来“洗白”原意。
之所以出现“洗白”现象,一是语言本身具有求雅的内在动力。随着文明素养的提升,人们在表达时往往会有意识规避粗俗字眼,有意选择别字或同音字代替,以求“信、达、雅”;二是社会的规范外在强压使语言自行过滤,由此产生了一批新兴詈语。
这给了“shabi”在现代语境、网络语境里何去何从一个启示,我们可以封杀“伞兵”,可以屏蔽“傻x”,但也要给它一个“洗白”的机会,比如用“沙币、烧饼”来替代,默认而不加以管控,最后约定俗成为一个统一词汇,在高频传播使用中逐渐淡忘原本意义,不失为大禹治水“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疏而不堵的古老智慧。
四
我们生在一种语言里,就像爱一个人,他/她的“优点”能接受,“缺点”也要接受,美能欣赏,丑也能包容。我们有幸以汉语为母语,千年之下,常变常新,其中的詈语,饱含着我们强烈感情的真实流露,积淀着我们传统和深层的文化心理,也折射着我们民族的观念和文化价值。在这里,少一个“伞兵”,可能只是技术处理下的无关紧要,但如何认知詈语,如何面对詈语,如何引导詈语,却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技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