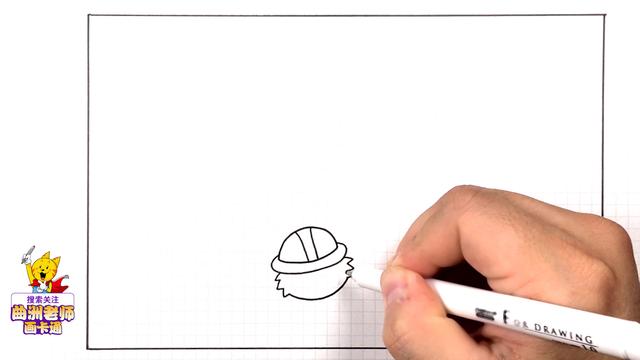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靡乱与希望比肩而行。茅盾的长篇社会剖析小说《子夜》以三十年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为现实背景,描绘以吴荪甫为代表的民族资本家试图挽救民族经济的奋斗与迷失,呈现了一幅真切而热烈的社会图景。在吴荪甫和赵伯韬等人明争暗斗的情节之外,有许多生动鲜明的女性形象活跃在文本之中。

她们当中,有养尊处优有钱人家太太和小姐,有在声色中讨好男人的都市交际花,也有卖命挣钱的工厂女工。她们处于社会阶级的不同链条之上,拥有不同的身份和地位,面临不同的生存境遇和人生选择。然而正是多样化的女性形象,为我们构筑了不同的女性生活图景。她们身上鲜少具有清晰明朗的进步色彩,却是背负着时代的牢笼,小心翼翼地想探出牢笼之外,最终也不得不瑟缩。失落的女性身上,其实寄托了茅盾对于女性发展的期待。

(一)抑制爱情的“无端扩大化”
林佩瑶是《子夜》中典型的知识女性的代表,与同时代受尽封建家庭与礼教束缚的女性不同,她接受过五四时期启蒙思潮的熏陶,属于受过教育的先进女性分子。茅盾认为“解放的妇女”首先要在精神上有人的自觉,然而林佩瑶作为知识女性,她的独立人格与自由意志没有突出的体现,更没有成为解放的妇女去帮助其他女性挣脱封建的牢笼。她好像只是试戴了一下“知识女性”这一桂冠。因为在教会女校读书时,她只是尽情享受着“五四”以后新得的“自由”,肆意畅饮着青春的美酒,对爱情充满幻想,满心期待着俊伟英武的骑士和王子的出现,却没有意识到自身与时代的关系,只关注时代给个人带来的快乐体验,导致人生格局的促狭。林佩瑶是知识女性,可是她与这个时代是断裂的,她向一个真正的新女性的跨越也是失败的。

林佩瑶从成为吴家三少奶奶时起,就彻底与她的“密斯林佩瑶时代”告别了,这也标志着她从知识女性重新走回了旧式家庭。父母相继死去后她嫁给了吴荪甫,说明她仍旧是依傍于家庭的。生活在吴家的林佩瑶似乎是困在一个瓶颈里,她在当下与过去之间徘徊而痛苦,充满了犹疑不定。虽然物质条件充裕,但她总有种“缺少了什么似的”的感觉,一本破旧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一朵枯萎的白玫瑰花时时牵扯起她和雷参谋之间的青春回忆。喷薄的情感和伦理的忠贞拼命地撕扯着林佩瑶,让她痛苦不已。可是雷参谋与徐曼丽勾勾搭搭,丈夫吴荪甫一头埋在事业里,平时也少不了逢场做戏。这就是林佩瑶人生格局的偏狭,一个知识女性终日为个人情爱迷茫和惶惑,承受内心挣扎的最终也只有自己。

茅盾新女性观的核心是“女性的自觉”,女性要自觉把自己当作一个人格独立、意志自由、有人的权利的人。显然,林佩瑶不具备“女性的自觉”。爱情不应该成为女性生活的全部,一个理性而独立的女性,不应该情感之上完全依赖男性的爱情。在特殊的时代环境里,知识女性不应该光对自己不圆满的爱情自怨自艾,而应该把目光投放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大环境之中去;不应该对于新思潮浅尝辄止,而应该为动乱的社会贡献出妇女的力量。只有女性摆脱狭隘的观念,真正走向理性与自觉,实施自己对自己的解放,妇女的解放才有可能。

(二)自主而理性的恋爱与婚姻
茅盾在《子夜》中也投注了他对于新女性道德观的看法,主要体现在女性恋爱和婚姻之上。林佩珊也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凭借着优裕的家庭环境,她的生活是无拘无束的,思想也自由而开放。她每天就是与范博文、张素素、李玉亭等人玩笑取乐,偶尔通过谈论时事来寻找乐子。
林佩珊先是与范博文关系亲密,后来又把相似的情感投向杜新箨。可见她对于爱情是摇摆不定,无一准信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爱,又都不可爱”、“老是和一个人住在一块,多么单调”是她的真实想法,说明林佩珊在爱情上缺乏理性思考。在林佩珊那样的年纪,她那小小的灵魂里并没有觉醒了什么是真正意义的恋爱,她一切都不过是孩子气的玩耍罢了。在林佩珊的婚姻选择上,吴荪甫不喜欢范博文而倾向杜学诗,林佩瑶心里暗暗希望妹妹能与雷参谋成为眷属,林佩珊自己也摇摆不定。

茅盾强调恋爱神圣和以恋爱为基础的婚姻,恋爱要灵肉合一,而婚姻正应该建立在这种高度浑融的爱情之上。《子夜》以林佩珊这一人物入手,深刻描绘她因为稚气未脱而在恋爱与婚姻上面表现得极不成熟,从反面说明恋爱与婚姻是神圣的,肯定女性有充分选择自由恋爱和婚姻的权利,选择之时要充分遵循自己内心的情感,但是同时也要尊重恋爱与婚姻。自由而理性,这才是女性对待恋爱和婚姻的正确态度。
(三)抓住知识女性的幽微希望
不同于林佩瑶和林佩珊两姐妹,吴公馆里的另一位女性张素素,落拓不羁而机灵精巧。她不受传统观念束缚,不满于吴荪甫的封建家长制的压迫,还乐于接受外来新思想。对于爱情她有自己的判断和追求,先后对李玉亭、范博文、吴芝生有好感,但是她不同于林佩珊的朝三暮四和游移不定,而是有自己的爱情判断标准和选择。她的身上还略微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时局的关注,在五卅运动中群众示威活动之后,既激动兴奋又害怕,即使这并不是真正积极主动地参与。相比于其他女性角色,张素素带有明显的进步色彩。

张素素身上具有一定积极的反抗色彩。即使不能完全摆脱保守色彩,但是相对于其他的资产阶级女性,张素素似乎具备了更多独立自主的品质,还稍微对时代有了关注。即使这是微小的近代性,但是如果大多数女性都能迈出这样微小的一步,那么女性的未来发展也是充满希望的。
二、沉沦的都市女性——真正的解放不需要依赖《子夜》中还有凭借个人力量在社会中谋求生存的都市女性形象,主要是徐曼丽、刘玉英、冯眉卿。交际花徐曼丽出卖自己的姿色,供买办资本家们观赏玩乐,她主要依靠肉体周旋于各种男人之间;刘玉英坚信“女人必须有自己的生财之道”,她一边谋划公债市场,一边也靠自己的伎俩诱惑买办资本家;而冯眉卿是被父亲诱骗之后,成为了赵伯韬的玩物。她们臣服于都市的纸醉金迷,在物质弥漫的上流社会里迷失了自我。
茅盾提倡解除对女性的性禁锢,但不代表茅盾提倡滥性。虽然这几位都市女性都离开家庭走向了社会,但是她们追求人生幸福的方式并不值得提倡,她们通过出卖自己的肉体来满足物质的需求,并不是真正解放了的新女性。一个真正的新女性应该是思想上独立自主而经济上也绝不依赖于别人,而这几位都市女性仍旧是依靠男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女性只有真正摆脱了附属品地位,才真正为解放。

《子夜》前面的章节,对于四小姐吴蕙芳的着墨并不多,她似乎是游离于这个大家庭之外。后面的章节对于蕙芳吴家生活的无名惆怅开始着墨,注重描绘从闭塞的农村到上海,繁华靡丽的都市文明令她无所适从。她时常感觉孤苦伶仃,都市文明若即若离令她无比痛苦,封建家庭的压迫致使她渴望逃离,无计可施时也只能把《太上感应篇》当作自己的精神依托。她暗恋范博文,却也畏畏缩缩,疑惑“为什么别人家男女之间就可以随随便便?为什么他们对于阿珊装聋作哑?为什么我就低头任凭他们的折磨”。
蕙芳的痛苦一面源于都市文明的刺激,一面源于吴荪甫的家长专制。都市文明的开放性冲击了她的闭塞心理,封建家长专制让她觉得身心都受到了折磨,于是她成为了吴老太爷在人世的延续,开始信奉一些虚无的东西,以此来麻痹自己。直到得到张素素的鼓舞,她才鼓起勇气留下字条走出了这个让她倍感压抑的家。

茅盾认为,社会解放是妇女彻底解放的根本出路,个人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必要准备和重要内容。个人解放就说明女性要学会自主在思想、文化、道德上提升自己,转变自己的观念,实现个人的精神解放。蕙芳个人应该转变原先的“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的传统观念,主动去接受都市文明。此外,女性如果若要取得自身的独立,就必须学会反抗与封建家庭的专制,只有勇敢地反抗家庭,走出家庭,才有可能去追求自身的幸福。
四、悲惨的女工——个人奋斗与正确指引相结合《子夜》的罢工风潮中涌现了许多女工形象,有以姚金凤为首的既想为自己谋取利益、也甘于被屠维岳等资本家利用的动摇派,还有何秀妹、张阿新、陈月娥等选择听从共产党人指引、最后走上正确道路的一群人。这些女工是社会的底层人物,她们想通过自身的努力摆脱资本家的压榨,希望成立一个公平的工会,为自己谋取合法权益。女工的生活是苦不堪言的,当吴公馆的女人拉开牌桌之时,她们只能在罢工浪潮里为自己的权益呐喊。社会底层阶级所遇非人,女工们受到的压迫很大程度上就是外在的社会原因,正是资本家肆意为自己牟取暴利。

茅盾坚信社会底层的妇女是社会运动的重要帮手,她们对于妇女解放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工人阶级是社会一大群体,她们是社会变革的一大力量。因此,工人阶级女性要遵循着正确的指引,通过不懈的斗争与反抗,来取得自身的解放。
五、结语《子夜》中的每个女性的人物塑造都有其指向性,蕴含着茅盾的深刻思想内涵。无论是哪个阶层的女性,都可以为妇女解放贡献她们的力量,都可以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在此之前,女性需要勇敢走出阶级和个人的局限性,以一种整体的时代视角来审视自身的发展,从而实现妇女的真正独立。在《子夜》中,茅盾通过塑造不同女性的命运与人生选择,从而提出了他对于女性的发展期待,同时也为不同阶级女性指明了未来发展道路。显然,这是茅盾女性观的内化与进一步发展,对于当时时代背景下女性的发展具有指导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