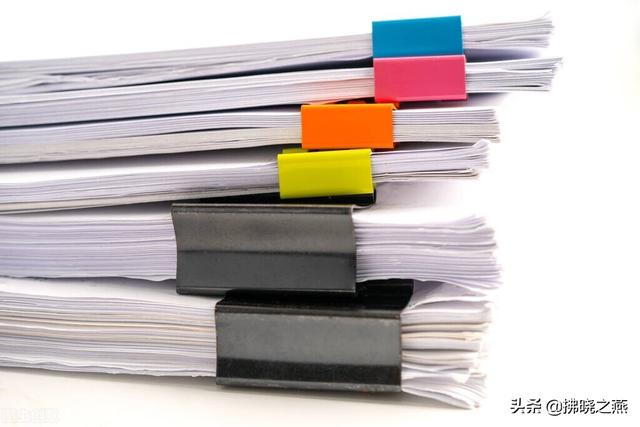宋宝颖/制图
本题来自中国一句老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里”有多长,以前是个模糊概念,民国时才规定1里为500米。再折合现代长度标准,行万里路,字面上的意思是行走5000千米。
车邮马慢、徒步丈量的年月,行走万里很难。
几百年前的徐霞客,活在世上的时间,大部分扔在路上。从《徐霞客游记》涉及的行程计算,几十年间他大约行走了50000千米,已经十倍于万里之行。关于他,还有两个数字,据说他写了260万字左右的旅游日记,毁于明末清初的战火,只剩了60万字。
你读过徐霞客的日记体散文吗?
“二十一日。早起,寒甚,雨气渐收,众峰俱出,惟寺东南绝顶尚有云气……从其外西向视之,又俱夹叠而起。中悬一峰,恍若卓笔,有咄咄表示惊讶书空之状,名之曰卓笔峰,不虚也,不经此不见也。……二十二日。晨起,为贯心书《五缘诗》及《龟峰》五言二首、《赠别》七言一首。晨餐后,复逾振衣台……此谷独飞珠卷雪,在深谷尤异。顾其危崖四合,已可名洞,不必以一窟标举也。时朔风舞泉,游漾乘空,声影俱异,霁色忽开,日采丽崖光水,徘徊不能去离开。”
上面一段,是我用心挑出来的,想让大家容易读懂和欣赏,但也是比较而言。这段话最后一句,要是翻译成现代汉语,大致是这样的:“当时北风舞动着泉流,那水流在空中飘飞,声响与光影都不寻常,忽然间天空放晴,眼前是太阳的光辉、壮美的崖壁、耀眼的水流,我徘徊其中舍不得离去。”
还有两段也容易欣赏。
“时浮云已尽,丽日乘空,山岚重叠竞秀,怒流送舟,两岸浓桃艳李,泛光欲舞。”这是写他在丹江漂流看到的景色。
“江清月皎,水天一空,觉此时万虑俱净,一身与村树人烟俱熔,彻成水晶一块,直是肤里无间,渣滓不留……”这是他在杨村忽然发出的感叹。
现代作家余光中特别欣赏徐霞客的文字,说他学识广博,文采高妙,无畏精神使他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发挥。于是,中国山水游记的集大成者,要推大自然的第一知已徐霞客。在这方面,他比历代的文学前辈好一些,也比直到民国初年的文学后辈好一些——那时候,有些作家的足迹延伸到国外,可是时代节奏加快了,生活内容增多了,让人总是很忙,少了领略自然的闲情。
有一位作家描述过徐霞客的快乐。他在香炉峰遇见了大雾,汹涌而来。在这样的大雾中,他突然看到了心中的幻象,再一看不过是往日的生活。一年年,一日日奔波流离,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我在这里?我到底要行去何处?一阵阵浓雾如同流水,穿过他的身体。直到雾气散去,山间寂然,万物坦荡,一切都是天地之初的模样。突然觉得万般思虑一扫而空,自己已经与自然景物交融。哪里是我的终点呢?徐霞客对自己说,比这更重要的是,我还行走在天地之间。
没有在大自然里的行走,就没有徐霞客心性中的快乐,没有他写作中的成就。
下面我们来看看在远处行走的另一种作家,他们去国离乡,打开了自己的眼界。
这样的作家有很多。
我想说两个例子,华盛顿·欧文,屠格涅夫,或者说我想注重一种文学现象:游历了文学大师更多的国家,把自己提升为文学大师,也让本国文学赢得了世界声誉。
华盛顿·欧文写过小说、散文、诗歌。他出生于北美独立战争结束的1783年,21岁就去了欧洲,游历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开阔了视野,让北美作家与欧陆文化的母体连接在一起。他32岁时再次旅居欧洲,时间更长,17年后回到美洲大陆,许多美国读者不认识他了,把他看成了欧洲作家。这时候的欧文,不像一个欧洲作家,也不像一个美洲作家,而是一位有自己的特点——不再跟在欧洲文学后面模仿,又摆脱了北美清教束缚的——第一代美国文学大师,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北美作家。
人们把欧文称为美国文学之父,把屠格涅夫称为首位有世界影响的俄国作家。
屠格涅夫出生于1818年,应该是俄罗斯军官从法国回到俄罗斯那一年。他们战胜了拿破仑,在法国生活了四年,感受到欧洲文明的震撼力量,得到了俄国废除农奴制的变革方向。很多读者都知道屠格涅夫在俄罗斯大地游历,写下了散文集《猎人笔记》,其实那本影响很大的书,是他去德国学哲学10年后写成的。他在欧洲先后生活了38年,被视为最纯粹的“西欧化”的第一代俄国作家。
首先,他们都有在国内国外行走的经历。
华盛顿·欧文深入西部草原考察游猎,出版了《草原游记》,为世界了解美国的自然与社会,提供了一个直观清晰的视角。
他笔下的山川自然,是心灵感受到的自然,充满了丰富的色彩变化,跟同时代作家们比起来,这可是个了不起的进展。
比如,他写到了一座群山:季节的每一次变化,甚至一天中某个不同的时辰,都变换着群山那神奇的色调和形状。四下里的家庭主妇都把这群山当做最好的气压计。天气晴朗稳定时,群山一片青蓝,傍晚的天际映出它们伟岸的轮廓;可有的时候,虽然其他地方并无云彩,山顶上却会聚起一大片灰色的水汽,在落日余晖照耀下,像辉煌的皇冠一般闪闪发光。
其次,他们在国内国外行走,比别人更深融入历史、文化、艺术和大自然。
只有融入,才有意义。
屠格涅夫寄回国内的一封信里,谈到了旅居国外的俄罗斯人,或是由于傲慢懒惰,或由于天生畏怯,或是不善与人共处,不能进入那个国家的历史,以及现实中的民众生活,于是感到疾病一样的苦闷。“他们在这方面也太缺乏素养。对他们来说,城市、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名称只不过是名称……”屠格涅夫说,他们欣赏大自然和艺术品的修养也不够,“我们这些人,没有必要假装成一副自己的东西绰绰有余的样子。”
第三,他们走到哪里,都深入人群之中,有了很多朋友。
比如法国作家司汤达去世时,送葬者仅三人,其中两位是作家,一位是年近四十的法国人梅里美,一位是二十多岁的俄国人屠格涅夫。说起法国作家圈,屠格涅夫的朋友比司汤达的还多,乔治·桑、福楼拜、都德、左拉和莫泊桑等,都是他的朋友。
梅里美评价屠格涅夫:“谁也不如这位伟大的俄国作家那样,善于让心灵掠过朦胧的陌生事物引起战栗,并在奇异故事的半明半暗中让人看到不安的、不稳定的、咄咄逼人的事物组成的整个世界。”
第四,行走四方的迷人之处,还在于能遇到有趣的事、可爱的人。
屠格涅夫狩猎时遇上的一位磨坊主的女儿,也令他心仪已久。他曾问那磨坊主的女儿:“你希望我送你什么?”那个美丽的姑娘脸红了,回答:“你给我从城里捎块肥皂来吧,好让我把两只手洗得喷香,你可以像吻贵夫人那样吻我的手。”
还有前面说到的梅里美,漫游了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他温和而高贵,像个骑士。他交友不论身份,有斗牛士、烟厂女工,有上层贵族。其中西班牙一位伯爵的4岁小女儿,蜷缩在梅里美的膝盖上,听他讲好听的故事。20年后,她成了法兰西皇后,还保持着与他的友谊。
特邀编辑:董学仁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