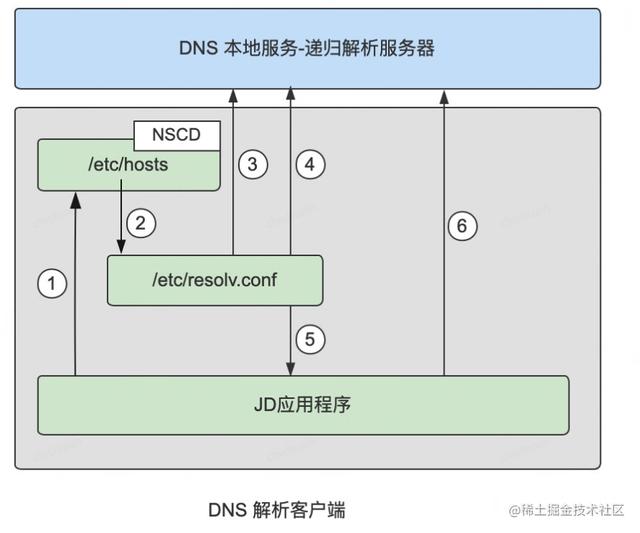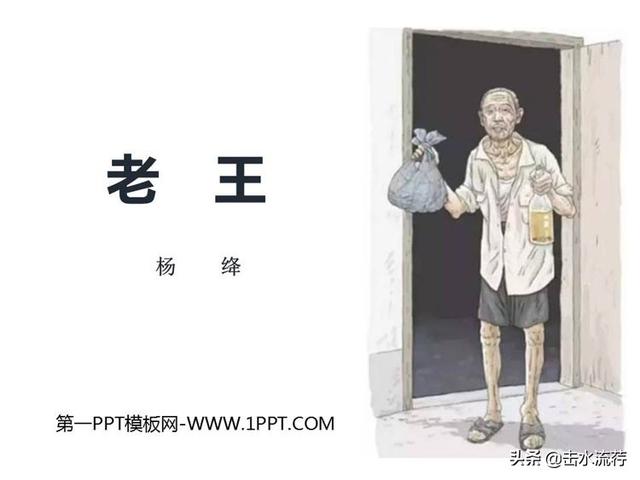
杨绛在《老王》一文的收官处写道:“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运者的愧怍。”如何理解这一句点明了课文主旨的话语,笔者以为,须厘清作家杨绛与她笔下的老王各自的“幸”与“不幸”来。不幸者仅就“不幸”而言是相同的,但不幸的原因未必相同。不幸之人有“幸运”之时;“幸运之人”也有“不幸”之日。作家杨绛和她笔下的老王既可说是“幸运者”,也可说是“不幸者”。只是他们的“幸运”与“不幸”原因各不相同。从他们的“幸运”与“不幸”的比对与映衬里,可以使人看到那些闪烁着人性的耀眼光芒。
杨绛与她笔下的老王可说是完全不搭理不搭边的两类人。老王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百姓,而杨绛一家则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之间在物质基础、精神世界、社会地位等各方面,有着近乎不可逾越的鸿沟。那么是因为什么使得他们有了交集呢?众所周知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前他们也曾相识。在那个荒唐动乱的年代, 杨绛一家落难了——学术权威当作“反动学术权威”被打翻在地,踩在了脚下——处境极为艰难。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一下子沦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比起本来就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百姓老王来,他们反倒成了社会弱势群体中的最为弱势者,其社会地位简直连老王都不如。这就是杨绛一家的“不幸”。显然这样的“不幸”是那个特殊的年代造成的。
杨绛在《老王》的结尾说她是一个“幸运的人”。这话出自杨绛的内心真心一点不假。杨绛夫妇明白,身为高级知识分子一下子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能够顽强地挺过来,“活”着走过那一段动乱的岁月,该是多大的幸运。那是不幸中的万幸,是极其不容易的。要知道文革中不知有多少高级知识分子承受不了人格的侮辱和非人的折磨而自杀身亡,更不要说那些被活活折磨致死的。杨绛的女婿王德一在文革中就被逼得自杀了就是无数悲惨案例的其中之一。
杨绛一家在文革中处境极为艰难,在遭遇到最为“不幸”的时候,却有缘遇到了像老王这样的好心人。 是老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了杨绛一家以帮助——送冰块价格减半;送老钱上医院看病。这可是杨绛的“幸运”。要知道,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像杨绛夫妇这样的“反动学术权威”是唯恐避之远离都还来不及,谁还胆敢靠近且援手相助?
杨绛笔下的老王,是一个生活在现实社会最底层的平民劳动者,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中的一员。老王的“不幸”具体表现在以下诸多方面:他是一个“单干户”,因为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进不了三轮车组织,所以“有失群落伍的惶恐”—— 他是一个被社会边缘化的落伍者;“他靠着活命的就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以此来艰难地维持生计,没有固定的收入——他是一个自食其力而没有生活保障的人力车夫;他孤独寂寞,是一个“老光棍”,“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有什么亲人”——他是一个亲情缺失的孤独者;他有严重缺陷,“瞎掉一只眼”,另一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他是一个手脚健全的残疾人;他一直居住在“荒僻的小胡同”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的“几间塌败的小屋”内——他是贫民窟的住户居民。老王的这些“不幸”跟文革不沾边。就是这样一位彻头彻尾的“不幸者”——老王却给了“不幸”之中的杨绛一家不少的帮助。杨绛与老王,他们可谓是“不幸”之中却有着“患难见真情”般的“幸运”。是极其难得的。
杨绛在《老王》中,叙写了老王的诸多“不幸”。远远不只是表明她对老王的同情和怜悯,更主要的是通过叙述与老王交往的几件事情,重在反映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草根百姓他们人性之中所具有的最为光鲜最为耀眼最为美丽的东西——即人性中的朴实真诚与善良。而这些品质正是当今现实社会所缺失而需要大力倡导的。老王就是这些品质的代表者与集成者。
很“不幸”的老王又是“幸运”的。他“有幸”认识结交到文革中处于“不幸”之中的杨绛一家,结识到了像杨绛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且认准杨绛他们是好人;因而才有机会出现在了杨绛的笔下。无数广大的读者才得以认识到了老王的朴实真诚与善良,才赢得了无数广大读者的心赞。所以像老王这样极其草根极其平凡的平民小百姓他们人性中的美丽才得以在散文艺术的殿堂闪烁发光。
而“不幸”过后又“幸运”的作家杨绛却是极有良知的。“有幸”得到了老王的帮助,深切感受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不幸”的老王他所具有的朴实真诚与善良,且在老王去世后的几年来,仍觉得有一种对老王的愧怍之情。这种勇敢的自责与反思,是杨绛之于老王“患难之中见真情”之后续的再延伸。正因为如此,所以杨绛在老王死后的几年来所生出的“愧怍”之情而又不得不令人深思“人性之美”所带给人心灵上的震撼以及所具有的真正社会意义上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