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拉杂印象:“十年的变速器”之朽坏?——为复刊后的《中国新诗评论》而作
一
大约是在10年前,收到同代诗人韩博的打印诗集《十年的变速器》,当时就觉得名字取得真好,恰切又具象,不要说大家过往的写作都到了10年这个关口,需要某种自我的总结、省察,“变速器”三个字逗引出的机械感,也吻合于成长阶段身心反复拉锯的经验。依照人生的通俗哲学,一个人的成长意味着向更高智慧的迈进,生理与社会的条件也决定这一过程必须遵循某种步调,而10年的时间正好构成一个平稳的台阶、一个可资盘点的阶段。这不仅对诗人的个体有效,对于当代诗歌的整体进程而言,似乎也可做类似的观察: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每隔10年,诗歌界的风尚就会发生剧烈的变动,一茬新诗人也会“穷凶极恶”地如期登台。2002年之后,《中国诗歌评论》无疾而终,如今恢复也大致经过了10年,某种时光内部的恒常节奏,好像暗中支配了许许多多人与事的安排。
其实,不只当代诗歌如此,即便广义的新诗,从诞生之日起,不是也受控于“十年的变速器”,逐渐从白话演为现代?无论“加速”还是“减速”,诗人先是与传统争吵、继而与“看不懂”的批评家和读者争吵,紧接着与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教条争吵,与诸多不公和压制的势力争吵,以致和冥顽不化、自命不凡的同行们争吵,10年的历程困厄重重,也能豁然开朗,危机养育了新诗基本的警觉,也形成了抗辩中柔韧、曲折的线条。久而久之,年轻的诗人会有这样一种印象,群体的、历史的节奏与个体的、生理的节奏并无本质不同,诗歌史的班车总会定时发出,以10年为间隔,只要少年时勤奋、并且足够紧张,就会有一班车停在身边,当然能否挤上去要靠运气和天分。
这种印象,显然是一种错觉。因为从某个角度看,“十年的变速器”或许只是一件20世纪特殊的装置,一件甚至可以废弛的装置。诗人们一贯苦心孤诣,想在文字与想象力的系谱中承担一切荣光和责任,但事实上文学的动荡只是20世纪历史动荡的一部分不甚紧要的投影。有一种说法,20世纪中国每隔十年,必有大事发生,改变社会与人心的走向,列举出一些特定的年份即可说明:1911、1919、1927、1937、1949、1958、1967、1977、1989。急遽变动的历史,加剧了价值重构与社会重构的速度,诗人们在文字中游击巷战,小小的抱负之一,即是挣脱外部他者的粗暴掌控,殊不知却歪打正着,有意无意分享了20世纪中国价值重构的频率。可以猜想的是,如果中国诗人只照猫画虎地取法欧美、按部就班地先锋且现代,我不相信新诗能够一度成为某种激动人心的文化,在“心声”与“内曜”意义上,一度成为某种唤醒的文化。大陆以外有些区域的汉语诗歌,在先锋且现代的方面发育更为完整、营养似乎更健全,然而做出的表率竟索然无味,这不出意外。
二
动荡的20世纪,变速的20世纪,革命的20世纪,在当代学术的视镜中,也可能是短命的20世纪,与所谓“漫长的19世纪”相较之下。这个“短的20世纪”,像历史中的另类,拒绝缓慢生成的合理化秩序,意图在普适的文明与经济之外,辟出另外一个体系。“短”,由此也引申出一系列的革命、冲突、重构、危机、转变,20世纪中国“十年的变速器”有更复杂的机械传动,但从这个角度去检修一下,应该也大致不差。然而,世纪末出现了一种时空错乱的奇观,有影响力的学人已经惊呼:革命时代的冲击和改造似乎没有发生过,经济的增长、全球化的深入、霸权的联盟与危机、社会问题的堆积,使得这个时代更像“漫长的19世纪”的复归或延伸,而与即将告退的20世纪相距更远。换句话说,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概有意要挣脱20世纪的节奏,冒着热腾腾的废气,一头要闯入貌似更为恒定的历史进程之中,这也让那个疲惫的“进程”有点猝不及防。
有影响力学人的说法,与其说在陈述事实,毋宁表达一种抗拒与思辨的诉求。事实上,怎样理解、评估两个世纪交错带来的冲撞,已让各界人士鏖战了良久。20世纪的结束不一定意味着某一世纪宏大方案的单调胜利,任何形式的“历史终结论”更多在修辞的意义上有效。或许我们注定要栖身在不同“世纪”、逻辑的相互纠葛与反对之中,注定还要寻找一种可能的语言说明自身的矛盾。在这里,对于习惯了坐在“十年的变速器”上,感伤地看待生活与世界的诗人来说,关键是:在这历史节奏又一次突变的节骨眼上,诗歌的群落怎样了呢?
简单地说,与十年前相比,大部分诗人写得无疑更好了,从乡镇到都会,诗歌界整体的技艺达到了水平线上。十年前的重要诗人,如今仍然乃至更为重要,少数人能够持续地掘进,写出了一批又一批可信赖的代表作,并将风格严肃地发展成各自的轨范。在这里,“严肃”取其中性含义,指的是某种正儿八经又心事重重的样子,不仅传统的人文主义诗人、“好诗”主义诗人,面对若有实无的外界非议或猜测,要端正着表情和衣冠,原来“反道学”的莽汉们,逐渐将反对事业扩大为广泛参股的公司事业,因而必须在“反道学”的章程中加入“道学气”,这一“颠倒”在招募新人方面,往往很有成效。等到一代少年诗人,刚刚登场就已深谋远虑,迅速地掌握了前几代人辛苦积攒的武备。在好心人的眼里,他们令人遗憾地老成,缺失了好勇斗狠、朝气蓬勃的时代。
与十年前相比,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诗歌的人口无疑更多了,诗歌的门槛也更低了,似乎先于教育、医疗,实现了真正的平民化,诗歌地域的分布也更为均衡,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冒出一两个欣欣向荣的诗人团伙。原本恶斗的“江湖”越来越像一个不断扩大的“派对”,能招引各方人士、各路资源,容纳更多的怪癖、偏执、野狐禅。出于对传统诗歌交际的反对,新诗作为一种“不合群”的文化,曾长久地培育孤注一掷的人格,放大“献给无限少数人”的神话。近十年来,诗之“合群”的愿望,却意外地得到报复性满足,朗诵的舞台、热闹的酒桌、颁奖的晚会、游山玩水的讨论,从北到南连绵不断,有点资历的同仁们忙于相互加冠加冕。这当然是好事,虽然加重了诗人肠胃的负担,但带来了心智和欲望的流动。
与十年前相比,批评的重要性降低了,集团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各方都在无意识中规避,但批评的社会功能却取得长足发展,有时候让人联想到某一类服务行业,比如,为毛头诗人们修剪出一个干净利落的发型,好让他们出现在“派对”和选集上的时候,能够被轻易地辨认出来。这种服务甚至不需预约,可以随叫随到。另一部分批评,则立足长远,忙着在当代思想的郊外,修建规模不大的诗人社区,好让德高望重的诗人集体地搬迁进去,暗中获取长久的物业经营权。影响之下,名气略逊一筹的诗人们,一定会自动在附近租住青年公寓,期望能够联动成片,成为郊外逶迤的风景之一种。这样的结果是,有抱负的诗人不喜欢具体繁琐的城市政治,更厌倦了资讯与娱乐匮乏的乡村乌托邦,他们乐得搬入熠熠闪光的诗歌传统中,在那里消费拟想自我的各类版本。
似乎,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十年后的诗歌的生态似乎更为健康、从容、平稳,诗歌界的山头即使还林立、丛生,但那只是衬托出文化地貌的多样性而已。唯一让人略略吃惊的是,诗歌写作的“大前提”较十年前,没有太大改变;诗人对自己形象的期许,也没有太大的改变;诗歌语言可能的现实关联,没有太大改变。真的,没有太大改变。如今,大部分诗人不需要再为自己写作前提而焦灼、兴奋,也不必隔三差五就要盘算着怎样去驳倒他人,或自我论辩。他们所要做的工作,无非是丰富自己的前提,褒奖自己的前提,并尽可能将其丰富。从“20世纪”的角度看,从充满争议的新诗传统看,这倒是件新鲜事。
换句话说,在“短的20世纪”看似终结的时候,当代诗也有幸从一个世纪自我凫进的逻辑中悄悄剥离开来,缓缓降落于新世纪热闹的、富裕的现场。这意味着,我们不再可能依靠惯性,以十年为限来看待身边的一切,或许十年间的诗歌没有太大改变,或许没有改变正是一种更内在的、更具结构性的改变的开始,这一过程远远超出了生理成长隐喻所能负载的说明力。那支配了历史节奏、那咬合在心头的变速齿轮,在这十年间是否已逐渐发福,并在发福中松弛、以致滑落,这需要更旷远的眼力才能洞察。对于年轻的又打算团结成一代的诗人来说,这个问题可能更早凸显,因为除了年龄、体力、心气儿的差别外,他们似乎很难找到与前代人在诗学旨趣方面的根本差别,10年的“代际”区隔不再是自明性的。当然,要澄清这个问题,还需要举办若干次高峰论坛,占据某些大学学报珍贵的版面。
三
简单地说,“短的20世纪”崇尚另类,发明阶级,鼓吹平等,特别将对时间的暴力揉捏看作创造力的源泉,由此而来的进化想象、路线斗争、线性思维,都成了20世纪需要不断批判的痼疾,诗歌界作为时代神经元密集的区域,自然更多被传染。以10年为间隔,总会有人斗胆站出来,以“时间”中崛起的姿态,站在历史制高点上,将以往的写作方案判断为无效,将大批同行归入落伍的阵营。“登山训众”的口吻真是让人讨厌,夸大其词的表述,也伤害了不少诗人的感情。然而,在时间齿轮的推动下,骤然的加速、减速,使得均质的空间也有了纵深和分布,类似左右、上下、前后、内外之类的方位,随时可以转化为诗歌政治与诗歌动员的标签。在时间的催迫下,在空间的选择中,诗人习惯了一种危机式的感受和写作,将主体交托给了那一系列不稳定转换中的平衡。
如果说“十年的变速器”,在一个新的世纪里已慢了下来,甚至可能在长久弃用中的逐渐朽坏,这也意味着时间和空间的逻辑的悄然转换。不知什么时候起,诗人捣烂了时间的机器,跳出紧绷绷的针对性,纷纷变成了文艺学者,更愿意在一个普遍性的美学框架下,看待自己的写作及伴随的快感:历史不再是一个需要急速穿越的箭簇横飞的峡谷,仿佛成为一间通透敞亮的书房,端坐在正中,古典的、浪漫的、现代的、后现代的、左派与右派、激进或保守,位置和资源不是选择的对象,而是随手取用的对象。更为实际的情况或许是,大家不仅适应了“时间”被“空间”取代,同时也拒绝了任何空间的特权化:我们精心地写作、大规模地出版、小规模地细读和交谈,其实每个人都身处高低错落的“千座高原”:这些高原无中心、非层级、不攀比,闷着头各自生长,彼此的重叠、褶皱、衍生,给了自我足够的滑行、变异的可能。这自然是一种自我解放的状态,从意识形态的诡计中真正醒悟的状态,也是诗歌进一步觉悟到自身的状态,不再能用道德教鞭随便指点的状态。
随着时间的“空间化”,较劲的、“拧巴”的诗歌不知不觉转变成跨界的、越境的诗歌,诗人身份的终于可以在不同的“场域”兑换,想象力简单加工,就可投入社会的再生产。时间紧张的变速,曾像一个密封的瓶子,束缚了诗意的生产力,那么在各种紧箍咒“祛魅”之后,仿佛打开瓶塞后升腾起的雾状魔鬼,弥散的诗歌空气,不仅迷倒了大众和地产商,也间接可以沸腾驱动“航母导弹”的铁血热情。在这样的情势下,被解放了的诗歌应该欢呼自身的胜利吗?被解放的诗歌,怎么反而有些沉闷?
无论19世纪,还是20世纪,现代性的核心诉求仍在于主体的确立。传统“家国天下”世界观分解之后,这一难题原本以为可以外包给自由的、革命的主义,但事实证明,这有点困难,冒牌的东西不太经得起磨损。在没有确定价值系统支撑的现代思想中,主体位置往往显现于批判性的张力,例如破除恶声,伸张灵明的鲁迅。直白地说,在你不知道“正路”、“公理”的时候,至少你还可以依靠反对什么、轻蔑什么,来确定自己,这不能简单归为西方人所谓“怨恨”的伦理,与现代中国精神的困局相关,而主体概念的本身,也必然涉及对抗、说服和较量。20世纪时间的骤然加速或减速,无疑提供了主体性生成的契机,因为变速的瞬间也就是可能性涌出的瞬间。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立场的权宜化、策略化,也带来了性格普遍的操切、不稳健,怎样深刻地检讨也不会过分。然而,时间性的紧张毕竟给出了具体的脉络和现场,无论是在山岗上游击,还是从广场上撤离。
或许是上世纪末的论争,透支了诗人的体力,最近十年诗坛虽然不缺少攻歼和斗嘴,但早已没有了整体的“抗辩”,这显示了空间挣脱了时间后的轻盈。本来,这应该是一个主体弱化的时代,是一个需要辨认危机、补充钙质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在现场扎根、掘井、张网捕兔、乱吃草药的时代,但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诗人主体形象的普遍高涨。作为剩余能值和力比多的代言人,作为新鲜感性的技术发明人,甚至作为风尚世界里的先生和女士,红妆素裹,行走天下,自信满满。当“抗辩”的逻辑不再构成主体的支撑,一些相对传统的价值、姿态,依靠惯性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就本能地延续下来,草草填充了被时间掏空的肚子,比如人文主义冥想与担当姿态,或反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不争气的颠倒)的草根姿态,无论哪种姿态,维持的只是“常识性”主体。所谓“常识性”主体,指的是没有困境和难度的主体,缺乏临场逼真感的主体,他没有创造价值的贪念,实际上却做到了被通用价值牢牢吸附。
四
出于公共道德,不断有人指摘当代诗不关联现实(这种指摘往往本身就是缺乏公共道德的表现),一些看似及时反映时事的写作,表面颇能迎合政策与人道的口味,实际上进一步强化这种不关联。20前,一批诗人尝试用新的语言和视角去建立与变化中国的关联,这一尝试最初方法简单、得当,很见成效,带来新鲜空气,后来也因此形成长久的美学僵局。
20年间,不是没有诗人继续尝试去回应、去试验,希图在语言承载并处理变化中国的经验。这些探索甘苦自知,令人尊敬,难度在于:诗人熟悉的人文知识、文学传统在抵抗历史压力、保持所谓内在自由方面卓有成效,而在理解历史变化方面,却派不上什么用场。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当诸多经济的、社会的、法律的、政治的显学,慢慢驱逐了“言不及义”的人文学术,占据阅读市场的主流,“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油腻腻的标签,虽然贴在一小撮诗人头上,但事实上,诗人早已从知识分子想象的共同体中退身出来,“知识分子”写作不需他人的丑化,本身已成为一个滑稽的、反讽性概念。这并不等于说各类主流知识分子一定比诗人更高明,而是说情愿或不情愿地,作为一个群体,诗人可能已从某种总体性的时代认知位置上退了下来。诗歌帮助不了现实,这也是一种常识,但诗人的写作不再希望帮助思想的进程,这种变化对当代诗歌的影响,较之资本、市场、消费,或许要更为深远。
人文主义还有一个关系不大显豁的近亲,即上面提及的“好诗主义”或“元诗主义”,经由语言中介同样允诺了独立个体的无限美好、无限能动。与呆头呆脑的“纯诗”主义不同,这是一个可以放纵的立场,世界驳杂万有可以被悉数吞下,终结于也是服务于一首诗的成立。语言,语言被设想为一种万能的永动搅拌的机器,它的发动造成空前的审美气息,大家干脆闭嘴,不需再进一步讨论,好好细读就是。
五
在一种看似烂熟实则陌生的环境里,十年变速的感伤框架,有必要放弃了,有必要开始习惯在没有时间推动的重叠空间里悬浮着行为、说话、与各色人交往。但自我辨识的要求、对于心智成长和扩张的要求,依旧朴素地存在。这种要求需要心理分析的协助(虽然我不认为中国诗人已经成熟无聊到可以坐在上百平的书房自我释梦的境界),同时还需要向空间之外时间内部的紧张感请教。特别是气喘吁吁的“中国”,尚未真的安顿在他不知所终的世纪里,那些辗转于城乡结合部的新进白领们,也许比诗人更先一步思考如下的问题:下一步该做什么呢?难道还要想到下一步吗?还有下一步吗?自己看着办。
获作者授权发表于中国诗歌网

姜涛,1970年生,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现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新诗及现代文学与社会文化,出版有诗集《我们共同的美好世界》《好消息》、《鸟经》、专著《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巴枯宁的手》、《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等。曾获“刘丽安诗歌奖”、“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十大新锐诗歌批评家”、“汉语诗歌十佳诗人”、“教育部名栏;现代诗学研究奖”、“王瑶学术奖青年著作奖”、“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诗东西》诗歌批评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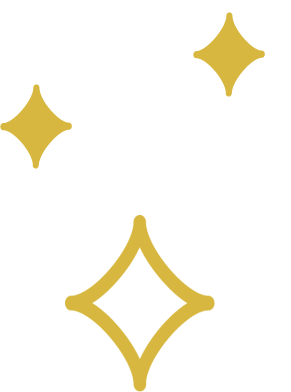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批评家专题之“姜涛”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