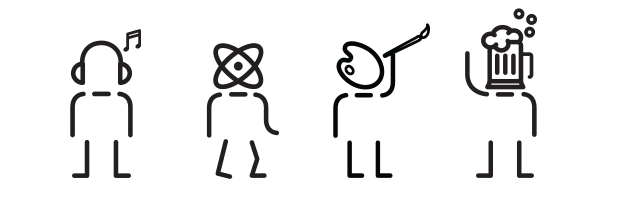文/马家骏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含着一股佛教文化的清泉,这是中印文化交流的结果。中国自古以来,不是宗教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这一点同西方、阿拉伯、南亚等国不同。(但中国有些民族如藏族、傣族等,是深受佛教等影响的除外)。汉族是一个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民族。世界上古代的各个有着高度文化成就的民族,如古埃及、巴比伦、古波斯、古印度、古代希腊与罗马,它们的文化都在历史长河中中断了。那些古代的民族消亡了或演变了,该地区的文化变了样,古代的语言死亡了,文字只有专家才认得。但是在诸种古老的民族文化行列中,只有中国的文化,一直延续下来。它不但没有消亡,而且以极大的生命力。吸收着、融合着其他的民族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是孔、孟、老、庄的学说,自汉唐以来,佛教文化也融入了进来,佛教渐次成为了中国的佛教。佛教汉化并在宋以后与道、儒合流,故而民间流传的观念、习俗与信仰,常是三者融合的文化。如“善”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重要的观念。但今天看来,不能就说“善”只是儒家或道家的观念,与佛教文化无关。这应是多种文化的融合。有如中国的“功夫”(气功、武术),也与佛教文化不可分。因此,了解和研究佛教文化应是了解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再者,佛教文化在中国不仅历史长、不仅与儒、道结合而具有民族色彩、不仅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占重要地位,而且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内容完备的佛经和佛教文化史料。这是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批判地继承这些富有意义的文化遗产,对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展。同样,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不是同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相隔绝的。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编辑出版一套佛教文化通俗读物丛书,这项工作是适宜的,有意义的。在这套丛书中,郭鹏同志注释的《佛国记》是一部伟大作品,而郭鹏同志所作的注释与评论,是作了精心阐释的有独创性和开拓性的。它不仅是一部通俗读物,而且是一部对《佛国记》进行了深刻细致研究之后获得的一项科学成就,是一部有份量和创见的文化学研究著作。
世界名著《佛国记》是一部影响深远的伟大作品。它记载晋朝僧人法显去印度取经并由海路回国的历程。法显以简洁典雅的文字记述了他的所见所闻。这部著作不仅对佛学研究有重大贡献,而且对中印文化交流史、交通史,对西域与印度各地的宗教、民俗、历史地理的研究有重大意义。有人说:法显由狮子国(斯里兰卡)向东航行九十天到达耶婆提国,这个国中崇信外道;住了五个月后,又向西北航行八十多天,到达了牢山(山东崂山);根据这个航程,推断耶婆提国,不是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而是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岛至美国洛杉矶一带。那就是说:法显到达美洲比哥伦布早了一千多年。足见《佛国记》的价值之崇高伟大。
郭鹏注释这部伟大作品,不是一般的语言学工作:像普通古文注释那样解释一下难词,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而是做了一番研究的科学著述。这需要有深厚的语文、佛学、地理、历史、文化学的基础。首先在书首,除了“序言”,郭鹏写了一篇长达20页约一万多字的论文《法显与<佛国记>》。而《佛国记》正文本身也不过万余字。这篇长度与《佛国记》相差无几的论文,是一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它不仅考释了法显的生平、西去天竺取经与海路回国的行程以及同行的其他十名和尚的生平与归宿。论文用大量的丰富而翔实的资料,考证了十多种史籍对《佛国记》记述中的正确与讹误,以及其他《佛国记》的存在与法显《佛国记》的异同。尤其对国内各种版本《佛国记》集录与考释,这些都对今后《佛国记》研究提供了途径。郭鹏的长论具有极大开拓价值。
在考据的同时,长论对《佛国记》进行了准确而适度的科学评论,指出它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与佛学史上,在中外交通与文化交流史上,在对印度等国的宗教、历史、地理、民俗、文化方面的研究上有极高的价值。长论印证当代中外学者的论断指出《佛国记》在今天的文化交流上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法显本人用三年时间穿过西域进入印度,在印度六年,经历三十余国与地区。正如印度的史学家马宗达所说:法显几乎走遍全印度,比希腊旅行家去的地方还多。法显精通汉语与梵文,翻译了近六百万字的经律。这些经典不仅是佛学的宝藏,连同法显的西游活动,正如印度史学家阿里说的,没有法显和他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可见法显及其《佛国记》深远的国际影响与现实意义。长论对《佛国记》意义与价值的论述,是有理有据的、鞭辟入里的。我还可以补充一句说:《佛国记》也是比较文学研究中较早的珍贵材料。在中国比较文学史上,从科际整合与媒介学角度说,《佛国记》与法显都占有一定地位。
郭鹏同志的长论,不是为学术而学术,它特别强调了法显奋勇精进、顽强不屈的精神,给这种精神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以高度的评价。由于《西游记》的影响,人们都知道玄奘去西天取经。岂不知,玄奘、义净等后人去印度取经,完全是受了法显与《佛国记》的影响。玄奘是25岁从长安出发去天竺的。义净在37岁登程出国。他们都是身强力壮的青年。而早于他们二百年的法显,从长安出发去印度,却已是64岁的老人了。在他之前,没有几个中国人去印度取经成功了的。法显从事的差不多是前无古人的冒险旅行。再有,与法显同行的先后共11人,冻死、病死各一人,中途返回6人,居留的2人。只有法显一人完成了伟大的文化交流工作,取回并翻译百万字的经律。这种精神岂不伟大?它对我们今天想干一番伟大事业的人,岂不是一种启迪?郭鹏同志论述这一部分的法显精神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长论不仅有学术意义,更有思想教育意义。
郭鹏同志也用法显精神完成了《佛国记》的注释工作。这项工作是难度相当大的:资料缺乏、佛教典籍晦涩难懂,不少佛教术语、典故、人名、地名很难搞得透彻。但郭鹏同志化了多年工夫,发挥他多种学识的雄厚基础的作用,查阅上百本的各种书籍,写出有创见的、详尽的注释。注文的字数远远超过了正文。许多条注文,就是一篇短论。如注“师子国”,就不是简单说“即今斯里兰卡”;而是列举由唐至今,该国十个名称与译名的“国名史”,之后引《通典》、《大唐西域记》、《佛本行记经》等书中的传说与僧伽罗与罗刹斗争的故事,考释国名之渊源。一条注释长达1200多字,写得生动有趣,使读者大长知识。
郭鹏的翻译,采用直译方式,这是十分正确的。他的译文,不避艰险,不添枝加叶的发挥,不把古人现代化。译得通俗明白,识字的人都一看就懂,这是一本优美的通俗读物。
还有一点值得称赞的是:《佛国记》原文是不分段、无标点的。郭鹏经过研究,从结构上,按行程,把正文分为“由长安西行”、“北天竺”、“中天竺”、“狮子国”、“海路归国”五大部分。其下又按地理分38节,每节,细分数目不等的小段。眉目非常清楚。《<佛国记>注释》,以小段为单位,把正文、注释、译文三者捆束在一起,这样不但便于对照,而且合乎思维进程,逐段阅读,以获完整印象。这比总引正文之后,吊很长书袋式的注释,最后附录译文的方式好。后者看似各自完整,但三张皮相加,反而不如目前编排。
《<佛国记>注释》的附录很好。“路线简示”表,是一项创造性的劳动,六则高僧传,很有价值。如果也能将注一并译成白话,或许对读者更有实际作用。“主要参考书目”一项,不仅说明注论的来源,也是对后来研究《佛国记》的一个重要提示。
郭鹏同志在“序言”中说他的工作是要使这部繁难的史著,达到雅俗共赏,使读物具有资料性、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他这个愿望是达到了。《<佛国记>注释》是一部有创造性、现实性、提高与普及相结合的优秀读物。
1995年10月写
[注]《<佛国记>注释》,郭鹏著,长春出版社1993年版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