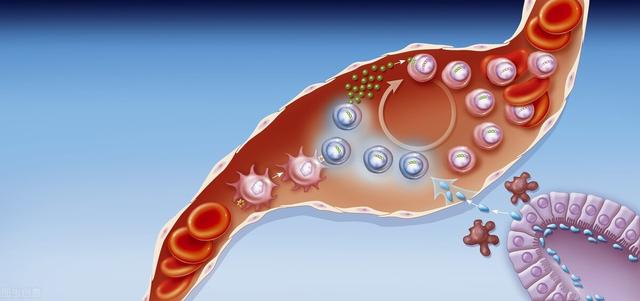题记:
在内蒙古开马场的三年,我天天都在和草原上的牧民打交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草原也不例外。我经常会问不同的人,这片草原上,谁玩马玩的最好?基本上每次都会得到相同的答案——班四。听上去像是一个汉族人。我会再问:"比蒙古人还厉害?""哎呀,蒙古人没有不服气的",大家都这样肯定的回答我。在我的概念里,蒙古人是天生的马背民族,从小接触马、骑马,马上的技术按理说比牧区的汉族同胞要更精湛。可是,"班四"这个名字的出现,让我对自己先前的判断产生了怀疑。我很多次和老村长提及,有机会一定要亲自登门拜访,看看"班四"到底是何方神圣,让蒙古人都能心服口服。直到2019年的11月,趁着不忙的时候,怀着崇敬的心情,终于踏上了这次"朝圣之路"。
——马场主,2019.11
不到腊月,西拉木伦河畔马场已是一片银装。难得闲时,有幸和马场主一行人等同去拜访听闻许久的草原传奇人物——班四。克什克腾旗大雪纷飞,我们找了一辆帕杰罗,冒雪赶往班四家中。

有些事情付出很久却无能为力,雪却只用一夜的时间就让世界重新变得洁白。在我看不出区别的那片白茫茫的道路两旁,三哥侃侃而谈,他出生自哪个村子,谁家搬了地方,以及班四英勇近乎于神的技术,那些如溪水般缓缓流泻的记忆把我从被空调热风包裹的昏昏欲睡中拽醒。
三哥是个老马倌了,他和班四曾是同一片草原上的邻居,班四的传说三哥全知道。得知我们要来,三哥自告奋勇带领我们找路进去。听说他已经十年没有见过班四了,我心里暗暗打鼓,十年没有见过的邻居,雪天登门,这合适吗?
八几年,在这片草原上,班四的名字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北到锡盟31团,南到围场,西到正蓝旗,班马倌都名声在外。有关班四驯马的故事也早已飘至草原的每个角落,时间长了,故事也就成了传说,无人没听说过他空手抓生个子的功夫,唯有发自内心的崇拜,碰杯定要下挪三分,有什么忙都会搭把手。

从柏油路拐上被厚厚白雪覆盖的砂石路,短短30公里进村的路程,开了1个多小时。一路上没有车辙的痕迹,全是新雪。司机是个年轻小伙子,没拿我们当客人,反倒当成了兄弟,蛮横地玩了一路雪地越野。屁股连番几次从车座上跃起,脑袋险些撞上车顶。下车后发现,我紧紧抓住把手的手指上已握出一道红印。趁着晃荡的功夫,三哥讲了另外一个故事:有一回班四去蓝旗办事,正赶上蓝旗那达慕,他在朋友的自作主张之下"被报了名"。当时距比赛开始只有2小时了,一共30个人比赛,班四排第29,贴上白色的号码布,一窝蜂地跟着众人在慌乱中做了热身。参加那达慕,需要经过一段长时间严格又专业的吊马,怎么可能有像班四这样毫无准备就来参赛的?可是谁知道他竟然稀里糊涂跑出个第二名,底下的人连冠军都不顾了,不停地喊"克旗的马厉害,克旗的马厉害"。

雪原之上,人眼导航指路,实在需要些能耐,即使是在这片草原上纵横三十余年的三哥也有些懵了。他用断断续续的手机信号跟班四通了话,一切又了若指掌。5G不是已经上了好多次微博热搜了吗?原来真的还有信号为E的地方,微信一直停留在"网络连接不可用"的状态。经班四指示,看见一匹黑马拐个弯就到了。唔,原来马还有路标的作用。不一会儿,在那一片白得金灿灿还反着光的天地里,竟然真看见一匹黑马,岿然不动的在雪地里等着我们。一丹说这叫缎子黑,待近了瞧得真切,果然,那黑色带着流动性的亮光,有如绸缎一般。很多年后当我再回忆起这个画面,如果世界也能像如此这般简单得非黑即白,该有多好。远远瞅见一个瘦高个儿向外张望,他所站的地方有几间矮屋子,环望方圆目所能及的地方,再没有其他住户。听说过大雪封山,这里虽然没有山,但一旦下起雪来就没有出去的可能。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冰雪荒原,时间似乎都被拉长了,从前不止车马慢,还天气寒,行路难。

狗吠声越来越响。外面零下二十多度,车门一开,没有过多的寒暄问话,班四领着我们几人,裹挟了满身的风雪赶忙进了屋。匆忙中都没能看清这位草原英雄的长相。和河北、内蒙许多北方的农村一样,班四家的屋子前面也有个风挡,放着一些日用工具。进了屋,倒比外面黑了不少,窗户里泻进来的白雪的光亮,显得格外耀眼。屋子很宽敞,没有装修,摆设简单。沿着墙边往右半拉是些厨杂用品,班四的妻子一直在烧水忙碌。左手边一张大床,床边上是一张老式圆桌,我们就坐在圆桌上开始了闲聊。刚一坐下,奶茶就上桌了,粉蓝印花盘子摆上切得整整齐齐的奶豆腐,奶皮子。此外,竟然还有一盘生切洋葱丝拌酱油,不禁令人想起了那道著名的新疆菜"皮辣红",这牧民的生活方式,还真是多有相似之处。这才有空仔细打量了这位草原英雄,他是1965年生人,过了年五十五,光看长相大概还要年轻十岁,全然不是草原上威猛汉子的那种形象,甚至可以说还有一丝白嫩。"说话语速极快""记忆力强",是我对班四最深的两个印象。好像那个在羌塘里走了七十七天的杨柳松,白净之下也是一张带点秀气的脸庞,同样"2X"的语速,说话时眼神明亮,无论如何也无法让人联系上"户外人"的形象,这二人倒是有着些许相似之处。叫我意外的是,已是十年未见的班四和三哥,完全没有电影剧情里故人相认的激动,反倒似每天都见的朋友,脱了鞋就能盘腿上炕唠嗑的东北老铁一般,天气中夹带着地名,几句话就交代清了十年的变迁。草原上的风,没有任何偏心,同样给予了他们脸上逐渐加深的纹路沟壑。有时我会想,时间、距离与人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那亘古长生的青草和冰雪见证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爱恨离愁?
(三)八岁"下夜"班四兄弟六个,排行老四,故名班四。他祖籍山西,上世纪五十年代时,他的祖父带着他的父亲,走西口举家搬迁至克什克腾旗好鲁库种羊场安家落户。班四的父亲正直、豪放,乐于结交朋友,迅速地融入了蒙古族人的生活,不仅说得一口流利的蒙语,顺带着还把蒙族人的看家本领——骑马和放牧学得丝毫不差,也算得上是他们那一代人中大名鼎鼎的马倌了。可以说,班四是又接了老爷子的班儿,续写了新的草原传奇。 哪匹马将来能跑得快,是可以从长相上判断一二的。"一是要看马的精气神,二是要看长相合不合规矩。"比如有没有一对跟支棱的竹签子似的大耳朵,还得是大鼻子大眼,前胸要宽,后腿和小腿的弯度大,以上每项都打了对勾,错不了是匹好马。说起相马的事,班四就是这片草原上的伯乐再世。

而谁是英雄,同样也可以从长相中窥出一二。见过班四的人,都说他毛发生得很重。班四的手背上,甚至是手指上都生有重重的的毛发,不像常人。而且,班四一脸的络腮胡长到胸前,这可是班马倌儿的标志性特点,他也从来都不剃,任其自然生长。再加上班四体态魁梧,如果跟蒙古人站在一起,根本分不出来。 班四八岁起就跟着老爷子下夜打狼了,这是什么概念?听说隔壁老王家的孩子今年上二年级,最喜欢看的是《蜡笔小新》和《家有儿女》。 阳历四月,马下完小驹子,狼早早就闻到了味道,所以夜里需要人去山上看着马群,以往万一。老爷子拿上场子里发的步枪,穿上又厚又重的军大衣,班四则拿着手电乐呵呵地跟在后面,爷俩儿就上山了。 "三岁看小,七岁看老",老爷子见识过多少风风雨雨,一早就看出来天性调皮好动,不少打架惹祸的班四能成点事儿,所以兄弟六人中,就偏偏只带他一人下夜,这大概是为人父母心酸又珍贵的疼爱了。 小孩子到了山上能疯一宿,玩儿累了在荒郊野岭躺下就睡。虽说是阳历四月,但夜里的气温也有零下十多度,吸一口气,鼻毛都能结冰。还没睡熟,"嗷——"的声音划过寂静的夜空,是马"xue"了(内蒙土话,xue,马受惊的意思)。狼在黑暗中伺机下手,引得马群慌乱,说时迟那时快,老爷子朝天上就是一枪,枪口的火焰和声音刺破了黑夜。八岁的班四,不慌不乱,不哭不闹,坐在树下,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回忆起年幼的经历,他说老爷子唯一叮嘱的话就是"一会儿狼来了,别怕,也别跑"。 班四说起来话来如同进入了一个只有他自己的世界,"突突突"好像机关枪,其中夹杂着不少陌生的人名和地名。他也不管听的人知道不知道,只自顾自说着,说到激动的地方,手势还上下翻飞。他不抽烟也不喝酒,始终翘着二郎腿,不时停下来催促我们喝茶,不时对我们客气地笑,眼神闪着亮,好似他身后的窗户那般透着白雪的亮光。

1983年,班四18岁,初中毕业,寻思着去机工队开拖拉机。谁知老爷子私自接了队里的马群,二话没说,把削好的套马杆直接交在了班四手里。班四虽带着埋怨,但父命如山,开始了他十七年如一日的草原放牧生活,最终也成就了他的马背人生。后来,老爷子的决定被证明为绝对正确,绝对英明,因为就在1993年,机耕队解散,如果班四当初真的去开了拖拉机,相当于中年失业,该是何等艰难。 正是荷尔蒙无处安放的年纪,纵横荒野的少年,唯天地与马为伴,红尘远在草原之外。心血来潮,放马也能玩出许多花样,比如抓生个子,骑着马捡东西,两匹马并排飞奔,从一匹马跳到另一匹马身上,没啥玩儿的时候连牛都骑。所有都是灵光闪现,挡也挡不住,用老爷子的话说是"瞎闹",用三哥的话说却是"无人能及"。 骑马关键靠悟性,一百个人里能出一个高手,讲究的是速度和身体的平衡。班四玩儿得是随心所欲,用现在的话说,叫做有"创意思维"。比如骑马捡东西这个技巧,放在现在,是马术特技的表演项目,难点在于"骑着马哈腰手能够到地"。首先人要坐得住,稳、准、狠,突然间就弯下腰拾起,不带任何停顿,而马照旧向前狂奔,一气呵成,只剩下草地上扬起一阵灰尘。 最难练的是站在马屁股上飞奔。玩自行车的人听过"摇车"的说法,即站着骑车,与这有几分相似。能站起来就很不容易了,别说还要让马跑起来,需要一股力量在双臂、胸膛、腿部之间流动,很难控制。而这在班四眼中最难的玩儿法,也仅仅是练了几天就搞定了。如果那时就有双微一抖快手直播,那班四是妥妥的流量带货网红。 想那天性爱玩的老顽童周伯通被困于桃花岛上十五年,为了打发漫漫长夜的无聊时光,萌生了"自己和自己打架"的想法,遂独创出"左右互搏术";杨过和小龙女一别十六年,一日在海边悄立良久,百无聊赖之中随意轻轻一掌,名曰"黯然销魂"矣。有时候,你很难界定,是英雄注定寂寞?还是寂寞造就了英雄?草原上的野花百开不败,太阳升起落下又是一天,时间打斑白的眉梢上流过,回忆就像骑在马背上看风景,根本来不及回想,刷刷往后退。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有一次,班四说要骑着马,用套马杆套狍子,老爷子眼睛都不带斜,嘟囔了一句"扯呢吧"。狍子,常见于东北、内蒙的小山坡和稀疏的树林中,体态轻盈,可以轻松跃过铁丝网,速度很快,猎狗也不一定能追上。常听说牧民们开车去打狍子,那是带着猎枪去的。谁知不一会儿,班四拖着只狍子回家了,不声不响地拾掇拾掇,连皮带肉卖了一百三十五块钱。那是九十年代初,据我父亲回忆,他当时在北京一所小学教书,一个月的工资是九十块。这下子老爷子也不吱声了,闷闷地继续抽烟袋,一口又一口。 说到这,班四也低下头嘿嘿笑。顽皮的小打小闹载入不了史册,可是若翻开那草原上牧民们的漫漫一生,谁人不都是一本厚厚的书?

"别人一家七口抓不住一匹马,班四则是想骑哪个就抓哪个",用三哥的话说,看班四表演,能看直眼(直眼:内蒙土话,意为目光紧盯着,表示因惊讶或被吸引住的眼神)了,这都是草原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事情。但要说班四最厉害的,还是抓生个子,而且是不用套马杆的那种。

生个子,也就是未经驯服的半野生状态的马,胆子小警惕性高,想摸一下都难,更何况给它戴上笼头?那势必要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抓生个子讲究速度、力气和智谋,缺一不可,用蛮力的后果只能是摔得浑身是伤,看似轻松的行云流水,实则蕴含着千变万化。 百来匹的马群说话间奔腾着就靠近了,脚底下都被震得晃荡,班四骑着杆子马,突然闯入马群之中,此时杆子马的速度应在50迈上下,约等于一辆小车正常行驶的速度。只见他撵上生个子,以迅猛之势用右手薅住马尾,横着一拽,马直接摔倒在地,班四跳下马,快步上前,用膝盖压住马头,使其休想再能脱却束缚,左手几乎同步的从杆子马上卸下笼头,立时套住,快得几乎看不清招式,笼头就已经套在了生个子的脖子上。薅、拽、转、按、压,以力使力,以柔克刚,飘乎来去,一气呵成,百发百中,行云流水,唯快不破,是为"此时无招胜有招"! 依照这样的招式,班四一小时能搞定10匹生个子,平均6分钟一匹。 班四总结,驯马有三狠:吊得狠,喂得狠,骑得狠。马不能打,不能揍,要骑服。人在征服马的过程有一种魅力,就像打太极的刚柔并济,最终达到下象棋的入神坐照。"用意不用力",在对手出招之前就能做出预判,力道绵绵而至,决不容对方有丝毫喘息的时机。看似不言不语,实则妙不可言。我想,对于人和马而言,这或许是他们之间相互自我介绍的方式呢,几股力量交织,好像在说"你好,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谁退谁进,谁胜谁负,互相憋着一口气,妙处往往只在几秒之间,玩儿的就是这微妙之间的制衡和变幻。一千年也是时间,一微秒也是时间,光速之下,手腕之间,恍然间明了世间万象,从此英雄不再少年。 马背上饮尽残阳如血,一往情深深赋草原,英雄不问出处,柔情不求人懂。余晖从云缝之间穿过,倾洒在万丈大地之上。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只听得草丛飒飒作响,马蹄经过的地方留下一阵烟。牛羊与万物是不变的观众,不声不响,不闻不问,唯见少年纵横驰骋,只身打马过草原。这,大概是孤独的最高境界了吧。

像每一个朴实、善良的草原女人一样,班四的妻子从我们进门起就忙着烧水弄饭,不打扰我们的聊天,却总是能在关键时刻提示一些线索,比如那次"老马识途"的经历。 早就听说马能带主人回家,草原上喝醉的,受伤的,或者无论遇见刮风、迷路还是沙尘暴,马就算是拖都能给你拖到家。班四也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那天出门时还好好的,午后突然就刮起了"白毛风"。这"白毛风"是当地俗语,意为"风吹雪"。一时间眼前白茫茫一片,风裹着雪呼呼得往脸上扑,直叫人睁不开眼,走几步路就压得人喘不上气。 据班四的妻子回忆,往常班四都是天黑前就回来吃饭,那天到了要睡觉时却还不见人影。班四的爷爷不多言语,烟袋不停地拿起、放下,几次抄起家伙出门找人,却走不出几步又被雪推着回来。老牧人心里明白,这回班四遇上的,是几年不遇的大雪,迷路事小,雪夜失温才是最严重的。就在二人心正悬着、一筹莫展的时候,院外响起了"哒哒"的马蹄声,正是班四!班四用仅剩的力气撑着下了马,已经说不出话,马却仍然是一副镇定、从容的样子。 进屋的班四俨然是个雪人,连睫毛上都是厚厚一层雪,脸上没有了血色,仿佛挂着一层冰壳面具,挨着炉子缓了好一会儿功夫,才张口说了第一句话:"多亏了红孬种"。红孬种,说的正是带他回家的这匹坐骑,用"孬种"形容马,并非不好,而是说这匹马性格异常暴躁,生人连碰都碰不得,只有主人才能驾驭。 班四遇上的"白毛风"是草原上极度恶劣的天气,下大雪的同时又刮大风,举目望去白茫茫一片,能见度只有几米,叫人乱了方向,即使是对地形熟稔于心的老牧民,也分不出东南西北。而马却能在狂风暴雪中送主人归家,不需要任何牵引,心中十分有数该往哪条路上走,人们经常说的"老马识途"就是这回事儿。 对此,老一辈通常的解释是,马有夜眼,但这种说法早就被证实是不符合科学依据的。马眼和其他一般家畜的眼没什么不同,马能在夜间认路的原因是马的大脑更发达,听觉、嗅觉也都很灵敏,特别是马有很好的记忆力。其实,不仅仅是识路回家,危机时刻,马还能救人性命。 那是多年前,班四被仅三岁(换算成人的年龄,三岁的马相当于人的十岁左右),才骑出来没多久的黑马救过一命。那天他下地圈牛,突然刮起了大风,紧接着就黑了天,大白天的跟夜里一样。雷声接二连三不断,衣服瞬间就被大雨打透,浑身湿漉漉的,胳膊沉得抬不起来。顶着风实在走不动,班四从马上下来,寻思先找个背风的树窝子躲躲。沿着河是一片茂盛的白桦林,笔挺的枝干深入天空。刚蹲下没一会儿,眼瞅着一个大火蛋从天而降,把刚黑下来的天又照得通亮。紧接着"咔嚓"一个响雷下来,班四蜷着身吓得够呛,下意识往旁边挪了一下,侥幸躲了过去,可几乎就在同时,又一个雷劈了下来,好像就在脑袋顶上炸开一样,大雨浇在脸上让人睁不开眼。这回来不及躲了,却觉得脑瓜上热乎乎的一片,原来,离着班四还有十好几米远的马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他身后,并且把下巴颏搭在了他头上!再回头,一米粗的大树已被劈成半拉,树杈子噼里啪啦往下掉。回去的路上,班四脸上的雨和眼泪已经分不清楚,但他始终记得,涌出的眼泪就像马脖颈儿处的温度一样,在冰冷之中热得滚烫。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三年,班四说起的时候仍然心有余悸,幸亏有这匹黑白玉顶的庇佑,他才命大躲过一劫。
(七)后继无人去年过年,女儿回家给班四注册了快手。班四关注的全是骑马的账号,他一心想知道现在人骑马比以前多了什么能耐。当我们聊到这里时,他连连摇头,说还不如他玩儿马的时候。 他想把浑身的技术传授给小儿子,无奈儿子喜欢玩越野车,没怎么摸过马。他也曾看上别的村儿的孩子,觉得是个好苗子,动了心思想好好培养。但现在家家都是独生子,骑马这事,少不了磕磕碰碰,受点伤不好给人家交代。再说了,在15秒看一个视频都不耐烦的网络时代,谁愿意在草原深处度过漫漫一生呢? 如今的班四,络腮胡没有了,腿上长了骨刺,过去受的伤开始隐隐作痛。去年,他骑马滑倒摔伤,住了40天医院,自此不敢再轻易上马。他自嘲到:"不知咋搞得现在只觉得浑身没劲儿",突然想到新疆民谣歌手马条唱"我已没有了山一样的体魄,我已丧失了波涛汹涌的豪情"……喂料,圈马,饮马,找马,十七年与马为伴的草原牧人,当初的疾烈已经不在,马背上的传说也随着风飘去了。 在一部讲述传统民间手艺人的纪录片《寻找手艺》中有这样的一幕:一位八十多岁做油纸伞的老人,因为年老而手脚变缓,在固定伞骨架时,线断了七次。老人也愣神了七次,焦急又沮丧,不如如何是好。导演张景回忆:"我端着摄像机在他跟前低头拍着,到了第七次的时候,感觉空气都凝固了,只剩下他手上的线在伞的骨架上磨得吱吱作响,然后是嘭的一声,又断了。"这个为了拍民间手艺而辞去高薪工作、卖了北京车房的四十岁男人,在遭到家人不解时选择了沉默,却在老人装不上伞架时强忍着不让眼泪继续。后来,《寻找手艺2》开拍,这个做了一辈子伞的老人,已经去世了。 现今七十三岁,用三十年时间采访了三百余名日本手艺人的盐野米松曾在书里写道:"出自工匠之手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有的工匠甚至因为没有继承人,现在手里的工作将成为最后一件。" 牧马也是一门讲究传承的技艺,班四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也不会说自己是一名"手艺人",我想他更不会懂得受到城里人以及新闻媒体中所推崇的"工匠精神"是什么意思。有一些人,他们用一生的时间,只做一件事。而那用来谋生的手段,是生活中最质朴的艺术,于日复一日的打磨中愈发锃亮。青草年年再生,冰雪终将融化,有许多遗憾,就像班四送我们出门时,不断叮嘱"再来喝茶"时嘴边的哈气一样,慢慢的消失在草原深处。 一篇单薄的文字远远道不完草原传奇的一生,如果有机会,我希望你能够亲自去拜访班四,去看看那匹黑骏马是否还孤独地站在道路的拐弯处,去看看他提到马时眼中熠熠的光。听见马蹄声响起,他一定会走出门来,远远的等着你"吁"的一声停住,然后拍拍你的马,夸上一句"这姑娘骑马挺ne呀!" 那里的云很远,天很高,阳光很刺眼,风声很响亮。你骑着马跑到林子边上,已快是落暮时分,夕阳把你的影子拉很长。你踏在承载了无数故事的大地之上,想起班四夹杂着内蒙土话所讲过的那片草原年轻时的样子,想起他遇到的马,受过的伤,直到夜幕来临,星星亮起,一切仿佛都未曾改变……

图片来源于网络
出品by西拉木伦河畔马场
想和马场主一起去拜访班四?参加马背旅行第9队,马场——西拉木伦敖包——达里诺尔湖
出行日期:2020年8月6日-8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