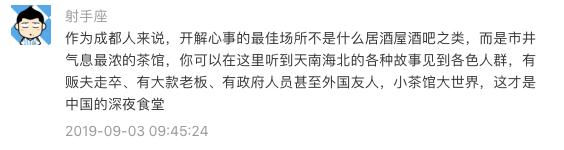1990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分类大会决议将同性恋自疾病列表删除。
2005年,加拿大大学教授和社会活动家路易斯-乔治·汀发起倡议,将每年的5月17日设立为国际不再恐同日。这一纪念日旨在呼吁人们关注因为恐惧同性恋、歧视性倾向而产生的一切生理和精神暴力以及不公平对待。
2020年5月17日,也就是今天,包含同性恋在内的性少数平权风潮在全世界许多地方仍然如火如荼,在另一些地方则似乎已经阶段性胜利。新观念搭建起新制度,向曾经饱受歧视、很难全然以真面目示人的性少数人群承诺出一种新生活。
“国际不再恐同日”的设立是希望唤醒世人关注对同性恋的恐惧,因性倾向及性别认同,而产生一切加在肉体上及精神上的暴力及不公平对待。
然而,一切远未结束。即使在不少发达国家,反歧视仍未告罄。据一项2019年经合组织国家的调查,有三分之一的性少数受访者因性倾向而受到歧视。此外,近年来全球保守主义呈回潮之势。在世界不少地方,人们仍因性倾向而遭受暴力、被判有罪。历史潮流浩浩汤汤,但若以一个较短时期为观察对象,这种潮流也许是混沌的。这也是所有性少数者共同的隐忧。
而那些走过了平权“初级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则有新的问题要面对。移动互联网和消费主义削弱了旧的性倾向歧视,新的歧视链在性少数人群内部形成。回首这些年,“同志亦凡人”也好,“同性恋骄傲”也好,理念看似相悖,却是同性恋平权同一路径的一体两面:一面对外宣示,一面自我激励。然而,如果这条路通向的是新的歧视与压迫,不得不令人反思未来应该如何修正方向。
十五年又十五年,反歧视今后何去何从?
撰文|张哲
移动互联网和消费主义削弱了旧的性倾向歧视
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勃兴的这些年,塑造了年轻一代同性恋者迥异于前辈的成长经验。
恐同的实质,是恐惧不同。
“我是怪物、变态吗?”“是不是全世界只有我这样?”无关生活在何处,每一个在前移动互联网时代度过青春期的性少数者,面对当时社会上有形无形的歧视、孤立与霸凌,大抵都有过这种漫长又痛苦的自我身份认同过程。
而放眼全球,对出生在千禧年前后的不少当代年轻人而言,这份深入骨髓的耻感却已经恍如远古传说。新闻和影视的激励,公众人物的示范,心理成型期社会风气的整体开明,帮助他们总体上避免了前辈们面对生活曾经举棋不定的姿态。《断背山》那样隐忍的生活方式与情感选择,已经难以让许多生活在大城市的最新一代同性恋观众感同身受,至多唤起他们肃然起敬的叹惋与怀古之情。

电影《断背山》剧照。
更关键的是,基于即时定位的交友App的出现,令他们不必再像公园时期和论坛时期的几代前辈们那样,苦苦在身份的迷雾中挣扎。他们不必扮演荒原上孤立无援的一滴水,只要他们愿意,随时可以将自己投入同类的汪洋,向陌生的身体和心灵找寻慰藉、建立交流。而此类交流几乎是一个性少数者真正认识自己、接纳自己的必经之路,也只有敢于做自己的人,才能勇敢地向性倾向歧视反击。
当然,移动互联网不止惠及新一代年轻人,先行者们也许曾经深陷自我怀疑的泥淖,但如今许多人已经摆脱了那份耻感,投身一种新的生活方式。2019年的阿根廷电影《世纪末》中,男主角诗人Ocho来到度假地点的当晚,就打开交友app,探索潜在的可能性。尽管本次搜寻没有出现令他满意的人选,但这短短一幕仍还原出当代同性恋者习以为常的生活经验。

电影《世纪末》剧照。
《世纪末》讲述了一个在回忆和幻想间漂移的三段体故事。世纪边界的1999年,刚成年的Ocho在小树林里和陌生人发生了关系,这令他恐惧不已,怀着迎接末日般的心情打开台式电脑,搜索艾滋相关知识,误以为自己必然中招。二十年后的2019年,当年那种方寸大乱,最终化成淡淡一句“我有吃PrEP(预防hiv的药物)”。
这部电影的经典场景之一,是Ocho与重逢的男二Javi(已婚多年,当然,配偶是男性)在天台上喝酒聊天。他们的闲谈跟恐惧和歧视毫不相干,而是轻松地分享感情和生活的开阔性。科技、政治的进步改变了人群的生活方式与心理状态,《世纪末》即是明证。
而另一方面,消费主义和全球化也反制了对同性恋的恐惧和歧视。
如今在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同性恋不再仅仅是一个政治议题,更是快速向经济领域蔓延。在平权意识高涨的国家和地区,性少数人群的购买力让人无法小觑。即使在平权仍处于初级阶段的国家,由于许多同性恋者不像异性恋同龄人那样需要面对抚养孩子的压力,也拥有相对更高的可支配收入和购买力。因此,专门迎合同性恋客户,或对其表现出友好的娱乐、影视、健身、美容、时尚、奢侈品、日用品、医疗、科技、旅游与色情等产业,在世界各个角落兴旺成长。
这种经济模式散发出新鲜而诱人的彩虹色光泽,正是在其映照下,一种新的男同性恋形象范本浮出水面,并逐渐固定成型。有别于过去那种阴郁、女性化、神经质、天然和艾滋病挂钩的刻板印象,它是阳光、乐观、健康、年轻、品味良好且男性特征鲜明的,因而也更易为普罗大众所接受。
在一片称赞、祝福甚至歆羡中,它当仁不让地为所有性少数者代言,仿佛可以庇佑他们远离过去那种基于偏见的歧视与恐惧,并为他们提供一种宝贵的群体归属感。上月告结的美剧《摩登家庭》最终季中,中年男同夫夫Mitchell和Cam参加一个泳池派对,结果放眼望去,泳池内外全是精致帅气、身材完美的年轻小伙子。而每年泰国宋干节前后的航班、夜店、餐厅和酒店,时常出现清一色须发精致、短裤大胸的华人男游客,则是男同性恋样板的东亚版本。
新的歧视链在性少数人群内部形成
无论外部社会还是自身内部,性少数都渐渐被视为一种常态,这不能不说是过去十五年——或者三十年——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玫瑰少年”叶永鋕的悲剧被流行歌手唱成金曲,成为后来者不该遗忘也不必重蹈的历史教训。而包含流行语在内的许多同性恋文化元素早已出圈,成为社会大众普遍接受的认知。
不过,旧歧视正待退场,新歧视却乘虚而入。消费主义出于营销策略所树立的那种新形象被目为同性恋样板,不仅损害了这个群体的性多样性,将他们生硬地推向主流社会接受的性标准,与此同时,许多不符合这一样板的性少数者也在无声中沦为了受害者。
于是,老、胖、丑、娘、艾、0、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等身份特征,非但要承受来自社会大众的普遍歧视,就连在性少数人群内部,也跌至歧视链的较底层。他们被忽视,被贬损,甚或被践踏。Mitchell和Cam原本奉行“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待你,重要的是你怎么看待自己”,但在泳池派对上持续被那些年轻男性视若空气,最终自信崩塌,仓皇钻进一间房间——结果那里躲着许多和他们一样上了年纪、身材糟糕、举止阴柔的男同性恋。

《深夜食堂》中的同性恋酒吧工作的小寿寿靠在黑帮大佬阿龙肩上的一幕,被认为是剧中“最有爱”的镜头之一。
本质上,这份歧视与自我歧视,仍是对“不同”的恐惧。香港社会学学者江绍祺在其采写的口述史《男男正传》中,将那种新生同性恋样板称为“良好消费公民”,并认为它“不但没有提倡团结与身份认同,反而将那些无法达到这种理想条件的人与那些符合其条件者加以区隔”。在江绍祺看来,新兴的同志世界比先前的同志环境更缺乏包容性,它“依照阶级、年龄、性别、性、种族以及身体类型而运作”。
这本出版于2014年的《男男正传》记录了江绍祺对十二位香港年长男同性恋者(时年63岁至89岁)的采访,借由口述文字回顾他们一生的故事。根据这些受访者的观点,在香港社会,同性恋曾是有罪的,出柜更不可能,但他们并不认为过去太过压抑,甚至还可以从聚居的家庭及公园、厕所等公共空间里创造出私密的乐园。相反,他们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男同性性行为非刑事化,同志场所也日益完善,但这些空间“都存在着阶级和年龄歧视”。
受到《男男正传》启发的香港电影《叔·叔》,便刻画了两位年长男同性恋者的情感生活。他们暮年相识,想要拥抱来之不易的爱情,却又无法抛开家庭与传统道德观的牵绊。这部电影参加了去年柏林电影节泰迪熊奖的角逐,并在本月刚刚举办的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由主演之一的太保斩获最佳男主角奖。
《叔·叔》在影迷中受到关注和热议,或许恰好反过来说明了这类电影此前十分匮乏,甚至几乎是空白。老年同性恋者从来也难于进入社会甚至性少数人群自身的法眼。毕竟,有多少人会真心想观赏两副衰老的面孔与肉体旁若无人地纠缠、摩擦呢?

电影《叔·叔》剧照。
香港的例子,也可以折射出其他商业社会的情形。无怪乎台湾作家郭强生在小说《断代》中要语带冷峻地感叹:“这个世界到今天只走到了青春健美的男孩们高呼同志无罪,没有人可以告诉他们接下来该怎样面对老与丑,病与残。”
彩虹,本应是参差的色彩。重新向性少数内部寻找精神资源,接纳不同,拥抱多样性,拒绝整齐划一的标准,并时时反省。如此,或许终能走出隧道,到达彩虹的一端。
作者 | 张哲
编辑 | 李阳 何安安
校对 | 何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