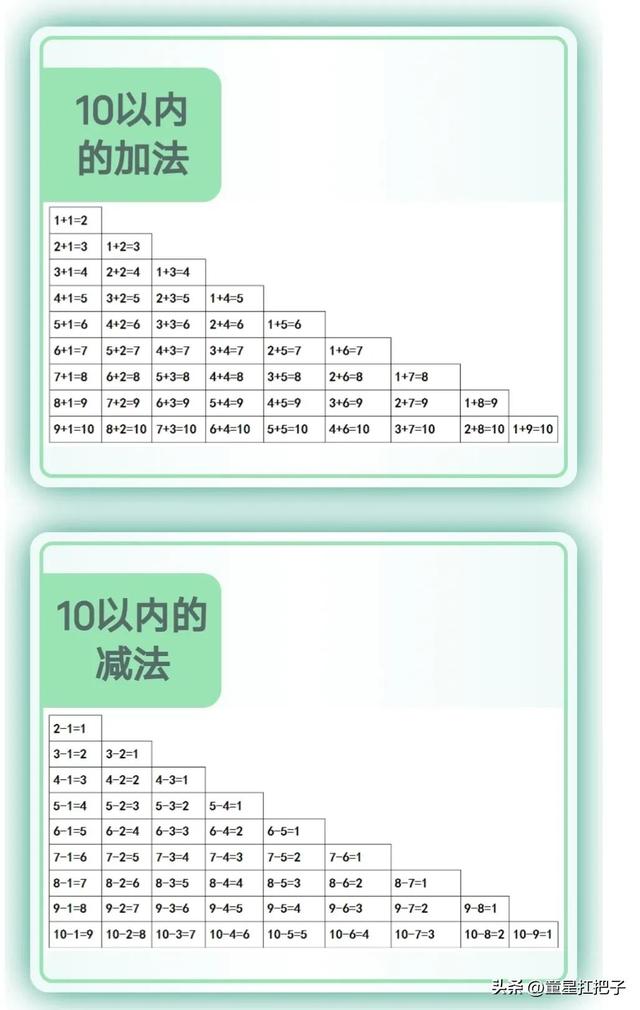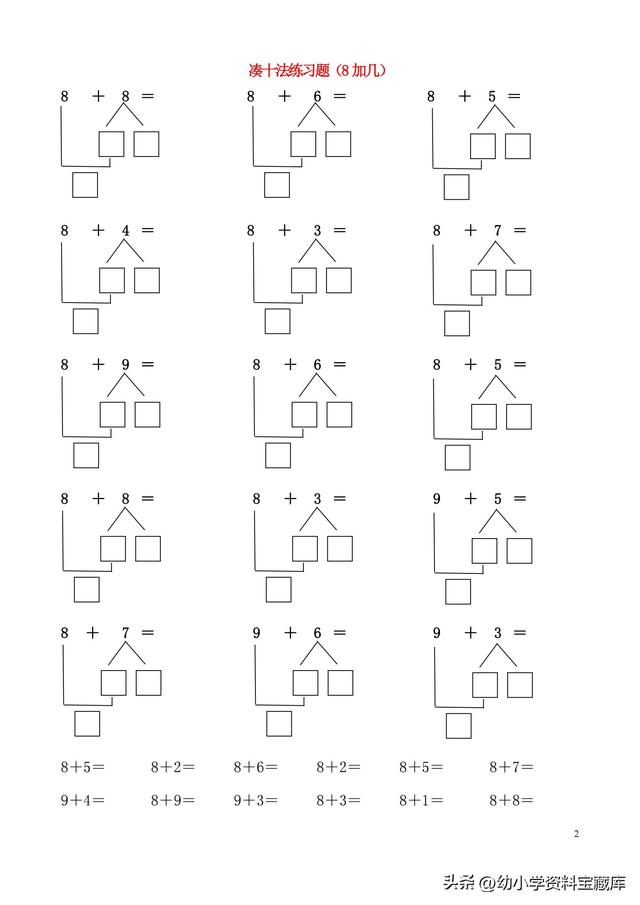上辈子我为薛昭众叛亲离,可他却为了娶我的妹妹将我生生勒死。
我的尸体被丢在乱葬岗,无人认领。
那些我素日厚爱不曾亏待的亲友,他们为了讨好因平乱而被封王的薛昭,一改往日与我的热络,皆同我割袍断义,朝着我的尸首大加唾弃。
最后为我敛尸的,竟是曾被我玩弄过的质子蔺珩。

1
在大婚之日被夫君、妹妹和贴身婢女一起害死之后,我重生回到了大婚前十日。
这一次,整个公主府的院门被我下令全部封锁,只进不出。
随后,我命人将贴身婢女碧云直接乱棍打死。
我算着时辰,今日初六,一会儿,传我进宫的旨意就该来了。
我冷眼瞧着她的尸首,让人看好了。
这可是我重生回来送给我那夫君的第一份大礼。
2
半刻钟后,父皇的贴身太监周公公就来我府上传了旨意,召我进宫。
我到御书房时,我的妹妹二公主岁夕正兴高采烈地从里面出来,瞧见我时,眼神瞬间倨傲起来。
她气冲冲地过来,用力撞上我的肩膀:「你别以为你拿着你母后的懿旨,就能一直困着薛昭不退婚,他心里没有你,就算和你成婚也不会爱你!」
她说的没错,我的确是拿着母后留给我的懿旨才能困住薛昭。
年前母后薨逝前,为我和薛昭下了这道不可退婚的懿旨。
她知道我喜欢薛昭,她知道我怕父皇反悔,将我同薛昭的这桩婚事给了岁夕。
这道懿旨,是她作为母亲死前唯一能为我这个女儿做的一件事了。
她奄奄一息地倒在我怀里,眼泪泅湿了我的掌心,血色一点一点地从她皎如春花的面庞上流逝。
她哭着说她害了我,可又不想让我难过,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她说她溺爱了我,只叫我贪了眼前的欢娱。
我哽咽着说我不后悔。
她艰难地擦着我的眼泪摇了摇头,说哪有不后悔的。
我那时不懂她的话,只当她是在说我,直到上辈子我死在薛昭手里才明了,母后的眼泪不是为我而流,临死前那些伤怀的话也不是说给我听,她是在说给她自己听。
她是琅琊王氏的嫡长女,江左百年望族下的闺中翘楚,自幼便是众星捧月,也该是眼高于顶的。
她驳了外祖父给他定下的世家子弟,只身入了宫门,欢喜地嫁给了他的心上人,桀骜得像是一匹最难驯的烈马。
可她最终还是死在了她心上人的手里,她那样明媚的一抹艳色,未曾在宫墙里傲然绽开,却死在那一碗又一碗掺了毒的补药里。
如此憋屈的死法,将她那样骄傲的人生生折磨了十几年,直到彻底熬尽了她最后一口气。
她自幼便研读医书,又怎么会不知晓父皇给她补药里下的毒。
只是心如枯木,但求灯灭而已。
她最后的那口气,终究还是和着多年的血泪懊悔咽了下去。
也就是因为这道懿旨,上辈子到最后薛昭也无力反抗,只能娶了我。
可这辈子,我不想嫁他了,我也不想再在大婚夜被羞辱了。
我同他成婚那晚,我满心期待地等他来揭我的喜帕,可我等来的却是岁夕。
她倒在薛昭的怀里,用秤杆挑开了我的盖头。
她讥诮地掩唇:「姐姐,你今天可真好看呢。」
薛昭抱着她倒在了我的喜床上:「她哪有你半分好看。」
我强忍着泪水去抓薛昭的裤脚,我哭着求他出去,我求他离开,我求他给我留些体面。
这,这是我的大婚之日啊!
哪怕他今晚不来,哪怕他不来,也好过如此羞辱!
他笑着踢开了我:「今晚本就该是我和你妹妹的新婚夜,你才是那个碍眼的,我若是你,现在就一头撞死才好。」
可我没死,我只是生不如死。
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夜,原来月亮的光芒是如此惨白,原来我的心可以昏暗到这般地步。
我变成了一潭薛昭满意的死水,任由他百般磋磨,也听不见半点响动了。
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能因为岁夕恨我恨到如此地步。
杀了我还不足以泄愤,还要将我的尸骨丢在乱葬岗,日日受风吹雨打烈日曝晒他才酣然畅快!
那样绝望的夜晚,每一秒都恍若凌迟,外面的寒风割着我的皮肉,就连四周的犬吠也在嘲笑我的无能。
我再也不要体会一遍。
我只想要他血债血偿!
3
岁夕盯着我,贴在我耳边:「你还有什么话说,朝华,你真可怜,懿旨能留住薛昭的人,可却留不住他的心,就算是你们有婚约又如何,不被爱的才应该被唾弃。」
我似笑非笑地觑着她,这是在御书房门外,一旁还有进言的老臣等着觐见。
我这妹妹,可是最爱自己的名声了。
我握住她的手腕,故意提高声调,言辞疾厉:「你贵为一国公主,虽是妾妃所出,却也尊贵,怎能因为一个男人便做出如此上不得台面的姿态。
「不就是一个男人,你若是要,便来同本宫说,给你便是,用不着跑来父皇这里一哭二闹三上吊。
「没得让百官知道,还以为我朝公主都没有人要,做出此等觊觎自己姐姐驸马的丑事!」
岁夕臊得脸通红,目光慌张地朝那些朝臣看去,抖着声音:「你,你胡说什么!」
她没想到我会这样不顾及皇室颜面,当众揭露出来。
她推开我,捂着脸哭哭啼啼地跑了,我心里冷嗤,果然人不能要脸,只要不要脸豁得出去,那就什么都不怕了。
4
御书房内,薛昭正捧着象牙笏板跪在地上。
我刚跪下,还未来得及请安,父皇便操起手边的墨条砸了过来,怒道:「你好大的威风啊!你就是这样做姐姐的吗?!」
我闭上眼,额前汩汩的液体滑落,打湿了我的睫毛。
我眼前所见,皆是一片染了红的模糊影子,腥气灌入我的鼻腔,阻塞了我的呼吸,吸入肺里的空气生疼。
墨条在地上滚了几圈,碎成两半,划拉出一条黑色的痕迹。
我心里有些惋惜,松烟墨珍贵,尤其是这方药墨,便是千金也难寻。
年前我被岁夕从阁楼上推了下来,摔伤了膝盖骨,一到雨天就如针扎般痛,连下地也不行。
外祖父知晓后连上三道折子,参岁夕与她母妃,父皇压着折子,只当没有这么一回事。
外祖父不甘心,势要为我讨一个说法,上朝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重新参奏,父皇却以一句姐妹间拌嘴轻飘飘揭过。
外祖父心疼我,日日守在我床边,太医说没有根治的法子,他便自己去翻药理的书。
最后不知在哪里听的民方,说是高平郡那边有匠人会制药墨,只需蘸酒研磨,再用盐袋热敷,便可缓解关节疼痛。
只是这药墨所需的材料昂贵难寻,小小一方说是价值万金也不为过。
上辈子直到外祖父病故,我才从表哥口中得知,高平郡那里会制这种药墨的匠人早已经去世。
外祖父在当地盘桓了半月,自己上山寻了药材,差点被毒蛇咬伤丧命,拖着病体不眠不休几日,这才给我制了这么一小块墨。
如今就这样被父皇砸得四分五裂。
我不忍看,强忍着压抑的愤懑,平静道:「父皇息怒,不知儿臣究竟犯了什么错,惹得父皇如此动怒,不论是为何,万不可因为儿臣气坏了身子。」
「岁夕是你的妹妹,你当着外面的言官如此贬损她,居心何在!」
我唇角扯出凉薄的弧度,我被岁夕推下阁楼差点摔死,他懒得去追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轻轻揭过。
如今我不过是训诫了岁夕两句,他就心疼得坐不住了,当真是慈父。
「我知父皇生我的气,但女儿就是因为外有言官在这才发作,岁夕贵为公主,一言一行都受百官监察,她与我的驸马不清不楚,若不制止,传了出去,恐坏了皇家名声,女儿也是为她好。」
薛昭不悦的目光瞥了过来,父皇哼了一声:「你总有话辩解,我问你这墨又是怎么回事?」
我惊讶道:「这块松烟墨昨日才到,一直放在儿臣的房里悉心保管,怎的到了这里。」
薛昭淡淡道:「公主何必细究小节,宰相大人奉旨北往赈灾,却在回来的路上为你大量花费人力物力,制作了这么一块华而不实的松烟墨。
「你作为公主享受百姓供养,如今灾民食不果腹,你却这样奢靡无度,岂不是寒了灾民的心。
「再者,你和二公主同为宰相大人的门生,他却只为你备礼而不顾二公主脸面,焉知不是故意挑起矛盾让你们姐妹阋墙、反目成仇?!」
父皇看向我的视线冰冷:「你做何解释?」
我叩头哽咽道:「这墨的确是我让外祖父寻的,可却不是为了我一己私欲。
「我同外祖父查阅古书,《本草衍义》有云松烟药墨可舒缓筋骨。父皇三年前御驾亲征肩膀受了箭伤,到如今也未能根治,孩儿不忍与此,这才托外祖父寻了此墨进献父皇。
「父皇明察秋毫,并不是外祖父想引起我同妹妹阋墙,只是为了寻找制墨的药材,外祖父被毒蛇咬伤,几乎丧命,实在是没有多的药材可制第二块了……
「薛大人的揣测实在是令人寒心。」
随着我话音落下,周围的空气都安静了下来。
上辈子因为这块墨,薛昭一箭双雕,不光罚了我鞭刑,还借机参了外祖父一本。
父皇本就忌讳外祖父是外戚,又是世家门阀的领头者,正好借题发挥,以外祖离间皇室姊妹亲情,致使两位公主不和给他定罪。
他下旨将外祖父拘禁在家,让薛昭父亲暂代外祖的官职,行宰相权力,还命我再也不许见外祖父。
直到外祖父病故,死前想见我最后一面,他也不让,命侍卫将我阻拦。
外祖父是两朝宰辅,先后辅佐过两任皇帝。
先帝薨后,其弟摄政王见父皇年幼联合薛昭其父意欲篡权,外祖父同谢将军分守内外,共同制敌,拥护父皇继位。
父皇当年恨不得将薛家与摄政王杀之后快,如今为了巩固皇权削弱世家,不仅启用本就有二心的摄政王,还将薛家女封为贵妃,放权薛昭等薛家子弟,妄图借此打击朝堂上的士族门阀。
上辈子我太蠢,一直对父皇抱有希望,直到知道母后死因那刻,我才真正对他死心。
我身上流着王家的血,从我出生那一刻起,就注定我和我的父皇是对立的仇敌。
不是他死,就是我死,只有厮杀,永无和解。
我的存在,母后的存在,王家的存在,于他而言,都是他集权路上的绊脚石。
所以他扶持薛家疼爱岁夕专宠薛贵妃,这些人都是他精心挑选用来对付世家的棋子。
上辈子他为了铲除祖父一家,逼反摄政王,命薛昭迎战。
薛昭却在降服叛军的时候,杀了王家满门,嫁祸给摄政王,一石二鸟。
薛昭最后因平乱受封琅琊王。
他平的是谁的乱?他受的是谁的封?!
他平的是我外祖父一家,江左琅琊王氏;受的是我王家数百口人的血、雄踞江左的封地。
封号琅琊王,何其讽刺!
不久后,新帝登基,新帝是薛贵妃所出,岁夕的弟弟,他登基当晚,我被薛昭所杀,毁了面容,尸体丢在乱葬岗无人认领。
唯有蔺珩,被我当作替身养了十三年的质子蔺珩,为我敛尸,替我报仇,同薛昭同归于尽,落了一个不得好死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