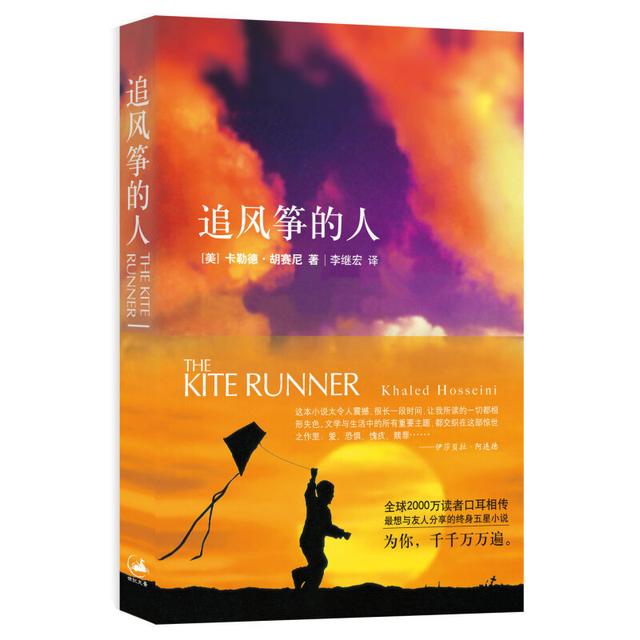一张不大不小的桌子,放满了各种书、杂志、表格,右边是一个很大的书柜,上面摆满了书。先生的办公室不大,因此每次进去总感觉先生被各种书包围着,而先生就很认真地伏在那张摆满书的桌子上写些什么,有时候,许是累了,半靠在椅子上,看着前方,但这样的时候总是少的。大多时候,先生一手拿着电话,一手仔仔细细地在电话簿上搜寻着相应的电话号码。先生声音很大,有时急促有时缓。每当这时,我总是不忍心去打扰,站在外面等,里面安静了才进去,有时候等几分钟,有时候十几分钟。这四年里,承蒙先生的鼓励和指导,学习了不少,不光是知识的传授,更多的是思维方式的启发。下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说说我的老师一一郭昭第。
一
先生曾在课上,多次教导我们要多读书,读好书,读“不懂”的书,当然,在这方面,他是我们的榜样,读了很多书。《美与时代》(下)2015年第8期中,曾刊登了先生的一篇文章一一《让本心昭然澄明于大地及筑造——我的智慧美学探索历程》。这篇文章深入地回顾了自己探索智慧美学的历程,对自己的读书历程也进行了梳理,从西方到中国乃至印度,从文选到专著,从文学到文艺学、美学、哲学、宗教学等等,所读之广、之深,让我真正见识了什么叫博览群书记得有一次写了一篇关于解读周大新中篇小说《向上的台阶》的论文,先生认为写得太表面,没有深入进去,像一篇读后感,然后便一口气给我列了十几本相关的参考书,以理论书居多。到图书馆我一查,除了一两本的书名稍有出入,其他的都正确,这确实让我大吃一惊。
先生不仅多读书,且多年来笔耕不辍,不断有著述出版:200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审美形态学》一书,且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2008年,又出版《审美智慧论》,这本书在深入反思传统美学学科困惑的基础上,探索出了走出美学学科困惑的新途径。之后又相继出版《文学元素学:文学理论的超学科视域》,《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生命智慧:易经道德经坛经心证》等著述。这些年,先生掌握学术动态,关心学术发展,潜心研究美学,认为:“就精神境界而言,宗教学高于哲学,哲学高于美学,美学高于文艺学,文艺学高于文学史。如果美学津津乐道于明快、匀称之类形式美,无异于表彰“好色”的本能。要使美学避免滞留于低层次美感甚或所谓新感性的局限,最好的办法只能是改造并提升为智慧美学。”由此,在他已出版的著作《审美智慧论》中便首次提出了智慧美学,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今年5月份又申报了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即美学原理,获得了同行专家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程金城先生的高度评价,认为:“该课程内容有鲜明特色,特别是在生命智慧美学、审美形态学、叙事和抒情美学、文学元素学,以及地域文艺美学方面形成了独特的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许多方面居于学术前沿水平。”

有时候我在想,作为文学院院长,先生平日里那么忙,他是怎么做到学术工作两不误?除了他长期知识的积累和勤学苦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对学术的热爱与执着。记得有一晚上我去图书馆上自习,忽然发现许多学生围成一大圈,指着天空吵吵嚷嚷,我一抬头,才发现夜空中出现了一年里最圆、最大、最亮的月亮,好多人纷纷拍照。在图书馆看了会儿书,翻开微信,朋友圈里到处是晒月亮晒心情的,先生平日里不怎么发微信,恰好这时,他转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作为中国美学核心范畴的意境》并附了自己的观点。我不得不感叹于先生的定力与执着,他从不人云亦云,从不追求时尚,从不被一些所谓的权威牵制,不为表面现象迷惑,永远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和思考。是的,一个人独立思考的精神决定于他花时间以及攀登的生命高度。
曾有好几次,看书看到不明白处,便发微信向先生请教,现在想来,多是一些极为幼稚又很自以为是的问题,然先生不管多忙,总会给我回复。有时候还将他认为好的文章发给我。先生曾告诉我一个读书的方法:“看书要能入进去,还要能出得来。先入后出。不能未入先出,这样便收益甚微。不要老是钻死角,万一不明白可以先缓缓,以后书看得多了,也许会明白,当年熊十力便不满徐复观喜欢批判眼光读书!”
二
先生热爱教师岗位,对教育事业抱有无限的热情和期望。大学四年里,先生是给我们代课最多的,而且也是同学们公认的最为枯燥难懂的课,从国学经典到美学、哲学再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路跟着先生,学习了很多。他深知死板的的课堂方式不利于学生发展,对于当下教育越来越功利化、浅表化更是深恶痛绝,不止一次在课堂上就今天的教育问题深感忧虑。他不只在教法上打破满堂官的授课方式,在教材的选用上也一样,不采用许多高校通用的课本,而是他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一突破使学生的视野拓展到了学术研究的最前沿。他还多次鼓励我们在课堂上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由于喜欢听先生讲课,常坐在第一排,有时先生提了一个问题,让学生举手回答。那时挺纳闷的:都大学生了,还让举手回答。后来才明白,由于先生多半给我们讲国学,讲美学,还涉及到哲学甚至人类学、心理学、宗教学方面,许是过于枯燥难懂的原因吧,认真听且能听懂的没有几个,许多学生听着听着就犯晕,索性盯着眼前的黑板发呆。先生便用这种方式集中我们的注意力,调动我们同他一起思考。
当然在更多学生眼里,先生首先是一名严师,甚至是出了名的严,有些学生由此产生了埋怨甚至害怕情绪。用我一同学的话说,就是“郭老师给我带了四年的课,指导了三年的论文,指导考研,指导复试,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过程我都觉得老师的要求超严格甚至到了苛刻,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做,即使从未被认可,但每次被严格要求过的我能派上用场,得到其他老师同学的肯定的时候,我甚是满满的感激,第一个想到的往往是我们的郭老师”。
对于我的毕业论文先生也是这样严格要求的。有一次我一个人去交论文,那是第一次写论文,当时什么都不懂,心气儿却很高,论文题目也起的很洋气一一《诗人何为》,仿佛当代诗人的成败与否就决定于我这篇论文了,写完自我感觉良好,没怎么改动就去找先生了,没想到先生一看我的题目很生气,再往下看,更生气,指着我的论文:
“瞧瞧,你写的这是啥?是啥?”
“就这次的论文”,我低声说。
“论文哪有你这样写的,还诗人何为?”
我还想继续解释,没等我开口
“你说,你能写好吗?你有能力写好吗?”
我还不服气 “我觉得好好准备一下,再掌握一些资料,应该差不多的”
“我跟你说,这都是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写的,一些哲学家,一些大文学评论家都搞不清楚”
我没再多说一句话,只是呆呆的看着先生。
仿佛觉得自己刚才说话的语气有点硬,先生放慢了声音,“我多次告诉你们,如何写论文,你们就是不听”,“一篇好的论文,与正确的选题分不开,论文的论题切记大而空,宜窄不宜宽,题目要细,还要新颖,有针对性,不要出现太广的范围,太广了你把握不住,容易把整篇论文架空,不能准确具体的去阐释,要结合自己实际,仔细研究,把选题做精,做透彻,做具体了才算真正的完成。”
说完,先生看了看我,“你给我说一下,你看了几本有关哲学方面的书?几个大评论家的文章或著作?读了几首优秀的大诗人的诗歌?”
我说了几个,再怎么也说不上来。
先生又说:“不是不让你写,能写好当然好啊,你才大二,读的书,论文写作的训练方面都很欠缺,从小处着手,慢慢来,一步一步要走好。”
而严师的另一面便是和,如春风化雨般。冯友兰先生有一句话:“春风化雨是从教育者本人的精神境界发出来的作用。没有那种精神境界,就不能发生那种作用,有了那种精神境界,就不能不发生那种作用,这是一点也不能矫揉造作,弄虚作假的”,诚哉,斯言!
由于先生指导我和同班几个同学的毕业论文,需经常见面。有一次,先生给我们讲论文,讲着讲着,便走向书柜,翻箱倒柜地找起来,嘴里不停地说着:“咦?我记着那本书就在这放呢,怎么不在?”“到底放哪了?”。我们纳闷,一问,才知道先生在给我们找与所写论题相关的书。又一次,也是交论文,先生批评我们没按照他说的做。我当时不知怎的,随口小声说了句:“我们都认真改呢,为了改论文都几天没见太阳了。”说完又很后悔,没想到先生听到了,没有生气,笑着说:“没见就没见么,太阳有啥可看的?”一句话,把我们几个都逗笑了。先生是西和人,地方口音极重,说一口不怎么标准的普通话,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交流。有几次,先生心情很好,有时就一个问题会给我们讲很多,当然我们也可以跟他辩论。记得我一朋友,写的是儒家知行观,先生觉得有一处没写好,需要改动,朋友觉得还可以,便反驳。先生问:“存不存在知先行后的情况?”朋友回答:“有,但是在某一阶段,是以知指导行,总的认识过程是知↠行↠知这样循环往复”,又觉得不对,马上补充了几句。又问:“那存不存在知行同时发生的情况?”朋友回答:“有”。先生便笑着跟她解释,我清楚得记得就这个问题先生讲了很多,朋友还是觉得不妥,再辩,来去几回,先生不讲了,靠在椅子上半开玩笑地说:“你看你,把我也绕进去了”,我们几个在一旁也笑了。后来我一直回想起这一幕,可以说,正是因为先生随和、平易,我们才敢跟他辩驳,也正是因为他一直教导我们独立思考,不要认死理,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出自己的观点。而反观平日里我所见到的,多是以老师为主导,居高临下,学生除了记笔记就是连连点头称是,还反什么驳?
由于先生读了很多书,且讲课时时而插入一些典故或故事,以增加趣味,活跃气氛。因此,每次听先生讲课,总是不失为一大享受。他是有儒家的入世之念的,也倾心于“圣人之学”,但更多的时候,是道家超世眼界和佛家的出世思想与平等不二思想影响着先生。因此不论著书还是为文,先生总是能以一种远超乎常人的视界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印象中,先生很是欣赏王阳明和慧能。而更让人赞叹的是,先生对于西方文化也能顺手拈来,出口便是大家之言,又能以自己观点阐述之,甚至是超越之,令人赞叹!然吾等不才,有些时候并不能理解先生的观点,只是睁着明亮的大眼睛眼巴巴地看着他,有时候先生提出一个问题,等了很久也没人回答,他便用不同的角度启发我们,还是没人回答,先生失望了,指着我们说:“你们这些学生,不趁着年轻多读些书,这怎么行?怎么行啊?”
最精彩的是一次给我们讲松尾芭蕉的一则俳句:“古池塘,青蛙跳入波荡响。”先生首先让学生说出自己的观点,并一一作了点评,最后说出了自己的观点:“青蛙跳入古池塘前是有,跳入古池塘后是空。跳入前,古池塘和青蛙是二,古池塘不是青蛙,青蛙不是古池塘。青蛙一旦跳入古池塘,情况便顿然有别,两者融为一体,青蛙即古池塘,古池塘即青蛙”,先生接着说:“真正的空是承认人们所感受到的现象界和精神界的虚妄不实,而不是绝对的不存在”。如此精彩的解读,却实让我们茅塞顿开,至今仍记忆犹新。记得当时还就这则俳句按先生的观点私下里和朋友讨论了好几次。有一次美学课快结束时,先生让我们用纸条写出对他的课的感受和建议,我不自量力这样写道:您的课有一个特点,不随便认同一个观点,也不随意地否定一个观点,大多时候是从肯定出发,然后又从另一方面否定之,再从更高的意义上超越之,以期达到思维的开阔,世界的敞亮,本心的澄明。我不知道先生看过之后,是否认同我的说法,总之,在先生的潜移默化下,我也不再以片面的,极端的态度去看待一个问题,偶尔也用先生的思维方法去想问题,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三
生活中的先生极为朴素,不怎么注重衣着,常着衬衫西裤,衬衫多为黑灰白三色,胳膊两端多挽起来。戴一副眼镜,走路时手多插兜里,步履极快,往往是前脚还没落地,后脚已迈出,头稍低着,思考着什么。先生待人真诚,路遇行人,多半笑着。他曾对我们说:“我的办公室门多开着,你们随时可以进来”。
有一次,先生去南宅子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那天我和几个同学也去了,先生在会上作了一个极为精彩的报告,其知识的渊博和谦虚谨慎赢得了掌声阵阵。会后下雨,人们纷纷散场,来了几辆专车接送与会之人。那天我们都没带伞,站在外面等公交,先生正要上车,忽又转身看了一下,看到我们几个在外面,便招呼我们上车。
“你们几个,过来!”先生喊着。
“不了,老师,我们再等等!”
“下这么大的雨,还等什么!”
“老师,您先走吧,真的不用了!”
“这车空着呢,快点!”,尤其最后两个字,语气极为坚定。我们几个再不敢推脱,纷纷上车。记得车上当时有四个人,丁楠老先生,郭老师,图书馆吴馆长还有司机。先生看到我们上了车,紧紧关了车门,问候了我们几句,便和老先生、吴馆长他们讨论那天的会议,一路上有说有笑,气氛极为融洽。事实上,那时我们才大一,刚入校不久,可以说先生对我们并不熟悉,许是国学经典课上,先生认下了我们几个其中一个。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每当提起,我们都不得不感念先生的好。
我一朋友曾告诉我,一次,她要去昆明理工大学参加美学复试,由于第一次出远门,许多手续因为周末也没有办理好,晚上失眠。凌晨两点左右,忽然收到先生的发的消息,问她是否什么手续没有办好,需要他从中协调。我不得不感慨,因为如此相似的一幕,也发生在我身上。今年3月末,我去云南参加复试,临走那天晚上,先生告诉我怎么回答老师的提问,他知道我写的论文是关于乡土方面的,不但给我发了一个关于研究乡土的相关书目的链接,还告诉我论文的大致框架和逻辑应该怎么构思,为了顺利起见,还让我看看他的那本文艺学专著一一《文学元素学:文学理论的超学科视域》。然而,我到底不是一个让老师省心的学生,走得过于仓促,该准备的东西没准备好,发表的一些文章没复印完整,连页码也标的牛头不对马嘴,面试那天,一个老师发现了,直接问我这怎么解释,我左右为难无法回答。第二天先生问我怎么样,我照实说了,那边便没了回复,我知道自己让先生失望了,过了很久,他发来了一句:“细节决定成败,你的前途终究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
回来的路上,我再次翻开那本书,在后记里他写到自己写完这本书后,生过一场大病,住了院,有时什么都不知道,只能躺着。读到这里,忽然觉得我手中的不仅仅是一本书而已,它凝结了先生太多太多。在他这里,时间不是被打发走的,日子不是被一天天虚度的,他是在抢时间啊,与时间赛跑,与生命赛跑!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大二时的一件事。有一次下课后和朋友跟着先生去旧家属楼取书,下着雨,我俩与先生并排着走,那天先生好像还有个会要开,走的很急很急,不几分钟,就把我们甩出老远,我俩紧赶慢赶就是赶不上,索性不赶了,跟随在他身后,雨越下越大,先生没带伞,朋友带着,要先生打上,他许是考虑到了我俩,没有要,只是走,甚至有点不顾一切,看着他不怎么高大却单薄的背影,心里说不出的滋味。我俩也没用那把伞,踩着先生走过的路,向前走,向前走……
我想在我的生命里,先生就是那个引路人。而作为学生的我,有很多方面并没有做好,我也不可能写出完整的先生来,只能以一支拙笔,记下这些点滴而已。最后,就让我用先生去年在教师节那天早晨所写的一段文字作结:
雨星拂面两袖云,堤上晨练似断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