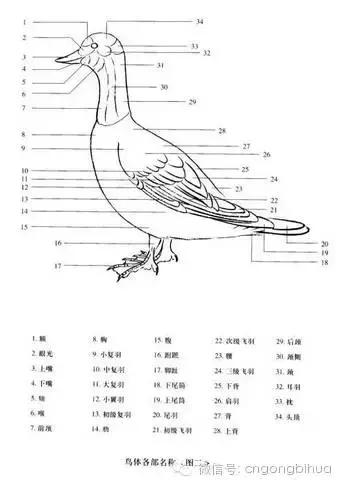文/宋彦

廖凡在电影《邪不压正》中饰演“大师兄”朱潜龙,姜文出演蓝青峰
“把西山做远,箭楼大点,我不希望地标性建筑那么虚。”姜文坐在沙发里,用手上的红外线笔指点着眼前的投影幕布。画面里的哈德门、箭楼、西山都远到模糊,它们在电影中最多出现几秒钟,但姜文心里有张比例尺精准的老北京三维地图,他容不得一帧含糊。
这或许就是我至今没有看到成片的原因,电影后期一直在和时间赛跑。
《邪不压正》是一个载体,它让姜文在继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之后,又有机会拍一拍他眼中的北京城。
10年前,好友史航把张北海的小说《侠隐》推荐给他。“不太适合改电影,随便看着玩。”站在编剧的视角,史航并不看好这本小说。姜文拿到书,一口气看了通宵,书里的东四九条、北海、前门他都再熟悉不过,男主人公李天然路过几次的“内务部街”就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
《侠隐》的故事发生在“七七事变”前期的北平,日本人尚未入侵,但已蠢蠢欲动,各种势力盘踞其中,错综复杂。自幼习武的李天然从美国归来,他想找到杀害师傅一家的大师兄朱潜龙,报一桩血海深仇。在那特殊的历史时期,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李天然眼中的江湖恩怨与国家的内忧外患掺杂在一起,复仇变得更复杂了。
讲的虽是复仇的故事,但小说更令人称道的是张北海对老北京生活状态的再现,这也是《侠隐》打动姜文的原因。
“有滋味,都是老北京的吃、喝、玩、乐,但要改成电影,需要重新解剖。”一时想不到该怎么做,“又不想做糙了”,姜文就把这活儿搁到一边,先拍了《让子弹飞》,又拍了《一步之遥》。
帮他找到《侠隐》改编灵感的是一幅画。“画展上看到的,画的是个屋顶。”周韵不记得画家是谁,只记得,姜文突然抓住了电影的魂,“白天一个世界,晚上一个世界,屋顶一个世界,屋下一个世界”。这就是《邪不压正》的故事和美学基础。

周韵饰演的巧红比原著《侠隐》中更硬朗,除了裁缝,还有另一重身份
“头顶上”的世界怎么实现?姜文电影里的人向来喜欢往高处走,《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总在屋顶晃悠,还跳了一把烟囱。《太阳照常升起》里,疯妈一犯病就往树上跑,最消停的时候是站在屋顶用温州话念“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一步之遥》里的人不再上房了,但在完颜英出车祸去世前,姜文还是把她送到了天上。
对姜文来说,头顶上的那个世界更自我、更纯粹,从前还是用作隐喻,到了《邪不压正》,这个隐喻就变得具体了。
“头顶上”的世界要怎么实现?在电影策划初期,大家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怎么才能让这个屋顶世界独立而自恰。首先,得从物理空间上解决。屋子挨着屋子,院子靠着院子,屋顶就有了单脊和双脊,就能走人了。“不能走着走着没路了,下来走一段。”史航说,大家商量着,用树、牌坊、电线这些东西来过渡。
更重要的是,得有一个屋顶上的生存法则。“那上面有树,有果,有花,人们在上面聊天,朋友和邻居可以串门。”男主角彭于晏说,姜文把所有最正义、最干净的戏份都移到了屋顶上。那里不只有男女主角的感情,还有一群不愿与地上的世界同流合污的人。
姜文说他不喜欢武侠,但这个“屋顶上”的浪漫逍遥却不输任何武侠世界。“他要复原一个北京城和那时人与人的关系,不是把它们从地里挖出来,而是直接送到了天上,这是极致的浪漫主义。”史航说。
实际拍摄时,剧组在云南搭了一个4万平方米的胡同场景,各式各样的胡同、街道组合都有了。像《邪不压正》一样,剧组也分天上、地下,两个世界被脚手架隔开,大家站在脚手架和搭建的木板上干活,所有屋顶戏份都是实景拍摄。
一天一地,两个世界,这已经让《邪不压正》与《侠隐》的美学气质完全不同了。

像他以往的作品一样,姜文是《邪不压正》的导演、编剧和演员,一人身兼数职
按姜文十分敷衍的说法,原著小说对他的意义就是“壮个胆儿”。“当小说跟我产生碰撞之后,我脑子里就想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已经跟小说不一样了,而我不得不去追这个故事。”在《骑驴找马——让子弹飞》里,姜文的解释还算严肃。
《侠隐》重在勾勒北平生活图景,但姜文追求的向来是强烈的人物情感和戏剧冲突,即便拍民国的上海和北京,他要呈现的东西也不是旧式的,而是具有极强现代性的情感与冲突。
电影中的人物大多具有多面性,可以用来做参照的是《让子弹飞》的改编。原著《盗官记》中,“张麻子”是假县长的本名,“张牧之”是媚雅的假名。电影里,姜文把这个设置对调了,名字的背后是身份的改变,张麻子从一个穷出身的绿林好汉,变成了一个逃避为军阀卖命,落草为寇的军人。原著里,葛优的角色汤师爷是个穷科员,跟了张麻子后任劳任怨,临了还惦记着领导的死活。但电影中的师爷油嘴滑舌,贪财惜命,善于在大佬之间周旋,但临死也说了几句善良话。
《侠隐》中目的单纯的人物当然不能满足姜文的胃口,他得动手大刀阔斧地改。
拍完《一步之遥》后,他和周韵去香港见了何冀平。后者是写过《投名状》《明月几时有》等名作的编剧,又是北京人,更懂怎么讲老北京的故事。
那次,姜文没像写《太阳照常升起》时一样,为编剧们讲了个几乎完整的故事,而是大致提了自己对人物和故事的要求,留下一堆参考资料就走了。
“三年三稿。”何冀平回忆,三年间,她和姜文还有几个编剧在北京、香港、古北水镇多次讨论,直到2016年春天,她才把手中的第三稿剧本交付给姜文。
“但那离可以拍还有很大距离。”显然,“姜文风格”在何冀平的剧本里体现得并不显著,虽然离开机已经没几个月,但剧本还是得再写。
这时,李非接到了姜文的电话。“你能不能来?帮我写《侠隐》的剧本。”李非一口答应,只是没想到姜文要得那么急:“别下周了,你明天就到。”李非连夜重读了张北海的原著小说。
“这是姜文三部民国电影里历史背景最实在的一部戏,前两部都是架空的。”姜文有自己的历史观,但他无意在电影里研究这个,对于他来说,时代背景只是展现人性的大舞台。李非说:“姜老还是关心一个个具体的人。”

廖凡和男主角彭于晏在电影中有很多对手戏,开拍前两人还一同训练动作戏
故事到李非手里时,男主角李天然的气质已经完全变了。原著中,他18岁经历师门不幸,远走美国,25岁回到北京时,已经成了一个心里装着事的沉默男人。但在《邪不压正》的预告片里,彭于晏饰演的李天然阳光帅气,撇嘴傻笑,一副美国大男孩的模样。
“电影里,他13岁出国,15年后回北京。姜老希望他简单点,和处于各种势力中的男人们在观念上有明显区别,中西方的冲突更强烈些。”李非说,不仅是李天然,姜文本人饰演的蓝青峰、周韵的角色巧红还有廖凡的大师兄,他们的身份和性格都比原来复杂得多。
人物的复杂化在意料之中,但感情戏的圆满却令人意外。一直以来,姜文都不擅长讲你好我好的爱情故事,《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是单恋,《太阳照常升起》里的情让人疼,《让子弹飞》和《一步之遥》里,爱和不爱都是一场空。
但《邪不压正》突然浪漫、温暖起来,没有人一直等待和牺牲,男人也不再推脱逃避,李天然和巧红的感情建立在信任、尊重和惺惺相惜之上,是一段能带给彼此成长和改变的关系。
张北海笔下那个似有似无的民国武林也被姜文改掉了——热兵器替下冷兵器,崇高被黑色幽默取代。作为一个怀疑主义者,他本能地排斥权威,想解构一切崇高,“武林”就是那个需要被解构的东西。

周韵在片场
熬出来的演员戏剧评论家童道明曾写到,青少年时代,姜文最爱看的是于是之主演的《茶馆》,他问过姜文,“《茶馆》的最大成功是什么?”姜文回答他:“是演员的表演。”
可见,演员出身的姜文多懂得戏剧和影视作品中表演的力量。
最近四处宣传电影,姜文对《邪不压正》剧情最经典的回答是:“就像李小龙闯进了卡萨布兰卡。”他想找一个像李小龙一样阳光、敏捷的人来演李天然,最终选定了彭于晏。
这是彭于晏第一次与姜文合作,听到“李小龙”这个造型要求,他立即节制饮食,开始控制体脂。健身,彭于晏很在行,如今需要的只是足够的时间和对训练内容的微调:“这个戏有跑酷,要在屋顶上跑一些动作,腿和腰的力量要非常好,平衡感也要好,所以这次对小肌肉群和核心的训练特别多。”
除了在身体上接近李天然,姜文还要求彭于晏练习北京话,而且是那种“没有太多儿化音的”北城的北京话。筹备期和拍戏间隙,彭于晏就念《侠隐》的段落给姜文听,让他一字一句纠正自己的语速、声调和重音位置。姜文也没闲着,找了很多说北京话的老电影、话剧给彭于晏,还让他没事听听《骆驼祥子》。
姜文是演员出身,他懂演员的敏感、脆弱和恐惧,在片场,他再急也不会冲演员发火。“他不是拉着你说戏的那种导演,他有自己的方法。”周韵说,她是亲眼见证彭于晏一点点在戏里戏外变成李天然的。“电影开拍一个月左右,他的戏都是在不停地跑,屋顶上跑,马路上跑,骑着自行车跑。这些戏可能很多最后都用不上,姜文就是想用体能上的消耗把他身上的明星气打掉。一开始,跑起来还注意发型,照照镜子,后面累得什么都不管了,那时彭于晏才真的成了李天然。”
我跟彭于晏提起这个导演训练演员的方法,他却一点也没察觉到,“只知道整部戏都在跑,二十、三十、四十条地跑,不知道导演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但他心里踏实,姜文有种气场,能让演员心甘情愿地暴露自己,把心和力气都献给他,这是种天赋。
十几年前,周韵就感受过这种天赋。“其实姜文是个非常尊重女性的创作者。”为了客观,周韵不是透过姜文来看他对女性的态度,而是透过他电影里的女性角色,“不管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米兰,还是后来陈冲、刘嘉玲她们那些角色,女人都不是又哭又闹的花瓶,是主动表达,主动选择生活的人。这种态度很西方,是高级的。”
周韵在姜文电影里的角色也从未柔弱过。在《太阳照常升起》里,她是独自抚养孩子长大的疯妈,《让子弹飞》里又成了投奔张麻子、劫富济贫的青楼女子花姐。《一步之遥》里的武六自由独立,她改变了马走日。这些角色的扮相和背景不同,但内核很像——都是有内在张力的女性形象。
张北海笔下的巧红是个传统的漂亮寡妇,跟了李天然就死心塌地,争起来,最多用“我又不是小孩子”搪塞了事。像无数旧时候的中国女人一样,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等。
姜文不准巧红等。《邪不压正》里,巧红根据真实历史人物改编,她不仅有个裁缝店,还有另一重身份,那个身份让她拿起枪,也让她与李天然越走越近。
新派,或正走在成为新派人的路上,这是姜文最擅长表现的一类女性形象。他所热衷的“现代女性”与她们所处的年代无关,只与“内在张力”有关,没了那精神内核,即便活在当代,本质上也是个裹脚老太太。巧红于周韵而言,只需要演出她身上的坚韧和现代性就足够了。
第二次与姜文合作,廖凡已经是柏林电影节影帝了。手中那座银熊奖杯有什么用?名和利都是顺带得着的,最重要的是,它让廖凡的表演越来越自信了。
八年前,《让子弹飞》里的“麻匪”老三戏份不多,但他亦正亦邪,能发狠的劲头让人印象深刻。八年之后,“师兄”朱潜龙的戏份比老三多,人物性格和背景也更复杂。电影很多幽默和荒诞戏份都由这个角色来承担。
但本质上,朱潜龙还是个心狠手辣的人物,与其他主角势不两立。“所以他在片场都不和人讲话,一开始我看他都害怕,心想廖凡怎么变得这么怪,后来才知道,他是绷着,怕出了那个角色。”周韵说,只要廖凡出现在片场,他就不把自己当廖凡,直接成了朱潜龙。

许晴在电影中饰演交际花唐凤仪,游走于各种势力之间,与男主角李天然有很多对手戏
刚出锅的剧本周韵觉得,姜文的电影有两个最重要的角色,一个是演员,一个是编剧,所以,他对这两类人是特别保护的。
电影辗转北京、云南、西安等多地拍摄,剧组生活给李非留下了很多难忘的瞬间。大家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塞罕坝拍师傅一家被杀的戏份,三天拍摄,天气冷得狗都跑不动,剧组上下每个人的脸都红成猴屁股。有火车的戏份是在唐山拍的,按姜文的要求,那场戏要有雪。雪是人工做的,道具组找来一节老火车,吭哧吭哧,没走几下就翻了车,那场戏拍不下去了。隔了很久,剧组重回唐山补拍,那次,唐山竟下了一场真雪。在云南拍戏时,那个屋顶世界不仅属于李天然和巧红,也属于全剧组,大家在屋顶拍戏、说戏、吃吃喝喝,晒得一个比一个黑。
这都是些带着滤镜的浪漫记忆,更多时候,李非和另一位编剧孙悦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彭于晏记得,进组时,导演发给演员一人一份剧本,剧本是完完整整的,大家还围读了三次。但开拍前,导演又把剧本收了回去。从那之后,他就再没见过剧本,每天拿到的都是新鲜出炉的“剧纸”。
这些“剧纸”都出自姜文、孙悦和李非之手。尽管剧本已经改了三四年,但姜文还是不满意,或者说,不到拍摄完成的那一刻,他对一切剧本都不满意。
“桥墩子已经搭好了,在组里就是抠细节,干细活的时候。”孙悦说,很多时候就是台词的删改,看起来是少了几个字,影响的是整部电影的节奏。
不要冷盘,每道菜都得是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这是姜文对每场戏的要求。在剧组的每一天,孙悦和李非都坐在酒店、房车和导演身后改剧本,“编剧的房间永远在姜文的隔壁”。那段时间,李非戒了酒,清醒得不像自己。
因为改剧本的时间太长,姜文得动用自己的一部分脑力来安抚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一到现场他就挑灯光的毛病,他一来我就知道,剧本还没写出来呢。”摄影师谢征宇说,这是种片场情商,有点混,有点江湖。
拍过很多导演的戏,彭于晏从未在任何剧组见到过《邪不压正》这种导演、演员和编剧的关系。“编剧花很长时间和演员对剧本,帮忙了解角色,每一句台词背后的意义,很多内容是自己想不到的,消化后再表演就会不一样。”彭于晏还记得,最后的大决战和几场天台戏台词很多,剧组给演员和编剧找了个小屋子,编剧不停改,演员不停练,拍出来的东西质感的确不同。
最极端的是一场姜文和廖凡的对手戏,戏特别长,演下来得10分钟。两个人不停地对话,台词量特别大。难度这么高的一场戏,剧本也是现场出锅的。写好当场戏的剧本,李非去找廖凡,连张“剧纸”都没有,直接把手机给他看。廖凡举着手机看台词,把微信对话框刷了又刷,还不见底,整个人都傻了。
李非也做过导演,比普通编剧更会指导演员。他让自己演姜文的角色蓝青峰,一句句帮廖凡对词。“姜老一般不让演员和演员对,一对就熟了,刺激没有了,他要演戏和写剧本一样,都是新鲜、有激情的。”
那场戏一共拍了三遍,每拍一次廖凡都得喝酒,最后把自己喝晕了。
在姜文的剧组里,写戏、拍戏和生活一样,大家常常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当创作上的直觉和技巧相撞时,姜文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直觉。
那是李天然和蓝青峰最后一场对手戏,什么结局、角色如何选择,导演和编剧都拿不定主意。那天,姜文和李非在酒店里想到凌晨3点,穷途末路,编不下去了。“算了吧,明天早上再做决定。”李非说,“就跟两口子吵架,分不分手,一晚上也吵不明白,一觉醒来自然会有答案。”
这种把编剧压榨到最后一秒的方法,姜文从第二部作品《鬼子来了》时就在用。一开始,李非想不明白,后来懂了:“他就是逼你进入一种编剧和表演状态,不知道下一秒发生什么时,给出的东西才是最直接、最有力量的。”
做导演20多年,一些老人走了,一些新人补充进来,姜文始终让自己身边保有一支年轻的主创团队。这个团队相对稳定,大家可以奢侈地花上些时间彼此了解和磨合。
姜文为《寻枪》做监制时谢征宇就和他搭档,他们很少在每部戏开拍前讨论具体的影像风格。“美学上的共识早在平时聊天时就完成了。”谢征宇说,不只是他,团队所有人和姜文的沟通都不局限于电影,有事没事,姜文就扔一些画作、视频或音乐作品到微信群里,话不多说,让大家各自感受。
团队里还有一些“黑话”,“香”“黏”“脆”,乍听起来都是吃货的词儿,其实是姜文的电影词汇。“香”指台词的层次,只有一个味道的不是好台词,有嚼头、有回甘的生活化对白才是上品。“黏”和“脆”说的都是故事和剪辑节奏,该紧凑的地方不能脱节,该快的地方不能犹豫。
于姜文而言,他不想把《邪不压正》拍成《骆驼祥子》,也不能是任何一部“京味儿”电影,别人做过的事他没耐心重复。和交出一部工整、明白的电影相比,姜文还是要在电影里实现自我表达,有历史观上的、美学上的,也有个人记忆的——他把故事从干面胡同搬到了自己曾经的家内务部街,母校所在地东棉花胡同也在电影里出现了。
看完电影后,史航踏实了,这一次姜文找回了《让子弹飞》式的与观众的关系:“《太阳照常升起》像是在和上帝对话,把观众晾在一边了。《一步之遥》情感真挚,但故事讲得太飞了。《让子弹飞》是把观众当成上帝,《邪不压正》大概介于《让子弹飞》和《一步之遥》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