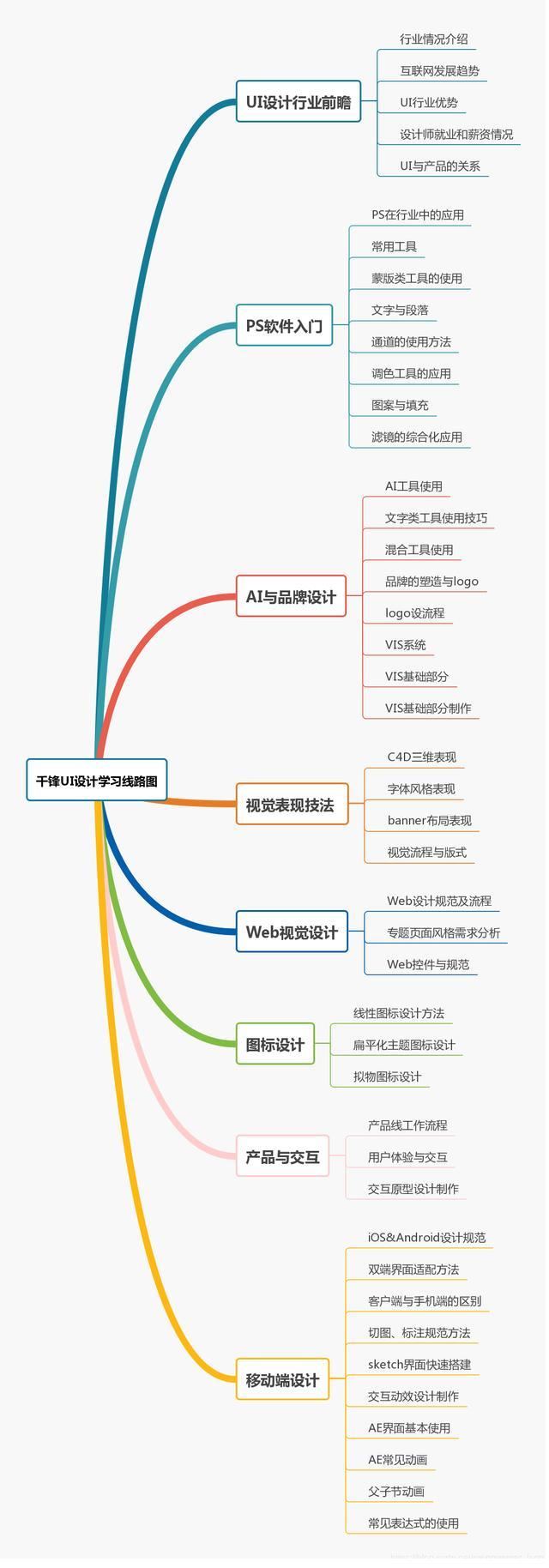故事从父亲的葬礼开始。“我”是父亲的长女,是艺术界的知名人士,“我”的两个哥哥高大俊朗、玉树临风,侄子侄女们个个漂亮出众。我们“以成规模的体面”,接待四面八方前来吊唁的宾朋,拓宽父亲死亡的高度和宽度。与“我”站成一排、举止粗鲁的乡村妇女,与体面的周家人格格不入,却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父亲真正意义上的长女……
邵丽的长篇小说《金枝》讲述了一位父亲在追求进步中建立了两个家庭,而他和他的子女们几十年陷入各自的人生和人性困境中。半个多世纪后,父亲从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悄然落幕。但他留下的两个家庭,和在这场困局中缠斗不休的妻子和儿女们,却无法走出漫长的阴影。
这样的故事,在过往的家族叙事中并不鲜见。但邵丽将寻根文学、家族文学的写作延续到作者本人以及下一代身上的写法,是一种新鲜的尝试。作者用一种超然的智慧、对人生的把握和领悟,把人世间的痛苦煎熬贯穿了起来。《金枝》不仅写历史,也写现实,它因关注几代人的人性成长而引人瞩目。
陈曦/文
__01
对邵丽来说,写一写家族这些事,早已是个念想。
一次采风的路途中,她接了孩子的一个电话。可能是声音和肢体语言太夸张了,让旁边的一个同行看得目瞪口呆。于是她便故作轻松地笑了一下,说是家里的事儿。谁知对方打破砂锅问到底,也极有可能是她自己想说,于是一路上她就聊起家族的事情来。同行听了之后,半天没吱声。车程快结束时,他认真地对邵丽说,这是一个好小说,如果写出来,对上辈人和下辈人都是个启示。
其实这也一直是邵丽的一块“心病”——父母亲和上一代老人都逐个老去,若不把他们写出来,一切都将消失殆尽。只是内心涌动的情感越多,越找不到合适的点。
直到去年疫情期间,邵丽先是用了两个月写出了《黄河故事》,给了《人民文学》。想不到《收获》的责编吴越看了非常喜欢,遗憾不止。邵丽就承诺说反正这些日子有时间,可以再写一个。原本是想写个中篇,写到十万字没收住,索性写到了十五万字,就是这本《金枝》。“金枝玉叶,可不是每个家族的梦想?只是没有那么多人把它写出来。这不是个秘密,更谈不上家族秘史。”邵丽说。

《金枝》
作者: 邵丽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现实中这样的家庭不少。书中的父亲,与他那代人中的许多人有着相似的经历。“看完这部小说,我的另一个责编和闺蜜与我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她的父亲是一个很著名的作家,也是一个地方作协的领导。她说,你写得太让我震惊了!写的分明就是我们家,是我父亲与他前妻和儿子的故事。书出来之后,又有一个年轻的女市长给我打电话,说‘你写的就是我姥爷,我姥爷是个南下干部,我姥姥就是那个穗子’。”邵丽说。
《金枝》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一部分以自己的成长为主线,是站在成年人的视角,审视父亲和自己的关系,是以“孤单”“恐惧”“仇恨”为主基调;另一部分是建立在对生活的体察之上的,是体验、记录之后,对中国现代家庭的反思。这一部分建立在爱与自省之上,是作者被生活不断刺痛之后又不断成长和升华的写照。
《金枝》中的核心人物、也是主要叙述者“我”周语同,曾是父亲的宠儿,但在特殊时代犯了错,差点害了父亲,因此失宠、长期遭到漠视。但“我”在成年以后,反而承担起了整个家族的使命,尤其是对后代,对侄子侄女的悉心栽培,不惜代价,各种帮扶。“我”对侄女周小语寄予厚望,把为她画的肖像命名为《金枝玉叶》。不过,“出生高贵”的周小语反而从自己的阶层掉了下去,失去了她的尊贵。而“我”同父异母的姐姐周栓妮呢?土里生、土里长,没有读过书,可她的孩子却个个有模有样,都成了阶层上升的榜样。二者放在一起,共同完美地诠释了周家的繁荣和发展,有如一枚硬币的两面。
邵丽说,开始写《金枝》的时候,她想到了自己的童年。“那时候,生活还很困苦,导致我没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所以,我成人以后,一心想的就是让家族的后代能功成名就。我确实渴望我的孩子们能够成为我想象当中的金枝玉叶,不再受到父母的忽略,不再受到任何歧视,生活在非常完美的一种状态当中。”
“事实上,我感受到的漠视,我的兄弟姐妹同样也感受到了,并且认为他们才是最受委屈的一个。但是,作为一个作者,我必须有我自己的视角。我所写的就是我体会到的感受。包括我写《黄河故事》也一样,强调的是,在家里最不受重视的孩子,反而后来会成为最强大、最有担当的一个。甚至在我的情感世界里,我会怀揣着一种‘报复心’,就是你当年是怎么对我的?我又是怎样对你的?至少在我的作品中,我是这样来处理的。”
邵丽为这部作品最初拟定的书名是《阶级》,意思是我们如何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攀登,努力向我们所希望的生活靠近的过程。“特别是父亲先后有过两任妻子,留下了两个家庭。我们代表城市这一支,穗子代表的是乡村那一支。几十年来,两个家庭不停地斗争,就像站在各自的台阶上,互相牵制着上升的脚步。但因为这个意思不容易被理解到,后来在《收获》主编程永新的建议下,才改为了《金枝》。”邵丽说。

__02
邵丽的语言是直抒胸臆的,颇有几分快意恩仇的特点。在她的观念里,写作是一种“对倾诉的需要”,同时也是对生活的记录。当然,作品是加工过的生活,但其生动的描述令人不得不相信这就是生活本身。
《金枝》中,父亲的原配穗子,是和朱安有共同之处的人,在时代中一般是一个消沉的、一事无成的形象。但邵丽为穗子这个人物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并且安排她的孩子们都有了更大的成就。邵丽表示,河南很多地方都是革命老区,在老区这样的事例真不鲜见。她想塑造的就是一个中国传统女性身上的那种韧性。
“我写的基本是原型人物,真事虚写。老根据地参加革命的男人多,穗子还算是幸运的,有的女人怀上孩子就再也没见过丈夫,一个人带着遗腹子支撑了一辈子,我们老家那地方称其为寡妇熬儿。我所熟悉的一个领导干部,祖母生下遗腹子,一辈子守寡,一个人把他父亲拉扯大,开枝散叶生了一大群孙子孙女,几乎个个成才。”
相比原配穗子,母亲朱珠的形象似乎单薄了些,只是善良和忍耐,都是女儿周语同充当“恶人”去与穗子母女做斗争。在写母亲时,是否有所顾忌而不忍下手?邵丽说,恰恰相反,她写母亲是最用力的。
“如果单薄的话,那是我的笔力不济,或者说,是我们很难看懂她。我最近在写关于《金瓶梅》的评论,我觉得吴月娘这个人不得了,她以不变应万变。她看到的不是一时一地之得失,而是全局和结局。她活得一点也不精彩,但就是笃定。我觉得完全可以站在这个角度看待书中的母亲,她可能压根就没有怨怼过。中国式的母亲大多是隐忍的,她们承受所有人生的份额,好的和不好的。母亲就是这样的母亲,她宽阔得像一个大平原,又微弱到做我们的母亲都做得孜孜矻矻。如果家族是一本厚重的书,母亲在书中只是一个影子,无所不在,却又若隐若现。她没有精彩的故事,也没有坚不可摧的原则。她不为玉碎宁为瓦全,她的所有智慧、能力和温情只够默默维系着一个家。朱珠是家庭的定心丸,亦是一本无字的书。”
《金枝》写得很顺,半年就完成了,但邵丽自觉“谋划得不到位”,写得有些仓促。她说,如果重新写这个故事,应该给穗子发言的机会。“穗子是一个反复被生活碾压的人,是一个真正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但又是一个横亘在父母和我、栓妮中间的一个矛盾制造者。她怎么考量自己的人生?她到底想得到什么?我们无从知道。她是一个狠角色,也是一个被大而化之的角色。”
不过,她对《金枝》并没有修改扩充的计划。因为写过的东西,很难再沉进去。写出来,那已经是别人的故事,写过了就过了。但她会另起炉灶,从另一个方向重新进入。
__03
邵丽生于1965年,与李洱、艾伟等差不多是同龄人,都属于最后一代具有革命历史经验的作家,而《金枝》和李洱的《花腔》、艾伟的《风和日丽》一样,也都涉及对革命经验尤其是革命者私人生活的书写。不过,邵丽之于那段历史有着更为切近的体验。“我的家族更可以贴上‘革命家族’的标签,因此家族史在更大程度上也是革命史。但处理类似题材并不是我的强项,我很难从个人感情上超拔出来看待当时的历史。说是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好,说是理论的储备不足也好,反正我在写这段历史的时候,情感往往把思想给淹没了。”邵丽说。
在评论家潘凯雄看来,邵丽只是在借“我”之口讲述一个家族的家长里短,几乎没有正面书写时代、环境这些社会的、历史的元素,但它们却无声无息地存在于作品的不同角落,为每个人物的行为与心理提供强大的内在逻辑。与其说《金枝》是一部有特色的家族小说,倒不如说是一部充盈着丰满的“精神的气候”的现实主义佳作。
近年来,邵丽写了很多父母题材的小说,从《天台上的父亲》《黄河故事》《风中的母亲》一直到眼下的《金枝》,长中短篇皆有。有人说,她在“审父”。对此,邵丽并不否认——“就算是吧!在我还有能力的时候,如果不从我这里开始,将来谁会对孩子们讲一讲他们的先辈?莫非所谓的先辈,就剩一个名字和牌位吗?饶是如此,先辈的过去,就是我的今后。我不忍心。那一代人平凡而又奇崛的人生,不能似孩子口中的口香糖,嚼一阵子就给吐了。”


对 话
读品:《金枝》中,最亲密的父女关系在一场风波之后突然变得冷淡,一直无法忘记这一创伤的女儿在很长时间内不能原谅父亲。小说中的周语同可以视为邵丽本人吗?她和父亲最终和解了吗?邵丽:假作真时真亦假,我的强项就是能把虚构写得貌似真实。但我还是愿意承认很多方面有我的影子。我们那个年代的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可能因为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大部分都是隔膜的,极度缺少沟通。家家都是一群儿女,父母没有精力关注孩子们的所思所想。而子女一直到父母老死也不会知道他们想些什么。这个创伤是时代的伤疤,也许连“和解”这个词语都过于矫情。现实很粗粝,作家自身又常常过于敏感,实际上把真实的生活给遮蔽了。
读品:小说的真诚打动我,我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感受到喷薄欲出的情绪,也许正因为代入了作家个人的真实经历。您在写作这本书时,需要费力气去处理个人情绪吗?你是如何做到冷静、克制的?邵丽:其实,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所否认的“和解”早已冰雪消融,至少表面上波澜不惊了。也谈不上什么克制,当你回望自己的过去,曾经那么活泼泼地生活过,你觉得连伤痕都值得抚摸和怀念。时间是最好的医生和药剂师。我写作时总是被感动追逐着,内心满怀着悲悯。我爱我笔下的每一个人物,他们是我的亲人。也许我还宽容不到包容所有的事物,但我会善意地处理上一代留下的疤痕,尽力把它们抚平。
读品:你在接受采访时曾说,父亲的原配穗子其实是有选择的余地,不一定非得“守活寡”。这是否是在以今人眼光去看当时的人、尤其是当时的女性?邵丽:那个时代是个非常割裂的时代,一方面强调“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一方面“三从四德”的影响也非常深。有些地方女性再婚非常普遍,而有些地方离婚女人一直到死都不会再嫁。很多因素取决于个人而不是社会环境,也就是说,像穗子这样的女人是有选择的自由度的。但她没有选择,在幼年的“我”看来就是一种“恶”。我丈夫大伯的前妻,三十多岁就离婚了,守寡到九十多岁。我曾经问过她为什么不再找一个?她说,哪兴啊?回娘家咋抬头见人啊?
读品:你说父亲抛妻弃子的行为,在当时可称为“壮举”,是否有一种站在个人立场的美化之嫌?邵丽:当时的很多革命者,与家庭决裂的标志就是冲破包办婚姻的牢笼。投奔延安的青年男女,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他们那个时代的婚姻,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当然无可否认,这种“解放”是给旧时代妇女扣上的另一副枷锁,但那就是“革命”的意义之所在。其实它并不是排斥所有的包办婚姻。感情的舒适度取决于自身的感觉,有的父母之命是自己愿意的。深山出闺秀,各花入各眼。江冬秀大约恰恰是胡适喜欢的适合他的妻子。但是那一代念过洋学、受过新思想洗礼、后来投身革命的新青年,你再强迫他回老家和一个不识字的小脚女人生活,对双方都不是真正的公平。因为公平来自于平等。
读品:面对自己的两次婚姻和多个儿女,父亲的方式是恐惧、冷漠和逃避。你觉得父亲对穗子母女有过真正的愧疚吗?还是仅仅认为她们是个避之不及的麻烦?邵丽:我觉得“父亲”对穗子母女的愧疚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逃避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而母亲对穗子母女的顺从和忍让,恰恰是读懂了父亲的心思。“父亲”那时毕竟是个15岁的孩子,开始的冲天一怒,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尴尬和愧疚所取代。他仍然有善良的底色和人性的底线。所以他的苦痛是最复杂的,也是他最无能为力的。想躲避而不能,想面对而无力,他一直活在这种无穷无尽的纠结当中。
读品:如果重写,你会以更加超脱的立场去写父亲的两个家庭吗?
邵丽:这个很难讲,一旦进入写作,作家是很难自己当家做主的,要看作品里的人物带着你往哪里去。但主观上是这么想的,祖辈父辈都渐渐地老去,而且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会更客观更公正地审视历史,打量自己的亲人。至少我觉得,“亲人”这个称谓,已经将过去的矛盾和纠葛稀释得差不多了。
读品:河南是文学大省,你觉得河南籍作家的创作有何特点?
邵丽:对于河南籍作家评论界喜欢用“中原作家群”这个称呼。我觉得还是有它的合理性的。实际上认真比较一下,一个地方的作家肯定和另外一个地方作家有地域差别,江南作家和中原作家的文风甚至看待问题的方式方法都有区别。这个自古皆然。河南的作家群体很有特色,从作品内容来看,中原特色比较鲜明,有态度,有担当,有天下意识。毕竟中原地区文化积淀深,天下意识有历史传承,所以作家更容易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站位。但这种特色也在与其他地方不断融合之中。既融合,又区别,这也是我们乐于见到的。
邵丽 当代著名作家,河南省文联主席,河南省作协主席。曾获《人民文学》年度中篇小说奖,《小说选刊》双年奖,第十五、十六届百花奖中篇小说奖,第十届“十月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等多个奖项。中篇小说《明惠的圣诞》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编辑:张垚仟
© copyright 读品周刊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父亲像一棵老树,历经岁月的沧桑洗礼,呈现出枝繁叶茂的盛景。但谁能知道,一棵树延伸出去的两条根脉,曾经经历过怎样的成长?那些盘根错节的忧伤,又曾经为两位妻子和各自的儿女留下过多少难以追问的生命谜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