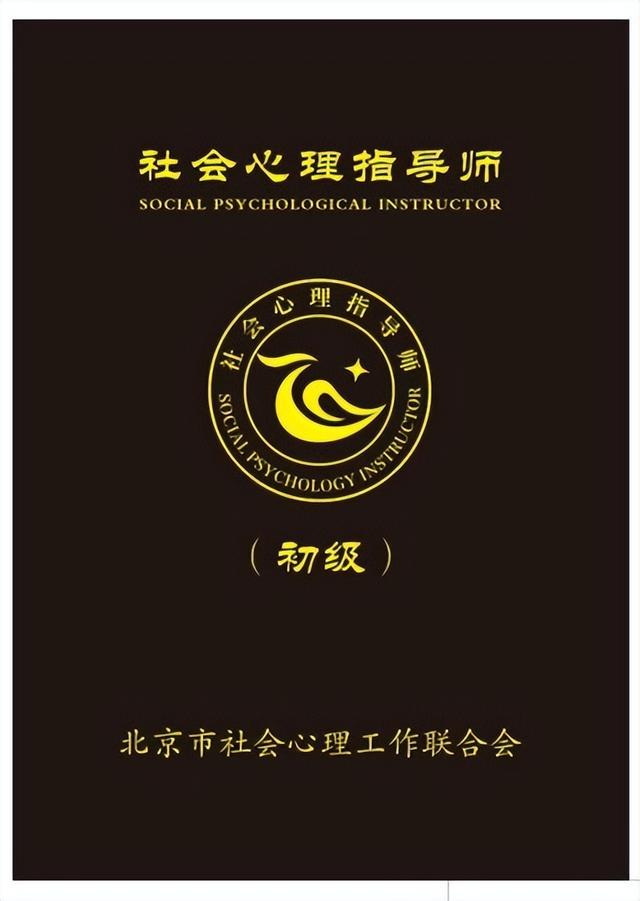问题不在于他是否有病,而是他如何被对待。
洛阳师范学院女生较多,李明是班上唯一的男生(黄宇 摄)
记者/张从志 实习记者/陈建凤
强制入院10月19日,我在河南郑州一家律所里见到了李明——网络上沸沸扬扬的大学生“被精神病”事件主人公。他今年31岁,剃着短平头,眉目显得清秀,个头不高,穿了一件旧的灰色长袖,眼神略有些不安和迟疑,加上身材瘦弱,他看起来似乎没有而立之年该有的成熟劲。走进会议室时,他拎了一个泛出旧色的书包随手放在墙角,里面装了一大摞案件材料,这是他现在最重要的家当,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今年5月,法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他起诉学校和医院的案件回到原点,但事情以“被精神病”为题曝光后,李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采访的几天中,媒体包围着他,电话从早接到晚。他向访问者一遍遍地讲述三年前的那段遭遇,永远都是一个语调,平缓,有条不紊。
2015年7月,28岁的李明刚刚度过大学第一年,他是以社会学生的身份在2014年参加高考,后被洛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英语教育专业录取。尽管大学生活晚到了很多,但顺利的话,三年专科学习结束,他应该可以考取教师资格证,如愿到某个学校当一名英语老师。
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使这一切变得遥不可及。大一暑假开始后,学校要求所有没有支教任务的一年级学生离校返乡,但李明没有按时离校。在此期间,学院团总支书记陈贯安多次致电其母刘英,说她儿子在校期间多次让老师调宿舍,跟人说话不正眼看人,认为他有病,让刘英找时间带去医院看看。恰好这段时间李明手机卡丢失,刘英未能联系上李明,她觉得儿子不会有什么大病,便没有放心上。
李明就读的洛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黄宇 摄)
7月18日,陈贯安再次致电刘英,称李明“失踪”了,次日又来电说在网吧找到了他。儿子夜不归宿让刘英担忧起来。7月20日,她从老家匆匆赶到洛阳。据李明讲,母亲告诉他,当时陈贯安在电话里说白马寺附近有精神医院,让她去找找。
刘英从网上搜到了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据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答辩称,刘英当时告诉该中心精神科副主任医师徐民从,自己儿子患有精神病,学校最近也多次通知她,说李明行为异常、精神有问题,要她带去医院看病。她自己管控不住儿子,怕其中途走失,请医院协助她把李明接到医院就诊。
总之,医院派车去了学校,徐民从和两名男护工随车前往。电话里已经提前说好,陈贯安在学校门口等着,带他们去宿舍。而李明此时还蒙在鼓里。当天,宿管说宿舍要装家具,让李明搬去另一栋宿舍楼的空房间,他打包好所有行李搬去了那里。东西放下没多久,门还敞着,陈贯安突然进了宿舍,告诉李明说:“你妈来了,赶紧带你妈去旅游吧!”还有两个陌生的男人在门框边探头探脑,李明被问愣住了。
他回忆,紧接着徐民从走进来,指着鼻子就质问道:“为什么你暑假不回家?为什么调宿舍?为什么跟你母亲断了联系?”李明被吓蒙了。他问对方是什么人,徐民从不作答,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的脸。李明说,这就是徐民从所谓的现场诊断。
陈贯安和徐民从出去后,母亲进屋跟李明说话,帮着收拾物品。门外仍有陌生男子向里观望,李明感觉不对,走到外面想看看究竟。一到走廊上,门口等着的两个男护工立刻上前摁住他,用束缚带将其反手绑住,便往宿舍楼外的急救车上推。李明要求放开他,但没有强烈反抗,他还没有意识到绑他的是什么人。
暑假的走廊空荡荡的,刘英听到声音跑了出来。“她哭开了,说你们不能这样做,把他放开。”李明回忆说,当时陈贯安还笑盈盈地告诉他,“让你妈妈带你去看看病吧!”
李明这才叫道:“陈贯安你虚伪,不配为人师表!”刘英哭着跟了出来。陈贯安对她讲:“带你儿子去治治病,医生开了证明,他还能回来继续上学。”还交代她去学校办休学手续。就这样,李明被送进了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在医院,他所有个人物品被取走,被脱得一丝不挂,换上了病服,成为一名精神病人,在精神病院“治疗”了四个多月,前后134天,“像一场噩梦”。
精神病院位于巷子深处,只有一条大道进出(黄宇 摄)
异常学生李明恨陈贯安,从医院出来后,他前后开通了好几个微博账号,封了旧号就用新号,总共发了3000多条微博,除了维权信息,攻击矛头大多对准了陈贯安。他认为是陈贯安在幕后导演了这一切,“非常恶毒”。然而仔细回溯两人的过往,李明也承认,这个做学生工作的团总支书记此前和自己并没多少交集,谈不上深仇大恨。
至于陈贯安当时为何告诉刘英,李明有病需要看医生,从洛阳师范学院的庭上辩护和陈贯安的个人陈述材料中不难发现,陈贯安当时已经断定李明不正常,有心理问题。庭审中,校方提供了种种证据,比如李明频繁更换宿舍、经常旷课、不跑早操、不配合班集体活动、言语威胁同学等,以此证明他在校行为异常。
本刊记者在学校找到陈贯安本人,但他表示,法院在二审期间,自己不便接受具体采访,“相信法院会公正”。李明则认为学校在捏造证据,污蔑自己。他曾找到提供材料证明李明短信威胁自己的前室友,并录下了对话。录音里,室友否认给学校作证,认为大家同舍期间相处不错,并没有什么矛盾。如今班上同学各奔东西,大都不愿提起往事,孰是孰非已难以弄清。
关于换宿舍一事,李明解释了来龙去脉。2014年高考后,为了选学校,他特地到洛阳、郑州等地考察过。他去看了洛阳师范学院老校区,虽然学校条件不算好,但他对洛阳存在许多浪漫的想象,觉得这是文明古都,很有历史文化底蕴,而且横亘在伊河、洛河之间,他还想亲身探究一下河流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上学,空闲时可以出来看看博物馆,走访当地社会,了解当地的文化。”
但当他拖着行李到老校区报到时,学校工作人员告诉他,他应该去新校区。坐公交近40分钟,他到了洛阳伊滨区,新校区在主城区以东20多公里外的一个村镇上,2013年才搬进第一批学生。李明去时,周围都是广袤的农田,校内道路上遍地黄土,工程车辆进进出出,掀起漫天的泥尘,他感到非常失望。
“我反应较慢,到新校区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这地方太差,设施几乎是一片空白,连图书馆都没有。”但给他造成困扰的主要是生活成本太高。其时,家里人还不知道他已经重新参加高考上了大学,学费和生活费都是从以前打工攒下的五六万元积蓄里开支,他想压缩生活成本,用自己的积蓄读完大学。学校周边没有其他的商铺,学生只能去食堂就餐,但他认为食堂窗口都是营利性的,饭菜价格太贵,他食量大,一顿中饭十五六块还吃不饱。老校区食堂比新校区要便宜,他想着搬过去能节省不少生活费。
在新校区待了三个多月后,他向学校申请换到老校区,他提供的理由是新校区装修的异味太大,他身体弱受不了。学校同意了他的申请,把他安排到老校区其他院系的大四本科生宿舍。但到老校区不久,来回两个校区之间上课,交通成了大麻烦。每天他要很早起床出门赶公交,当时公交车次少,发车也不固定,常常晚上天黑才能回宿舍。他又向学校申请换回新校区,他说:“当时没考虑太多,主要是生活压迫着,温饱都解决不了,只想尽快搬过去。”
学校再次同意了他的申请,李明一个人住进了一间没有家具的空宿舍。正是在换宿舍的事情上,陈贯安与李明有了第一次交流。按照陈贯安的说法,在交流过程中,他发现李明有较严重的心理问题,和人说话不敢直视对方,敏感、多疑,周围没有朋友,无人交流,并且和宿管发生过语言冲突。这为后来发生的事情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此时的李明已经萌生了退学提前就业的念头,他说是因为自己对学校极差的教学水平和官僚作风无法接受。但在陈贯安的说法里,这是因为他们的劝导。学最终没有退成,直到徐民从的到来。
李明原本有机会上一所更好的大学。2009年第一次参加高考,李明觉得自己应该可以上一本的,但发挥不好,分数线没有达到。他极度失望,急迫地逃离了家乡,打算忘掉一切。直到第二年,他才知道自己被四川一所二本院校录取了,阴差阳错下与大学失之交臂。其中细节,他说已经记忆不清,“很多不该忘的都忘了”。他只告诉我,高三那年自己过得很不好。
外出打工的五年里,从南到北,他去过不少地方,做着不起眼的工作。后三年,他进了一家小型课外补习机构,开始给人辅导初中数理化功课,一个班20人左右,刚开始工资2000元,后来涨到3000多元。这份工作让他燃起了当一名老师的想法,后来下定决心报名参加了高考。
进入大学后,李明才发现自己是班上唯一的男生,比女同学们大了近10岁。“我一直想和她们交流,经常在QQ群插话,平常也主动聊天,只是这些小女孩很多都来自农村,非常内向,圈子化很重。”他没能融入进去。
事情曝光后,洛阳师范学院在网上成为众矢之的,招来铺天盖地的批评。不少同学对此感到义愤填膺,觉得有人在“搞事”,故意黑学校。有同学告诉我,10月正是学校教学评估的关键时期,全校上下都在为评估冲刺,这个时间点突然发生负面新闻,会对学校很不利。
洛阳师范学院原本是一所专科学校,2000年升格为本科院校,现有在校生近4万人。从2013年开始,逐批地搬到如今的新校区。新校区占地2000多亩,建筑风格整齐划一,图书馆复制了老校区图书馆的模样,但更加恢弘气派,直到今天仍在建设之中。教学楼内开辟了专门的考研自习室,楼道走廊里也满是备考的学生,他们自带小凳子,对着窗外小声地背书复习。
在李明看来,陈贯安之所以叫母亲带自己去医院,究其根本就是出于管理成本的考虑,“有人抑郁了,在学校里生气,把大家扔到那里去,他就不用管了,包袱就甩掉了”。陈贯安在自述材料中则写道:“作为学校来说,我们可以监控他的行为,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且我们担心他伤害自己或是伤害别人,留在学校是一大安全隐患。”校方庭审中也辩称,学校只是尽了告知家长的义务,是李明母亲自己联系的精神病院,学校不存在任何过错。
沉默“病人”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在洛阳东北角,离主城区约40分钟车程,公交下一站便是著名的白马寺,小镇的名字也以白马寺命名。医院大门是西向的,要拐进一条巷子才能看到,走进医院,一路穿过门诊大楼,进入一个院子,里面布置有假山、水池和牡丹园,看起来与正常的医院并无两样,甚至环境更好,只有走到住院楼内,紧闭的大铁门和回荡空中的怪异笑声提醒着来客这里的特别之处。
出院后,李明曾特地返回这里拍摄周围的素材照片,心里依然感觉“恐怖,阴森”。一闭眼,医院的情景全都浮现于眼前。他在纸上画出了住院楼的结构,总共四层,由四栋楼合围而成,呈回字形,中间是供病人活动的水泥空地。他住在三楼的精神五科,大铁门将病房与外面隔开,只有经过医护人员允许才可进出。
刚开始去的病人都住在80人间的大病房,像一个大厂房,床位一字排开,便于集中管理。等到病情稳定下来,就会转到20人间,继续好转,就可以享受6人间待遇。李明进去后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住进了大病房,开始时他还总告诉医护人员,自己是大学生,没病,但很快学会了顺从。他默默地观察着里面的一切,把看到的、听到的都刻进脑海,盘算着出去后怎么曝光出来。
病房里有固定的作息时间。早上不到7点,病人被广播叫醒,洗漱、早餐、吃药、到大厅活动;中午,吃药、午餐、进病房午睡;到下午3点左右,广播再次叫醒,到大厅活动;下午五六点,晚餐、大厅活动、吃药,然后沉睡到第二天。每天循环往复。
一天早中晚要吃三次药,李明说:“如果拒绝的话,就会把人绑在床上,手脚捆住,然后扒开嘴灌进去。”许多病人学会了把药藏在舌头底下,等医护人员走开后偷偷扔到窗外的草丛里,病人们对此有一个专门的用语叫“藏药”。
最让李明觉得恐怖的是“电击”治疗。据他描述,每次治疗前,护工会把他带到另一幢楼,躺下来输液全身麻醉,然后开始“电击”,人进入昏迷状态,醒来时近半年的记忆都会消失。第一次做完,李明就忘记了自己在学校被带到医院的经历。“不记得自己上大学的事了,不知道这是洛阳,不知道这是精神病医院,而且这种状态要持续一个多月,记忆才会一点点恢复过来。”这样的“电击”,李明一共做了四次。
李明所谓的“电击”指的是无抽搐电休克治疗(MECT),是在麻醉状态下,让电流通过大脑诱发抽搐,以治疗精神疾患的方式,是目前国际公认的疗法。在临床上应用普遍,其副作用主要是认知功能受影响,例如可逆性短期记忆受损,基本上在3个月内可以恢复。
李明逐渐适应病房的规则,他努力像其他人一样行动,按时吃饭、吃药、睡觉、接受治疗,大厅里活动时,他喜欢看人下象棋,或者在一旁背英语。他见过一两次病人发病的情形,非常躁狂,冲过来夺人东西,他有时感到害怕,但待久了觉得,病友们其实只是像孩子一样控制不住自己,顶多是撒野,不会有目的地去伤人。
最小的病号是一个19岁的高中生,他爱写小说,成天幻想着当亿万富翁,家里人只好把他送了进来。正是因为劝他不要搬去大病房,李明和一位男护工发生了冲突,双方打斗中,李明受了伤。从此逃出去的念头越发强烈。他告诉我,后来他趁着护士有次忘关铁门,偷偷跑到护士站里拨通了医院院长的电话,告诉他徐民从“把一个没病的大学生关了进来”。院长表示很震惊,赶到病房和他谈。后来医院组织专家对李明会诊,结果是精神分裂症诊断无误。
2015年11月29日,刘英接到徐民从的电话,通知她李明病情基本缓解,可以出院。刘英赶到洛阳,才知道儿子被打。据其回忆,徐民从曾威胁如果不和解,就不让李明出院,他们只好和护工签订了和解协议,护工赔了7000元抚慰金了事。但徐民从向媒体否认了威胁一事。为了求证李明所述种种事实,本刊记者在医院见到了徐民从,但他以保护病人隐私为由拒绝接受采访。
“在里面是怪圈,无法自证无病,越说自己没病,他越说你有病,他看谁不顺眼,给你写上一笔,本来下个月可以出来的,你这一年都出不来。”李明说,护工、护士、医师都对病人握有权力,每个人都有权记录,什么时候出来全凭他们的书写。作为亲身经历者,他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将一切公之于众。然而,谁会相信一个曾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人的话,这会不会是另一种妄想的表现?李明极力想摆脱这顶扣在头上的帽子,却陷入另一重困窘之中。
孤身维权出院后,他开始维权,起诉、上访、网上曝光、求助媒体……2017年11月23日,洛阳市洛龙区法院做出一审判决,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向李明公开赔礼道歉,赔偿医疗费2167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法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李明有自伤或伤人行为,不属于必须强制治疗的情形,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属侵权。
判决同时认为,洛阳师范学院在对学生管理过程中,对存在问题的学生及时与其家长联系并反映情况,是学校对学生管理职责的体现,且并未参与原告的送医、就医及治疗,不存在侵权行为。双方都提起了上诉,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对判决结果不服,李明则认为自己是在学校当着老师的面被强行带走的,学校不应免于责罚。
一审判决被撤销后,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表示将向法院申请司法鉴定,鉴定李明住院治疗时的精神状态。李明告诉本刊,鉴定的不应该是自己,而是精神卫生中心及其医务人员在收治过程中是否违法。他的代理律师常伯阳也强调,本案的关键并不在于李明是否有病,而是医院能不能拿出证据证明当时强制收治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不过,外界最关心的问题还是李明到底有没有病。一有关于自己的报道出来,李明就会拿着手机反复地研究,查看一条条评论,网友从报道文本里找到只言片语做出自己的判断,有人断定“这个人肯定有病”,也有的抨击学校、医院坑害正常大学生,支持他维权。
从医院出来,他至今仍未撇清与精神病的关系,原本希望通过维权摘掉这顶帽子,但随着舆论的发酵,反倒越陷越深。母亲原来还会配合李明接受媒体采访,后来发现有人开始在网上曝光李明的身份和家庭住址,她给李明打来电话,气得发抖。她担心,家乡人看到后,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遍小县城,以后李明该怎么正常生活。自此以后,她拒绝再接受任何采访,李明劝也没用。
事实上,家里人开始就不支持李明的维权,母亲也劝他早点开始正常生活,但他不甘心。打官司这几年里,他大多时候都是孤身一人,在洛阳、郑州来回奔波。涉及早年经历和家庭关系,他要么沉默不答,要么言语躲闪,小心翼翼地遮掩着家里的一切,但他又不是一个擅长说谎的人,掩饰的方式总有些笨拙、刻意,让人不免心生疑窦。
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确和亲朋好友来往不多,他自己也称,大家平时最多春节走动一下,自己有什么事并不会和他们讲。自2009年高中毕业后,李明在外打工五年期间很少回家,甚至2014年重新参加高考上了大学后,很长一段时间,家里人对此也是一无所知。
相处的几天里,李明更是只字未提父亲。在他那里,这似乎是一个禁忌,他想竭力避开的话题。只有从他自己前后的不经意讲述、律师和母亲的采访、学校的陈述等材料里,外人才能勉强拼凑出一个藏于背后的父亲形象:在家乡的小县城,他父亲算得上一位成功人士,但父母感情很早破裂,双方争吵不断,母亲又一直不愿与父亲离婚,父亲很少回家,李明从小到大跟着母亲生活。
李明说,自己很小就有了自强的心理,希望尽早独立、强大起来,脑子里有许多不切实际的、过于理想化的想法。他做不到像周围其他同学一样按部就班,考学就业,然后结婚生子,但是现实狠狠打击了他。后来,小时候的伙伴都慢慢断了联系,大家都走向了不同的人生轨道,只有他还困在原地。
李明的家乡在河南北部一个小县城,本刊记者曾寻遍法院文书等材料上涉及的与李明家有关的地址,试图找到他在这里生活过的痕迹,但在他从小长大的城中村,没有找到一个听说过他们的人,老人们甚至否认村里存在李姓人家,母子身份证上的住址里提到的道路也早已更名,在城区扩张的进程中正在新一轮翻建,两旁竖起了高高的围挡。
他童年最美好的回忆就发生在老城区的某条街道上。“小时候我是孩子王,每天早上5点钟,天黑咕隆咚的时候,我和我们院里的五六个小孩就从家里跑出来,上学路上车很少,我们可以在路上赛跑,还可以数星星、看星星。到了学校,楼道、教室也都是黑洞洞的,我们在走廊昏黄的灯光下坐着等天明,有时会找一些娱乐项目,捡来一些石子,趴在地上玩扔石子游戏。”他说,这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这以后越来越差。
大多时候,李明听完提问都不急于回答,回答时语速也十分平缓,字斟句酌,旁人看起来像是反应迟钝,但他的表达能力又不免让人惊讶,思维清晰,话里行间还穿插着许多书面语,说话时目光总是低垂,死死地盯着某处虚无的地方。
他从小爱读书,人文、历史、自然、科幻等都有涉猎,在交谈过程中,看得出书籍对他的影响,他的知识面比许多人都广。他说,自己打小的梦想是当一名物理学家,研究人与宇宙的关系,他最向往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那个基础科学不断取得重大突破的时代。有一段时间,他完全沉浸在科学世界,研究那些科学家的生平和他们的研究成果,看科学家之间如何辩论、实验、互相质疑,推进科学进步,他说这是非常痛快、美好的时刻。但如今,他觉得,小时候读书太多也不好,“不宜过早接触这些太宏大的东西,容易让人胡思乱想”。
(李明、刘英为化名)
被妖魔化的精神疾病为了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2012年10月,我国正式通过《精神卫生法》并于2013年5月1日开始施行,法律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用老百姓的话说,精神卫生法保护的是患精神疾病的人不看医生的权利、不去医院的权利、不吃药的权利。其中只有两条例外,一个是伤害自己或有伤害自己的危险,一个是伤害他人或者有伤害他人的危险。”在某市精神卫生中心工作的一位副主任医师王锋(化名)告诉本刊,这不仅尽量尊重和保护了患者的本人意愿,也限制了医生的滥权
李明显然属于例外情形。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在答辩中称,根据李明当时的病情、症状等,医生可以判断其具有伤害自身的危险,而且是其监护人护送住院,医院诊疗行为也没有过错。
王锋则告诉我,按照医疗规范,诊疗行为一般应当在医疗机构施行,而非院外。无论如何,医院派车出诊这件事会被人质疑。通常情况下,如果的确是出现了在非医疗机构的伤害自己或者伤害他人的情况,应该是由家属或所在单位将他送去医院就诊,如果当事人不愿意配合,可以寻求公安机关的协助送诊。
在非自愿治疗的情况下,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判断危险,由谁来判断。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教授、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鉴定人、主任医师胡纪念告诉本刊,在具体实践中,家人、公安机关等参与人员都会对患者的危险性提供意见,但最终由医生判断。“精神卫生法对危险原则已经有明确的规定,但还是比较含糊。关于危险的规定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有现实的危险行为,一个是有危险性。前者相对容易判断,比如说他扬言要拿刀杀谁,或者已经有了暴力攻击行为;关键是对危险性的评判,他没有实施暴力行为,但可能会发生,法律上比较通行的说法是迫在眉睫的、重大的,不过都是描述性的,没有细致规定。”
王锋说,尽管精神科的主观色彩是不可避免的,但所有记录的东西必须是真实发生的,一切记录都有据可查,一个接受过正规训练的精神科医生不会随便滥用自己的权力。他认为,普通民众对精神科存在普遍的误解,例如“如何在精神病院中证明自己无病”。其实这样的情况原则上不会发生。“因为我们默认普通人的精神健康,如果说某人有精神疾病,需要证据。实际工作中就是需要符合国内外公认的诊断标准,包括:症状标准、病程标准、严重程度标准、排除标准。”
但不可否认的是,总体上精神科医生的数量还是不够多。“当缺人的时候,为了完成相同的医疗工作量,有可能就会牺牲掉质量。另外就是医生的规范化训练存在地域差异,北上广规范化培训出来的医生专业能力会强一些,但部分基层精神卫生机构可能接受的训练就不太充分。还有就是部分年纪大的医生,因为中国通常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即使有更完善的办法出台,通常对老医生是没辙的。”
李明被搅进的正是这层模糊地带,然而跳出法律范围,他面临的是更大的社会压力。在媒体报道里,李明都会反复要求记者使用化名,他害怕自己的真实身份暴露出去。他告诉我,最怕的还是周围人的议论。在医院接触了许多病人,亲身体会了精神病人的处境,但即便这样,他依旧无法抵抗根深蒂固的偏见与歧视。
一提到精神病,大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躲远点。“精神病”天然地与暴力、犯罪,甚至反社会联系在一起,这种意识已经扎进人群心理之中。然而不止一位精神科医师告诉我,简单地将精神疾病与暴力危险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常见的误区。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要从两个层面来考虑。一个是群体的层面,实际上,精神障碍患者群体暴力危险性并不比普通人群高;一个是个体的层面,我们确实观察到有些病人在精神症状的支配之下实施了暴力攻击的行为,但这里面有很多具体的影响因素需要进一步研究。”胡纪念告诉本刊,恰恰是后面这部分患者给人留下了所有精神病患者都有暴力危险的印象,再经过媒体或者文艺影视作品把这种印象进一步加深了。
“每个人,无论他是智障、残疾人、精神病人,不能表达或者表达困难,他内心世界都是非常丰富、灿烂的,就像大自然的一棵树。生命发展到人这样的高级阶段,都很复杂,每个人都是有人权的。”李明出来后也开始反思对精神病人的管理模式,他觉得无论如何不能限制精神病人的自由,除非他真的有危险,“可以用半开放的社区,给他们提供生存空间,像专门为智障患者设立的工厂、餐厅一样,空间并不需要很大,给他们教育,稍微有一点点管束,但不是限制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