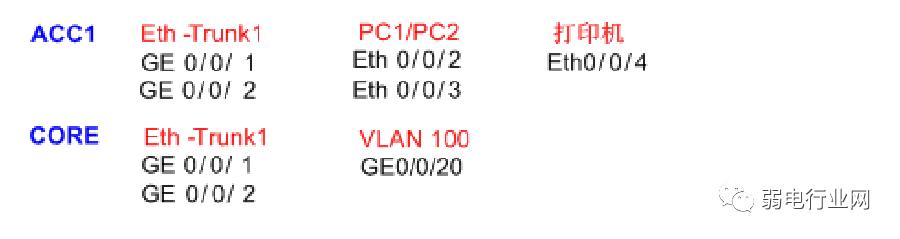【译者按】4月12日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日当天,一个涉嫌反犹主义的说唱组合获得素有“德国格莱美”之称的回声音乐奖,引发德国社会的巨大抗议,最终导致该奖被停办。4月17日,一名男子因为佩戴犹太小圆帽在柏林街头而遭到三名阿拉伯男子的辱骂和殴打,录像上传至网络后引发德国多地集会。
自1960年代始,纳粹屠犹成为德国文化纪念的中心,对大屠杀的记忆成为现代德国身份的一部分。而近期中欧传统的反犹主义和穆斯林对犹太人的敌对态度在德国频现,触及了德国社会的终极禁忌,也折射出当代德国巨大的身份认同危机。
当代德国大约有2250万或五分之一的人口有移民的血统,拥有约500万的穆斯林群体,随着2015年叙利亚难民的进一步涌入,身份认同之间的龃龉愈发凸显。对于穆斯林移民而言,大屠杀始终是别人犯下的罪行,他们没有义务纪念,也不理解如此强烈的禁忌意识,他们的文化背景是阿以冲突,而非纳粹屠犹。
六十年代发明的身份政治在今天引发难以驯服的冲突,身份政治的初衷本是期待完全个人的生活方式,最终演变为族群和认同之间的对抗。六十年代世俗化的遗产也逐渐式微,宗教回到舞台的中心,重获早已丧失的影响力,小圆帽、十字架和头巾成为一场文化战争的象征。4月24日,巴伐利亚州州长宣布十字架是巴伐利亚历史文化身份的一种表达,并要求所有州政府大楼入口处悬挂十字架。随着德国身份的确定性消失,右翼民粹主义和保守势力开始运用基督教传统对抗外来的非西方的异质性文化力量,以笼络选民。
本文梳理了近期德国的文化战争相关的时事,并回溯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遗产与今日事态的关系,试图在身份认同的迷雾中思考“德国身份”的本质内涵,最终本文仍坚持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表达了对普遍主义的怀疑。本文原载于2018年5月3日德国《明镜》周刊,作者包括Laura Backes、Jan Fleischhauer、Jan Friedmann、Lothar Gorris、Sebastian Hammelehle和Jérôme Lombard。

社区,一个唤起舒适感和熟悉感的词语,一个狭小的温馨区域,或者至少是一个没有公开冲突的地方。赫尔姆霍尔茨广场(Helmholtzplatz)是柏林的一个微型社区,也是首都最著名的街区之一,当地人亲切地称它为“赫尔米”(Helmi),它是宽容和国际生活方式的中心,在这里,英语与德语相匹敌,成为人们最常用的口语。自从前几年老鼠问题被消除后,世界公民们就能在此彻底安逸地生活,至于困扰其他人类的冲突,他们只能摇摇头表示无奈。
这至少持续到了4月17日星期二那个温暖的春日傍晚。当天晚上,有着阿拉伯人、犹太人和基督教徒血统的21岁以色列人亚当·阿默什(Adam Armoush)进行了一项大胆的实验。他最初来自海法(以色列北部港口城市),在德国生活了三年,三个月前搬到柏林学习兽医。他有许多犹太朋友,但其实并不特别关心中东的敌对现状。一个熟人送给他一顶犹太小圆帽(kippah,音译为“基帕”),但警告他在柏林的街道上戴这顶帽子很危险。亚当不以为然。
于是,他戴着犹太小圆帽和朋友一起出门,向赫尔姆霍尔茨广场出发。在他快走到广场时,遇到了三个阿拉伯男子,他们开始侮辱他。阿默什打开了智能手机的摄像头,而他拍摄的这段录像如今成为了当代德国的历史性记录。
其中一个男子是19岁的叙利亚人,他开始用皮带抽打亚当,一遍一遍地大喊:“犹太人,犹太人。”录像显示他在亚当身上反复抽打推搡,镜头摇摇晃晃,还能听到亚当说:“我正在拍你,我正在拍你。”过了一会,另一个人来了,把攻击者赶走了。然后亚当对他说:“犹太人或者不是犹太人,你必须处理这件事。”这段是视频的时长只有47秒,但它发布当晚迅速蹿红。47秒的视频将德国的许多问题——即便不是所有问题——摆上了台面。
崩塌的绝缘
长期以来,德国人一直试图让自己绝缘于世界其他地区面临的问题。自2005年以来,选民们反复推举一位曾为实现这一愿景而付出了艰辛努力的总理,以确保德国在总体上成为“赫尔米”一样的地方。这个超大规模的社区是如此国际化和自由,甚至在2015年夏天准备好接收近百万难民。
但现在,这种绝缘似乎正在崩溃。而宗教,这个在德国早已丧失其重要性的东西,却重新站到了最前线。宗教又一次在世界上扮演了强力的角色,甚至在德国最田园牧歌的社区中也能感受到。
结果是,任何关于今日德国的讨论都必须将犹太小圆帽、十字架和头巾纳入考虑。乍一看,他们都是宗教的象征,但如果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会发现它们同样也是这个国家身份的象征,或者至少是人们正在寻找的身份。
许多德国人很难说出这个身份到底有何内涵。德国宪法中规定的价值显然是其中一部分,但除此之外呢?对垃圾分类的痴迷,就像最近德国难民帮助组织(Pro Asyl)在难民指南中极力宣传的?还是德国人的守时?抑或是众所周知的效率?
绝大多数人可能会同意,对纳粹罪行的记忆是德国身份的一部分。大屠杀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个污点,而这个国家选择不对此保持沉默,并使其成为德国文化纪念的中心,这是思想自由的德国喜欢自我标榜的成就。
对欧洲犹太人的谋杀是终极的禁忌。那些质疑这一禁忌的人超出了社会所能接受的范围,这也同样适用于德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缩写AfD)。另类选择党图林根州分会的负责人约恩·霍肯(Björn Höcke)在2017年1月说,柏林的大屠杀纪念馆是一个“耻辱的纪念碑”,并鼓励德国人减少对战争罪行的关注,这对他在该党内部的声望造成了永久性的损伤。
但能否要求外国移民也采纳德国文化认同中这一重要因素?毕竟,德国穆斯林移民家庭中的父亲跟大屠杀有什么关系?他何必要送孩子去奥斯维辛集中营参观?对生活在德国的500万穆斯林来说,大屠杀是别人犯下的罪行。
也许亚当·阿默什戴犹太小圆帽上街的行为是幼稚的,也许这只是一个愚蠢的巧合,在柏林的某个地方,一个阿拉伯人仅仅因为另一个人戴了一顶犹太小圆帽就把他误认为是犹太人。也许你可以把这段视频看成是一个孤立的不幸事件。但亚当的47秒最终发展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充满暗示的力量——犹太人在柏林的大街上被反犹分子毒打。
对现代德国的重大打击
这47秒是对战后开明、现代和自由德国的重大打击。德国犹太人中央理事会主席(Central Council of Jews)主席约瑟夫·舒斯特(Josef Schuster)此后警告人们,不要戴着犹太小圆帽在街上行走,这也是对一个开明国家的重大打击。
但这47秒之所以成为对开放和容忍的严重打击,还有另一个原因,因为这段视频中的年轻人来自叙利亚,2015年作为寻求庇护者浪潮的一分子来到德国。
赫尔姆霍尔茨广场攻击者的名字叫克南·S(Knaan S.)。在事件发生两天后,他向警方自首,他必须出庭受审。他被指控犯有严重的人身伤害和侮辱罪,根据德国法律,这应该受到惩罚。据报道,他的家人有巴勒斯坦血统,克南住在柏林郊区的一家难民旅馆,他的脸书资料表明他是单身。他和SV Stern Britz 1889球队一起踢球。他的脸书封面是柏林勃兰登堡门前的一场亲巴勒斯坦示威游行,而他个人主页上有一张年轻人举着火箭推进榴弹和机关枪的自拍。YouTube上有克南和另一个住在柏林的巴勒斯坦犹太人一起制作的短片,短片试图向警方解释发生了什么,视频上方的一条文字写道:“我们并不仇恨犹太人。”但是这段阿拉伯语的视频并没有解释发生了什么。
这段47秒的视频很可能令人深感不安。70年前,德国人把犹太人送上死亡列车,2015年,叙利亚难民坐上了前往德国的自由列车。大多数德国人对他们给予了巨大的欢迎,这可以被视作为纳粹祖辈的罪行最后一次赎罪——但现在正在生产出早已不被允许在柏林和德国存在的事物:反犹主义。
让事情更令人担忧的是最近关于德国穆斯林反犹主义的大量报道。有报道称,一些犹太学生在柏林几所学校受到欺负。然后是4月中旬的大规模丑闻,素有“德国格莱美”之称的回声音乐奖(the Echo Award)颁给了歌曲中包含反犹歌词的说唱歌手高里加(Kollegah)和法里德·邦(Farid Bang)。在两周内,愤怒的情绪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回声奖被完全停办。
德国的形势变得复杂起来。以前的确定性正在消失,旧的战争正在重启。例如,在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索德(Markus Soder)的内阁最近采取行动,要求在每个州政府大楼的入口处展示十字架。在4月24日的内阁会议之后,这位巴伐利亚州州长自己迈出了第一步,在州的首府大厦的接待处安装了一个十字架,摄像机拍摄了这一事件。在政府大楼里,十字架与蓝白相间的巴伐利亚州旗保持着相近的地位。内阁的决定宣布,这是巴伐利亚历史文化身份的一种表达,是“基督教-西方文化遗产的基本象征”。索德说,这不是一个“宗教象征”,更多与“人们保持自己身份的渴望”有关。
文化战争
索德领导的基督教社会联盟是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领导的巴伐利亚姊妹党,它一再强调,它更多将十字架视为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象征,而非宗教象征。1983年,为了支持新当选的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回归保守的价值观和道德的运动,基社盟的内政部长弗里德里希·齐默尔曼(Friedrich Zimmermann)亲自出面干预,削减了一部被视为亵渎神明的电影的政府补贴。在电影的一个场景中,导演兼演员赫伯特·阿克特恩布希(Herbert Achternbusch)扮演的耶稣从十字架上爬下来,要求被给予“狗屎”。
尽管这一场景亵渎神明几乎是没有疑义的,但当时齐默尔曼的行为却是一场充满侵略性的文化战争的表现,它成为了激烈辩论的主题,知识分子将其视作反动倒退。但齐默尔曼的举动得到了天主教会的支持,包括后来成为教皇的约瑟夫·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
同年,巴伐利亚州政府再次将耶稣受难像用于政治象征,下令在公立学校的每一间教室里悬挂十字架。不过在一群父母提出质疑后,德国最高法院最终裁定,该规定是违宪的。
在这里,索德将基督教十字架用于政治象征,这一事实当然可以归结为传统。皮短裤、发泡啤酒、oom-pah-pah乐队、十字架:这些不都是巴伐利亚的一部分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然而,索德的提议也是一种试图讨好极右势力的尝试,在这场为西方而战的斗争中,它严重依赖于基督教文化的象征和传统——或者至少是它认为的西方的象征。在这场战役中特别活跃的是艾里卡·斯坦巴赫(Erika Steinbach),她因担任德国“被驱逐者”联盟的主席而出名,所谓的“被驱逐者”指的是二战后被东欧地区驱逐出境的德意志民族定居者。斯坦巴赫是默克尔的基民盟的成员,但今天她被认为与另类选择党关系密切,尽管她不是正式成员。斯坦巴赫在推特上抱怨说,大型百货连锁店销售的巧克力复活节兔子在收据上被称为“传统兔子”。她曾哀叹在,石勒苏格-荷尔斯泰因州(Schleswig-Holstein)埃尔姆肖尔(Elmshorn)的圣诞市场现在被称为“灯节”。事实上,网络上对圣诞市场的愤怒正在病毒式传播,埃尔姆肖尔市长收到几十封仇恨邮件——其中一些人忧虑的是另一件事,那就是“灯节”宣传材料上的小天使是个黑人。
当然,一个人可以简单地将这些愚蠢行为付之一笑。但是这些运动背后有一个体系。在法国,斯坦巴赫式的十字军东征将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推为主流政党,因为它试图在圣诞节宣传传统的基督诞生形象,并公开表示对学校食堂里没有猪肉的现象感到愤怒。
乍一看,这些似乎都与实际的十字架没有直接联系。但这里的利害关系比正确的信仰更重要。小圆帽、十字架和头巾是一场文化战争的象征,它标示一个社会的身份——就像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这一身份在近几十年在德国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德国大约有2250万或五分之一的人口拥有移民的血统。现在我们发现自己在努力确定我们是谁,我们曾经是谁,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在担任内政部长期间,托马斯·德·迈齐埃(Thomas de Maiziere)对“我们不想变成什么”这一问题有着相当清晰的认识。2017年,在定义德国的主流文化(Leitkultur)的辩论中,他为《星期日图片报》(the Bild am Sonntag)撰写的专栏文章中提到:“我们不是布卡(伊斯兰国家妇女穿的蒙面长袍)。”很容易将德·迈齐埃的主张斥为民粹主义,也可以说他试图挖走另类选择党的选票。也许这就是他的目的。
“我们时代的法西斯主义”
但关于布卡的议题还要稍微复杂一点。一方面,它是伊斯兰的象征;另一方面,它与开明的西方女权主义观点相冲突。布卡和头巾等同于宗教符号吗?还是说,它们只是前现代的狭隘的父权制的遗物?如果一个女人穿什么出于她的自由意志,那么年轻的女权主义者不会天然反对头巾,但一些更加传统的女权主义者,比如德国最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艾丽斯·施瓦泽(Alice Schwarzer)已经提出公然的反对。2015年新年前夕,科隆发生了大规模性犯罪,施瓦泽甚至还说,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将暴力侵害妇女正当化。她还将伊斯兰主义描述为“我们时代的法西斯主义”。
一般而言,德国人在指责其他文化、宗教或国家是法西斯之前,应该三思而后行。但政治伊斯兰的历史也是镇压的历史之一。保守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复兴始于1979年的伊朗革命,接着1989年的法特瓦(fatwa,伊斯兰宗教命令)要求追杀《撒旦诗篇》作者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这本书亵渎神明吗?现代性的中心成就之一就是亵渎必须被容忍。
1751年,巴伐利亚州的法条仍规定将屡教不改的异端分子斩首。而在那以后,巴伐利亚已经取得了进步,但并不是所有的穆斯林国家都取得了这样的进步。
头巾是这种形式的伊斯兰教的准确象征吗?或者它更像是一种仇外心理的晴雨表?富尔萨(Forsa)民调机构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四分之一的德国人认同伊斯兰教是“令人畏惧的”。2010年,整整73%的德国人认为伊斯兰教与西方世界格格不入。曾在默克尔内阁中担任德国内政部长的基社盟领导人霍斯特·泽霍费尔(Horst Seehofer)今年3月表示,居住在该国的500万穆斯林教徒属于德国,但伊斯兰教并不属于。这是他出任内政部长后所讲的第一件事,而默克尔很快就反驳了他。她说,穆斯林属于德国,伊斯兰教亦然。
现代版本的德国已经历经了将近整整50年的时间,这个正在与自己的身份进行斗争的国家于1968年4月和5月建立。4月11日,左翼学生抗议领袖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在柏林街头被枪杀,就在此前不久,通俗报纸《图片报》(Bild)向读者呼吁:“立即停止对年轻左翼分子的恐怖!”当年的复活节爆发了柏林的街头冲突,国家在5月下旬进入紧急状态,著名学生抗议组织“议会外反对派”(Ausserparliamentarische Opposition,缩写APO)将这一举动与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独裁政权的授权法案相提并论。
这是一场儿女针对他们父母的起义,一场针对德国纳粹的文化反叛,反对社会的狭隘和不开放。1968年的运动也犯了很多错误,包括极端边缘地带的恐怖主义,以及许多原教旨主义形式的共产主义倾向。
今日德国的基石
然而,今天德国的基石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奠定的。一个致力于反法西斯主义、与以色列和犹太人团结友好的民主自由国家,一个争取平等权利的、寻求保护少数民族的国家,就像它试图保护环境一样,一个想要和平和行善的国家,基本上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国家。
如果没有那些之前所有的历史性年份,1933年和1945年,纳粹罪行和大屠杀,历史性的1968年可能永远不会到来。如果没有对几个世纪以来反犹主义大屠杀的明确承认,那么今天人们就不会那么确信地谈论犹太-基督教文化。的确,那些谈论欧洲犹太-基督教传统的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把犹太教排除在欧洲文明的历史之外完全是不可接受的,尤其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
二战中对欧洲犹太人的系统性屠杀被认为对1968年的事态发展是决定性的。在1963年法兰克福开始的奥斯威辛审判期间,广大公众首次面对大屠杀期间犯下的滔罪罪行。审判的结果之一是,大量年轻的德国人第一次认真地看待这些罪行——他们中的许多人得出的结论是,资产阶级与纳粹结盟。
他们对所有年长的权贵都失去了尊敬。毕竟,教皇对希特勒的罪行保持沉默。战后的西德在基民盟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领导下深受天主教和家长制影响。当时,教会在大多数时候都非常保守,但随着1968年的自由化运动的开展,教会的影响开始退潮。而今天,许多新教地区教会,甚至是天主教的主教教区重新回到中心,就像默克尔领导下的基民盟一样。
1968年最终取得了胜利。默克尔成为德国首位女性政府首脑,为同性婚姻扫清了道路。2015年,默克尔也从布达佩斯接收了大量难民。最近一期《经济学人》的标题是“酷德国”(Cool Germany),尽管在同一周,高里加获得了回声音乐奖。该杂志写道,德国已经变得如此开放和多样化,经济成功,政治稳定,它可以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榜样。这种描述过于诱人而让人不敢相信。
在最新出版的关于1968年遗产的著作中,定居慕尼黑的社会学家阿明·纳斯西(Armin Nassehi)写道,除了对德国历史的持续反思,和广泛认识大屠杀对当今德国的到的影响外,今天的流行文化是当年的第三大遗产,尤其是它所提供的美学意蕴,使我们在保持进步和反文化的同时,减轻了我们不断反思的负担。更简单地说:如果你听流行音乐,你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不需要想太多。
没有天堂
高里加和法里德·邦获回声音乐奖,很难用一个更简明的方法来描述这一丑闻背后的困境。
1992年,回声音乐奖第一次颁发,德国唱片业协会想要推广“德国音乐”,当时颁给了赫伯特·格隆迈耶(Herbert Grönemeyer)和蝎子乐队(the Scorpions),还有名气不太大的歌手佩·维尔纳(Pe Werner)。26年后,两个名叫高里加和法里德·邦的说唱歌手获得了这一奖项,这与1968年开始的德国社会自由化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国家是文化多元的。然而,与许多1968年和后来的绿党的梦想相悖,这个文化多元的国家并不是天堂。在这个国家,民族认同的冲突也延伸到了流行音乐的世界。它也是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冲突的温床——这些冲突由中东进口。
法里德·邦把他的身体与“奥斯威辛囚犯”进行比较,这是一个明显的污点。然而,高里加在一段音乐视频中展现了一个戴着大卫之星的恶魔仆从,却更明显地落入了反犹主义的范畴。在这个案例中,进口的穆斯林反犹主义与中欧传统的反犹主义并没有什么不同。
曾经有一段时间,十字架只是流行世俗世界中的时尚配饰。但是,关于身份的斗争早已进入流行音乐的文化。
在新德国诞生50年后,这个国家的环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主流文化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怀疑。这些怀疑来自那些要求回归基督教价值观的政客们;这些怀疑来自穆斯林移民的后果,这最终会摧毁德国社会整合他们的能力;这些怀疑来自民粹主义者和另类选择党,他们更愿意忘掉纳粹统治下的12年;这些怀疑来自过去的恶魔,如今它们爬到了光天化日之下;这些怀疑来自全球性的独裁回归及其普遍主义冲动;这些怀疑来自最近几周引发的震惊,一个想要在犹太人和穆斯林移民身上做得尽善尽美的国家,只能被迫认识到,它所渴望的那种完美的世界其实并不存在。
什么让我们站在一起?
问题不仅在于,普遍主义的逻辑是达到了极限,问题还是1968年一代人发明的身份认同政治,它突然引发难以驯服的冲突。享受完全个人化的生活方式的权利以及受保护的期望,不应该仅仅适用于柏林的心脏地带,而且也必须有效适用于那些留在萨克森州村庄里的人,那里没有所谓的性别流体(gender fluid),萨克森方言是唯一的日常口语,大多数居民把票投给另类右翼党。
那么,什么是属于德国呢?是什么让我们站在一起?无神论者和犹太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左翼和右翼,西和东,巴伐利亚人和萨克森人,城市居民和村民。谁来做决定谁属于德国,基于什么标准?德国的反犹分子属于德国吗?另类选择党的政客呢?把女人叫做“婊子”的大男子饶舌歌手?还是坚持自己与大屠杀无关的穆斯林移民?或者在反默克尔示威游行中高呼“抵抗!抵抗!”的天主教原教旨主义者?我们可能不得不忍受以上所有。毕竟,不同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十字架、头巾和犹太小圆帽,应该可以随时随地地展示而无后顾之忧,在柏林的市中心,在嘻哈音乐会上,在巴伐利亚州首府大厦里。他们都是我们自由民主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