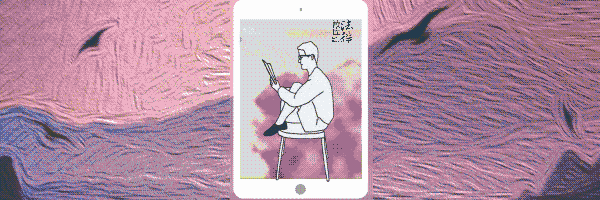
作者:丽鹿
我是读高三那年,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大舅爷。
1987年夏,爸爸从江南出差回来,带回一个眼镜盒大小的景德镇瓷水牛,放在书桌上。那尊卧牛微微昂着头,通体灰黑,十分逼真。爸爸视它为心爱之物,还为它写过一首诗,收录在他的诗集中。

记得那首诗题目叫《答谢大舅父》,开头两句是:
舅舅赠我一瓷牛,
恭恭敬敬放案头。
……
我很好奇,就问妈妈,爸爸诗里的大舅父是谁?他在哪儿?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呢?
妈妈似乎很不愿意说起这个长辈亲戚,也不愿回答我的问题,但架不住我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执着,就略带着些鄙夷语气说:“你这个大舅爷啊,就是柴村你那个舅爷的亲哥,你奶奶的大弟,这个人是个大才子,在江西水利厅,编过《长江水利志》呢。”
我很纳闷。既然大舅爷这么有才、又在大城市生活,他老人家也算是有出息的人了,但为什么从没见他衣锦还乡回来过?而且爸爸也从来不对我和哥姐说起他呢?为什么?
我继续好奇地追问,但妈妈只幽幽地吐出来两个字:“可惜......”
“可惜什么呢?”我追着问她。
妈妈坚决地回答我说:“别问了。以后不许你再提起他。”
好吧,不过,这可真是个谜。越是不让问,我心里就越好奇。
﹏
﹏
﹏
﹏
大三那年暑假,我从武汉回来,爸爸让我去街上帮他取照片。
我到了照相馆里,厚厚一沓照片上,几乎都是爸爸陪着两个陌生老人,在县城各处景点和村子里照的,里面我只认得八十多岁的姨奶奶。
照片中那个谦和儒雅的老头儿,在我看来有一种天然的熟悉感,他慈眉善目、神态安静,爸爸的五官和神情和他十分相似。
回到家中,我把照片交给爸爸,问他里面的人都是谁。爸爸说,这是春天大舅爷从江西回来探亲时他照的。那个瘦高个的老头儿,就是我的大舅爷。这是他离家四十年后,第一次回来。
爸爸说完就去忙了。我想大舅爷一定是个有故事的人,或许这故事里还有什么惊人的秘密。不然,大家为什么都从来不谈论也不愿提起他,为什么四十年间,他都不回老家?
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我和妈妈依偎在沙发上,缠着她讲讲大舅爷。她依然不愿告诉我那些陈年往事,只说这次舅爷回来探亲的经过。
舅爷和舅奶是清明节前,从江西坐火车到洛阳,又从洛阳坐车到了县城。
到了我家后,他和我爸爸讲,自己七十多了,自觉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医生说他的心脏不好,他怕再不回来看看,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他想让我爸爸陪着回老家村子里,给自己的父母上坟。
第二天,从城里出发时,舅爷坐在车上,面色沉郁,一言不发。车子快到汝河桥的时候,舅爷情绪突然激动起来,坐在车后排靠窗位子上的他,扭头贪婪地望着外面的景色,不时掏出衣兜里的手帕,掩面抽泣。仿佛桥下那一弯清冷的水面,在他思念已久的目光中纵情奔流。
过了汝河,遥遥就望见舅爷家的村子了,他不停地指着那个绿树葱茏的地方,反反复复地对舅奶说:“就是那,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车到村头,舅爷怯怯地低声恳求爸爸停车,说想自己下来走进村里。车子停在了麦田旁的土路边,舅爷有些艰难迟缓地推开车门,当他的双脚踩着泥土站稳之后,他抑制不住地忽然放声大哭,引得爸爸也两眼泪花、搀扶劝解他。

那天妈妈讲完后,任凭我在软磨硬缠,她看看爸爸在书房里写字的背影,还是不肯告诉我大舅爷怎么离家去南方工作、安家的经过。
直到大舅爷和父亲相继因病去世十几年后,我帮八十多岁的妈妈整理回忆录时,她才对我说起大舅爷的陈年旧事,但交代我不要将大舅爷的事,写进书里。
妈妈是用“不成器”作为对大舅爷评价的基调,来讲他的故事。
﹏
﹏
﹏
﹏
上世纪二十年代,舅爷出生在豫西乡村一个耕读之家,他的爷爷是清末举人,到了他的父亲一代,家道中落,读书人变成了乡野郎中。
舅爷姐弟五个,我的奶奶是长女,他是老二,下面还有一弟两妹。
大舅爷天资聪颖,诗文俱佳,写得一笔好字,人也长得帅气。他自幼奉父母之命定有一门娃娃亲,女方是邻村远房表姐,大字不识一个,且瘦小貌丑。
舅爷十六岁就成了亲,一心想要出人头地的俊秀少年,就这样在懵懂中蒙受命运的捉弄。
我爸爸一岁时,他的父亲被抓壮丁,一去十年、生死不明,期间我奶奶带着他常住柴村娘家。大舅爷比我爸爸大十岁,便成了他的启蒙老师,甥舅感情深厚如同父子。
大舅爷二十出头,就有了一子一女,那年豫西解放后,不甘埋名乡村的大舅爷,考取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了一名教师。大舅奶带着孩子,和二舅爷一家住在柴村老宅里。
才华出众的大舅爷,有着温和的性格、儒雅的风度。非常吸引解放初那些职业新女性。在女学生眼里,他是魅力十足的良师,在女同事眼里,他是可信赖的益友。
那时候,新婚姻法刚颁布,反对包办婚姻、追求恋爱自由的新风潮很流行,有不少优秀的女孩子主动追求大舅爷,但都被他以有家室为由拒绝了。但当那个命定的女人出现后,大舅爷终于迷失沦陷在从未体验过的爱情中。
那个叫蔓萍的女子,是新从师范学校分来的教师,她一见钟情地爱上了大舅爷这个有妇之夫,并在大舅爷多次拒绝后,依然痴心追求,还用她那一套爱情至上、婚姻自由的新理论,把传统守旧的大舅爷给洗脑了。
蔓萍家是城里的,父母独生这么一个宝贝女儿,自幼骄纵疼爱,说一不二,女儿爱上了不该爱的人,父母觉得抬不起头,学校里也议论纷纷,任性的蔓萍便鼓动大舅爷私奔。
正好当时部队招收有文化的人,大舅爷就投笔从戎,随军南下,蔓萍紧随其后,后来二人转业定居南昌。
大舅爷离家后,撇下妻子和四岁的女儿、不满一岁的儿子,艰难度日。不久,那男孩暴病而亡,大舅奶疑心是妯娌加害,逼迫她再嫁离开,从而独吞房产家业,便无奈带女儿改嫁邻村。
爸爸参加工作后,对大舅爷的女儿时有关照。听妈妈说,她心里一直怨恨当年抛弃她的父亲。不过等到大舅爷晚年回来看望时,她又原谅了这个给她生命、白发苍苍的老人。
我问母亲,那次大舅爷回来,见没见他的结发妻子,母亲说见了。他独自在我父亲陪伴下,去看望了那个被他遗弃的女人,两个年迈的老人,在离异四十多年之后,相逢无语哽咽泪流,握着彼此枯藤老树般的双手,泯灭了曾经的爱恨恩仇。
舅爷和蔓萍倒是相爱相守了一生。但命运似乎总喜欢捉弄世人。婚后蔓萍没能生育,四十多岁时,她从福利院中抱养了一个女婴,长大后招赘了女婿,老两口晚年就和女儿一家生活在一起。
听完妈妈的讲述,我猜想大舅爷几十年都不回来看望家乡和故人,是不是因为他无颜面对过往的一切,而当他终于鼓足勇气耄耋之年回来看看时,他痛哭的眼泪,又是为着什么而伤感?
我有时会感到困惑,人们赞美的爱情,是一种带着什么魔力的东西呢,竟可以让世人不顾一切、痴缠着迷,而人与人之间的缘分际遇,又有谁能看得清、参得透、悟得开呢。
大舅爷当年为爱私奔,几十年来被看成是家族丑闻,以至于亲人们不愿提起他的存在。他也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惨重代价。当岁月无情而逝,那些是非对错又有谁能说清楚,至于后人如何评判,想来也是无用而惘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