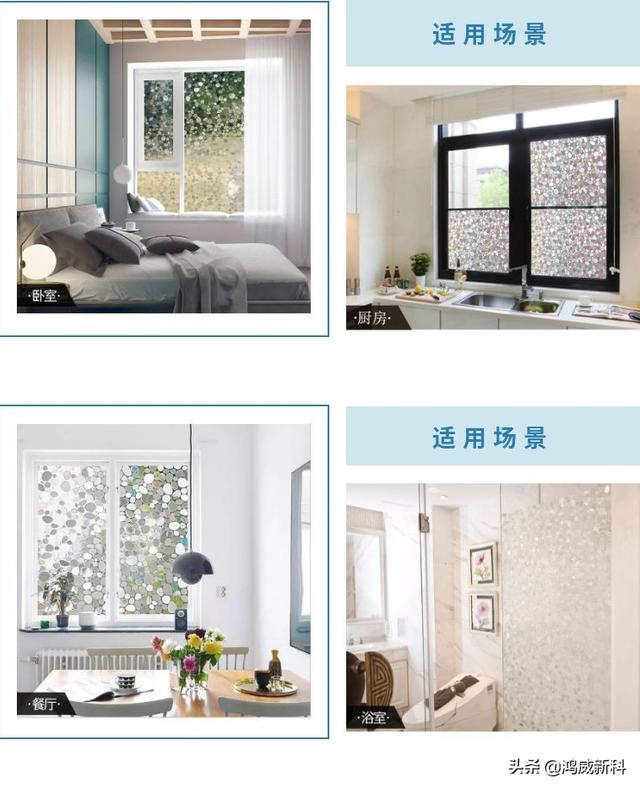本文转自:写作兴趣小组
编者按:说沈从文可能获得诺奖,是否有点一厢情愿,我不敢肯定。这篇文章从内容上似乎可以放在“译史”栏目吧。——翻译教学与研究
众所周知,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文学领域的第一大奖项,从以往的奖项授予情况来看,其侧重点在欧洲和美国。近年来,瑞典文学院渐渐开始注重对所谓第三世界国家文学或者边缘文学的推荐,使得欧美作家越来越难问津诺贝尔文学奖。这表明,在“国际化”潮流的裹挟下,民族的藩篱正逐渐被突破,“第三世界”的文学作品不断被翻译成西方语言,接受世界读者的检验,并逐步寻求融合与认同。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沈从文便已经凭借抒情性散文化的小说从中国文坛走向世界文坛。

一、诺贝尔文学奖对沈从文的认可
在2012年凭借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所绘制出山东高密乡文学版图的莫言,成为有史以来首位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这一突破在激发中国人诺贝尔文学奖情结的同时,也引发对鲁迅、沈从文、贾平凹等一流作家在诺贝尔之路处于遇冷状态的反思。然而,早在1987年和1988年,沈从文就先后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1988年,沈从文已经进入候选人名单最前列,但就在当年的5月10日,龙应台打电话告诉汉学家马悦然,沈从文已经过世,马随即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秘书确认此消息,并给他的好友文化记者李辉打电话询问消息,最终确认沈从文已过世了。因此沈从文称得上是中国作家中最接近诺奖的人。这足以说明沈从文在成为世界性作家的道路上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
而沈从文入围诺奖的主要动因是他善于借鉴外国文学名著,并善于从外国作家人生经验中吸取养分。他以一种人生的间接形式或者艺术借鉴为范本,内化为艺术探索的动力,缩短了与世界读者之间的文学距离,从而实现了作品的可译性。
在二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沈从文充分吸收“五四”前后译介到中国的外国文学作品的养分,进行了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游记、戏剧等形式的文学实践,把对现实人生的怀疑和战争带来的社会混乱上升到形而上的人生悲剧层面,深入到人物的潜意识当中,创作了轰动文坛的《看虹录》、《摘星录》和《烛虚》。这是沈从文在弗洛伊德、乔伊斯的影响下所进行的进一步地创作实验。现代派手法使他的文学技巧达到一个新境界,但最能代表其创作个性的是以二十世纪初湘西现实生活为背景,表现湘西普通大众悲欢离合的作品。这类作品通过把对原始性的追求与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进行完美结合,重塑了诗意的中国形象。沈从文的这类小说往往极力渲染湘西世界的奇幻浪漫以及原始初民的生机与强健,经过作家纯朴温情的描述,即使是杀人越货、酗酒打架、狂放淫乱的行为都显得天真可爱,寓言式地反映了湘西苗族从孤立隔绝逐到渐渐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艰难过程,同时折射出中国从传统的朝代国家逐渐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的历史过程,为后发国家被动回应现代化提供了更具本土性的样式,具有鲜明的异域文明色彩。
此外,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中西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政策的贯彻实施,许多重要的中国文化、文学典籍均已译介到西方,西方读者对了解中国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沈从文笔下所呈现湘西文化的独特性和异质性、简单纯粹的爱情和人的真善美成为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的作品刚好契合西方世界读者对东方的浪漫幻想和神秘情结,代表了中国优秀作家的风格与特色。
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团队对沈从文的认可,其实也是对其译作的认可。因此翻译活动是不同语言之间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问鼎诺奖的必由之路。考察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机制可以发现,评委们倾向于将欧洲语种作为评选语言,那么相应的,对于不具备亲缘关系的汉语来说,翻译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媒介。换句话说,中国作品只有翻译成英、法、德等在西方通行的语言才能进入评选。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从来不是平等的,英语以世界性语言的身份受到诺贝尔奖的青睐,泰戈尔更是通过自译为西方世界呈现出一个散发神秘宗教色彩的印度而得到奖项。而当时中国作品的外译情况不容乐观,作品的翻译数量较少、质量较差、影响力较低,这些因素都成为了中国作品角逐诺贝尔文学奖的短板,这也是中国作家长期未能获奖的重要因素。沈从文之所以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主要归功于中国文学的知音和挚友,翻译家马尔姆奎斯特(中文名马悦然)。汉语作为一门博大精深的语言,我们同样清楚其从一种语境转换到另一种语境的准确再现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但是马悦然作为一位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专家,不仅巧妙地保留了原作的文学民族性和文化内涵,彰显中华文明的底蕴,同时也帮助作家赢得了瑞典读者善于发现美和审视美的心,契合了西方读者的文化观照。而其他瑞典翻译家翻译的《边城》和《沈从文作品选集》正式出版也是沈从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沈从文著作的潜力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沈从文经历了初次登上文学舞台进行文学创作到被排斥、被批判、被迫放弃文学创作,和在放弃文学事业之后被高度评价的历程,可见长期被国内忽视的沈从文是先在海外获得了众多汉学家的认可与研究之后,中国大陆才开始对沈从文的作品进行出版与研究,形成一股强劲的“沈从文热流”。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和90年代各有29种沈从文作品及相关的新书出版。
沈从文作品在海外的翻译规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沈从文在世界的被关注、被接受的程度。其发表于1926年3月的《母亲》,次月就被翻译成日文发表在《北京周刊》上;1927年10月柳湘雨将《盲人》译成日文发表在中国大连期刊《满蒙》上;1935年竹内好将原名《晚晴》译为《黄昏》发表于日本期刊《文艺》12月号上;1936年,《边城》首次被埃米莉•哈恩译成英语,以《翠翠》为篇名在《天下月刊》1-4期连载;《柏子》被埃德加•斯诺译成英文,编入《活的中国》一书在伦敦出版;《颂》被艾克敦与陈世骤译成英文编入《现代中国诗歌》一书在伦敦出版。
在作品集方面,1932年,张天雅译的法文版《沈从文小说选》由北平政闻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出版社首次将沈从文的作品以外文结集出版。从1926年到1949年,沈从文的作品被翻译的又在期刊上发表的有27篇之多,作品集有5部,译者多达数十位。由此可知,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相比,沈从文作品的翻译起步较早,数量也较为可观。但在翻译选材方面缺乏系统性。其中被国内学者视为沈氏乡土小说经典,亦受到西方学界盛赞的唯一的长篇小说《长河》甚至没有完整英译,使得西方世界无法全面了解沈从文的创作与思想动态。
沈从文的乡土作家地位不仅因其作品数量,更因其浓厚“乡味”。金介甫直言:“今天,沈的作品在大陆上首次又在有限范围内发行,这主要应归功于这些作品的乡土风格力量。”夏志清认为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沈先生善于将民俗风情、民谣和景物融入作品,把动人的故事娓娓道来。由此可见,以湘西为创作源泉和着力点的作品成为译者的首选。
综上所述,沈从文的创作与诺贝尔文学奖所期待的具有理想倾向的原则不谋而合,体现了人类精神与艺术创造的美学理想,以世界性的眼光预见人类所共同面对的现代化问题,执着于某些永恒的主题如人性、美、死亡等,越过既有的一些价值观念,细腻地深入到生活和人的精神肌理,发现现实中左右人们内心和灵魂的东西,洞察到一个民族文化、性格、品质,思考人的生存状态和现存文化形态,从而形成一种对全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和忧患意识,蕴藏了小说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日语、挪威语等十多种语言的潜质。
三、问鼎诺奖的助力因素
沈从文享誉国内外与多位译者的反复翻译密不可分,新译作既提供了重温沈从文经典之作的机会,也为研究注入新鲜血液。沈氏乡土小说译介主要依赖于外语译者和外语环境中的华裔,尤其是1940年代以后,本土学者基本未译沈氏乡土小说。自1970年代始,金介甫出于沈从文对中国社会状况的敏锐感受,致力于沈从文及其作品译介,引发国外研究者的关注。
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共有四个英译本,分别出版于1936年、1947年、1962年、2009年。不同译者对待文化所持的态度不自觉的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制约着译者的选择,既表现在拟译文本的选择上,也表现在翻译策略的确定中。项美丽与邵洵美的合译本发挥了对诗意中国的浪漫想象,金隄与白英的合译本则强化了对现实中国的指涉,戴乃迭译本充满政治禁忌,金介甫译本则致力于对乡土区域文化的深入挖掘,将《边城》中那个神奇丰厚、未曾被近代文明沾染的湘西世界的文化原原本本地呈献给目的语读者,显示出翻译向文化翻译靠拢的嬗变过程。由于初期翻译原则主要是为西方人介绍中国乡村生活,对中国文化缺乏深度了解的译者在增译及错译中消解了文学所蕴含的张力,导致西方读者无法真正认识沈从文所传达的文学精神、审美价值和语言技巧的运用,延迟了世界对作家的认可度。而金介甫在吸收前三版译作长处的基础上,以一种译入语读者喜爱的方式,将译作呈现在西方读者面前。
在沈从文奠定世界文学地位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依靠学者和译者的助力,引起世界文坛的注意。西方推荐沈从文第一人夏志清所言:“沈从文在中国文学上的重要性,当然不单止建筑在他的批评文字和讽刺作品上,也不是因为他提倡纯朴的英雄式生活的缘故……但造成他今天这个重要地位的,却是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对艺术的挚诚”。学者们的评价进一步提高沈从文作品在翻译领域的影响力,给予译者更大的诠释空间。因为当作品地位在目的语系统中不再处于边缘地位,译者才能超越翻译规范,试图进行不同的文本创作,所以翻译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不断地批判和改进,不断更新的动态进程,从而使作品获得“来世生命”。从沈氏乡土小说具体译介情况看,40年代以首译为主,80年代首译和复译对半,90年代首译和复译分别占61%、39%;初期创作与译介步调较近,但创作与译介同步者较少;1920年代的乡土小说英译较多,但复译者偏少。30年代的沈从文把驾轻就熟的中国传统语言文字与西方现代文法的融合,练就了自己独特的叙事模式,作品的生命力更强,但学贯中西、精通双语译者的稀缺不能保持译作的延续性。因此复译最多的是30年代的乡土小说,《边城》已由11个国家用9种外文出版。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译作数量明显减少,20世纪80年代以后,译介选材涵盖作品的方方面面,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毫无疑问,作品的影响力和赞助者的因素也会促进作品的经典化,奠定作家的文学声誉。沈从文当年有望问鼎诺贝尔奖,正是因为瑞典翻译家马悦然对其作品的译介。所以,中国文学外译离不开外语译者。
当然,中国政府的努力也很重要,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文学》杂志译刊了沈氏部分乡土小说,通过“熊猫丛书”出版了沈氏小说英译集,让杨戴译本得以畅行于世。杨戴的成功示范了中国文学翻译离不开中外翻译家的通力合作,只有优秀的翻译才能使作品重新得到阐发的空间,焕发新的生命力,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完成出版的四大名著就是最好的例证。作者与译者的共同研讨也成为翻译成功的关键因素,金介甫对沈从文进行十二次深度访问,才能准确把握主题,把读者的关注由作品外部引向作品内在,较好地在译作中呈现湘西民风民俗的语言和语言背后的民俗文化。因此,只有精通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学的汉学家才有可能完成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作的优秀译本,而这些作品也将成为英语国家读者了解中国社会的窗口。

沈从文的逝世,使中国在20世纪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但他这位天才作家用坎坷的文学之路鼓舞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同时运用对生活的敏锐感受和观察开创了乡土文学传统,为世界带来新鲜的文学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