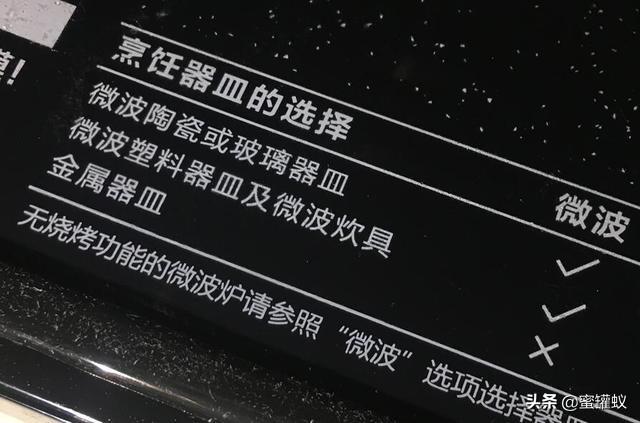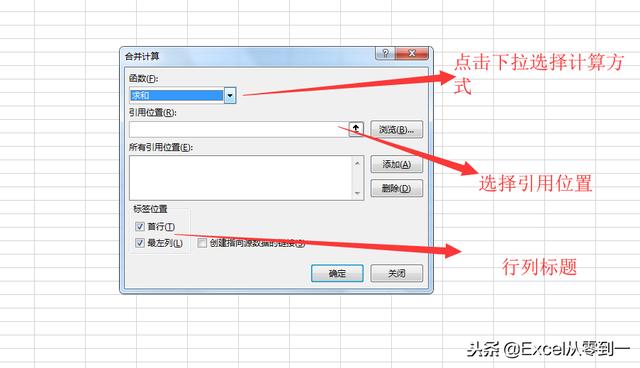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川北农村的老家,大人小孩身上都养着“小虫”。不是我们想要养它们,而是这些小虫太过皮实,繁衍猖獗,除之不尽杀之不绝,生生不息于人的身体之上,以噬血为乐,咬人为快。它们就是让人们头痛的虱子和跳蚤。
说起虱子和跳蚤,其实并非“中国特产”,在著名的《格林童话》中,有一篇寓言故事就谈到了虱子和跳蚤,可见在全球范围,这两样小虫都颇具“知名度”。
人们常常将虱子和跳蚤弄混淆,其实它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虫种。简单说来,虱子比较“专一”,喜欢群集一处,它们在人的内衣领襟、腋下、裤腰、头发根等地方寄宿,动作迟缓,慢慢爬行,缓缓移动。而跳蚤生存范围比虱子大得多,人的衣缝里、家畜的皮毛上、地上、床上、灰尘中,到处都能留下它蹦蹦跳跳的身影,因它有一项跳跃技能,捉之不易,逮之头疼。
虱子和跳蚤,对我而言,是司空见惯的小东西,随身“随时携带”。自己从未数过,身上到底养着多少虱子,今天消灭一批,明天又有“新生代”卷土重来,与之搏斗,仿佛永无休止。但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特色”,我家里上至母亲,下至兄弟姊妹,整个队、整个村,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生活的那一片区域,每个人身上都长有虱子,生过跳蚤。既然大家都是虱子和跳蚤的“寄主”,用血肉之躯“养育”着这些惹人厌的小虫,捕杀和消灭它们,也就成为生活的必须技能了。

一
农闲或艳阳天,就是人们捉虱子的好时机。大家三三两两地走出屋子,或靠在墙根,或搭根小板凳,或搬把椅子,坐在院坝里,一边懒懒地晒着太阳,一边进行自我光合作用。而人们的双手却不闲着,利用这样的时间,专心致志地捕捉虱子。男人洒脱地三两下脱掉衣服,翻开里面纫线的地方,对着阳光一照,线缝处已密密覆盖了一层褐黑的小虫子,正在慢悠悠地爬动。人们的指头敏捷而果断,两个指甲掐紧,用力一捏,发出啪一声脆响,指甲尖端处,便会留一丁点儿血迹。掐挤得高兴,索性翻出裤腰来,稍微搜寻一下,虱子就会暴露在眼前,双手发力,两个大指甲合拢,一堵一挤,从不落空,“啪啪”声不绝于耳。
男人在田里松土或园中除草,身上痒得受不住了,不管三七二十一,脱掉上衣,或解开裤头裤腰,站在那儿专专心心捉虱子,不时搓捻两下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这两个指头劳苦功高,掐虱掐得指甲发酸发疼,看到指尖残留的虱子尸骸,男人脸上露出兴奋表情,仿佛自己壮实的身体,养的虱子都比别人肥大一些。
鲁迅笔下的阿Q,顶着日头在街上走,看到王胡在墙根捉虱,他也并排而坐,脱下破夹袄翻检。因为自己身上虱子不如王胡的多且大,咬在嘴里不如人家虱子咯嘣声响亮,阿Q竟然还生了嫉妒之心。可见人们对这“自养”的虱子跳蚤,还颇有“敝帚自珍”之感,既恨小虫咬得自个浑身瘙痒,红斑点点,若“虫不如人”,又觉得不够体壮脂厚,寒酸了——岂知人越是穷,越怕他人笑自个寒酸。像是贾平凹暗讽的那样,有人自大,认为自个身上生的虱子都格外俊气,是“双眼皮的”。
虱子可谓“行无止处,口不择地”,毫不客气地将它们的寄主身体,视为自己的“疆域”,浑身乱爬,遍体乱咬。虽说被它吸血后,不会留下鲜明血口,那一小小红点,也痒得人心里发慌。后背是手指难以抵达的“盲区”,虱子在后背留下一串串红,一拨拨痒,简直令人难以忍受。于是,在当初的乡村,你会不时看到有人干活干得好好的,忽然就丢下农具,跑去紧贴树干或屋檐下的柱头,上下左右蹭来蹭去,一副既吃痛又痛快的模样,五官扭曲又舒展,不知到底该摆成怎样的表情,一心反复磨蹭,只为了能遏止后背的痒。他们非要蹭得墙灰飞、枝叶晃,背心一片火辣辣的感觉,才感到稍微舒服一点。自己难以捉住后背虱子,便寄希望于这种“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强烈蹭磨方式,能让虱子被碾压成一团肉饼。
捉虱子这件事,既可以“各人自扫门前雪”,又能“合力互助火焰高”,自捉与互捉,相辅相存。甚至对于后背、头顶等盲区,有人相助,才事半功倍。能将手伸到对方衣服里,贴着肌肤捉虱子,无疑是一种亲昵举动,彼此若不亲厚,感情不融洽,还难以完成这样的亲密动作。
女人捉虱子要麻烦一点,得关上房门,在屋里脱掉衣服,从内衣中翻捡出“自养”的虱子。有时掐得指甲盖发痛,索性绷起衣裤的线头,拉成直线状,在煤油灯上快速燎过,便听一连串噼啪声,空气中迅速弥漫一股肉体焦糊的味道。她们内心既厌烦又有点莫名的兴奋,觉得自己肚子从未吃饱过,怎么这一身血肉,还能养得了这些肥嘟嘟懒洋洋的虱子呢?
大方一点的小媳妇,在屋里脱下内衣,只穿一件空心棉袄,坐在自家院坝,就着暖暖的阳光,将内衣翻转,仔细查看线缝里蠕动的虱子。小媳妇留着长长的指甲,掐虱子的声音便格外清脆,如掐死一只,眉头紧紧地皱一下,直到将一件内衣里的虱子杀得落花流水,才伸个懒腰,舒舒服服地叹口气。
村里有的大爷眼神不济,他们也不会在手指上蘸着唾沫捕捉虱子,既没那个眼力,也没那份耐心。他们的捕虱方法简单粗暴,用的是“滚水烫老鼠”的法子,老鼠也好虱子也好,除了在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翻筋斗的孙猴子,没有哪个动物不怕热烫。有个大爷晚上在脚旁生一堆火,脱下棉袄,里子向火,因为拿得近,自己脸皮被热风炙得紧绷绷的,这让他尤为兴奋,眼里迸出欢欣的光来,暗自念叨:让你狗日的喝我的血,这下烫得你们断子绝孙!棉袄烤得发烫,大爷快速叠起,压在屁股下,让虱子热得找不着北,再让它们尿滚屁流,尸横遍野……
这种方法捉虱是否有效不好说,但有位大爷在一次捉虱时,棉袄着了火星,他未看见,以臀压之,结果火烧起来,差点燎去大爷屁股一块皮肉。受到惊吓的大爷从此变得格外“佛性”,虱子就算横行无忌,他也不管不问,好比那佛祖割肉饲鹰,成天将手插进袖筒,目光冷淡地看着太阳底下忙着捉虱的老人,脸上一副看破红尘的样子,舍下一身血肉,满足虱子的饕餮。
但大多数的人,积极面对虱子,“生命不息,捕虱不止”。
捉虱子这种事,堪称我们当年的“日常活动”。即使农忙,总会有歇气的时间,坐在田埂地头,大姑娘小媳妇互相帮忙,捕捉头上的虱子。那时许多农村女性,都有一把篦子,和梳子相比,篦子更为齿密,大概专为梳下虱子而生。女人头发长,放开辫子,篦子从发根梳到发梢,会有一群被迫“离乡背井”的虱子,随着篦子的细齿而迁徙,若小股洪流一般,滑落到为它们准备的平展硬物上。我头上的虱子太多,三姐和四姐让我把脑袋靠近院子的石桌,她们用篦子一遍又一遍地“篦”过我的头皮,桌面上落了不少活物,它们离开了温暖的头皮,正无奈而张皇地蠕动着。我翻转大拇指,用指甲盖一一按下,噼啪声响之处,石桌上顿时“哀鸿遍野”。
对于捉虱子这种事,我们已经练成了“意到、手到、虱子到”的高超本领。坐在教室里正认真读书,或是躺着床上睡觉,或是在路上行走,或正在吃饭时,身体某处一痒,伸手进衣,捉出来一看,好大一只虱子,通体褐色,肚子圆鼓。看到自己鲜血喂养长大的虱子,当时的我和众多人一样,习以为常,丝毫不会有羞涩之感,也没有对它产生憎恶,能稳稳地捉住它们,那是一种莫名的成就啊。

二
乡村学童淘气,常常使用虱子作“道具”。一个同学上课时,捉到一只异常肥大的虱子,叹为天“虱”,得意无比,一番把玩之后,觉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竟将它潇洒一抛,丢到前排同学脖子里。那位同学正在听课,“虱”从天降,一时暴跳如雷,竟不顾课堂纪律,回过头来,双手一撑就要翻过桌面进行讨伐。老师要求住手的喝声,不料到了前排同学耳中,犹如“加油”一般,更加骁勇地扑过去,吓得旁边女生尖声惊叫。
老师扶了扶滑到鼻梁的眼镜,像拉斗鸡一般将两个学生拉开,得知是虱子惹的祸,老师并未多加指责肇事者,只是指戳着他鼻尖恨恨道:“人人身上都有的,你非要割爱送人,多事不多事?”学生们拍桌跺脚大笑。老师若脱下身上的蓝色中山装,也是有虱子的,但他大概不会割这个“爱”,悄悄将自家“养”的虱子捉起,强行送给他人“惠藏”。
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乡村知识分子”,他时刻都记得自己是“灵魂的工程师”,在面对虱子问题上颇有君子之风,看作抛虱学生淘气,前排学生冲动,各自训诫一番了事。老师对待虱子的这份冲淡态度,让人联想起晋朝时的王猛。
王猛是个地道读书人,虽家境贫困,但从小就有青云之志,热爱读书,学识渊博。听说东晋大将桓温打进关中,特地到灞上求见。桓温想试试王猛的学识才能,便请他谈谈当今天下形势。王猛侃侃而谈,将南北双方的政治军事形势分析得一清二楚,见解精辟,桓温听了不免暗自点头,内心赞服。正谈得高兴,王猛一面说话,一面将手伸进衣襟里,摸起虱子来。桓温左右的兵士忍不住笑了,他丝毫不受影响,既不减谈兴,也不就此端正仪容,不做“扪虱”之举。后来,周总理曾以诗句评价王猛,“扪虱倾谈惊四座,持螯下酒话当年”。王猛扪虱,真是极富历史色彩。
也许是文化差异,我的家乡人捉虱,王猛这样的古人扪虱,说明在中华大地,虱子从来都属于“过街老鼠”的地位,人人喊打,人人也打得。哪知有人翻到思想家罗素的《结婚与道德》,其中一章是将中古时代思想的,真真令人匪夷所思了:“那时教会攻击洗浴的习惯,以为凡使肉体清洁可爱好者皆有发生罪恶之倾向。肮脏不洁是被赞美,于是圣贤的气味变成更为强烈了。圣保拉说,身体与衣服的洁净,就是灵魂的不净。虱子被称为神的明珠,爬满这些东西是一个圣人的必不可少的记号。”
国外的虱子,曾在中古时享有这么尊崇的地位,竟是“神的明珠”,倘若一个圣人身上,不披挂几只虱子,恐怕都不好意思出去见人的。在王猛等人“捉虱为乐”时,难道国外圣人们正在“养虱为荣”?我只想隔着遥远时空与重山江海,问问当初国外圣人,难道就不怕在教会布道时,忽然身上奇痒,不但要当场做出抖肩跺脚等动作,甚者还要挤眉弄眼做怪相吗?
俗话说唯有爱和咳嗽不能忍受。其实不能忍受的哪里只有这两样呢?痒也是让人无法忍受的。我在乡村生活时,夜晚睡下,却又奇痒无比,就像一柄羽毛不停拂我痒痒肉,这比疼痛还要让人心烦意乱。一怒之下,掀开被子,重新点亮煤油灯来查看被窝——翻开一看,草席下、枕头旁、被子内侧,虱子们还在闲庭信步呢,一个一个去掐捏捕猎,不顾唯一一条棉被上,斑斑点点都是“血染的风采”,心中带着一种狠狠的快意,诅咒虱子:喝了我的血,就该还回来!
虱子藏身之处,必是“缝”。比如衣缝、裤腰缝、被褥缝,我曾经就是一名“养虱大户”,褂子的几条衣缝里,整整齐齐排列着两行虱子,比受过特殊操练的士兵站得还要齐整。只有哪一只虱子不小心掉下来了,那些被褥缝的才会赶紧“替补”上去,依附“前辈”的位置,认认真真站好自己的岗。若是在平整布面上,虱子反而存不住身。
而头发缝,也是虱子的高产区域。
我和小伙伴一旦理发,就会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少了遮掩,头发上暴露出粘挂着的一层白白的虮子来——这种虱子卵,你若不理会它,大概七八天,就能养出一只只肥硕的虱子。《淮南子·虮虱》说:“牛马之气蒸,生虮虱。”虱子微小,它下的卵更是微细,但即使如白芝麻三分之一大的虮子,也十分讨厌,光是看到盖着头皮的一层“白麻麻”,已经让人心里提前叹口气了:为啥这种小东西,就这么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呢?头虱在人的头皮上,吸食血液时会分泌出唾液,令人觉得很痒,还会不时感觉有东西在头上爬行。民间有句俗话叫“莫在太岁头上动土”,可见“头上”对于人人都是重要部位,轻易不可触碰折辱的。这些虱子却偏偏不认这个理,将它的子子孙孙都铺排到人的头上,安营扎寨,繁衍后代。
村里一个小伙准备相亲,说媒的亲戚特意嘱托他,相亲前一天要洗头洗澡,干干净净见人。小伙提前搓洗掉一层黑泥老皮,借了同村伙伴的一点头油,将自己抹得像个上海小生。用伙伴的话说,这么一打扮,他如同鸟枪换炮一般,姑娘要是看不上,简直天理不容。
小伙踌躇满志,全家人都欢天喜地,等待未来儿媳前来相亲。姑娘爹妈跟着一起来,他们对小伙甚为满意,返回的路上,只有女儿闷闷不乐,倒不如相亲之前快活。姑娘爹是个通达人,让女儿讲讲个人感受。姑娘一噘嘴一扭腰,直截了当告诉老爹,她不乐意!至于为啥不乐意,老两口缠问了一阵,姑娘才说出原委:“他鬓角停着一只虱子”。
老爹嗨了一声,觉得这根本不是一回事,贫下中农,哪个身上没有虱子?宝贝女儿拿两只大拇指掐一掐,一会功夫就能杀掉一队“虱子兵”。姑娘还是坚持着,她似乎也没说错,就算大家都长虱子,你好好将虱子养在头发里,拿出来招摇什么?
小伙不明白,那虱子平日在头发缝里当“宅虱”,从无僭越之心,实在是被伙伴的头油熏得睁不开眼吸不进气,奄奄一息地爬到鬓角,呼吸两口新鲜空气,结果害得主人丧失了一段大好姻缘。可见在对待虱子问题上,男人大多比女人豁达,女人要比男人拧巴:我养得虱,但说不得。细品之,竟有一种禅味了。也有少数女子,才思敏锐,不以为忤,敢拿虱子开玩笑。比如苏轼就曾和他小妹两人戏对:阿兄出门迎双月,阿妹窗前捉半风。这“半风”,就是虱子的别称。

三
汉代王充在《论衡·变动》中说:人在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之内,蝼蚁之在穴隙之中。
将人比作跳蚤和虱子,是士大夫的谦逊,也是他们的天真,因为即使他们能忍受这样的比喻,到了广大劳动人民那里,却是深恶痛绝的,要是你对哪个老农念叨这层意思,他恐怕会瞪眼发怒:你骂哪个是跳蚤?你祖宗才是跳蚤!
虱子固然可恶,跳蚤也很可恨。单从逮捉难易来说,翻转内衣裤,甚至袜筒内部,能看到密密麻麻的褐黑小点儿,它们牢牢粘在衣缝或发根上,即使猛烈抖摆衣裤或摇晃脑袋,犹如给这些小东西带来飓风或地震,它们也能忍受天旋地转,抓紧脚趾握紧拳头,就是不从人身体这片“沃土”撤离。人们还得用手指甲一个个地捕捉,拿篦子一次次地梳理,若能烧一锅滚水,将衣裤全都丢进去好好烫上一番,都不能驱之灭杀,更何论那时我们连洗衣的冷水都金贵得要命,更别提沸水灭虱。与之相比,跳蚤简直是“跳高健将”,它的特点不是像虱子这般“死皮赖脸”,而是“偷袭神速,撤退敏捷”,倒比“宅虱”更难对付。
有个寓言故事,说的是虱子常年居住在富人床铺上,它吸血时动作轻柔缓慢,在安乐窝呆了很久,富人竟没有发现它。虱子和跳蚤是好朋友,跳蚤蹦蹦跳跳地前来拜访虱子,虱子高兴之余,不禁炫耀自己的“高档住所”,说富人的床铺是软的,血是甜的,要是你不信,今晚也留下来饱餐一顿!虱子这样做,有点像“有朋自远方来”,怎么也要请朋友吃顿饭,尽一尽地主之谊,只是它这美味佳肴都是借于富人,并非自产。
天终于黑了,跳蚤口水直流,待富人响起甜蜜的睡鼾,跳蚤迫不及待地跳到他身上,狠狠咬了一口。富人吃痛,顿时从梦中惊醒,他大喊大叫,仆人急忙跑来点亮了灯,照得房间如同白昼一般。富人怒气冲天地要求对房间进行全面搜查。
跳蚤腿脚有力,动作敏捷,很快就蹦走了,可怜那慢腾腾的虱子,一生只会缓慢爬行,于是成了这次大搜查的替罪羊,为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
寓言生动说明了跳蚤和虱子太不一样了,它在吸血咬人这方面,更为狡猾,也更矫健,不会像虱子那么呆头呆脑地“束手就擒”。
鲁迅曾有一篇《夏三虫》,论了夏天的三虫:跳蚤、蚊子和苍蝇。让人惊讶的是,“三权相较取其轻”,先生竟然认为跳蚤还不算顶顶讨厌。他这样写道:“假如有谁提出一个问题,问我三者之中,最爱什么,而且非爱一个不可,又不准像“青年必读书”那样的缴白卷的。
我便只得回答道:跳蚤。
跳蚤来吮血,虽然可恶,而一声不响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蚊子便不然了,一嘴叮进皮肤,自然还可以算得有点彻底的,但当未叮之前,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却使人觉得讨厌。如果所哼的是在说明人血应该给它充饥的理由,那可更其讨厌了,幸而我不懂。”
鲁迅先生提示了跳蚤咬人的特点:叮而不喊。这种“沉默的美德”,反而使它更难防范,蚊子像个饶舌鬼一般招摇过世,苍蝇翅膀扇起的风,也能让人提前预知它的可恶和讨厌。但跳蚤却是彻头彻尾的“马后炮”,当你“开始防范”时,它已经吸饱了血,心满意足地跳到别处凉快去。
在我记忆中,不仅仅是人被跳蚤侵扰,猫、狗、牛、羊猪等,几乎所有的家禽牲畜身上都有跳蚤。若论对人精神的折磨,跳蚤是比虱子更为可恶的,它也像虱子一般吸食人的血液,传染疾病,但还会制造奇痒的感觉,使人寝食难安,烦躁得要命。有人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将一直跳蚤放进玻璃杯,发现它蹦跳的高度,一般可达到身体的400倍,这就相当于一个身怀轻功的大侠,双脚轻轻一点,已能含笑淡然飞越重重障碍,可见要逮它多么困难。跳蚤真是十足的滑头,上蹿下跳,云里雾里,来无影去无踪,仿佛“影子战士”一般,你休想用捉虱子那一套方法捉住它,它一蹦老高,善于和人们打游击战。
在长期和跳蚤作战的过程中,人们也被迫发明了一些简单实用的捕捉办法。发现被窝里有它时,快速掀开被窝,拿煤油灯一照,这时跳蚤还有点“发懵”,不会跳远。看准之后,用沾了唾沫的指头,眼疾手快地一按,手到擒来就能捕捉一只。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捕捉时,人们一气之下,便在草席上、尿桶旁、茅房边,涂抹或倾洒敌敌畏或605农药,依然收效甚微,跳蚤照样我行我素,四处乱窜。
从张爱玲留下的遗书中得知,她晚年频繁搬家,几乎达到了每星期搬一次的频率,而每一次搬家都和跳蚤有关。她被跳蚤深深困扰着,认为这种来自于南美、小到肉眼难以看见而生命力又格外顽强的跳蚤,摧毁了她整个精神世界的安宁。为了躲避和灭绝这些跳蚤,张爱玲不断搬离原址,在各地旅馆辗转流徙,随身只带几个塑料袋,又购买了大量昂贵的杀虫剂。但即使这样,她认为自己也没有逃掉跳蚤,在和跳蚤的搏斗中,她缴械落败。当然,后来人们在张爱玲遗体居所没有发现一只跳蚤,怀疑那些折磨她的小东西都是缘于心病,但即使是心病,也是现实的投影之一,现实世界的跳蚤有多可怖多可憎,才会造成一代才女最终的心理崩溃。
小小的跳蚤,不仅会让人烦恼不已,据说还曾让“皮糙肉厚”的恐龙发疯。在侏罗纪时期,这些“巨型跳蚤”和现代跳蚤不一样,体形巨大,口器坚固锐利,能刺穿恐龙厚皮,以它们的血液为食。想着恐龙长了一身“肉铠甲”都无法避免被跳蚤吸血,甚至因为这痒疼而狂躁时,我又为自己身为人类而稍感宽慰了,至少,我们还长着灵巧的两只手,一个能想主意的大脑,能和跳蚤斗争。

四
生活在红尘俗世,多少年来,跳蚤和虱子像是影子一般,与人“共享”生存环境,气过恨过之后,发现要彻底摆脱它不易,便有文人站出来,宽宏大量地表达了“与虫共在”的自嘲精神。比如日本的俳句大圣松尾芭蕉,在旅途中被跳蚤虱子叮咬了满身的包,还能思如泉涌,挥笔写下著名俳句:跳蚤虱子闹得欢,马尿声声枕边响,文化苦旅也是乐。至于中国文人,因为有了王猛的“扪虱而谈”,王猛偏又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人,肚里真是装了锦绣乾坤,他所做的出格行为便被定义为“名士之不羁”,非但不丑,还成了世外高人的俊逸形象。于是,不少文人都将“扪虱夜话”用于自己的诗文创作,以此来表示一种洒脱态度,一种高洁风骨。比如陆游《剑南诗稿》中的“扪虱夜谈空自许,诗情恰在醉魂中”,还有王安石《和王乐道烘虱》中的“时时对客辄自扪,千百所除才几个”。
文人骚客再怎么使用文学语言描绘虱子跳蚤,到了底层百姓这里,却没有那个“精神高度”去关注这两类“小动物”的可爱之处,只觉得它们是造成身痒难耐的源头,打扰平常日子的克星,恨不能一夜醒来,他俩物种均告灭绝。
要消灭虱子和跳蚤,方法很简单,爱清洁,讲卫生即可。遗憾的是,当初我们生活的乡村环境,是压根儿做不到这一点的。
夏天还好,男孩子们能去河里水塘自在地游泳洗澡,即使女孩子不方便下水嬉戏,也能打一盆水,太阳晒得温热了,晚上躲进房间,拿毛巾擦擦身子。但漫长的冬天到了,我们也就到了一连几个月,都无法清洗自己身体的时间。
那时节,冬天谁会费劲巴拉烧水洗个澡呢?头发的油垢,许久不换的内衣,都给虱子的生与长提供了温床。甚至有这样的极端例子,说一个人一生只洗过三次澡,一次是出生,一次是结婚,一次是死亡。
洗澡不易,太费柴禾,将一锅水烧热,总是要浪费珍贵的燃料,为了坡上一根枯枝,邻里都会吵闹成仇,柴禾有限,要优先用在煮人饭或猪食上,洗什么澡呢?再说大家都没有讲究卫生的意识,放眼望去,所有人都不洗澡,每个人身上都“养”虱子。就算你洗得再干净,和别人一接触,立马就会“过继”到身上。
那时大家一件衣服,都是家里老大穿了老二穿,一个挨一个地传下来,等差数列一般排列的孩子们,到了寒冬腊月,身上将能套的衣服,都重重叠叠套在身上,还是冷得打哆嗦,没有一件多余的或能换洗的衣裳。即使你将自己清洗一番,照样穿的是线缝吸满无数虱子和虮子的脏衣服。即便有一件旧棉袄,穿得棉花都东一蓬西一朵地绽出来,穿得两只袖子油光发亮,仍旧没有衣服换洗,等到春暖花开,才能脱下身上的厚衣。
家中床上,一般铺着麦秸谷草,充当“床垫”和褥子功能,可以提高冬季的抗寒性。在这些枯干植物之中,谁都不知道藏匿着多少跳蚤和虱子,有时闲得无聊了,随手抓一把草杆子,都能从中寻出十来个肥硕的虱子来。有些人家,冬春换季时抖床铺,清理“草床垫”,跳蚤多得要用扫帚赶到墙角,拿火来烧。能将善于逃遁的“跳高健将”扫成堆儿,可见跳蚤之多。“全民参战,全民皆兵,把侵略者消灭干净”的激昂歌曲,不仅适于打鬼子,同样适用于人与虱子和跳蚤的激战。
我有个北方亲戚,她婆家那边有一个民间习俗:二月二炒虱蚤。说是“炒虱蚤”,真正下锅炒的却是黄豆和玉米。人们平时逮捉虱子和跳蚤,都习惯用大拇指狠狠一挤,发出解恨的脆响,与炒黄豆和玉米时发出的哔哔啵啵声音,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到了农历二月二的头天晚上,借着一盏煤油灯,家人聚在厨房里来大力“炒虱蚤”。女人持锅铲,如同持刀剑的大将军,威风凛凛地站在灶台边翻炒,男人要发问:“你炒啥?”女人和娃娃大声回答:“炒虱蚤!”“炒死没?”“炒死啦!”随着锅里黄豆和玉米的爆炸声越来越频繁清脆,一家人的问答也就越来越激动响亮,喊出了节奏,喊出了气势,仿佛真的将这些讨厌的小虫都“炒死”了,再也不能来影响人们的生活。
二月二的这项习俗听来颇有趣,就算是当时人们无法彻底“除害”,也要让自己痛痛快快出口恶气,算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吧,但回到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是一秒被打回原形,倍感无力。
那时若谁家有块肥皂,已经是了不得的“高级洗涤用品”。母亲捡皂角来给我们洗头洗衣,皂角绿色生态,但它对于小虫而言,无疑太“温和”了,虱子不怕它,虮子也不惧它。后来随着日子一天天变好,农村人也和时代接轨,肥皂香皂自不必说,还用上了洗衣粉,其中所含的化学制剂大约是寄生虫的天敌,虱子和跳蚤逐渐减少。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乡亲们的生活水平、居住环境一点点变好,卫生条件越来越向城市靠齐。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农民喜气洋洋安装了热水器,卫生间里设施齐全,日常的洗漱沐浴,用的是和城里人差不多的洗发水沐浴露。缤纷时装涌入了千家万户,人们不再是“冬夏一身”,夏天掏出棉袄里已板结的棉花,冬天又将发黑的老棉花塞进去。虱子和跳蚤的生活习性,喜欢在肮脏和恶臭的环境下生存,当人们打破了脏臭的诅咒,哪有它们的容身之所?
虱子和跳蚤曾猖獗横行,那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生活状态。以前村民为了生活,劳作一整天,回家匆匆吃两口食物,脸脚都懒得洗,往床上一倒,便鼾声大起。现在种地的许多步骤,都运用了农业机械的便利,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打扫住所,讲究清洁,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虱子和跳蚤大概被人们频繁的换衣洗澡给迷花了眼,再也无处藏身,失去了生存的环境。它们闻着这些洗浴用品的香气,大概就像李闯王的起义军,进入北京城后,被城里富丽堂皇的房屋醉了眼,被奢华精致的生活俘了心,丧失了野性的进取,不久就变得不堪一击,进而全军覆没。
乡村的人们,在奔向“好日子”的进程中,并未像过去那样,拿剧毒农药擦洗脑袋,或火烧虱蚤,竟在不知不觉间,摆脱了古老的诅咒。“好日子”不仅仅意味着吃饱穿暖,还有多重丰富的含义,从物质到精神,对自我的幸福感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个周日下午,孩子在看经典的革命故事《我的弟弟小萝卜头》,她指着书中一句话问我:“爸爸,这到底是什么呢?”我侧头一看,她手指肚点着的是“牢房里阴暗潮湿,虱子跳蚤多如牛毛”。这一代孩子,他们生下来就没见过虱子和跳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