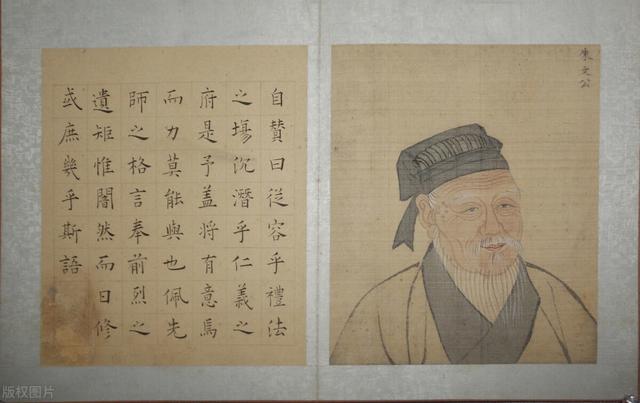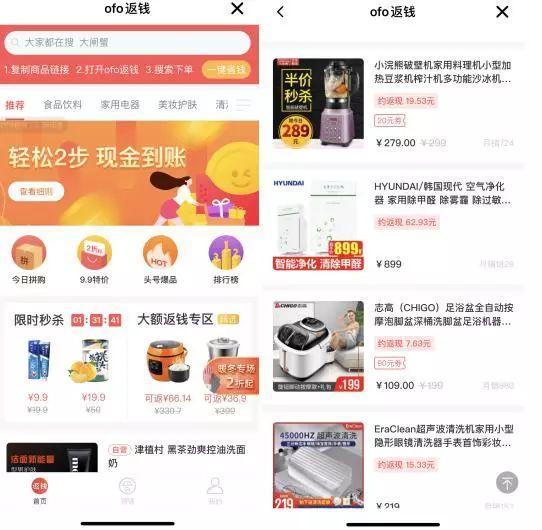我自己的外甥在高中,我就坚决不让他读《红楼梦》因为他根本读不懂。
先重复一下:红楼梦是一本关于一个公子哥跟几个女孩之间的感情纠葛的小说,但是作家在叙述小说故事的过程中随笔穿插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小说与历史之间水乳交融天衣无缝。脂砚斋在关键处会跳出来指指点点但并不会把话说透。作家只写了八十回,他压根就没想到要写八十回后的内容。
在如何阅读方面,我们从三个层面进行介绍。第一关于小说的爱情故事层面;第二,关于小说与历史的水乳交融层面;第三关于这种水乳交融的叙事艺术层面。
只关注《红楼梦》的小说层面客气点说是个基础,不客气点说的话等于读书而只是光认书上的字。因为对于作家来说,小说只是个手段或工具,他的最终目的不是讲一个公子哥的爱情故事,而是要借这个故事传达人们不知道的历史真实。而只就《红楼梦》表层的小说层面而言,尽管作品许多章回写得确实十分精彩,但从整体的角度看,还是有不少瑕疵的。比如贾敬像个隐形人,老是躲在别人的转述中,只有死了以后才露了一面,存在的必要性很值得怀疑;贾瑞的故事似乎游离于整部小说的主题之外,可删;贾菖、贾菱像一堆蛤蜊里的两个空壳一样,除了名字啥内容也没有,更无留下的必要;李纹、柳五儿等许多人物空里来空里去,可删;
从小说艺术的角度说,秦可卿整个人物毫无内容,她除了安排贾宝玉在自己闺房里睡了一个午觉外,再露面的时候就是病了,等死了不但殡礼超乎寻常,而且贾府上下的人都很悲痛宝玉甚至为之吐血。总起来说,从现代小说艺术的角度看,红楼梦是不是能配上“古典文学的最高峰”之誉真是很难说,也无怪乎西方人看不出它多优秀而当代的年轻人也少有真正觉得它多好的。
遗憾的是,目前大学里的红楼梦研究基本都还在这个层面打转转。别的就不提了,单说人物形象吧,按照西方小说理论这是一部小说最重要的内容,可在红楼梦人物形象的理解方面,三十年前是什么结论,三十年后也不见其有什么突破,比如三十多年前王昆仑先生的《红楼梦人物论》就说林黛玉是诗人而薛宝钗会做人,三十年后学者们对这两个人的认识基本也不出此窠臼。聪明点的学者无非再填上魏晋风流之类的学问点缀一下门面罢了。从来没有人提这两个人物其实和《水浒传》、《三国演义》差不多,也是出场定型,与鲁迅先生说的“传统写法都改变了”并不一致,而且人物性格也并无多少变化,这与西方小说理论所谓的立体人物、个性化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比如许多中学老师教学生把握林黛玉的性格时多以“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为核心,而这是人物一出场作家就明确交代的。
说到中学就更遗憾了。据我所知初中教材选了黛玉见凤姐的一节,高中选了黛玉进贾府(小说回目是荣府,作家深意是有区别的),很难想象中学老师会讲什么。我很担心万一有较真的中学生问“金丝八宝攒珠髻”中的八宝指哪八宝、“五凤挂珠钗”是不是有钱的女人就可以戴、洋绉裙和缕金百洋缎是不是当时的平常家居服装等问题,中学老师该怎么回答他们。
估计红学专家们恐怕也要张口结舌,因为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位专家解释清楚。倒是有一位博导研究了红楼梦的服饰文化,他的结论是红楼梦里面的服饰具有质料高档、颜色鲜艳的特点,唉,还能说什么呢?这样的结论一个初中生总结不出来吗?更荒唐的是,要是有学生往下读了两页书,会发现不但凤姐脖子上挂着一个金灿灿的赤金盘螭璎珞圈,(螭可是一种龙),后来宝玉、宝钗的脖子上也有一个这玩意,要是这三个人同时出现在电视镜头里会是什么样呢?不像三个奇异的囚徒,大概也像三个带着项圈的哈巴狗吧。幸亏目前的电视剧里没出来这样的镜头。但是不知道是编剧大爷们没注意小说的描述呢还是觉得不好看。
第二,在以小说隐写历史层面上,这是作家的全部心血所在。作家生前在苦苦呼唤能够在读完了小说回头看他的批语的读者,为此甚至写下了“泉涌相酬”四个字,可见其内心的期待之情。应该说,在这个层面上,由于学院派专家教授们不屑一顾,草根研究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过由于草根研究者学术素养的参差不齐,也出现了许多荒诞不经的结论,如明史说、孔尚任说、顺治帝说等等,都与小说的实际相去甚远。在此不一一评点,只略提一句,红楼梦第一回中提到的吴玉峰、东鲁孔梅溪二人都是作家顺手拈来的名字,是虚构的、用来掩人耳目的,更别提吴玉峰是吴伟业、孔梅溪是孔尚任了。(同理也可知,提到其弟棠村的批语也是后世人装模作样的妄言。文字狱背景下作家如此小心,岂肯连自己的亲人都透露出来?另外,曹雪芹这一名字在当时应该是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的。这其中就包括敦诚、敦敏。这两个人与曹雪芹的关系我们回头会细说。)
在这儿,我们需要重点提一下霍国玲女士。她差不多是红学史上第一位将前八十回小说与文中批语对照理解的研究者,而在三十余年的努力之下,她的许多研究成果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这其中首先包括小说隐写历史、大观园隐写圆明园、八十回即为全璧等。当然,由于专业能力所限,她的研究中也出现了许多失误,比如对诗歌的解读太多主观臆断、说作家组织武装抗清更是半点根据没有,而最大的失误是所谓红楼纪年的说法,她把小说看成了作家家史的历史档案,当然由于这一错误,她的许多建立在红楼纪年基础之上的观点也失去了可信性。关于红楼纪年的问题,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犯了忽略小说不需要也不可能逐一记录历史的错误。无论怎么说,将来的红学史必有霍女士的一席之地,而许多专家教授们的研究成果倒是可能被扫进垃圾堆。
第三,在这一水乳交融的叙事艺术层面,作家叙事手段之高明显然超乎现有的想象。我们目前还无法对这种叙事策略有明确的归纳,但是可以借用小说中宝钗的一个灯谜予以描述,顺变说一下,宝钗的这个灯谜本来就是对红楼梦巧妙穿插历史真实特征的描述:
镂檀锲梓一层层,岂系良工堆砌成?
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梵铃声!
可以补充一个例子,小说七十一回写司棋和她表哥的爱情被发现,可是这个内容作家在四十多回前就埋下了伏笔,二十七回中写道;“红玉听说撤身去了,回来只见凤姐不在这山坡子上了。因见司棋从山洞里出来,站着系裙子。”(这可不是撒尿的暗示。)可见作家在整体内容的安排上是多么严谨。
其他诸如妙玉的杯子、甄士隐、大量的诗词歌赋等等,无疑都凝聚着作家的超人才华。
放眼世界,红楼梦的这种叙事艺术真正属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过由于表音文字的局限,西方读者恐怕很难真正体会到这一叙事艺术的绝妙之处,而这,何尝不是汉字之幸、民族之幸。